郑克鲁:译海一甲子,半壁法兰西
2020-10-20陈竹沁
陈竹沁

郑克鲁 (1939-2020)
恒河沙数。《基度山恩仇记》序言的第一句话,郑克鲁摒弃了“汗牛充栋”“多如牛毛”这些常见成语,独独选用这个有宗教意味的词汇,来说明世界文学史中通俗小说之多。
翻译生涯一甲子,郑克鲁翻译了1700万字,超过傅雷、许渊冲、郝运三位著名法语翻译家译作字数总和,被誉为“凭一己之力,把半個法兰西文学搬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他还著述和编著2000万字,留下从作家研究(普鲁斯特)到法国文学通史的8卷著作,一本《外国文学史》教材,更影响了几代学子,将“文学即人学”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
而在65岁时接手“女权主义圣经”《第二性》的法语全译本,更为他赢得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晚年的他笔耕不辍,由经典文学作品转向挑战难度更高的学术著作翻译,始终保持着每日2000字的高产,曾自嘲“只不过就是没事干,用翻译来充斥时间的流逝”。
中国翻译学奠基人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比郑克鲁小5岁,2020年4月去世)曾忍不住惊叹,郑教授是“超人学者”和“超人翻译家”!但事实上,他更像是与时间赛跑的赤子。
在他,翻译是一种“爱的劳作”,是余生唯一的兴趣,也是灵魂的终极归属,“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总是这样淡淡地说,在世上留下什么,就是人生的意义。
“红衣主教”与《第二性》
对于翻译家郑克鲁来说,十万字译文里总要塞两个不大常见的词,有意让读者翻翻字典。于是《巴黎圣母院》里的路易十一不是“病得快死了”,而是“病势尪羸”。但郑克鲁同样重视原文的意译,《巴黎圣母院》里的“Bienvenu”(音:卞福汝)主教就罕见地采取了意译人名,成了“福来主教”,以体现雨果取名的特殊用意。

郑观应
如今,这位法语翻译界的“红衣主教”走了。这是郑克鲁的微信名,寄托着他对法国文学的一生挚爱,也是人们记忆中一道永恒的风景线。
春去冬来,他的红T恤换成了红羊毛衫,衬得一头银发仍显得活力四射。夫人朱碧恒形容他是“热水壶”性格,外冷内热。用谢天振的话说,“仿佛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让人联想到他一直以来对研究和译介法国文学的满腔热情、充沛精力和不懈追求。”
邻居江妙春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在小区里看到郑教授进进出出,总是一手牵着夫人,一手提着拉杆箱,里面装满了翻译资料。退休后,这对译界伉俪仍然日复一日,不分周末,并肩前往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工作,三餐均在学校食堂解决。

江妙春与郑克鲁结成忘年交,缘起于《第二性》全译本出版。2013年春节,江妙春在楼道里认出这位翻译家,慕名找他签字,没想到《第二性》在书店脱销,分两次才凑齐上下册。近年来性别成为社会热议话题,《第二性》热度不减,常被援引。郑克鲁在选择翻译作品和和参考评价时,一向重视读者反馈,这一市场反响也足以佐证其判断眼光。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缪伶超是《第二性》的责任编辑,她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作为法国著名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代表论著,《第二性》篇幅很长,而且涉及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存在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等多门学科,翻译难度很大。
过去国内只有一个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中译本,该英文译者自行删去15%的内容,且有多处错译,不尽如人意。上海译文买下法语原著版权后,邀请郑克鲁翻译,他以“如履薄冰”的心态,用了整整两年才译完。
缪伶超举了两个细节处理的例子。比如,对féminisme的译法,郑克鲁根据女权运动的阶段做了精确的区分:上世纪中叶欧美国家女性争取投票选举、同工同酬等权益,这一时期翻译成“女权主义”比较合适,而后期女性要在意识上摆脱“后天形成”的束缚,扭转社会的偏见,所以用“女性主义”更为贴切。
而对于惯常使用的“波伏娃”这个名字,郑克鲁特地改为“波伏瓦”,因为de Beauvoir是父姓,选词不应带有强烈的女性特征。
那时,每次缪伶超问郑老师最近在忙什么,他总是很兴奋地说“在翻译某某书!这本书价值很高啊”,“他对翻译的热情有目共睹,看到一本好书,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要翻译出来能给更多人读,他对翻译的兢兢业业、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和坚持尤其令人由衷敬佩。”
不怕说真话
总有读者挑剔译本,对充满理论词汇的“学术腔”不买账。作为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法语文学翻译家余中先高度肯定了郑克鲁的重译,“若要弄懂波伏瓦的思想高度和语言深度,除了郑译本,没有其他的选择。”余中先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作品中谈及的克洛岱尔,他核对过郑先生的翻译,认为十分到位。
“郑门弟子”、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评价,郑克鲁的翻译风格朴实无华,讲究忠实原文的句式句法特征,挖掘字里行间的深意,郑译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艺术效果。虽然集翻译、研究、教学三位一体的大成,“他从不故弄玄虚,从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从不摆弄新词套话,从不堆砌批评术语,从不膜拜西方的所谓理论,从不吓唬青年学者或普通读者。”
缪伶超对郑克鲁的直言不讳印象颇深,“他看到别人的翻译里有错误,哪怕对方是前辈或功成名就的翻译大家,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认为翻译上的探讨是纯粹的,是就事论事的,不应该因为人情就扭曲事实。”
曾有出版社想让郑克鲁重译《约翰·克里斯朵夫》,他拒绝了,一来他认为《约翰·克里斯朵夫》在法国算不上一流作品,二来傅雷先生原来的译本“也还可以”。“重译,我的标准是要超过前人,不然没有意义。”接受媒体采访时,郑克鲁就曾直言,不少经典作品需要重译,但“即使是重译本,有的译者是‘拆烂污的。”
谢天振曾撰文回忆,前几年,有位文化官员读到其纪念傅雷的文章,竟勃然大怒,致电编辑部兴师问罪。郑克鲁获悉此事,立马发来微信语音力挺,直言“莫名其妙,怕真话的人很可悲!”尽管只是只言片语,但谢天振分明感觉到郑先生温和宽厚的外表下流淌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血液和凛然正气。
郑克鲁对年轻人始终很和蔼,交流专业问题时尤为耐心。缪伶超说,“他愿意和我们讲平时翻译中的细节,遇到某个词,以前大多是怎么翻的,最近发现在某个语境下似乎有新的翻法更好,年轻编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无论是专业上还是敬业态度上。”
郑克鲁曾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先锋派作家马原对他说,“傅雷的文字比较老。”“我当时说,‘老吗?还不觉得傅雷的文字老。他们年轻的作家比较敏感,如果年轻人说文字老了,可能就过时了。”

全家福,右一为郑克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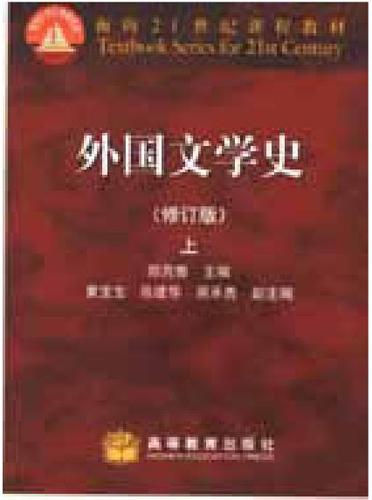
郑克鲁最早研究巴尔扎克,后来接受了卞之琳先生的建议,“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 “文革”结束后,他与袁可嘉和董衡巽合编的4卷8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版,其中他翻译了6篇,包括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加缪的小说《沉默的人》等。这套丛书是国内第一次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品进行大规模翻译,在80年代产生巨大反响。
郑克鲁留下的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是由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史》,至今仍是中国高校学习外国文学的权威教材。它突破了以往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禁区,给予20世纪现代派文学应有的地位,被视为“反映了编写者的见解和学术勇气”。郑克鲁曾坦然承认,当时考虑亚非文学的重要性无法与西方文学比肩,理应只占五分之一左右,此外前苏联文学地位也并没有那么高,因此只选高尔基和肖洛霍夫作为重点作家。
参与这本教材编写的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蒋承勇评价,郑先生主编这部作品,率先重拾“人学”议题,重新探讨了文学应该研究什么,应该如何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研究摆脱了非文学因素,也对后世中国的文学研究影响很大。
余中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谈到,自己曾几次从郑克鲁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中,查阅某些比较冷门的短篇小说,都能读到清晰的作品概要、情节以及对风格主题的分析,感到心服口服,“有些作者在编写文学史时,不一定会去通读原文。郑老不是,文献中提到的诗歌、戏剧、小说,他一定读过原著,这个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2018年4月7日,江妙春与郑克鲁在《 郑克鲁文集》 发布会上合影
“绿帽”文学史之路
作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人,郑克鲁师承李健吾先生,他曾说,“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取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是他从李先生这里获得的最大财富。因此他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注重搜集法文材料,看法国人如何评价作品,进一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观。而他撰写的译本序言,也因丰富全面的背景介绍以及独到的艺术价值分析被传为佳话。
郑克鲁对法国文学史的研究从诗歌史起步。上世纪80年代去法国进修时,他留意收集了许多诗歌,第一本法国诗歌选集以《失恋者之歌》命名。他不仅推崇失恋诗的抒情艺术价值,还特别关注到诗人的母子关系,自谦于“一得之见”。
对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译介,他特意选出“怪诞(惊悚)篇”,以《奥尔拉》为代表。这也是参考法国人的观点,这部分在中国读书界一直被遮蔽。
在撰写法国文学史的阶段,郑克鲁补充了此前缺少研究的18世纪启蒙文学,加深了对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的研究。晚年,他继《第二性》之后又啃下皮埃尔·勒帕普的学术著作《爱情小说史》,并以伏尔泰的三本重要历史著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查理十二》收笔,完成了学术和翻译的回环。
有趣的是,郑克鲁也乐于“拆伏尔泰的台”。根据他掌握的法国专家的考据,伏尔泰曾谈及路易十四赠予拉斐尔很多贵重的礼物,但事实是:拉斐尔没去过法国。郑克鲁觉得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应该对读者负责,还原真相。
曾有记者问他,当年为什么喜欢看法国小说?
他大大方方地说,“年轻人都喜欢法国小说,因为写的都是偷情、美女之类的故事。”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國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
“绿帽文学”当然是戏称。郑克鲁说,“法国文学从来不脱离政治,而且能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人物形象突出,艺术技巧发展充分”,正是因为这样的魅力,法国文学才吸引着他一直翻译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
江妙春深感难忘的是2018年4月7日,46卷本的《郑克鲁文集》发布会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在上师大召开。江妙春意外自己受邀,“忝列”170余位教授专家之间,郑教授夫妇还特别安排他上台,敬赠墨宝。
此前郑克鲁落款时未留意,将“文集”误写为“全集”,很快江妙春就接到朱碧恒代发的请求修正的微信,“写全集就是寿命到了盖棺定论咯,郑教授看到落款瑕疵,觉得不能混为一谈。”
江妙春注意到,在研讨会上,听着全场的赞美,郑克鲁丝毫没有喜形于色。他在最后发言时说,“这些话都说早了,不靠谱,应该等我死后再说,好不好交给读者和历史来评判。”
郑克鲁 (1939-2020)
集翻译家、文论家、文学史家及教材编写专家于一身,师承李健吾,夫人为翻译家朱雯之女、英语翻译家朱碧恒。曾祖父为晚清改良派思想家、《盛世危言》 作者郑观应。曾获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金棕榈勋章”、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译作包括:《悲惨世界》 《巴黎圣母院》 等雨果小说全集,《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等巴尔扎克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选,《茶花女》 《红与黑》 等经典名著,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 和加缪的 《局外人》 等存在主义力作,《海底两万里》 《八十天环游地球》 《小王子》 等科幻和儿童文学畅销书,还有跨越中世纪到现代的 《法国诗歌选》,总计1700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