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壁画中的手持宝珠莲花图像研究①
2020-10-20史忠平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史忠平(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根据佛经描述,用鲜花供养佛,不但能够让诸佛欢喜,所求必获,而且还能积累功德、获得福报②如[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千佛因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佛灭度后,若诸四众,若持一华供养佛像,得二种福。何等为二?一者常得化生;二者形色端正。复得二果:一者恒得值遇诸佛;二者多生天上。”见《大正藏》,第14册,第69页。[隋]瞿昙法智译《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中说:“若有众生奉施香华,得十种功德:一者,处世如花;二者身无臭秽;三者,福香戒香,遍诸方所;四者,随所生处,鼻根不坏;五者,超胜世间,为众归仰;六者,身常香洁;七者,爱乐正法,受持读诵;八者,具大福报;九者,命终生天;十者,速证涅槃”。见《大正藏》,第1册,第895页。。同时,鲜花供养的对象也不仅是佛,还可以是佛塔、菩萨、金刚、诸天等③如[唐]输波迦罗译《苏悉地羯罗经》中说:“若献佛花,当用白花香者,而供养之;若献观音,应用水中所生白花,而供养之;若献金刚,应以种种香花而供养之;若献地居天,随时所取种种诸花而供养之。”见《大正藏》,第18册,第669页。[宋]天息灾译《分别善恶报应经》中说:“若复有人,于如来塔施花供养,功德有十。何等为十?一色相如花,二世间无比,三鼻根不坏,四身离臭秽,五妙香清净,六往生十方净土见佛,七戒香芬馥,八世间慇重得大法乐,九生天自在,十速证圆寂;如是功德,以花供养佛舍利塔获如斯果”。《大正藏》,第1册,第900页。。由此可见,鲜花供养在佛教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敦煌壁画、绢画和纸画中,描绘了大量表示供养的花卉,并主要以持物形式被执于菩萨、弟子、飞天、供养人等的手中。
考察敦煌绘画中手持供养花卉的结果表明,无论是手持的折枝花,还是手托的盘花和瓶花,基本都是莲花,这当与莲花和佛教的特殊关系相关。而在各类手持供养莲花中,有一类宝珠莲花,形象突出,且主要集中于莫高窟隋代前后的壁画之中,比较特殊。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将其作为佛教的一类装饰图案、供养具,或出现在墓葬里的一种佛教元素来讨论,而且,着眼点也主要在宝珠图像上。相对来讲,将宝珠与莲花组合图像放在手持供养花卉序列中所作的论述较少。由此,本文拟针对莫高窟壁画中的手持宝珠莲花图像,就宝珠莲花作为一类手持供养花卉的相关问题做一探讨,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宝珠与宝珠莲花图像
宝珠又称摩尼宝珠、如意宝珠。据佛经描述,宝珠不仅是清净光明、清澈轻妙的象征,而且具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功效,依此宝珠,可获功德、福德和佛道。如唐不空译《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曰:“心性宝珠无有污染”。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五十九曰:“此宝珠名如意,无有定色,清澈轻妙,四天下物,皆悉照现”“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能烧,有如是等功德”“是宝常能出一切宝物,衣服饮食随意所欲尽能与之,亦能除诸衰恼病苦”。后秦鸠摩罗什译《法华经》曰:“净如宝珠,以求佛道”等。正因如此,宝珠不仅是佛教众宝之一,而且是佛教主要供养物品之一。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印度佛教图像中以宝珠供养佛陀的实例比较少见,[1]34-35而在中国南北朝、隋代的佛教石窟、墓葬中,宝珠图像却比较普遍。其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宝珠莲花图案。出现范围遍及南北多地。如在河南邓县、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中,就有较多模印于砖上的宝珠莲花。其中小横山M1号墓中的棱锥形宝珠,周围有火焰,置于覆莲座上,两侧对称生出修长的忍冬叶,形象比较明确。[2]16(图1)大同沙岭北魏M7甬道顶部伏羲、女娲像中间绘有棱锥形宝珠,周围有火焰,下带长茎,长茎末端有覆莲。河南洛阳北魏元谧石棺前挡和升仙石棺前挡门楣上方正中线刻有圆形宝珠,周围有火焰,置于覆莲座上,两侧对称生出修长的忍冬叶。[3]178-190类似的宝珠形象在佛教石窟中也常有发现,如克孜尔第38窟、炳灵寺第169号龛上部、麦积山第4窟窟廊正壁龛上部、云冈石窟第7洞后室南壁门楣上部、第9洞门口天井中心部位等。[2]16就敦煌而言,宝珠莲花图案也是从北魏开始流行,并成为隋代的主流纹样之一(图2)。总之,单从形象来看,作为装饰图案出现的宝珠莲花,多为宝珠、火焰、莲花和忍冬纹叶的组合,其基本图式是宝珠在上,周围有火焰,覆莲座在下,忍冬纹叶对称分布两侧①在宝珠、火焰、莲花、忍冬纹叶的组合中,宝珠周围有火焰,是为火焰宝珠,忍冬纹叶从莲花中生出,是为长有忍冬叶的莲花。单独的火焰宝珠和忍冬叶莲花在佛教石窟和墓葬美术中比较常见。所以,宝珠、火焰、莲花、忍冬纹叶的组合,实际上就是火焰宝珠和忍冬叶莲花的组合。鉴于此,本文将宝珠、火焰、莲花、忍冬纹叶的组合样式称为“宝珠莲花”。。

图1 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宝珠莲花图案(采自刘卫鹏:《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M1分析》)

图2 莫高窟隋代第405窟宝珠莲花藻井图案(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96)
第二类是宝珠莲花作为持物。日本学者逸见梅荣曾将佛像所持宝珠从形式上分为两种,一是与诸尊所持其他佛具一样,直接手拿,另一种是安置于莲华之上。[4]对于宝珠作为持物的现象,学界研究较多。其中包括一些带有穿孔的桃形造型,在以往的各类图录和报告中,学者们为慎重起见,将之称为桃形物、锁状物或桃形器。但据有些学者研究,应当是摩尼宝珠,因为,“穿孔只不过是变相表现摩尼宝珠,让观者感觉那样才不至于从手中滑落”而已②见李静杰:《北魏金铜佛板图像所反映犍陀罗文化因素的东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5期。另外,据冉万里介绍英国学者也有相关说法,冉万里也支持这一说法。见冉万里:《略论长安地区佛教造像中所见的佛教用具》,《西部考古》,2008年第三辑。。“手持这种摩尼宝珠的雕像主要为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还偶有所见,此后则极少见,而且造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5]。其实例不仅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魏菩萨造像的手中比较常见,而且在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中也有不少,另外也出现在克孜尔第175窟主室正壁右侧上部供养天人的手中(图3)。由此,李静杰认为,虽然龟兹壁画中此类图像的年代不算太早,“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文化交流情况,应该是西域早期同种造型因素的延续,汉文化地区摩尼宝珠供养图像应由西域传播而来”[1]35。

图3 克孜尔第175窟天人(采自《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图版17)

图4 酒泉穆善石塔线刻神王(采自《北凉石塔艺术》第116页)

图5 莫高窟隋代第394窟西壁菩萨(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55)

图6 莫高窟第285窟(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43)
除了造像中所反映的手持穿孔桃形宝珠外,在酒泉北凉时期的穆善塔线刻神王中还能见到手持宝珠的例证(图4)。在敦煌莫高窟隋代第394窟(图5)、第420窟、第402窟、第313窟等壁画中也绘制了大量手托宝珠的图像。
至于将宝珠安置于莲花之上并持于手中的图像,则不及直接手持宝珠或莲花那样普遍。但也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第一种是力士、飞天共举宝珠莲花的图像。例如,在云冈石窟第6窟有四身飞天共同持护宝珠的雕刻。莫高窟西魏第249窟窟顶东披绘有二力士共托宝珠,飞天左右护持的图像。图中宝珠为棱锥形,下有覆莲座,两侧有忍冬叶。西魏第285窟窟顶南披两身飞天共扶宝珠莲花,(图6)东披二力士共持宝珠莲花,(图7)其图像仍为棱锥形宝珠、覆莲座和忍冬叶的组合。但在覆莲座中突出了莲蓬,底下增加了可供手持的细长花茎,宝珠周围绘制了云气纹,忍冬纹叶中增加了花朵和花蕊,整体变得更加繁复了。在莫高窟隋代第305窟西披和东披也表现了簇拥宝珠莲花的飞天。这些都可以视为向单人手持宝珠莲花过渡的一种征兆。第二种是单人手持宝珠莲花。陕西麟游县慈善寺石窟南窟初唐时期的立佛,左手施与愿印,掌心托莲花火焰宝珠。(图8)另,日本法隆寺有6-8世纪的梦殿观音像,手持圆形宝珠,宝珠上有透雕火焰纹,下有莲花座。[6]而表现单人手持宝珠莲花最多的则是莫高窟隋代前后的壁画,相关例证将在后文列举。

图7 莫高窟第285窟(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42)

图8 慈善寺南窟立佛(采自李凇《佛教美术全集·陕西佛教艺术》第96页)
通过前文论述,初步可得几点认识:第一,宝珠在佛教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其图像在中国较为流行,从前文所举各地墓葬、石窟相关图像可见一斑。当然在日本等地也有图例;第二,中国宝珠图像盛行的时间段主要集中于南北朝与隋代;第三,从宝珠自身的造型来看,早期主要为棱锥形,这当是佛经所谓“八楞宝珠”的忠实表现①北魏菩提留支所译《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卷第一云:“譬如离垢八楞摩尼如意宝珠置在高幢,放大光明随众生愿雨令满足,其光殊胜照曜显现遍照十方”。宋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所译《杂阿含经》卷二十七云:“何等为转轮圣王出兴于世,摩尼珠宝现于世间。若转轮圣王所有宝珠,其形八楞”。。到了南北朝后期,宝珠形象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八楞形”变为圆珠形,并相对稳定了下来;第四,宝珠的呈现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单独作为持物,另一类是与莲花组合,形成装饰图案或手中持物;第五,敦煌的宝珠图像从存在方式、风格与流行时间来看,基本与其他地方同步,但也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点。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手持宝珠莲花增加了花茎等便于手持的元素,表明了宝珠莲花由装饰图案向手持花卉过渡的痕迹;第二个方面,是出现了力士、飞天共持宝珠莲花的明确图像。除此之外,宝珠莲花还大量出现在单尊佛教人物手中,而且被花卉化,成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手持莲花图像。这是敦煌宝珠莲花地域性特点的第三个方面。
二、莫高窟壁画中的手持宝珠莲花
从敦煌石窟和我国其它佛教石窟、墓葬中宝珠莲花图像的现存情况来看,敦煌手持宝珠莲花图像显得微不足道,但就宝珠莲花作为一类花卉化了的持物而言,却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就敦煌石窟来讲,手持宝珠莲花主要集中出现在莫高窟隋代前后的壁画当中,并以北周第461窟、第297窟,隋代第402窟、第420窟、第295窟、第427窟、第380窟、第407窟、第313窟,隋末唐初第244窟等为代表。根据造型,可分为以下四类:

图9 北周第461窟西壁南侧弟子(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北周》图版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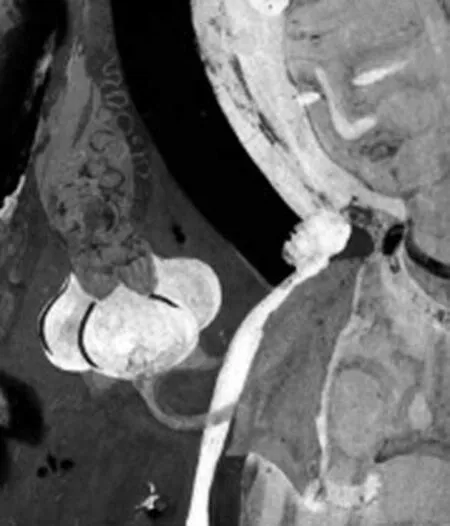
图10 第297窟西壁龛外北侧菩萨(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北周》图版160)

图11 第420窟西龛内北侧菩萨(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隋》图版108)
Ⅰ类:折枝宝珠莲花。这一类莲花的主要特征是有长茎,花叶多为忍冬纹叶,花瓣下翻或向上内抱,莲蓬凸起,上有宝珠,宝珠周围有火焰。一般被菩萨、弟子单手或双手持于胸前。如莫高窟北周第461窟西壁南侧弟子(图9)、第297窟西壁龛外北侧菩萨(图10);隋代第420窟西壁北侧供养比丘、西龛内北侧菩萨(图11);隋代第427窟方柱北龛西侧菩萨(图12)、第380窟南壁西侧说法图中的菩萨(图13)、第407窟西壁龛内南侧菩萨(图14)、第390窟主室东壁门上和主室北壁菩萨、第402窟西壁龛内南侧上部弟子、第295窟西壁北侧菩萨、第302窟中心塔柱南向面圆券形龛外两侧菩萨手中都持这一类宝珠莲花。
Ⅱ类:无茎宝珠莲花。这一种莲花没有花茎,花瓣向上开放,宝珠从花心生出,周边有火焰纹,一般被单手托在掌心或双手捧于胸前。如莫高窟隋代第402窟西龛内南侧菩萨双手托无茎莲花,上有宝珠(图15)。第420窟主室西壁南北两侧下部各绘弟子五身、菩萨四身,其中多持此类宝珠莲花(图16)。
Ⅲ类:托盘宝珠莲花。在莫高窟隋末唐初第244窟西壁南侧,一供养菩萨胡跪于莲座上,双手捧花盘,盘中有莲,莲花中心有宝珠,宝珠周边有火焰纹(图17)。
Ⅳ类:烛台宝珠莲花。在莫高窟隋末唐初第244窟东壁和北壁说法图中,有菩萨手托烛台,顶端开敷莲花,莲花上有宝珠,宝珠周边有火焰纹(图18、图19)。
上述分类表明,在敦煌莫高窟隋代前后这一段时期的壁画中,Ⅰ类折枝宝珠莲花数量最多,最有特点。Ⅱ类无茎宝珠莲花与装饰图案最为接近。Ⅲ类托盘宝珠莲花和Ⅳ类烛台宝珠莲花数量少,造型最为特别。下面就影响敦煌手持宝珠莲花的因素作一分析。
三、影响莫高窟壁画手持宝珠莲花图像的因素
莫高窟壁画中的手持宝珠莲花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同时又不能游离于宝珠莲花图像演变发展的整体脉络之外,所以,对于这类图像的出现,既要考虑其宗教和文化的因素,也要考虑其作为绘画本身的规律和发展等因素。
首先,从佛教文献来看,有关莲花与宝珠组合,以及手持宝珠莲花的记述虽然不及对单独宝珠和莲花的描述丰富,但也不是无源之水。如《经律异相》有这样的描述:“如是莲华有八万四千大叶,一一叶间,有百亿摩尼珠王,以为映饰。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释迦,毗楞伽摩尼宝以为其台”。[7]另如《憨山老人梦游集》中云:“莲华挺生。枝叶自长。摩尼宝珠。体净圆洁。堕溷迹中。光明不缺。佛性在缠。染而不污。泥中之莲。厕中之珠。日用行藏。昭昭不昧”。[8]这两则材料从文本与寓意两方面为莲花和宝珠的组合提供了依据。《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五中说:“次于第二重大日如来左方画除盖障菩萨,……左手持莲华,华上置摩尼宝珠,右作施无畏手。此菩萨及诸眷属皆是大慈悲拔苦除障门,正以此菩提心中如意宝珠施一切众生无畏满其所愿也”[9]。这一记载,不仅说明了手持宝珠莲花的功能,而且说明了宝珠莲花的组合样式。其“手持莲华,华上置摩尼宝珠”的描述与敦煌手持宝珠莲花形象是一致的。
其次,从图像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虽然印度的宝珠图像并不多见,但从新疆石窟的表现情况来看,约在公元4-8世纪的壁画中还是保留了一些宝珠图像的痕迹,并且棱锥形和圆形是并存的。如克孜尔石窟第123窟后室券顶有手持圆形宝珠的飞天。库木吐拉第23窟(公元5-6世纪)主室券顶左侧佛右侧一人手持棍,顶端有圆形宝珠。库木吐拉第16窟有带莲花座的圆形火焰宝珠。在克孜尔第48窟后室券顶绘有棱形宝珠。森木赛姆石窟第41窟(公元4-5世纪)主室券顶左侧、吐乎拉克艾石窟第3窟(7世纪及以后)主室券顶右侧均画一人蹲跪,双手捧楞形宝珠。吐峪沟石窟第41窟顶部北披东端坐佛头顶、第42窟窟顶东披(公元327-640年)也表现了棱形或方格形宝珠(图20)。与南朝墓砖和中原墓室壁画、石窟壁画相比,新疆石窟中的宝珠虽然也有棱形和圆形的基本造型,但却少见与莲花、忍冬叶的组合,在表现风格上也体现了很大的不同。
另外,力士、飞天共持宝珠莲花的图像渊源可追溯到印度键陀罗造像。比如在茂哈迈德·纳里出土和昌迪加尔博物馆藏的犍陀罗浮雕中,就可看到飞天共举宝盖的图像[1]29(图21)。这些迹象都表明,南北朝时期的宝珠造型仍然是受印度、西域影响的结果,只不过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融入其它佛教元素和中国固有的传统元素,最后形成了宝珠、火焰、莲花、忍冬相组合的新图式罢了。

图12 隋代第427窟方柱北龛菩萨(笔者自绘)

图13 隋代第380窟南壁菩萨(笔者自绘)

图14 隋第407窟西壁龛内南侧菩萨(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91)

图15 隋代第402窟西龛内南侧菩萨(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06)

图16 隋代第420窟主室西壁北侧菩萨(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71)

图17 隋末唐初第244窟西壁南侧菩萨(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75)

图18 隋末唐初第244窟东壁北侧菩萨(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82)

图19 隋末唐初第244窟北壁中部菩萨(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77)

图20 吐峪沟第42窟窟顶东披(采自《中国新疆壁画全集·6》图版2)

图21 茂哈迈德·纳里出土犍陀罗浮雕(采自赵声良《飞天艺术》图版3-3)
隋代前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次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另一次是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这两大变革的直接结果就是促进了南北文化大融合,而敦煌作为地处边陲的佛教圣地,最能反映南北融合的例证就是以西魏第285窟及以隋代诸窟为代表的壁画艺术。相关问题,前贤论述颇多,此不赘述。与此同时,佛教的外来输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盛。由此,对于莫高窟的宝珠莲花图案和手持宝珠莲花,考虑到敦煌地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这一图像又在隋代前后流行等因素,即可推断,其中单人手持、二人共持宝珠莲花的基本图式主要源自键陀罗的影响,而宝珠莲花图像本身则较多受到南朝和中原的影响。
再次,从敦煌自身的发展来看,敦煌艺术虽然受到印度、西域和中原的多重影响,但整体上又有着自身的图像体系。就手持花卉而言,其每一个阶段的图像演变除遵循同时期佛教思想和同一洞窟造像风格的规范之外,更大程度上受到装饰图案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莲花化生思想影响下手持花卉与装饰图案的一致性。莲花是在佛的世界中产生一切生命的象征。[10]30日本学者吉村怜曾在讨论云冈石窟中莲华装饰意义时,分析了手持莲花与天人诞生之间的变化轨迹,并指出,存在于化生连锁关系中的莲花“不是仅仅作为圣华纹饰来装饰壁面。而是作为一种其深处内藏着一切生命根源的华,存在于空中,和佛、菩萨、天人等同样都是构成佛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10]30依此可以解释,佛教石窟中一些作为装饰图案的花卉,即是从手持莲花中化生的某一个中间环节。而宝珠莲花中的宝珠,也可以视为莲花化生之物。第二个方面是鲜花供养思想影响下手持花卉与装饰图案的一致性。佛教所说的鲜花供养,主要有持花供养和散花供养两部分。敦煌石窟中绘制了大量一手持花盘,一手散花,或一手持花,一手散花的飞天。从中可以看出,盘中之花与散落之花,以及部分图案装饰之花都是一致的。而这一现象在印度和中国其它石窟中都普遍存在。作为佛教石窟,整体设计中一直贯穿着营造佛国境域的理念,所以,凡是绘制在洞窟之内的,与盘中之花和手中之花一致的花卉,甚至所有与建筑紧密相关的花卉图案,都“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象征着一种佛教的礼仪——散花供养礼仪”[11]。正因如此,敦煌壁画中每个时期的手持花卉都与同时期同一洞窟中的花卉装饰图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换句话说,由于手持花卉在石窟中占据面积远远小于装饰花卉,而画家则将受时代装饰风格影响下绘制出来的花卉图案移植到人物手中。这一方面符合化生思想与供养礼仪,另一方面体现了绘画表现本身的便捷与风格统一。
另外,还需注意几个细节。第一是莫高窟手持宝珠莲花中普遍描绘了硕大而凸出的莲蓬,莲蓬上复置宝珠。凸出莲蓬的莲花是印度桑奇、巴尔胡特装饰雕刻中惯用的样式。在南朝、中原墓葬和石窟中,虽然也有不少手持莲花表现了硕大凸出的莲蓬,但在莲花与宝珠的组合图像中却弱化了莲蓬形象。而莫高窟北魏至隋代的时间段内,不仅绘制了大量凸出莲蓬的手持莲花,而且将这一特征在手持宝珠莲花中沿用了下来。第二是莫高窟手持宝珠莲花中不仅增加了手持的细长莲茎,而且增加了忍冬花叶的数量和花头。同时,还打破了左右对称的定式,弱化了宝珠的主体地位,使手持宝珠莲花花卉化,增强了手持宝珠莲花的绘画性。如果考察这一时段的手持折枝花卉以及莲花图案中缠枝纹的盛行,则可理解三者之间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情况。第三是在莫高窟隋代第297窟西壁龛外北侧菩萨手持宝珠莲花中,宝珠周围绘制了云气纹,这与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力士共持的宝珠莲花完全一致,也体现了莫高窟绘画内部的继承关系。而Ⅲ类托盘宝珠莲花和Ⅳ类烛台宝珠莲花,则是受莫高窟手持盘中莲花的直接影响以及瓶中莲花间接影响的结果。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莫高窟手持宝珠莲花在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同时,更多地受到敦煌绘画自身的影响。
最后,从绘画表现来看,莫高窟手持宝珠莲花不仅在形象上较为特殊,而且受到中原画风的影响,在绘画技巧上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如前所述,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在尼寺里长大的隋文帝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在经营河西、交通西域方面不遗余力。所以,在整个隋代,莫高窟开窟多达七、八十个。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涌现出了以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为代表的画家群体。他们不仅有过表现佛教题材的经历,而且开创了“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绘画风格。这种精致绚丽的画风影响到敦煌,在莫高窟隋代第402、第407、第420、第427等窟中有了突出的表现。从前文所举诸例来看,隋代第402、第407、第420、第427窟中的手持宝珠莲花正是这一密体画风的反映,其中不仅线条细密精致,设色臻丽,而且使用了贴金的手法,从而达到一种高雅而富丽的效果(图22)。

图22 莫高窟第402窟西壁菩萨(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07)
结 语
莲花与宝珠在佛教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其图像也被大量表现在佛教美术之中。从相关资料来看,在南北朝、隋这一段时间里,莲花和宝珠图像除独自以装饰图案、持物等形式出现外,还存在一种组合样式——宝珠莲花。
宝珠莲花因结合了宝珠和莲花光明、清净、无污的共同寓意,叠加了二者的多重功能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佛教内涵。其图像不仅被大量装饰于佛教石窟之中,引入地下墓葬之内,而且被拓展为一类手持之物。作为持物的宝珠莲花在敦煌莫高窟隋代前后的壁画中出现,具有时间集中、数量大、形象鲜明等特点。考其类型,究其成因,则可发现,莫高窟手持宝珠莲花是印度、西域、中原和地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能看到敦煌壁画的绘制者面对多元文化时的种种选择,也可以窥见他们在敦煌绘画体系之内如何吸纳外来元素,继而进行的种种创变。
从手持花卉供养图像的发展与演变轨迹来看,无论是手持花朵、折枝花,还是盘花、瓶花,都以莲花为主,并可在印度寻其根源。在敦煌手持花卉供养图像序列中,不仅能看到对印度同类图像的继承,而且也能看到对这一图像的创新和拓展。莫高窟唐、五代、宋、西夏各时期,手持花卉在莲蕾、折枝莲花、盘中莲花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净瓶莲花、缠枝莲花、地生莲花、交茎莲花、折枝牡丹、盘中牡丹,以及花鬘、画扇和一些难以命名的象征性或变体花卉,同时还出现了用于插花的玻璃器等。可以说,唐代以后,敦煌绘画中的手持花卉五彩纷呈,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绘画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也反映了唐宋以来,我国花鸟画高度繁荣的广泛影响。而隋代前后出现的宝珠莲花则正是敦煌手持花卉发展链条上形象特殊而又不可缺少组成部分,其所包含的综合性和创新性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