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师严道尊
2020-10-10刘强
刘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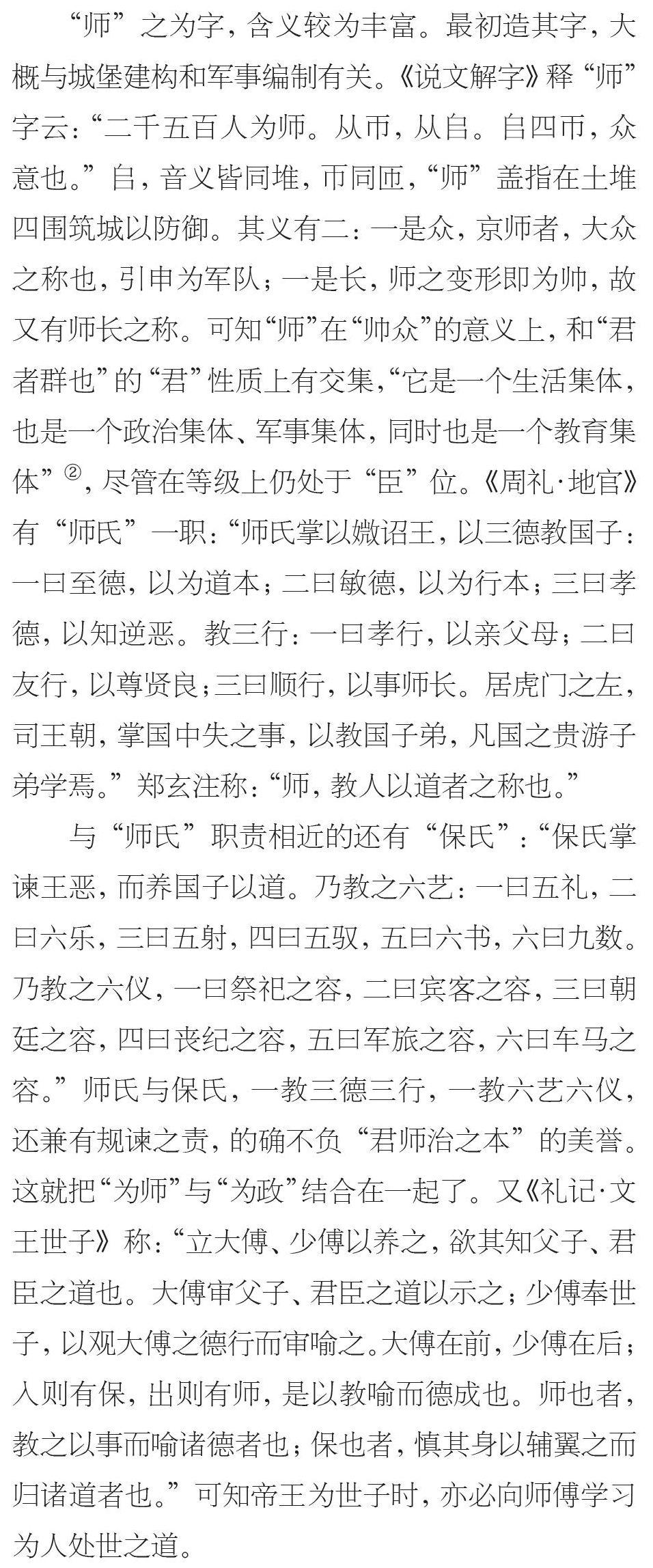
教育之道也即为师之道。为师必先为学,故教育之道自然以为学之道为始基。换言之,师者必从学者来,一个好老师首先一定是一个好学生。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说:“老师自己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伟大的心灵,或者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糊其词,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心灵。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我们不可能在课堂上遇到他们任何一位。我们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他们任何一位。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孔、孟、程、朱、陆、王这样的圣贤,才能算得上是“不再是学生的老师”,称得上是“最伟大的心灵”吧。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配被称作“师者”,儒家的教育之道又是怎样的呢?这个话题似小实大,下面我们就结合经典文本,择要做一介绍。
“为师”与“为政”
在儒家设定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中,虽然并无“师”之名目,却隐含着“师”的角色与内涵。大体而言,“师弟子”(即师徒)的关系是兼容于父子、君臣和朋友三伦关系之中的。班固《白虎通义·辟雍》篇说:“师弟子之道有三:《论语》‘朋友自远方来,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视予犹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义教之,君臣之道也。”一道而含三伦,这在所有的人伦关系中恐怕绝无仅有。
古有“礼之三本”说,如《荀子·礼论》篇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大戴礼记·礼三本》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里“君师”并称,同为“治之本”,足见师者地位之重要。古时耕读之家,中堂常设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就是上承“礼之三本”说而来。
要了解“师”的更多职能,还是必须诉诸字源学的考辨。
与“师氏”职责相近的还有“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师氏与保氏,一教三德三行,一教六艺六仪,还兼有规谏之责,的确不负“君师治之本”的美誉。这就把“为师”与“为政”结合在一起了。又《礼记·文王世子》称:“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可知帝王为世子时,亦必向师傅学习为人处世之道。
《孟子·梁惠王下》引《尚书·泰誓》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里君、师并言,所指也即政、教二端。孟子还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之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其实就是抬高“师道”,以之与“君道”相抗衡。又,《礼记·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所以,儒家的为政之道虽非“政教合一”,却有着“以教代政”的特点。只不过这里的“教”,非宗教之“教”,而是教化与教育之“教”。“善教”之所以“入人深”,乃因其比“善政”更具人文性,更有人情味儿。《周易·贲·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人文化成”强调了“文化”的动词性意义,“教化”也是如此。毋宁说,中国文化的“教”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因其應天顺人,故能深入人心。而这一切,都须有师者来担当。
温故知新,教学相长
古语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后汉纪·灵帝纪上》)分明将师者分为“经师”和“人师”两种境界。究竟该如何区分“经师”和“人师”呢?我们可从《论语》中找答案: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这是孔子对“师”的经典表述。“温故”与“知新”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递进关系,两者中间的“而”,既可作连词,表递进关系,也可作助动词,训为“能”。朱熹注称:“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c显然是把“温故而知新”当作“人师”的必备素养。子夏也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这里“日知其所亡”相当于“知新”,“月无忘其所能”则是“温故”,子夏有此良知良能,故后来终成儒门一代宗师。
《礼记·学记》是最早的一篇教育学文献,其中多次提到“人师”。如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显然,“记问之学”是指只能“温故”不能“知新”的死记硬背。“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矣。”一个好的老师,必须知道在何种情况下教育比较有效,何种情况下教育已经失效,这又涉及教育学的深层原理。前引“能博喻然后能为师”的“博喻”,孔颖达解作“广晓”。一个好老师,要善于打通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界限,触类旁通,左右逢源,也即孔子所谓“温故知新”“告往知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否则,就只能做“经师”,而不能做“人师”。“经师”,大概相当于所谓“专家”,而“人师”应该是“通人”。“经师”只面向文本和知识,可以著书立说,授业解惑;而“人师”却能通过“教书”以“传道”,通过“传道”而“育人”。就此而言,汉代许多五经博士充其量只能算是“经师”,而历代兴学传道、泽被后世的圣贤人物才是真正的“人师”。同理,西方那些著作等身的“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等少数人外,恐怕大多也只能算是“经师”了。所以,黑格尔讽刺孔子“只是一个求实惠的世间智者”,《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不过是“经师”对“人师”的基于误解的“酷评”罢了,钱锺书谓其“无知而掉以轻心”,真是一语中的!
好的老师必须好学与善学。孔子所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便是好学之境;“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则是善学之境。善学不是指对既有知识的学习,而是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发现可以“师法”的人和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这句耳熟能详的经典格言其实大有深意在焉。它是对“师”之内涵的“下沉式释放”,言下之意,虽然“人师”难求,但师者却无处不在,每个人皆有长处可供“师法”。发现别人的长处,同时也意味着认识自己的短处,这样的人反而更容易进步。《淮南子·人间训》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却。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颜回之“仁”、子贡之“辩”、子路之“勇”,孔子皆自叹不如,但三人却以孔子为师,追随终生,原因就在于三人有“能”,而孔子有“道”。根据孔子“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却”的自陈,可知此道正是“中道”。“中道”虽然是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智慧,但具体到“师道”,便是孔子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礼记·学记》有“择师不可不慎”的告诫,实则也等于说,“择师”如“择善”,能够“择善”,便是能够“择师”。因为“善”无处不在,故“师”亦无处不在。能够“择善而从”,则“不善”亦有“善”处。《老子》第二十七章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师资”一词盖由此而来。又《尚书·商书》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论语·子张篇》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杜甫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韩愈也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似此,都是强调为学者应取长补短,转益多师。
因为“无常师”,故能“教学相长”。《礼记·学记》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话阐发“学”与“教”相辅相成之关系极为明晰。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注:“《学记》者,以其记人学教之义。”可见,“教”与“学”密不可分,故“学记”者,实亦可谓“教记”也。
所以能“教学相长”,“自反”“自强”固然是一方面,但就教学而言,又与师生间的问答互动有关。盖有学必有疑,有疑必有问,有问必有答。前引“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一句,其原来的语境如下: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礼记·学记》)
细审文义,不难发现,“善待问”其实就是“善答问”,“记问之学”相当于“不善答问”,而“必也其听语乎”,则是“善答问”的另一种表达。类似的说法亦见于《易·系辞》:“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荀子·劝学》也说:“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响)也。”由此可知,能“听语”和“善待问”,其实就是“君子如响”,作为老师,也就是要能应机设教,应声答问,如钟之待撞,鼓之待捶也。
话又说回来,“教学相长”是相互的,老师的“善待问”,必以学生的“善问”为前提,所谓“小叩小鸣”“大叩大鸣”“不叩不鸣”也。如果把老师比作钟,学生就是“撞钟”人。孔门弟子中,如子贡、子路、子张、樊迟、宰予等,都是很好的撞钟人。偏偏孔子最欣赏的颜回,曾引起孔子的感叹:“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不过,把这两章连起来看,则颜回的“不违”看似“不叩”,但其“无所不说”和“亦足以发”,恰恰说明他对老师所说的道理,无不默识心通,心悦诚服,这种“默而识之,学而不厌”的境界,反倒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君子如响”!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师”,孔子以一人之力,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其门下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余人,形成了春秋末年最大的“学术与教育共同体”,孔子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及教育成就首屈一指,古今中外罕有其匹。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此可谓孔子教育之宗旨。大意是: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尊卑、高下、贤愚的等级差别。
《论语集解》引马融注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朱熹《集注》称:“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盖孔子认为“人之根性虽近而有等差,加之习性相乖,出身不同,故有上下、智愚、贤不肖之别,‘实质平等非不欲也,实不能也。故其兴办私学,有教无类,盖欲通过机会、起点之平等,弭合出身、根性之不同,此真大悲心、大愿力也。”e广义地说,整部《论语》几乎可谓孔子的教育实录。举凡邦君、大夫、士人、乡人、朋友、儿子、弟子甚至是“鄙夫”,皆孔子教育之对象。可以说,孔子所倡导的正是一种“全民教育”。
在此基础上,再去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感觉会大不一样。既然是“有教无类”,则教的范围一定包括“民”,故“由之”本来就含有“教之”之意,而“不可使知之”则是说,通过“教之”,虽然不可使“知之”,至少可以使“由之”(也即“行之”或“用之”)。就此而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是客观表达“教民”之结果。孔子说“有教无类”,与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皆是出于对“民性善”的基本信任。《白虎通义·辟雍》篇所谓“顽钝之民亦足以别于禽兽,而知人伦,故无不教之民”,正此意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以往对于此章的解读,多停留在对“束脩”的辨析上。有以束脩乃贽礼之物,即十条干肉之薄礼者,也有以束脩指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带修饰”之礼者。正如《礼记·曲礼上》有“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训,《易·蒙》有“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之言,皆为强调尊师重教之礼。故朱熹说:“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连《老子》第二十七章都说:“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
以上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我以为,这句话的重心不在前而在后,孔子所要强调的绝非“行束脩”之礼,而是“有教无类”!“吾未尝无诲焉”,其实就是宣布:我的私立学校不设“门槛”,不论“出身”,只要有向学之心,明尊师之礼,我都欢迎!试想,这在教育被上层贵族垄断的春秋时代,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创举!美国学者顾立雅在评价孔子的教育理念时说:“他的确在倡导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使他们真正成为协作社会的成员。他还提议,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应该受到进一步的教育,并让他们得到政府机构的位置。做到了这一步,他情愿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治理国家。他还相信,全体人民最终会有能力对善恶之官员做出区分的。”可以说,“有教无类”的目的就是开启民智,促进阶层的上下流通,打破等级制度带来的资源垄断和身份壁垒。
进一步说,孔子之所以提倡“有教无类”,恐怕与其个人的成长史大有关系。孔子虽系殷商王族之后,但至其父叔梁纥时已家道中落,孔子又系庶出,加上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贫寒孤苦,确实是一介布衣。《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孔子也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可见孔子在社会阶层上,颇以“贱民”自居,未尝以“君子”自任。须知“君子”一词,本指“君王之子”,即在位有爵之人。严格说来,孔子及其门下众多寒门弟子在社会地位上皆属“小人”阶层。但孔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了一个道理,就是“性相近,习相远”——无论出身于“君子”还是“小人”阶层,作为人的本性也即“忠信之质”是彼此相近的,都可以通过“好学”达到更高的境界。孔子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等级壁垒,赋予“君子”以更为深刻的道德内涵,使“君子”成为高于世俗爵位的理想人格。当他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时,等于在宣告:“贵族君子,宁有种乎!”毋宁说,孔子主张教育的权利平等,不是受到任何理论和主义的蛊惑,而是基于对人性和自性的一种大确信!
不过,作为一个智者,孔子对于人性觉知能力的确信是整体性的,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当然存在着先天或后天造成的种种差异。故“性相近”绝不等于“性相同”,“有教无类”也并非“有教无别”。也就是说,“有教无类”是强调“机会平等”,却不能承诺“效果平等”。因此,一方面要贯彻“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追求“普及”,避免“垄断”;另一方面,也要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追求“个性”,防止“一刀切”或“格式化”。“因材施教”一词,虽出自近人郑观应(1842—1922)的《盛世危言》,但其真正的源头却在孔子。这里的“材”,其实也即“人”。我以为,“因材施教”大概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因人施教”,一是“因时施教”。
所谓“因人施教”,是就人的差异而言的。孔子对于人性有非常深刻的洞察,认为人性虽然相近,但资质、根性或者说天分却有高下之分。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意思是: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形而上的高深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形而上的高深道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显然是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等,也即所谓“三品论人”说。孔子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可见孔子是以“中人”自居的。但他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下学而上达”,“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言下之意,只要拥有“中人”的资质,便能够“下学上达”,上达则为君子,下达则为小人。
这还是大体的分类,具体到每个人,还要根据其不同特点予以针对性的点拨。比如,不同弟子问同样的问题,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皆“问孝”;子贡、子路、司马牛皆“问君子”;颜回、仲弓、司马牛皆“问仁”;子路、子张、季康子皆“问政”,孔子的回答却大不一样,这便是“应机设教”,“问同答异”。再比如: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子路和冉有同为“政事科”之选,皆问“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却恰好相反。公西华大概得不到“标准答案”,十分困惑。而孔子的解释是:冉有懦退而不及,故勉之而使进;子路勇进而常过,故抑之而使退。可见,孔子对弟子了如指掌,故而才能对症下药。
所谓“因时施教”,是就学生的年龄及学习程度而言。《礼记·学记》说:“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躐等”犹言“越级”,也即《论语》所谓“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学习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我们由“学不躐等”,自然可以推出“教不躐等”。同樣一个学生,在受教的过程中,也有先后次第、深浅不同,故必须根据其不同的时段予以不同的教诲。比如,孔门弟子中,樊迟的天资不是很高,却喜欢发问,而且一问多发。他曾三次问仁,孔子的回答竟然都不同。依次如下:
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樊迟第一次问仁,孔子答以“仁者先难而后获”,颇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之意;再问,告以“爱人”;三问,则以恭、敬、忠三义答之。盖樊迟长于行动而悟性稍逊,故孔子乃从最切实可行处启发之,皆教其从事上磨练,真可谓循循善诱之“方便法门”。前引列奥·施特劳斯说:“我们必须得出我们不能成为哲人的结论,我们也无法获得这种最高形式的教育。”孔子的教育,在当时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人才,的确堪称“最高形式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