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深的学问,都是要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去”
2020-09-26徐琳玲
徐琳玲

图/沈煜
张定浩的主业是当代文学批评,另一重身份是诗人。近些年,他在默默做着和两样都不相干的事——读解《孟子》。2020年,他出版了新作《孟子读法》。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南宋末年文天祥在被俘就义前挥笔写下的绝命诗句。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汉以来,《孟子》被一代代的学者、思想家、胸怀政治抱负的官员士大夫们注疏、解意、阐发,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人生理想投射其中。北宋朱熹之后,《孟子》位列“四书”,成为每个识字的中国人必读的书目。
酷热的午后,在满地是书的包围下,我和张定浩啜着冰咖啡,一路从尧舜、孔孟、战国诸侯、王安石、朱熹聊到康有为以及今天形形色色诸多人。绿色藤蔓植物爬满了办公室的落地钢窗——这栋巨鹿路上的老花园别墅原是民国时一位刘姓大亨的住宅,1949年后成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办公所在地。
比冰咖啡更提神的,是两千多前孟子和他同时代的人抛出的那些尖锐、切己的问题和相关讨论。
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些对话和讨论依然让今日的我们感到戳心与慌张。
人:人民周刊 张:张定浩
“它就跟一条长河似的,到今天对我们依旧有作用”
人:你的主业是当代文学批评和诗歌,怎么会对孟子的思想学说感兴趣?
张:我从事的工作虽然是和当代文学批评有关,自己也一直喜欢诗歌,但对于先秦古典这一块,一直抱有很深的兴趣。至于这次完整地读解了一遍《孟子》,属于某种因缘际会。《孟子》本身在秦汉时期也是阅读六经的辅导书,是通往经的一条正路,在我看来,它比六经、《论语》还有庄老都要容易理解一点。另一方面,《孟子》又开启了后世所谓的儒家乃至儒学,我们今天对儒家的理解,其根源都可以从《孟子》以及历代对孟子的理解中找到端倪。所以,《孟子》是一本承上启下之书,也是现代普通人用以理解中国古典思想的入门书。
我觉得自己在心性上和孟子也更契合。他有很强的文学性,然后,他也是一个蛮喜欢辩论的人,我好像也总是在跟人辩论,因为写批评文章主要就是在说理,希望把道理讲清楚。孟子的逻辑性很强,事实上先秦诸子里很多人的逻辑性都很强,这种思想的逻辑性是我觉得当代人文学科尤其缺少的一块。通过读《孟子》,我们也可以看看古典哲人们是如何讨论一个问题的,看看他们是如何辩论的。
反观我们现在的辩论,比如《奇葩说》和早年的“大专辩论赛”,那些辩手的目的不是说服对方,而是通过偷换概念,通过滔滔不绝、攻击性言论来让对手猝不及防,最后,他并不是把对方说服了,而是把一些“吃瓜群众”给说服了,然后由他们按个投票键来决定辩论的胜负。这种在古希腊,就是苏格拉底所痛恨的智术师,用言语的修辞来败坏人的心性。
在孟子的时代,辩论不是这样的,是为了把一个概念搞清楚,是为了求真。为此,你要先理解对方,在理解的前提下再讨论一个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比方说孟子跟杨朱学派、跟墨子他们辩论。有很多其他学派的人来找孟子讨论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他们的学说都很熟悉,是先理解了对方在说什么,然后通过各种精彩的譬喻和思维推演,努力为双方找到一个“视野一致性”的平台,最终让对方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思维矛盾或谬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值得今天的人学习的。
人:作為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家经典,《孟子》被历朝历代思想家不断地注疏、阐发。在这个深入过程中,你自己的认识上有没有一些修正和特别的感触?
张:我老早听过张文江老师细读古典文本的课程,因此大致上有一个方向和认识基础。而在自己读解《孟子》的实际过程中,会有一种不断得到验证的感觉,觉得确实如张老师所说——学问之道是要切身,所谓“反身而诚”,所有的事情都是回到自己身上去检验的。

孟子,绢本( 画),明代,江环绘
最高深的学问,都是要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去,这种生命体验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的主观性,而恰恰是在泯灭个人之后慢慢探索到的那个新的自我,如果用孟子的话说,那就是“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
你会发现一代代杰出学者之间都有相通的地方,当然也有分歧。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常会说到儒家的分歧,譬如汉学、宋学之别。但其实读了先秦的这些著作以及后来一代代的著作,回头再来看,你会发现先秦跟现代人的心灵反而更加契合。
我们常常会说儒家很虚伪或者很伪善,对吧?但这些让人产生“伪善”感的概念和意识其实不是孟子或孔子的,他们的著作里面并没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宋以后一代代学者慢慢生产、积累,他们不断地把自己的东西加进去。比方说在朱熹的时代,他加入了一种新哲学,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性,也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当那个时代过去之后,这些东西被抽空,就变成了一个虚伪的口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封建糟粕”。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东西比较反感。但我想说,这些东西是后来的人造成的,孔、孟都没有责任去背负。
所以,我们要回到经典本身,同时又要看历代最杰出学者对它的解释,把经典与解释结合起来,才能作用于我们今天、当下。它才不是一种概念化体系化的知识或者一本让人生畏的古籍,它就跟一条长河似的,到今天对我们依旧有作用。
人:每一代思想者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也要回应他这个时代的需求。刚说到宋儒和汉儒,到晚清,像康有为为宣传、服务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孔孟学说进行某种事实上的“革命”和颠覆。你对南海先生这一路的“六经注我”怎么看?
张:在《孟子》注疏史上,康有为的《孟子微》是一本很重要的参考书。当然,这个又涉及“今古文之争”,涉及一个经学史上很学院派的问题。我只是想说,康有为他们这一代人古典学问底子都是很好的,至少比我们都扎实得多。只是他对他的时代有新的感应,比方他会从《孟子》那里看到很多民主政治的东西,会拿来跟西方对照,会更加强调“外王”这一面。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经典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东西。《孟子》本身其实有很多对抗君权的东西,它并不主张完全要服从君权的。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大一统”的专制还没有形成,《孟子》等于是思想自由时代的一个产物。等到了秦汉以后,这个思想的威力才一点点地显现。尤其到了宋元明清,《孟子》“外王”的一路被一再打压,“内圣”的一面被反复拔高。
在西方也一样的,一代代人谈论柏拉图,其实每代人谈的可能都是和自己有关的一个柏拉图。它不是一个革命的过程,不是一个要打倒重来的过程,而是一代代地叠加、累积,让一个思想变得越来越丰富的过程。我想《孟子》也是这样一本日益丰富的典型著作。
是失败者,还是成功者?
人:其实,孔、孟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失败者,在列国间游说,向诸侯推销自己的“王政”想法,屡屡碰壁,然后再转向著书立作、投身教育。这是不是这一类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一种历史处境?
张:这涉及你怎么看待失败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失败者”的处境,其实都是我们现代人加给孔子和孟子的,因为现代人会觉得我一生不到百年,只有在我活着这段时间成功了才叫成功,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现代以来的、宗教慢慢退去之后的观念——现世生活当中没有获得认可,就是不成功。
但在过去并不是这样,过去一直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在古人看来,这三件事都是可以让人不朽的。“立德”是第一位的,就是你首先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孔、孟在“立德”层面上是没有疑问的;在“立言”上,教育和著述上,他俩也都是成功的;只是在“立功”这个层面上,孔、孟可能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只有他活着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存在;在他们身后,这个被他们影响的世界依旧存在。他们有这样一个不朽的信念在那里,这是中、西古典社会都有的信念。
即便从当时来讲,我觉得他们也是“成功人士”,你看他们被那么多学生围着;然后到每个国家,至少都是一方诸侯来接见他们。我们现在哪个知识分子跑到美国、欧洲去,能惊动哪个总统或国王出来接见,能让各国的名流学者前来讨教?在春秋战国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这么多国家林立,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两个人的存在,从这个层面,他们其实是获得广泛尊重的“成功人士”。你看孟子晚年回故乡,鲁国国君还来求见他,却被他拒绝了。
你说他不成功吗?那你到底怎么理解成功?
人:但他们的这一套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孟子的“王政”理念在现实政治中是失败的。
张:你说这个失败想问的是什么?
人:我是说儒家这一整套“外王”学说。“内圣”,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作为个人的修养,不管是立德还是立言。但是,说到政治实践这一块,他这一套在现实世界里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张:你这么说,还是把“内圣”跟“外王”割裂开了。但是,要知道在孟子的思想中,“外王”并不是一套用来统治别人的术,并不是“富国强兵”,而是希望国君爱民如子,希望治国者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有良心和良能的人。他说齐王有恻隐之心,他是希望去激发齐王心里面的那个属于每个人都有的东西。你说,他激发人心里面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外王”还是“内圣”?
在孟子那里,“内圣”和“外王”是一体的。当时还是一个贵族社会,所以孟子只对士君子和治国者有要求,他知道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是所谓的“民”。那么,当一个治国者内心被激发,从而成为一个足够好的人,他就成为一束足够强的光,周围的民会被他吸附、向他聚拢,这是孟子所意图的“外王”。
况且,在孟子的观念里,其实没有这两个词,“内圣”和“外王”本来就出自后人的总结。“外王”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会,仿佛是一种向外扩张的行为,但其实,从《孟子》中我们可以得知,它应该是一个由内而生的对他者的吸引力,因此,“外王”跟“内圣”原本是一体的,“外王”其实是“内圣”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人:在列国争霸的现实世界里,“富国强兵”的兵家、纵横家的学说会更有市场。孔子和孟子这一套“王政”理念是不是太道德理想主义了?
张: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所谓纵横家的市场也是翻云覆雨,朝生暮死,它并非一直屹立不倒。苏秦、张仪也就是风光一时,其下场都不是很好。
所以到底你用多长时间来衡量所谓的成功,是一个人活着的那段时间,还是说在整个历史时间中。孔子和孟子没有说服当时的国君,但他们慢慢地让后面几代人都听进去了,而且后面一代代中国人还是不停地吸收他们的东西。
这就是文明产生的力量,它跟野蛮不同,野蛮可能就是直接征服你这个民族。但文明就是慢慢地让这个民族一代代的人受他影响、被他滋养。因为野蛮(的胜利)是暂时的,就是一场战争,打赢了就打赢了。你问文明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只能说它本身的运行规则就不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

康有为
先秦著述是自由思想时代的产物
人:我们现在一说到儒家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觉得和“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但阅读原典后,会发现孟子思想里有挑战权力秩序的内容。一个是我們比较熟悉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有一个很有意思,齐王曾向孟子讨教“卿”(高级官员)的区别,孟子说有“异姓”和“贵戚”之别:如果国君有大过,反复谏言不听,异姓之卿可以离开,而有血缘关系的“贵戚之卿”更可以直接起来把国君换掉。
张:对,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到后来的康有为,他们接受过一点西方思想以后,就会在孟子里面“发现”这些所谓新的东西。
孟子思想是有这种革命性在里面。但这也不是孟子的发明,它是古典思想的一个基础部分。禅让、世袭和革命,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三种基本方式。
最好的时代是禅让给贤人。你看《孟子》里面有提到禅让制,他讲得很清楚,禅让绝不是我们后来想象的那样,比如完全是由禅让者尧或者舜说了算,在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还要听很多人的意见,还要考察这个继任人很长时间,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可能是更加严格的淘汰制度。禹和启之后,便是世袭与革命的交替。当世袭制下的昏君当道,民不聊生,革命就会爆发。
我们读的先秦著述,是在“大一统”之前的一个产物,是自由思想的产物,而这种自由思想恰恰是可以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相呼应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亲近性的。这种亲近性其实不是我带给你的,是先秦著作本身有这样的东西在。但问题在于,许多现代人从来没有读过儒家著作,有可能头脑里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对儒家的观念和看法。那么,他头脑里的这些陈词滥调是从哪来的?其实就是被“洗脑”了,甚至是被最糟糕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给洗脑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而且要尽量争取读最好的书,就是希望用最好的东西来对抗那些流俗的影响。
人:所以,你是希望带着今天的读者去读真正的经典本身,以此破除那种别人灌输给他们的想法。
张:如果只是我带着大家读的话,我又成了新的灌输者了。我首先是希望把读者带到一个会客室里面,大厅里坐满了古往今来对儒家所提出的问题感兴趣的杰出心智,读者可以在里面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我的书里面涉及了很多书,后面也列出基本参考文献。
在这样一个大厅里,如果你想跟康有为多聊一会儿,你就再去读康有为的《孟子微》,你想和南懷瑾多聊一会儿,你再把南怀瑾的《孟子七讲》拿出来看看,或者你因此对朱熹和赵岐产生兴趣,去找他们的书,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一个朋友就是看到我这本书里提到唐文治《孟子大义》,就对《孟子大义》产生了兴趣。阅读,就是从一本书走向另外的一些书。我希望我能起到这样一个基础作用。此外,古典著作最重要的是微言和大义,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来自时代语境的变迁造成的词语意思的变迁,阅读古典著作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用今天语境中的词语意思去理解古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文生义。这几个最重要的和最易被误解的地方,也是我这本书希望用力的地方。
我希望我这个书是普通读者的入门书,甚至我觉得我的目标读者是中学文化程度的读者,是他们就可以读的。但即便是资深学者,我也希望能对他有所启发。
人:我们今天去读《论语》、《孟子》这一类古代经典,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靠近古代圣贤们留下的思想?
张:我觉得,首先你要把“经典”的这种想法给破掉,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经典,而且也要把“思想”这个障碍给破掉,不要把它当作一种思想,它就是在谈论具体的某个事情。
你看孔子、孟子他们谈论的都是具体而微的事情。比方说有个人问孟子,自己该不该在这里做官,那么孟子就会根据对方的性格来给出自己的回答。都是很具体的事,是可以跟我们的当下生活相对应的。你不要把它抽象成思想,抽象成经典,把它固化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僵死的东西,你再来评判跟它本来不相干的这个东西是好是坏,这个我觉得是对古典著作很不公平的态度。我们阅读古典,还是要回到孔子和孟子当时的思想现场,回到他们和其他人活泼泼的对话中,到他们中间去体会对话中每个人的心态。
当然,这种体会的过程,你肯定需要一些知识的储备,你知道得越多,你越能体会他当时的心态。譬如“孟子去齐”的表述,在《公孙丑下》的结尾反复出现四次,他在昼城等了齐王三天才离开,非常失望。这个时候,他的弟子就拿他说过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的话来质疑他。然后孟子就说了一段话,意思是“彼一时,此一时”,人要对“时”有清醒的认知。这样的例子很多,《孟子》里几乎每一篇都是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
中国过去没有“哲学”这个词,思想都是在活泼泼的日常交往谈话当中的,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你就是去了解,去体会,耳濡目染。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经常倾听一些比你更杰出的人的对话,那么自然你就会慢慢变得比以前更好一点。
人:孟子所在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有很多思想学说,彼此竞争得很厉害。他花了很多精力在“辟杨墨”,批判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墨家和杨朱一派,说他们是“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记者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你怎么看孟子对竞争学说的这种批判火力?
张: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是被后人所简化的。从孟子角度来讲,当时有很多思想学说并存,他也不是一个四处去找茬、要把谁谁都灭掉的状况,都是别人来见他、向他讨教。当时墨子有个学生来见他,他都不见,他是通过别人转话。他和来客谈论时,其实是他更倾向于辨明两个学说之间的差别。
对于这种思想层面的辩论,你不能仅仅从它的结果来讲,把它看成一个征服。孟子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学说后来会到达这样一个地位,我觉得每一种学说肯定会跟别人辩论,为此,它就始终要保持自身的说服力,或者说有能力让别人慢慢地被说服、慢慢地相信它。

《奇葩说》节目
非蠢即坏的“国学复兴”
人:近二十来年,有一股复兴国学的势头起来。具体分析,大致有两路。一路是知识精英们对政治儒学的新阐述,包括“新天下主义”,还有重新解释“外王内圣”,包括早几年的“儒家宪政主义”。你对这种“大陆新儒家”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张:他们都是很不重要的,而且基本上都是非蠢即坏,要不就是一些读书读蠢了的人,要不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我觉得有一个基本方式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儒家,你看看他的学说到底是要求别人的多还是要求自己的多。很多人都是嘴上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别人干这干那,好让他自己当教主。但是,在孟子那里,永远是“反身而诚”,回到自身,不存在什么“新天下主义”,不存在什么“儒家宪政主义”。回到你自己——你如果是一个王,你把王做好;如果你是一个官,那你把官做好;如果外部环境让你没办法做好,当你自觉跟这个国家没什么关系时,你就可以离开,如果你自认跟这个国家关系深厚,你就跟着它生死相依。
孟子的思想永远是回到自身,是在你自己这个位置上把属于你自己的事情做好,教每个人认识他自己心里那个善念种子的珍贵。他强调的是这一点,而不是搞出一套学说去鼓动别人干什么。
人:中国历来的读书人还是有一种做“帝王师”的情结在那里。
张:那是后来这些人有问题,所谓的“帝王师”都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在孔、孟那里,他们并没有想成为什么“帝王师”,即使他们去游说君王,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消除当时国与国之间不停息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君子如果得到这三种快乐,即使把天下给他,他都不要。“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我觉得这种志向比“帝王师”的志向更高一点,因为所谓的“帝王师”,你所有的荣光还是建立在帝王身上,建立在一个外在的东西上——你是帝王的老师,对吧?你实际还是个“狐假虎威”的状态。但在“君子有三乐”的诉求中,人生的快乐和满足,一是来自于命运,二是来自于自身,而不是说成为什么“帝王师”。
至于一個读书人在人生某个瞬间被某个帝王邀请,做他的辅政,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外在事情,是读书人遭遇的偶然结果,而非读书人期待的一个必然要求。
人:中国历史上这些读书人不管心怀“治国平天下”,甚至想为后世立法、成为当代董仲舒这样的角色。他们跟真正的儒家之间,在你看来究竟是什么关系?
张:我觉得他们更多是一种纵横家了。像你这样的描述,他们其实不是儒家,是纵横家,用自己的三寸之舌,以一套观念、理念去说服某个有权势的人,然后达到某些目的,只是拿儒家的外表来包装一下。
孟子曾说到舜的例子,说舜很贫穷的时候,一日三餐吃野菜,他的态度是“若将终身焉”,好像大概他一生就是这样了,一生就是个什么作为都没有的人。但是,后来尧把天子之位让给他,还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然后他日子一下子过得很好,他的态度则是“若固有之”,好像他以前就一直是这样的。
人:孟子这一段的描述或者想象很吸引人——无论外界和个人际遇如何,他的态度非常安然,非常有贵族气。
张:这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了,不是把经典看成一种思想、一个知识,就是你去体会当事人的这种状况,体会他为什么这么说。“若故有之”,这些富贵自己来了,我很坦然地接受;如果没有富贵,一生不得志就不得志,也没关系。“若将终身”,这是因为他所有的衡量标准永远在自身,或者还在于“天”,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的状态,是和天地之间对应,不是跟世间的帝王对应。所以他不管处在什么状态,有可能是飞黄腾达,也有可能默默终身,都没关系。最终都是要“反身求诚”,都是要回到你个人身上去。
你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里的一段话。从“修身”到“平天下”,它好像是一个次序。但是,我觉得这四样在过去是平行的,是一致的:“修身”、“齐家”就是“治国”,就是“平天下”。反过来,“平天下”也不是一个更高、更飞黄腾达的阶梯。到个人身上,它是一以贯之的,是在自身实现自己的志向。
人:说到政治儒学,譬如“新天下主义”。有知识分子看到中国现在经济崛起了,崛起了以后怎么跟列国相处,在全球格局里建立一种怎样的国际关系,他会想从孔孟那里找到一套可以和西方价值观相抗衡的本土理念,它里面有来自儒家的“天下”观念。
张:这是忽悠人的,就是一种政治话术,跟孔、孟完全没有关系,他们只是把孔孟拿来包装一下。现代政治里有许多就是忽悠来忽悠去的东西。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比如过去说“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其实用的也不是黄老,都是法家和兵家的“术”。
价值观最终是要在人身上践行的,如果只是包装的一套政治话术,那就谈不上什么价值观。孔子说“观其言,察其行”,“己欲立而立人”,是具体的行为在起作用,而不是说你包装出来的那套话术,那东西最终就是指鹿为马的政治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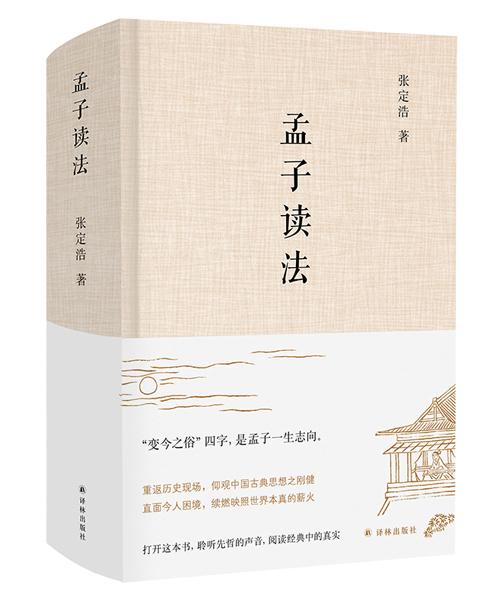
人:近二十年,民间的、更为草根的“国学复兴”也很热,譬如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德班”之类。你对此怎么看?
张:基本上都是割韭菜。学者李零以前就说“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这些东西从学理、从思想学问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值得讨论,和儒家还远没沾到边。
但是从实际上说,你可以想想,出现这些现象,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缺了很多东西,“病急乱投医”,大家可能对社会层面、道德伦理层面有诸多不满,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去找,这些东西就应运而生了。
人:不管贩卖的是真货还是假货,这说明大家普遍有一种精神饥渴。在你看来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不管是孔子或者孟子,能成为解决当下这些中产阶级或者普通民众不满、焦虑感、精神迷茫的一种出路么?
张:如果我简单地回答你,我会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具体到每个人身上的话,能不能解决,其实在于每个人他自己希不希望解决的问题。
这永远是取决于自身,不是说我有困惑了,你给我片药,我马上解决。思想它不是药,不是说我吃一片药就好了,没有这么便捷的。打个比方,思想可能是一种精神锻炼,一个想锻炼身体的人必须自己去跑步,自己去健身,不能说你给我吃片药,我就变成一个健壮的人,然后就百毒不侵了。所以,这种解决最后都是有赖于每个人自身,最后解决的也不是一个社会阶层或者说一群人,它解决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你我他中的某个人,这个人慢慢地感受到一点东西,慢慢地有所改变,再去影响自己周围的人,是这样一点点波及开来的。
“兴”与“命”
人:两年前采访你,提过一个问题——身为作协体制内一员,怕不怕得罪人。因為你的文学批评以尖锐犀利著称,常对功成名就的文坛大佬们开炮。
张:我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提到“得罪”这个词。我们现在说“我得罪你了”,意思是让你不高兴了是吧?这个“罪”是取决于你的高兴不高兴。比方说我写个批评文章,然后你不高兴了,我是得罪你,如果你高兴,那我就没得罪你对吧?这个“罪”是取决于“你”的。
但是,在孟子那里,这个“罪”是取决于一个客观原则和标准,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错,有错,我就得罪了,说起来,是我得罪于“天”。
回到文学批评,如果我写的某段判断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从古典角度来看,我是得罪了,因为我这段判断不对,而不是我说的这个话让某个人不高兴。但如果我的这段判断本身没有问题,以我的理解,在让别人高不高兴这个层面的所谓“得罪”,并不重要。
人:具体到个人,这些历史先贤的思想言说,给你带来了多大影响?
张:当然有影响了,你会对表面的名利没有那么在乎,会对自我的要求更高一点。在个人欲望的层面,你会没有那么焦躁,就是你说的那种中产焦虑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在我身上好像相对没有那么严重。
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糟糕消息,对吧?我觉得微信朋友圈里很多人都表现得很焦虑,天天搞得好像世界要完蛋了。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所有信息都是经过过滤的,另一方面,社会和时代不是一个外在于你的东西,它就在你自己身上。那么你自己做得好一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就会好一点。
如果你觉得现实很糟糕,甚至在这个时代里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楷模,那么可以到过去的时代去找一个楷模,使你自己照样被激发,使你自己的好坏不依附于这个时代,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
《孟子》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待文王而后兴,凡民也”,“凡民”是指一般的老百姓,说他遇到文王了,他就很感动发奋,那就是一个盛世了。但“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真正杰出的人,在一个没有文王的时代依旧能够振作。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读过书的人来讲更应该这样,而不是整天处在一个怨天尤人的状况。具体到自己 身上,就是如何具体地过好每一天,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你对周围的影响。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能做,你就去做,你如果觉得不能做,你也不用抱怨,也不要老是去怂恿别人当烈士。孟子说“反求诸己”,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有一条很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应该是这样的。

2019年2月6日,杭州湘湖景区道南书院,孩子们体验国学课堂
人:小到我们个人,大至国与国、国与整个世界,若能有一份“反求诸己”的自我要求,许多剑拔弩张的对立、撕扯就不存在了。
张:对,不要把所有自己遭遇的问题习惯性地归咎到外界去,归咎到外部环境,是他人、时机或者形势不好,等等。其实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自己的问题。孟子还讲过一句,“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你做不好,最好先问问自己,问题是不是在自己。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命”的问题。孟子也说“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在命运给定自己的生命时间内,尽力成就一个完整的人。“立命”,就是在必然与自然之间谋得一条属于人的上出之路。
我自己做好了,但是我等待命运。我做好了不一定有回报,不是“修身以俟功名”,不是说我做好自己,等待名利的到来,那你有可能是等不来的。我等待命运,等待属于我的命运。
那些造就“黄金时代”的人们
人:如果生在一个不太理想的时代,一个人该怎么生活?他能做些什么,不去做些什么?
张: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的时代。我们翻翻历史,从过去人的言谈中就会发现: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糟糕的,过去的一代是理想的。但是当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又过了几百年,后面的人们会觉得那个糟糕的时代是个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到底是谁成就的呢?就是那些具体的、在时代里面不沉沦的人,慢慢地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时代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那些不愿沉沦、不愿荒废自己一生的这些人身上,而不在于外在的东西。时代就在这些杰出的人的身上,是不是?
孟子说他的志向就是“变今之俗”,他始终是有这种心智和毅力要去实现。他生活的时代是战国,当时他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过了很多年,我们现在觉得那是一个思想空前繁盛的时代。为什么?尤其是在一个漫长的“大一统”之后,我们回看,它又变成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了。到底为什么呢?这个时代理不理想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只能在这个时代中,所谓“不要此身要何身,不生今世生何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