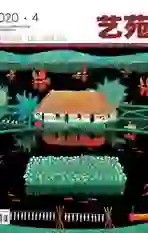《古田军号》: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突围与文化创新
2020-09-24赖宁娜苏文健
赖宁娜 苏文健

【摘要】 《古田军号》作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之一,打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注重说教的固有模式,立足于“讲好故事”这一电影艺术的本质,在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又结合了戏剧矛盾、立体人物形象刻画、美学构图布景等艺术性表达手法,创新了红色历史叙事的表达方式。《古田军号》成功地将“古田会议”的历史价值与传承红色地域文化相融合,为红色记忆注入了当代活力,使这段蕴载红色地域文化的历史更加具体真实可感。影片对福建电影产业发展、传播福建形象意义重大,为福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跨界融合发展及福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 《古田军号》;主旋律电影;历史叙事;艺术表达;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电影产业化、商业化模式的发展转型升级,主旋律电影已逐渐呈现出多元化风格。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叙事技巧与艺术表达、艺术审美与商业运营兼顾的类型化主旋律电影不断涌现,如《战狼2》将爱国主义与动作戏相结合,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以“湄公河惨案”为原型的《湄公河行动》的公安影视作品,较好地影像化当时的惨案真相;由“也门撤侨”事件改编的《红海行动》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将军事题材影片推向新高度。这些主旋律电影在强大的主创团队运作下,取得了政治、艺术与商业的多重成功,成为近些年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现象。其中,红色题材电影《古田军号》也在“古田会议”召开90周年及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献礼上映。该片的叙述视角一改惯用的宏观叙事手法,采用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1],以其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础之上的艺术创新与审美表达[2]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赞赏。影片也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特别奖”、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最佳音乐奖”等奖项。
值得关注的是,《古田军号》对红色地域文化的艺术渲染颇具文化创新性意义。影片以“古田会议”为史实基础,将宏大历史题材与古田当地的生活常态相结合,实现在宏大与微观之间的转换与平衡,既讲好红色故事,又兼顾地域性。“福建土楼”“板凳龙”被赋予了新的红色文化内涵,成为象征“共产党团结人民群众”“心齐方可成龙”的地域性符号,对于促进福建红色文化传播,及推动福建电影、文旅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从叙事模式、人物塑造、文化创新三个方面对《古田军号》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其在历史叙述与艺术表达方面的双重突破,并由此思考电影产业对旅游跨界融合而催生新兴业态的文化创新之路。
一、颠覆成规的叙事创新
传统主旋律电影讲求宏观叙事,通过宏伟壮烈的影像场面将红色主题进行升华。与之相较,《古田军号》的叙事策略有着明显不同。《古田军号》响应时代号召,致力于“讲好福建故事”,从小军号手池有田的视角回忆历史,由小军号手之孙来讲述这段历史,将人物的塑造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巧妙运用蒙太奇手法进行层次化叙事、多线叙事,广泛使用物品和场景的象征意义,让历史故事从细节铺展开来。影片将历史与现代的发展内嵌互现,营造出强大的视觉震撼,让观众能从今昔对比中感受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曲折与坚守初心的不易。
首先,《古田军号》一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宏观叙事风格,将镜头聚焦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鲜活个体上,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增强了历史叙事的现实感与真实感。小军号手跟随毛主席,亲历了“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的过程,影片以故事外的小军号手之孙作为旁白来叙述历史,打破了以往历史题材单一的时间叙事,运用蒙太奇手法将叙述者“我”的现实与亲历者“爷爷”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呼应。土楼、板凳龙等场景符号的多次切换比对,将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生活物品的对举,暗喻着两个时代生活的不同与新变,从侧面体现了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与当年党团结人民群众的艰苦斗争密不可分;舞龙场景的前后呼应,很大程度上能增强观众的代入感,让之深切感受到“古田會议”以来的山乡巨变。过去和现在自由切换,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无形中建构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自新中国电影“献礼展映”的电影文化模式开展以来,一直都在向度不一的电影叙事实践中探寻政治与电影表现平衡点之上的新的叙事范式。[3]从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前往井冈山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师,到“三湾改编”整顿军队、加强军队由党领导的思想建设,再到之后朱毛井冈山会师整编队伍为“红四军”,构成了电影的宏观叙事背景。而作为军长的朱德和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军民关系、军队内部肃整等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争论时有发生,刘安恭的加入更使矛盾激化,毛泽东只好前往上杭。毛泽东离开后,错误的指导思想导致军队管理混乱,在战争中人员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直到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确立了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和军队建设的中心思想,红四军才重新回到正轨。电影以此历史背景展开微观叙事,将“朱毛之争”融入生活细节之处,通过层层矛盾带来的艺术张力营造了紧张感。让观众在复杂的内外矛盾与危机中认识到会议胜利召开的不易,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红色故事影视化的创新突破。
其次,《古田军号》以矛盾冲突推动多线叙事。影片从小军号手和魏金奎的冲突开始分化为三线叙事,即以整治军风纪律为主线,小军号手家族的吹号使命与个人成长为第一条辅线,毛泽东前往上杭开展群众工作和启蒙教育为第二条辅线。影片最初以军队出现“军阀作风”问题为切入,代表着旧军阀作风陋习的士兵魏金奎因被小军号手撞见抽大烟而对其大打出手,通过个人冲突展现了军队存在的不良风气。红四军队伍中有不少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士兵,但他们加入部队的目的并不单纯,只为吃喝不愁,没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的红色革命理想,反而做出强取百姓钱财、调戏良家妇女、对战俘使用暴力等不耻之事。由此展开朱德和毛泽东在军队管理上的分歧,这条叙事线在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来之后,更是愈演愈烈,从小团体内部急剧上升为中央和前委的矛盾,领导人内部内部剑拔弩张。深受苏联革命影响的刘安恭,认为中国红军应该照搬苏联红军的理论来实践,坚持以攻打城市为首要任务,反对毛泽东发动群众势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这条叙事线,为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而被迫离开埋下伏笔,直到毛泽东回来召开“古田会议”才扭转了此前军队由错误指导而造成的惨烈局面。
小军号手是剧中毛泽东行为活动的主要旁观者,以第三视角见证了前面两条叙事线的发展。他见证了毛泽东与朱德、刘安恭二人在军队管理和作战策略上的分歧,以及军队管理在毛泽东离开前后的变化对比,也亲历了毛泽东前往上杭办教育开展群众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小军号手又不仅仅是一位旁观者,他肩负着继承革命事业的责任。小军号手的哥哥和父亲也是吹号手,父兄二人在战火中壮烈牺牲后,小军号手接过哥哥手中的军号,延续着为军队吹号的使命,期望吹响一次次冲锋的号角来换取革命的胜利。
影片注重内部矛盾的叙述,这是导演的勇气,亦是主旋律电影的突破。虽然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但最终多线叙事合一,矛盾在加反对令章加黑边与最后加黑边的镜头下化解,黑边的意义也由纪念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变成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中牺牲的同志,铭记军队指挥思想错误的教训。故事在中铺垫的脉络收束,推动了观众的情感升华。电影在红军动身远征中结尾,颇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叙事内涵。
二、真实可感的人物塑造
在人物塑造上,《古田军号》将宏大的历史进行语境化、细节化,通过合情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彰显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温情的一面。相对于以往空洞的伟大形象刻画,影片将历史的真实融入到鲜活的个体中活动中,并展开符合逻辑的细节补充,使人物塑造变得立体、真实、可感,创新了主旋律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这部电影颠覆了观众此前对于红色革命电影、伟人英雄形象的认知,让观众意识到是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其一,细节制胜,以小见大。陈力导演的《湘江北去》《血战湘江》等主旋律电影均关照宏大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与人物关系,却又始终保持着对细节的观察与捕捉:《湘江北去》中,在图书馆打零工的毛泽东深受陈独秀的情绪感染,竟不自觉地为其革命信念奔走呼喊,不顾管理员的阻拦冲进馆内高声叫好,彰显出毛泽东热血激情、昂扬向上的斗志,这从细微小事入手暗示了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转折;《血战湘江》亦是如此,在描绘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等人激烈争论的场景时,既通过激烈言辞体现其直率的性格和坚定的革命态度,又以叹息和沉默的动作反映其内心的纠结无奈。但是,以更加鲜明的姿态运用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陈力导演的新作《古田军号》则更进上层楼。影片借助生活场景来展现人物性格及人物关系,将大矛盾体现在微小之处,突显出毛泽东和朱德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烟火气十足。特别是通过床板隔断一拉一合等小动作的妙用,展现了朱毛关系的紧张与舒缓。电影还塑造了多位形象鲜明的古田人,在毛泽东离开上杭后,张素娥接过粉笔,终生致力于当地的教育事业,意味着毛泽东在群众中播下的启蒙种子得以薪火相传,党的事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军号”这一符号背后的意义也借由传递这一动作得到延伸,独特的传承精神也寓于其中——“古田会议”精神代有传人,红色革命精神薪火不断。
同时,影片也因对细节的高度关注而突破了主旋律电影中常见的“脸谱化”问题。在《湘江北去》中,陈力着重表现青年的救国热情与昂扬斗志,正面赞扬敢为人先、奋发有为的精神,但仍不可避免地对毛泽东、萧子升等正面青年形象进行了过于理想化的刻画。如影片对毛泽东、陶斯咏、萧子升之间不同救国理念的冲突展现不足,以无波澜的状态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诸多富有深度的内容在影片中被淡化,使观众难以从影片中理解时代背景下领袖人物的抉择。但在《古田军号》中,可以明显看到陈力的改变,其中的领导人物不再仅仅只是单一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输出,而是在丰富细节的呈现下更加鲜活立体。如毛泽东和朱德因矛盾而争吵不休,陈毅夹在两人关系之间斡旋周转的刻画,不回避伟人之间的个人矛盾和治理军队理念上的分歧;但是又通过朱德给小军号手安排做衣服,毛泽东便即刻掏出写有小军号手尺寸的纸条递给裁缝的细节,来凸显二人相互配合的默契,说明了矛盾也不是绝不可调和。又如在毛泽东和朱德争论中语言的使用,毛泽东的对白设计注重针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朱德這一角色的语言使用则暗含对苏联模式的亲睐,以此展现出不同的人物形象。
此外,对刘安恭形象的刻画也是《古田军号》的一大突破。影片并未对刘安恭进行以偏概全的评价,而是站在中立立场上对刘安恭的思想坚持和牺牲进行陈述,既没有猛烈批判,也没有过度渲染。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转折期,人在历史洪荒中前行凭的是坚定的信仰与满腔的热血。刘安恭这一人物形象总体上是偏正面的,影片对人物进行了立体多元的审视,形象刻画不偏不倚,让历史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其二,人物青春浪漫化呼应时代审美。《古田军号》能吸引大批的年轻观影群体,得益于其对人物形象的青春浪漫化构建。如何将红色基因的传承熔铸于时代语境之中,打造一部可以“让历史照进现实”的年轻化主旋律电影?导演陈力说道:“在新时代如何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力求创新和突破,力求宏大叙事与个性表达的融合。”为了和当代的青年人保持同样的语境,营造代入感,《古田军号》在故事构架、艺术表达、背景音乐选取、镜头拍摄状态、画面剪辑等方面都选择了青年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影片对人物塑造一改传统红色人物形象的成熟稳健,将36岁的毛泽东、28岁的陈毅、22岁的林彪,这些青年时代青年人该有的青春、浪漫、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如电影中毛泽东在造纸劳作中提到妇女解放时的意气风发,拿起毛笔蘸墨挥毫,是符合其年龄性格的到位表现。人物气质与革命气质水乳交融,可见电影制作团队对革命历史的深入考究与性格艺术化的深入分析。
综上,《古田军号》试图与年轻化的市场流量体系达成有机融合,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商业化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影片选用“小鲜肉”来扮演领袖毛泽东,可谓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毛泽东的扮演者王仁君也被年轻观众称为银幕史上最俊美的毛泽东形象。“演员阵容上的明星化,题材与叙事上的类型化,视听效果上的奇观化,是主旋律电影最近几年来在商业化道路上所主要做出的几项尝试。”[4]这一次年轻化尝试有效打破观众对领袖特型化扮演者的审美疲劳,使之在艺术上追求神似高于形似。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激情澎湃、血气阳刚,既有年轻人的急躁冲动,也有革命者的英勇无畏,让荧幕前的观众一赏伟人青春浪漫的真性情,并为年轻群体重新定义“青春”带来了正面深刻的影响。
三、文化创新中的符号化生产
电影影像是一种符号化的语言表达。导演往往借助符号载体来进行艺术生产,彰显文化创新的自觉诉求。符号的构建各有不同,包括色彩符号、物质符号、地域符号等。而符号标识的差异性逻辑,导致了景观社会的视觉认知,符号通过形象生产而生产自身。在影像中,符号消解了自身的抽象,并将自身再生产为一种符号,从而赋予符号特有的魅力。特定文化空间中表意符号的编码,可以形成一条能引起情感共鸣的纽带,将时代、作品、观众关联在一起,正是电影艺术的魅力所在。影片《古田军号》对符号运用十分成熟,引领观众通过具有特殊象征的符号编码体味意义深远的关键点。
首先,红色主旋律的视觉化运用。红色作为革命的象征,红色在我国的意识形态环境里往往被赋予了神圣等意义,为避免在影像化世界里刻意表述,《古田军号》采取了类似于美术构图的取景角度与色彩选择,将色彩的明暗度与革命事业的发展阶段相呼应。起初电影主体色调是陈暗的,这与故事所处的历史背景相一致,红四军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转折关键期,革命道路正在“大雾”中一步步摸索。但在电影中能经常看到一抹亮眼的红色点缀画面,如毛泽观看舞龙时发出“心齐方可成龙”感慨时,连接板凳的红色布条鲜艳明亮;又如小军号手挂在腰间的军号在不同的场景颜色也不同,在战争中是染满鲜血的,而在“古田会议”现场则是鲜红且干净的——红色在电影场景中随着人物情节的变换切换不同的色调,它的颜色变化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
《古田军号》专注“红色”意象的艺术化表达,没有在宏观叙事上展现革命道路的曲折和军队的越战越勇,而是通过红军战士流血牺牲时那一抹红色体现悲壮与英勇。如椿娃子的死,毛泽东将他抱在怀中,如古典浪漫主义油画般的构图,让那血的鲜红庄严肃穆、意义非凡。还有军号上的红穗,象征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点亮前方的光明之路、叫醒世人勇于反抗,震撼人心。不经意间露出的红旗,长镜头中忽明忽暗的红色背景,不刻意不突出地表现着红色,但在潜意识中影响着观众,让红色成为特殊的意象又不失宏大的意义,与电影叙事相辅相成,使观众能有更强的情感共鸣。
其次,物质符号的隐喻性营构。影片对物质符号所指涉的象征寓意也匠心独具。故事以小军号手的视角展开,军号在故事开篇就被赋予重要意义,即革命启航的象征。小军号手的父亲和哥哥都作为吹号人战死沙场,军号作为一种遗志的继承从个人上升为集体,活着的人继承烈士的斗志,听到号角齐心协力,不畏牺牲,浴血奋战。同时,军号也成为了连接历史时空的符号,其现实意义也被升华,象征红色精神生生不息。此外,板凳的运用也颇为巧妙,舞龙的由板凳连接而成,象征着人民群众团结凝聚在一起,也暗示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关系的变化。在影片结尾开会的场景上,刚开始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坐在各自的板凳上,到后来三人坐在了同一条凳子上,象征着革命领袖矛盾化解,思想统一。板凳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生动展现了毛朱陈三人关系的变化,从一开始的分歧、争执和分离,到最后坐在一起探索寻找党和国家的事业和出路,确立建立党和军队的正确思想,展现了他们团结一心完成时代使命的信念,体现了他们在革命摸索道路上的不易,也是军队团结、军民一心,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缘由所在。
最后,地方性形象的符号化编码。《古田军号》中,与“红色”紧密相连的是福建的地域化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福建土楼,其反复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福建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地域化特色。土楼是古田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建筑,是当年客家人团结起来抵御外部危险的遗產。福建土楼已然成为福建的一张烫金名片。《古田军号》将青年毛泽东站在过去与现代的土楼前观看舞板凳龙的镜头拼贴在一起,并通过毛泽东“心齐方可成龙”感慨赋予舞板凳龙新的内涵:无数板凳连接成的舞龙,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群众心连心,也暗示着党的强大与成就皆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来自群众的支持,党的艰苦奋斗和成就也是为了人民;人民因支持党而翻身做主人,获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事实上,影片中呈现的舞板凳龙是福建的传统民间文艺活动,更深层次地表明了红军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也象征着人民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美好生活终将会来临,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了新时代人民生活的镜头,民众舞板凳龙,寓意真正的繁荣祥和、国泰民安已经到来,革命的付出是值得的。
《古田军号》善于对福建地方性文化特色的符号化编码、生产与再生产是绝非偶然的。此影片的导演陈力是福建人,她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致力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和传播正能量。此次《古田军号》的明显突破在于对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红色符号的守正创新,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与古田人民、福建名片的土楼文化结合起来,赋予了红色新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强旅”“科技强旅”的新思考。就在此时,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于2019年11月19日至23日在厦门举办,此后永久落户于福建厦门,这对福建电影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因此,《古田军号》的成功,为福建影视产业的发展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经验。红色历史成功的影像化、符号化,不仅对于讲好福建故事、传播福建形象,提升福建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促进意义,而且由此推动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形成,促成产业链重构,电影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重要路径。
结 语
《古田军号》作为当今我国主旋律电影的优秀作品,不仅在红色地域化表达方面堪称典范,而且在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上取得了双重的突破,打破了过去主旋律电影普遍存在的“与主流意识形态过于紧密的结合,连影评的形式只有一种单一的政治评判”[5]现象。影片既有历史人物的抉择,也有普通人物的奉献和牺牲,伟大源于平凡,通过丰富细腻的主体情感营造和可感真实的细节把握,较好地消解了那种“因为这是一部主旋律‘红色电影就心生抵触”的负面观影现象。《古田军号》为主旋律电影树立了时代的新标杆,在主流意识形态、文本创作、历史考究、艺术理想、市场需求等方面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让我们看到了一部求真、融合的红色历史题材影片。传统的福建土楼在其中被赋予的红色意义焕发出了新活力,舞板凳龙这一民俗活动在影片中得到了新的诠释,成为象征地域性特色的红色符号,也是特色鲜明的福建文化名片。作为红色福建符号化的视觉影像艺术,《古田军号》背后潜藏的对福建形象、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具有重要的文化创新意义。在当下的产业、科技背景下,这种文化创新实践更能让人意识到,主旋律电影与地域性结合,可以催生出文化创新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昭示出不可限量的新动能,值得人们重视。
参考文献:
[1]王一川.《古田军号》:今昔对视中的微宏叙事[J].电影艺术,2019(5).
[2]胡智锋,陈寅.《古田军号》:历史真实的艺术创新与审美表达[J].当代电影,2019(8).
[3]虞吉.“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新中国电影文化模式与叙事范式的创生[J].文艺研究,2014(3).
[4]路春艳,王占利.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与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J].当代电影,2013(8).
[5]章柏青.中国电影批评:反思中前进[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作者简介:赖宁娜,华侨大学文学院本科生;苏文健,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批评、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