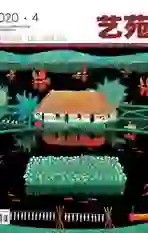《迷途的羔羊》与《生路》
2020-09-24韩若冰
【摘要】 《生路》是首部在我国公映的苏联电影,其中改造流浪儿童的社会主义事业启发了蔡楚生的同题材影片《迷途的羔羊》。二者均取材于社会现实,也都在家庭与社会的双线模式下展开叙事,并思考社会变革的可行之路,但所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生路》中作为政治新人的流浪儿在《迷途的羔羊》中则作为道德喻体而出场,折射出同一时代的中苏双方不同的儿童观、社会主体观。
【关键词】 《迷途的羔羊》;《生路》;流浪儿童;中苏电影比较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1932年底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随之而来的是苏联电影在国内的规模化引入。《生路》是双方复交后首部在国内公映的苏联电影,夏衍、陈鲤庭、于伶乃至鲁迅等文艺界的进步人士纷纷为之捧场。据司徒慧敏回忆,自己和夏衍曾多次将苏联电影用倒片机挨个记录镜头学习,其中就包括《生路》,可见它影响之深远。[1]765不仅如此,影片中苏联的社会建设经验同时亦启发了中国影人思考具体的社会问题,《迷途的羔羊》即是一例。同时期的两部影片,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社会问题解决思路。
一、从《生路》到《迷途的羔羊》:作為社会文本的电影
《迷途的羔羊》(以下简称《羔羊》)是左翼导演蔡楚生拍摄于1936年的电影,讲述了主人公小三子的流浪经历。蔡楚生对于流浪儿的关注并非偶然,当时国内已有大量介绍国际流浪儿救济的资料,其中最引起震动的是在儿童改造方面曾经落后,而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取得巨大成功的苏联。毫无疑问,电影在此不但是作为视觉艺术,也是作为一种现实经验被中国观众们所接受。1933年,《苏俄评论》上刊登了名为“凝冰”的作者对苏联“扑灭流浪儿童”现象的系列报道。文章中列举了苏联的种种举措:“一九一九年人民委员会议决,凡十四岁以下儿童之膳食,俱由国家供给,并建造许多儿童家,供彼等住宿,一九二三年,创立‘改造儿童生活列宁基金,其目的即为扑灭流浪儿童。”[2]这构成了观众理解《生路》的直接知识背景,同时也提供了想象苏联社会现状的资源。
这部引起巨大反响的《生路》是苏联的首部有声片,拍摄于1931年,1932年2月16日在上海大戏剧上映,随后在国内公映。其明快雄健的美学风格与现实主义题材获得了广泛的赞许:“(电影)清清楚楚在二小时中给你明晰的解释:就是社会最下层的群众,正是社会的建设者!”[3]671“《生路》把社会视野与个人关系解释得清楚而切实。”[3]669《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这一重要的电影宣传阵地用三天的版面,共计发表了8篇评论和14篇短文,足见其轰动程度。
实际上,苏联的儿童改造问题对于中国文艺界来说,并不是首开先河,至少鲁迅等学者对于苏俄儿童文学的翻译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但作为文学文本,它始终局限在文学和儿童心理学领域,鲜少像《生路》这样上升为公共问题,引起普遍的关心。1934年至1935年鲁迅翻译了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创作的儿童小说《表》,这是一个与《生路》在故事内容和主旨上有着极高相似度的作品,时人对它的接受方式可以与《生路》作一个比较。胡风给这篇译作的总体评价是:“浮浪儿,这是一个具体的儿童,旧社会和变乱时期所留下的疮疖之一放浪习性底脱除和蜕变,被描写在这里的是一个真实的过程,……这是《表》底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的最有力的反抗,也就是《表》底最基本的特色了。”[4]351胡风尽管注意到了这类儿童文学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的革新作用,但他并没有对其现实意义作出深究,在儿童文艺史的范畴内讨论是理解苏联儿童文艺作品的主流范式。
在这样的接受背景之下,蔡楚生对于流浪儿题材的改编和创作才彰显出他的独特性:在《羔羊》当中,他试图采取和《生路》一样的手法,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而非止步于艺术本身。在《〈迷途的羔羊〉杂谈》中他提到,自己最早受到郑应时的启发,开始关注鲁迅的译作《表》,并希望将它改为中国电影,或者使用国人演员翻拍《生路》,但最终这两个念头都被他自己否决了。究其原因,正在于“撇开社会问题单谈电影,我们是在没有勇气去违背‘艺术的良心,在银幕上替一班流浪儿童们建筑一个‘乌托邦。”[5]虽然歆羡于苏联的建设成就与《生路》的艺术效果,蔡楚生仍然清醒地知道,电影的光明结局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反而会沦为腐朽政府粉饰太平的帮凶。而如要将教养院这样的社会机构付诸实践,在中国将苏联儿童的幸福“变现”则难度极大。这也使得《羔羊》暴露的成分多于展望的成分,底蕴上的晦暗多于光明。但这无损于《羔羊》和《生路》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少观众在观看了《羔羊》后表示联想到了“《生路》里流浪儿童的出路,又想到《冬天乐》里对富有者的嘲弄”。[6]同时《羔羊》也成功地激发了观众对变革现实的要求,有的要求解放劳苦大众来保障儿童的幸福[7],有的在对比了《生路》和《羔羊》后感慨“只有在为人类谋幸福的国家,儿童才有出路”[8],有的则将矛头指向了富人的虚伪[9]。如果说对《表》的阅读还局限在少部分关心儿童文艺的群体当中,局限在文学史上的话,那么《生路》和《羔羊》则借助电影这一大众媒介成功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且使得《表》《生路》与《羔羊》由于和眼前现实的紧密关联被纳入到同一谱系当中。
《生路》在国内的传播,改变了以往对于儿童文艺局限于学科内部的评价方式,同时也开启了将此种文艺现象视为社会文本,投射到现实、从中寻找社会改造方案的观看方式。然而电影作为艺术形式始终保留着溢出作者创作初衷的危险,蔡楚生面对艰难重重的中国现实,为流浪儿改定的结局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30年代社会主体观念自身的困境。
二、《迷途的羔羊》:社会道德隐喻与家庭叙事
出于“艺术的良心”,蔡楚生对流浪儿的命运做出了谨慎的处理,使之更符合中国的现实。主人公小三子出生在农村,因盗匪猖獗、旱灾肆虐而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之际,他在沈家老仆人的帮助下偷偷混进富商沈慈航的船上,偷渡来到上海,从此成为街头流浪少年的一员。而在小三子为温饱发愁的同时,沈慈航则面临着家庭危机:他的原配夫人与她所生的孩子都已过世,而续弦的太太则是一名摩登女性。她与一名年轻男性有染,并且长期服用避孕金方来避免生育子女,这令一心渴求后代的沈慈航束手无策。一次偶然的机会,沈慈航发现老仆人接济的小三子与自己夭折的儿子十分肖似。为了防止自己断子绝孙,也为了捍卫自己作为丈夫在家中的话语权,他决定收养小三子。而小三子则因为与富人家庭格格不入,加上撞破了摩登太太的外遇而被陷害,被迫离家出走,投奔老仆人。老仆人与他所收留的众多流浪儿们组成了新的家庭。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结尾,老仆人去世,孩子们失去了庇护,由于偷抢赈灾救济物资被逼上绝路,而这一片段在新中国则被删减。
在电影上映之后,读者问蔡楚生为什么不专注于表现流浪儿的悲惨生活,而要在电影中穿插一段富人夫妻的闹剧。他的回答是,如果撇下富商作为流浪生活的对照,那银幕上小瘪三的“丑态”多少会引起一些观众的抵触情绪,从而损失一部分社会教育意义。[10]但这个回答的说服力相当有限。一个影坛同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蔡楚生如能将小三子被驱逐设计为从他自己的苦难经历与自然性格出发,而不是借助艳闻巧合,贫富之间的对立就会更加自然和鲜明。[11]358真正削弱了故事的现实批判力度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与家庭的双线叙事。有学者认为,《羔羊》中作为主线的流浪儿童命运对卓别林电影的借鉴十分有限,相反真正纯熟的却是讲述收养小三子的沈富商家庭婚姻纠葛这一部分。[12]1-6蔡楚生的不少电影均采用了这种主副线的情节结构,而副线中的噱头和闹剧常有喧宾夺主的嫌疑。他对于臃肿的家庭喜剧割舍不下,恰恰反映出家庭空间在他思考社会出路时的重要性。
这部社会题材的影片始终围绕着家庭的破碎与重建展开:片头小三子农村家庭的破产构成了他进城、成为沈慈航螟蛉之子的契机,而沈家破碎背德的家庭關系同时却是将小三子从这个家庭驱逐出去的原因。全片称得上真正的“家”的,只有老仆人与流浪儿们组成的临时家庭。小三子的被收养经历,乃是导演设想的一种问题解决方案,即流浪儿问题能否通过让他们重新加入家庭而获得改造。答案显然是不能。蔡楚生将这种冲突嵌套在一个家庭伦理问题,小三子是因为无意撞破了摩登太太的奸情而被迫离开,听信谗言的沈慈航也缺乏真正的同情心,对穷人存在偏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虽然贫困而有着热心肠的老仆人。导演对于家庭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表露了对于摩登家庭的不信任与担忧,另一方面则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正义纯洁的“道德家庭”之上。增加沈氏夫妇家庭生活的副线并非如批评家尘无所理解的“对于布尔乔亚女性的暴露……都是不必要的”[13],在结构上它或许使得故事情节稍显混乱,但在观念层面上,其叙事功能在于建立一种通俗批判,而不威胁家庭自身作为最终价值载体的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蔡楚生对于婚姻家庭纠葛的偏爱,继承自市民电影传统。从开家庭情节片风气之先的《孤儿救祖记》开始,家庭关系的错位与恢复、贫富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就成为了国产电影的重要创作资源。随后的《苦儿弱女》《冯大少爷》《最后之良心》《醉乡遗恨》《小情人》《儿孙福》等作品,无不流露出深刻的儒家伦理传统的印记,围绕着夫妻之间、代际之间的家庭生活展开。而深受影响的蔡楚生,在《粉红色的梦》《都会的早晨》中也延续了这种道德诉求,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城市和乡村、传统和摩登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在最后总是由一名纯洁善良的人物予以化解。矛盾制造与纾解的惯性也延伸到了《羔羊》当中,净化与说教的任务由小三子和老仆人这两个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值得同情的角色来完成。惩恶扬善的通俗趣味始终盘旋在蔡楚生的电影艺术上空,他在《羔羊》这部电影中展示了现代的社会矛盾是如何在家庭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规范中寻找出路并将之与阶级批判相结合的——小三子与老仆人所构成的家庭,建立在两人相近的阶级身份之上,而此种身份又被蒙上了一层道德性格的面纱。尽管从电影表层的情节来看,不论是老仆人还是富商,都无法根本解决流浪儿问题,但在无意识层面上,这种家庭伦理的情节设计依然以迂回的方式暗示了价值取向:小三子尽管在物质条件上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社会问题少年,但在道德层面上,他却成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隐喻。导演通过小三子的悲惨经历表达了自身对于建设社会的担忧,正如蔡楚生所呼告的:“为着民族的生存计,对这些新中国的主人,是应该如何地来尽最大的努力?”[14]未来社会的主体呈现为被压抑然而正直天真的儿童形象。
三、《生路》:批判家庭叙事与构建集体
《羔羊》在有意识地揭露出社会救济的破产时,也悬置了一个问题:这群迷途的羔羊应该往哪儿走?《生路》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也正是因为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整体化的解决方案,即依托新的社会制度将他们转化为社会建设力量。拍摄于苏联的五年建设时期,《生路》集中展现了新社会给这群流浪儿童带来的面貌转变,作为旧社会改造的代表性成就。影片开场,麦司他法等流浪少年抢劫了一位妇女,造成她意外死亡。他们因此被扭送到孔姆那劳动公学接受教育,指导员赛盖尼夫则代表新政权对他们施以照顾、矫正他们小偷小摸的习性。麦司他法最终成为了合格的铁路工,为了保卫铁路安全而牺牲。《生路》展现了流浪儿们从社会毒瘤到人民一份子的身份转换。
在《羔羊》中,小三子尚且是社会所要拯救的失足儿童,而麦司他法等流浪儿童则不然,通过参与集体劳动他们彻底建立起自己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主体身份。影片末尾的《铁道建设歌》唱道:“抛弃了我们的懒癖,举起了建设的旗号!用我们的手将旧世界连根的推倒!……打走了全国的基础,创造起新生的根苗!……我们大家融合成一个伟大的劳动的家族!”[15]457尽管这里也涉及到“家族”这样的意象,它指涉的却不是个别小家庭,而置换以集体、社会这样的宏大对象,构建起与家庭相区别的公共空间。对于《羔羊》而言,小三子不得不被纳入到家庭叙事中,这是因为作为中国儿童,他与社会的关联很大程度上只能在宗族空间中发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16]39而家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为一种组织单位,起到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作用,肩负着不但是社会的而且是乡村自治意义上的政治功能。近代乡村的破产破坏了这种稳定结构,小三子这类儿童流落到城市后,并没有类似的社会机构接管他们。30年代的社会调查指出,流浪儿童如果不被收容所或普通人家收养,大部分会受制于非法团体(《羔羊》中有所表现),成年之后沦为社会闲散人士。[17]不像工人那样能够形成具备组织能力的阶级,他们构成了毛泽东所谓“游民无产者”群体中的一员,生活不安定,尽管具有革命性,破坏性却也很大。[18]13因此蔡楚生在《羔羊》中设计的收养情节,从现实来说注定无法实现,但这种设想同时也表明,崩溃的家庭单位切断了小三子被组织进社会的最后可能。相反,《生路》中的劳动公学则代替家庭肩负起了责任。
拍摄于苏联五年建设时期的《生路》有着明确的历史基础。参与电影工作的人员研究了当时苏联的柳别尔崔公学,并且参加了消灭儿童流浪现象委员会的工作,影片的演员也是具有相关亲身经历、从莫斯科附近的公学中挑选出来的。这一时期的流浪儿童改造服务于动员一切力量参与新社会建设工作的现实目的,劳动公学则是为了配合这项工作创立出来的机构。20年代初,马卡连柯创立了首个工学团(一年后改名高尔基工学团),从事违法青少年的改造与教育,此后他又领导了捷尔任斯基劳动公社等流浪儿收容改造机构。在1927年起草的《哈尔科夫区儿童联合工学团组织草案》中,他明确指出这类儿童机关的目标是“培养健康的、有劳动能力的、守纪律的和有政治知识的苏联公民”,同时联合工学团下划分出基层工学团与作为改造所的工学团对街头儿童和违法少年进行教养,进行职业训练、日后分配到生产部门或学校中。[19]4251934年马卡连柯又起草了《儿童联合工学团组织草案的说明书》,在这份带有总结性和指导性的材料中,他进一步指出了儿童之家作为儿童走向社会的过渡机构的性质:“应当采用一切措施使儿童之家不再是消费机关,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劳动教育机关。”[19]463并非偶然的是,《羔羊》中也有这样一个情节,老仆人在收留了小三子后,教育他要“好好做工”。在此,“做工”強调的是生存意义上满足温饱的手段,而《生路》中的“劳动”则更进一步,强调阶级意识的萌发与劳动者的自我启蒙。在《生路》中二者的差别被颇具深意地表现出来:麦司他法过去常常在街上用袖里藏刀的手法割掉时髦女性身上昂贵的皮料,而在劳动公学中他的刀法则被应用在制皮工艺上。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制皮是生产性的、能够参与到社会系统分工中的。
不过,尽管《生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主题上也符合五年建设的主旋律,它也与《羔羊》一样遭遇了对副线剧情的指摘。影片中,家庭的崩溃与重建发生在配角柯尔卡身上。柯尔卡的母亲在小流氓抢劫的过程中被撞倒,不治身亡,他的父亲因此酗酒消沉,殴打柯尔卡。他在离家出走之后同样进入公学接受教育,并成为列车的管车手。故事的末尾他终于和父亲团聚。电影以柯尔卡的家破人亡开始,以柯尔卡父子的团圆结束。对此,苏联《无产电影》的评论家指责它“用感伤的人道主义和软绵绵的手法来表现现实”[20]124,陷入了资产阶级的庸俗情调。列别捷夫在评价这部电影时也十分严苛地批评道,“作者把柯尔卡这个偶然的家庭生活故事加以典型化,同时赋予它以擦眼抹泪的感伤的情调的做法”[20]126遮蔽了流浪儿现象的社会根源。如果说《羔羊》对家庭之社会功能的坚持体现了旧社会的道德本位观念的话,那么苏联方面对于《生路》的苛刻批评则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对于家庭生活的不信任,对家庭温情可能损害社会主义动员能力的焦虑。这是中国观众在接受《生路》时所未能明察的。
四、结语
流浪儿童作为一支极具不确定性的队伍,所造成的社会困扰是多层面的。它不但从属于教育问题,同时也挑战着社会主体的培养。蔡楚生的电影揭示出家庭单位瓦解后流浪儿童作为被抛弃的“主人公”的尴尬境地,以及他们可能面对的灰色未来。这种社会断层既意味着秩序的破坏,也意味着政治自觉的丧失,个体缺少与国家对话的媒介,也就无法从中生成现代公民。蔡楚生所能设计的挽救方案,乃是从道德层面重构了一个由高尚的穷人组成的临时家庭。而《生路》及整个苏联的消灭流浪儿运动则提供了相反的例子。通过集体化的收容制度,儿童不是作为家庭的继承人而是作为社会生产的参与者而加入到社会当中,作为“进行分工的、生产标准产品的大生产中具有熟练技术的现代工人”[19]463的储备军,他们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两部电影中对家庭叙事的不同处理手法。对于蔡楚生而言,家庭的位置是暧昧的,一方面它过去有效地发挥着吸纳和教育儿童的作用,这使得他仍然对家庭与相应的道德观念抱有相当的期待;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模式在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已丧失必要的社会功能,非社会改革不能恢复。而对于《生路》导演尼古拉·艾克所处的环境来说,家庭叙事则与五年建设时期的集体叙事、宏大话语相互抵牾,尽管他将家庭小心翼翼地处理为社会状况的投射,仍然无法摆脱对影片小资2产阶级情调的指责。应该说,重要的不是两部影片之间的情节异同,而是家庭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媒介以及其功能是如何丧失、如何被想象和被置换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羔羊》和《生路》两部电影放在一起比较,有助于探索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应对策略与社会心理。
参考文献:
[1]司徒慧敏.往事不已 后有来者——散记“左联”旗帜下进步电影的飞跃[M]//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凝冰.一月来之苏俄(二月份)[J].苏俄评论,1933(04).
[3]蒋君超,王乾白,等.中国电影从业员的《生路》观后感[M]//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
[4]胡风.《表》与儿童文学[M]//文艺笔谈.上海:文学出版社,1936.
[5]蔡楚生.《迷途的羔羊》杂谈[J].联华画报,1936年(08).
[6]雷欧.儿童年对《迷途的羔羊》评话[J].新天津画报,1936(161).
[7]张杰.看了《迷途的羔羊》以后[J].新少年,1936(06).
[8]王达夫.关于《迷途的羔羊》[J].现世界,1936(01).
[9]江之.迷途的羔羊[J].新人周刊,1936(02).
[10]蔡楚生.会客室中[J].电影戏剧月刊,1936(03).
[11]影坛同人.迷途的羔羊[M]//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
[12]袁庆丰.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制片生态与电影形态解读——兼析《迷途的羔羊》(1936)[J].电影评介,2017(21).
[13]尘无.《迷途的羔羊》试评[J].大晚报·每周影坛,1936-8-16.
[14]蔡楚生.故事说明书[J].联华画报,1936(01).
[15]夏衍.夏衍电影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1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17]吴政达.中国的流浪儿童[J].教育研究,1933(03).
[18]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9]马卡连柯.马卡连柯全集(第七卷)[M].陈世杰,邓步银,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20]H.列别捷夫.有声电影的诞生[M]//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电影艺术问题论文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
作者简介:韩若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