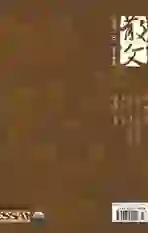不语似无愁
2020-09-23王晓莉
王晓莉
清水明月的优美
中年以后,似乎隔些日子不听到一则熟人或是耳熟的名人死讯已不太可能。前阵子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御用女演员树木希林老太太走了,我顾自难过了一回。老太太演技好不用说,做人保持个性、酷冷到底却是难得可爱。老太太患乳癌近二十年,最后全身扩散,拍个长时间的镜头都要歇息很久。不仅视其如母的是枝裕和,即连观众如我,也是有些心疼她。这两天又传来阿涅斯·瓦尔达的死讯。阿涅斯去世我倒不是太难过,九十高龄不说,关键一直没病没灾,生机勃勃的,八十九岁时还拍了那么好玩好看的《脸庞·村庄》。奥斯卡评委也很凑趣,新近刚给这位新浪潮电影“老祖母”颁了终身成就奖。一生也算活得春风骀荡,尽兴尽情。
纪念这些挚爱艺术家离开尘世踏入仙界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观赏他们的作品。阿摩司·奥兹去世时我拿出了那本厚如砖头的《爱与黑暗的故事》,此前这本书一直是当收藏品一样摆放在书架。太厚了,厚得可以当打人工具。这回还未读毕已是惊艳。惊艳得简直要感谢老先生去世——他要不去世,我真没有勇气去读那么厚的书。电影人去世就“好”多了,一部代表作耗时也不过两三小时。当然,自杀的胡波是个例外,他的《大象席地而坐》整整四小时——我怀疑他如果把电影拍短一点也许就不会这么年轻即决定去死。四小时的电影里,他可能把想跟世界说的话都说完了,想想此后无话,只好跟世界说再见。我在视频里看“金马奖”颁奖会,李安把最佳影片奖座交给胡波的母亲,并搂住那可怜母亲的双肩,不禁也随之落泪:一个可以表达的抑郁症患者,相比那些至死沉默的病人,毕竟还是留下可堪回首的记忆,毕竟还是没白来世上一趟。
这都是题外话。这回我纪念瓦尔达老太太,是重温了一遍她七十岁时拍的纪录片《拾穗者》。老太太真是有趣之人,扛了摄像机跑遍法国,从米勒油画《拾穗者》带给她的灵感开始,将“捡拾”这一主题扩大,追寻、探访那些丰收过后捡麦穗的人,随潮汐涨落赶海的人,树下捡苹果、地里掘土豆的人,以及城市垃圾箱旁捡旧冰箱、电视机的人。所有这些拾荒者,都非是出于贫穷,而是出于凡物不能浪费的理念。他们不使用也不购买新东西,因为路上捡到的已经足够用了。消费社会若是一个大胖子,这些拾荒者则是在竭力为社会减肥减负。面对瓦尔达的镜头,他们不卑不亢,令人肃然起敬。镜头最后追踪的一个“拾荒者”,应该是瓦尔达老太太意味深长的安排。这个专门去市场捡拾商家丢弃的蔬菜、面包用以果腹的中年人,如果电影不交代,你会以为他是身无长物的流浪汉,然而其实他是个法国大学助教,白天他去捡拾,夜晚则来到难民营,免费教那些黑人难民法语。
这个衣着朴素,有足够学历,足够文明的人,穿行在清晨五点钟的市场,俯身捡起一块即将过期的面包,和寻常一样往嘴里送,即使镜头对准,他也完全没有想要有所遮掩——他也许还希望被更多的人看到,以此带动更多的人来践行这样的生活。我看着,想,这场景多优美啊,不是鲜衣怒马的美,不是万众瞩目的美,而是清水明月的美。
这就是清贫之美。
不语似无愁
波兰电影《艾迪》,有一个最主要的情节颇能让我想起白隐禅师那个著名的私生子故事。艾迪是个在城市里收废品的普通人,因为爱读书,被卖酒的两兄弟叫去给他们十七岁的妹妹做家庭教师。两兄弟向来霸道凶残,近似黑社会。他们的心理活动是,艾迪长得丑,又穷,不会给漂亮的妹妹带来危险。谁知妹妹早已经与他们的生意伙伴、一个每周送酒来的吉卜赛男人有私情。不久,妹妹有孕,被两兄弟发现。他们暴跳如雷,逼问是谁干的好事。妹妹想要保护情人,随即想起家庭教师,便说:“是艾迪。”两兄弟立即去找艾迪算账,艾迪为了不出卖妹妹,没有作声。他们残忍地阉割了艾迪。不久妹妹生下孩子,两兄弟拎了婴儿筐来找艾迪,限他一周内带着孩子离开此地。艾迪什么也没说,带着孩子,还有自己收废品的搭档、好朋友尤里克,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在这里,艾迪他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平静美好的时光。直到有一天,两兄弟和妹妹开车找了来。原来妹妹思念孩子,又受良心谴责,说出了实情。这一回他们想来要回孩子。艾迪回屋里长久地亲吻摇篮里的孩子后,交还给孩子妈妈。即使是这样不舍得与不公平,艾迪依旧还是什么也没说,倒是尤里克,愤怒地把两兄弟赔偿的钱掷到了地上。
白隐禅师几乎是遭遇了和艾迪一样的事,两人做出的反应也是几乎一样的。只不過白隐禅师在两次事件转折时比艾迪多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成为禅宗非常有名的一句话。白隐禅师两次都是轻轻说道:“就是这样吗?”然后就全部地接受了现实。
艾迪可以说是一个波兰的当代“白隐”。当然,他与白隐也有不同。白隐的日常主要是在乡下修行。艾迪则是个城市收破烂的。艾迪读很多书,在等待废品过磅的间隙他也拿着一本书看。尤里克问他:“你看书有什么用啊?”艾迪回答说:“可以得到安宁。”
尤里克不太懂,但是这不妨碍他们成为生活中最靠谱的朋友和搭档。尤里克捡了一台全新的电视机,他太高兴了,虽然两人住的地方连电都没有,他还是宣布这是“非卖品”。他对艾迪描绘他最想要的生活,就是“有三台电视,一台放卧室,一台放卫生间,一台放厨房。三台电视都有四十二个频道,想看哪个看哪个”。这样的理想,每个人在自己物质匮乏的时期都会有。但是艾迪对这样“美好的理想”完全不动心。在尤里克眼里,艾迪是个搞不懂但又叫他崇拜的怪怪的哥们儿。
比如,艾迪看见一个孩子非常垂涎一种汽车玩具,却又买不起,天天来店里看一眼。艾迪回家打开旧冰箱,冰箱里并没有吃的,他看到书橱上放满了自己收来的旧书,拿个袋子把书装进去,拎到二手书店。尤里克不解地跟着,问他,你不是喜欢这些书吗?艾迪说,有时候为了某些事还是要卖掉的。他把卖书的钱拿去买了汽车玩具,放在孩子家门口。两人偷偷躲在楼道拐角,欣赏孩子回家发现玩具时的狂喜。尤里克说,六十五块买个玩具!你是过圣诞节吗?艾迪回答说:“圣诞节什么时候想过就可以过。”
艾迪和尤里克之间有点像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的关系。他们都是朝夕相处,但其实彼此相差还是挺远的。这“挺远”的一点就在于“内心”。艾迪接受一切现实,穷,被欺凌,被剥夺,但是他不愤怒,他也几乎不设想将来。他长期不回家乡,也是因为多年前他的女人被另一个男人抢走了。两人结合之后却没有孩子,成为憾事与哀伤。现在这个男人看见艾迪带着个孩子如此平静地回来,内心有点惭愧。他们两人在屋子旁边有段交流,男人最后感叹地说:“没有想到我有一个女人,却没有孩子;你有一个孩子,却没有女人。”艾迪回答说:“这就是生活。”艾迪全部的人生观都在这句话里。不须选择,生活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不须愤怒,承担“现在”就是真正的生活。不选择,就是选择,甚至比选择更有力量。
白隐禅师说:“就是这样吗?”而艾迪则说:“这就是生活。”两人的话实出一辙,都是深具禅意。过去不忆,未来不想,当下不执着———这是禅宗的态度。白隐是日本十八世纪著名僧人,他有一句好诗,“不语似无愁”,用于形容平静如水的艾迪,也是非常贴切。
白菊花还是不肯低头
夜里没睡着,把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又拿出来看几段。这部1953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的电影,很多年前第一次遇到时,只几分钟就知道这是此后必定会时常重温的那类。电影里的黑白影像,三味线特有的那种随时要断的弦音,田中绢代的形体语言,以及沟口无与伦比的镜头,这一切通过某种化学反应,聚合成一种能把人紧紧拽住,叫人浮不得、躁不得的力量。那力量是往下拽扯的,直拉着人往人心里去,往海心里去,往地心里去。叫人想要一探生存更深处的究竟。
故事我已经很熟悉了:阿春年轻时是宫内侍女,冒犯规矩与武士相爱,武士被杀,阿春也贬回家中。恰逢领主遣人来她家乡一带选妾,阿春因美貌懂规矩而获选。她给领主生下一个男孩,这成了她再度被遣送回家的原因,因其已帮助领主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阿春回家,世故而贪财的父亲厌憎她,迫她去了妓馆。阿春性傲,开罪客人,老板根本不能容留这样的女人。幸好遇到卖扇子的忠厚男人有意于她,阿春遂与他结为夫妇。谁知男人出门做生意竟被强盗劫掠杀死,成为寡妇的阿春走投无路,去一个富人家帮这家太太梳头,却遭太太嫉妒而再次被扫地出门。阿春想要皈依佛门,却被女尼误会。寺院待不下去,阿春不得已靠弹三味线乞讨。有一天,在远远看见自己的儿子一眼之后,又激动又冷又饿,她昏倒在地。几个年老色弛的卖春女救了她,阿春也因此入了这一行,在不断的遮羞之中出卖肉体维持生活。此时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成为领主的他不允许有个卖淫母亲,阿春被允远远看一眼儿子以做个母子间的了结,再次肝肠寸断。
影片最后,老迈的阿春看破世事,成了托钵尼沿路化缘。敲开门的人家,给食物也好,不给也好,高看她也好,低看也好,阿春都是无悲无喜,波澜不惊。寺庙塔尖在不远处高耸,阿春合十作礼,继续往前。
这真是个彻头彻尾、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从一开始,田中绢代饰演的女人阿春的生活就可以说是没有最衰,只有更衰。每一步背后似乎都有一个魔鬼在跟随作弄,想要整死她。然而这个电影的伟大之处也在于,阿春总不肯死,或者说,连头也不肯低。为了活着,她拼尽了全力。就像晚秋的白色菊花,尽管天寒的消息早已渗透每一角落,还有秋风一刻不停地吹刮,白菊花还是不肯低头,还是要开。
今晚重温的一个情节是,阿春做了卖春妇,年老色衰,无人问津。她倚在砖墙暗影处,以头巾遮面。一个老者过来要领她去。她带了一线希望,几乎是喜悦地跟着。进了屋,老者招呼四五个年轻男子来围观阿春,并“教导”他们说,你们想知道人生苦短,看看这个老妖婆就知道了。原来他是用阿春来警示这些男子的。阿春本还是头巾一直遮着脸,此时她接过钱,几乎是坦然地面对了那几个男子。她去玄关处穿鞋。想想,又带着轻微的讽笑回到几个男子前,出乎意料地,她冲着他们,竟然做了一个鬼脸。一个看似与她的年龄、她悲酸的经历都不够相称的鬼脸。然而,我觉得这个鬼脸又是最恰当,甚至最精彩的。乞求他人哀怜是不可能的,即连同样生活辛酸的人也当她是一个笑话;乞求命运的转机或垂怜也是不可能的,她哪样苦痛没有经历过?那么,就对命运做一个鬼脸吧。即使天要亡我,我偏要叫自己不亡。
復习完这个情节犹觉不满,又去搜索电影的相关资料。竟真有有心人上传了年老的田中绢代接受采访的珍贵视频。这位年轻时脸容犹如花开一般饱满的演员,此时脸颊已松弛,眼睛还是熠熠有神。她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作为一个演员,我当然是向往荣誉的。但是我更愿意做的事,是帮助沟口导演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彼时沟口已因白血病去世——有些至关重要的话,原来是这样,是要在人已离去之后才说得出口。但是,说与不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沟口早已助力田中成为最伟大的女演员。她则帮他成为最伟大的导演。英雄相惜,莫过于此。完美合作、彼此成就,此亦是典范。绝不是谁提点谁,谁仰赖谁那种,而是交相辉映,不可或缺。与此类似的还有小津安二郎和原节子,成濑巳喜男和高峰秀子。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电影搭档,影史的一代传奇。那是多么辉煌的年代、多么明亮的星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