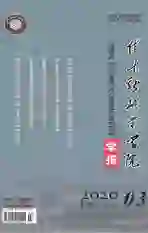信天游歌舞剧《想你哩》简析
2020-09-10高一丹
高一丹
摘 要:《想你哩》是陕北信天游歌舞剧《山丹丹》选曲,由词作家韩继新、曲作家张千一、姜哲新编配伴奏的一首抒情女高音独唱曲目。本曲选自第四幕“想亲亲”,以石柱哥和山丹这对年轻恋人间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本文以演唱该作品的体会为基础,从音乐本体和美学角度两方面,简要分析该曲所展现的美学精神,力求更好地演唱该作品。
关键词:《想你哩》;歌舞剧;美学;演唱体会
中图分类号:J6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3-0111-02
一、《想你哩》创作背景
信天游是流传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汉族民歌形式。这是一部用老镢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这是黄坡黄水之间的一朵奇葩。其歌词是以七字格二二三式为基本句格式的上下句变文体,以浪漫主义的比兴手法见长。在陕北它叫“信天游”,又称“顺天游”“小曲子”,在山西被称为“山曲”,在内蒙古则被叫作“爬山调”[1]。
歌舞剧(opera)是将音乐(声乐与器乐)、戏剧(剧本与表演)、文学(诗歌)、舞蹈(民间舞与芭蕾)、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通常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组成(有时也用说白和朗诵)。《山丹丹》正是将歌、舞、剧三者紧密结合的一部荡气回肠的黄河恋歌,将陕北信天游推向一个更具感染力的艺术舞台[2]。
《想你哩》选自陕北信天游歌舞剧《山丹丹》第四幕“想亲亲”,以石柱哥和山丹这对年轻恋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在小两口被迫分离之后,石柱哥生死未卜的背景下,以“想”为主旨,生动地展示出陕北地区女性性格淳朴、对美好爱情大胆追寻、至死不渝的人格魅力,体现出陕北地区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影响下自由、勇敢、胆大的性格。作品展现了陕北人民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质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诠释了‘爱情和黄土文化与天地共存,人性与民族精神与日月同辉’这一深刻主题。全曲约长5分钟,旋律优美,多为四、五度的大跳音程,体现出陕北地区歌曲豪迈热情的特征,歌词简洁朴素、情感真挚,全曲由F大调转到G大调再转到A大调,每一次转调情绪更加激动,速度在热情而饱满的中强结束。在创作过程中,《想你哩》借鉴西方创作技法,使作品音樂丰富多样化,既保留民族特点意蕴,又具有现代作曲气息。
二、《想你哩》美学情感
(一)“真”的体现
真,体现在歌者生动、真实的演唱中。演唱者在演唱时通过音色的变化将歌者内心的情感真实表达。比如在演唱第一段“口唇皮皮想你哩,不由人就说出你哩”时,首先将陕北地区高亢的音调用纯四度的音乐完美体现,口语化的歌词以及哭腔的巧妙运用,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情感更加饱满,将女主人公山丹心中焦急万分的惆怅和溢于言表的思念跃然纸上;在演唱“红头绳绳”、“眼睛仁仁”时结合了陕北地区善用叠字的语言特点,来表现山丹对石柱的想念与期盼,感情害羞而又真实;又比如作品的后半部分中,以级进的方式连续重复地演唱,情感一次比一次激动,情绪一次比一次热烈,生动而真实地将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思念之情真切地表达出来。这种真实不做作的感情,不正是每一个在热恋中的人所表达的情感吗?
(二)“善”的体现
善,首先体现在主人公善良、直率的个性[3]。词、曲作者打破传统的艺术思维,将农村普通女性推向了艺术舞台,将山丹这样一位单纯、积极向善的人物形象描写得活灵活现。如那句“想你,想你,想你哩,实想你哩,想你,心花乱哩。”在最简洁质朴的语言中,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她对石柱哥的思念之情。这样质朴的人物刻画,展示了人性中的大爱大恨,为爱情“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回头”的执着追求。再者,速度、音调、情绪的递进变化,使听众对人物情感的认知更加感同身受。而旋律中每一次级进,伴随着音调越来越高、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形成了速度与情绪之间的强烈对比,将山丹的情感与命运一层层地展现在众人面前,也让观众追随着山丹对石柱哥的思念之情。而山丹历尽艰辛、坚强不屈、大胆示爱的精神,也正是陕北地区的文化中所蕴藏的向善的精神,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展望。
(三)“美”的体现
美,体现在演员在舞台的表演中,从舞台布置、服装道具及灯光设计上都渗透着浓浓的陕北韵味以及创作者对舞美的最高追求。服装上以朴素为主,凸显陕北劳动人民传统服饰之美,体现出陕北地区人民朴实无华的自然美;灯光上由最先开始的蓝色,到山丹一人在舞台时,灯光转红,而山丹代表着美好希望的红灯笼,红蓝两种灯光的变化对比,塑造了山丹饱满而丰富的人物形象,当观众随着人物的演唱进入山丹的情感之中,更加真实地感受山丹的内心活动,从人文上追求一种自然的美感,使舞台效果更加生动具体。这种舞台效果向观众传达了饱满的情绪感、故事感,是一种情景美,一种意境美,也向观众展现了一幅唯美的画面。
三、《想你哩》演唱分析
(一)练声练习
“yuo”练习:在演唱歌曲前,先将整首歌曲用yuo的一条练习来进行练声:5-4-3-2-1
练声要求:
1.位置
即歌唱部位,众所周知声带发声的地方叫声门,而人类也只能通过声带发声。在练声过程中找到发声的位置必然是重中之重,要搁贴得当,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演唱部位。每个人音色不同、生理器官不同,搁贴位置自然因人而异。喉部在发声时要找准声音的支点后,不要轻易挪动位置,演唱时保持在固定位置,搁到声门处歌唱,找准声带的支点,在演唱时不随意提喉或者做其他多余动作,保持‘点’稳定不变,这个点是集中的‘点’、适合自己的‘点’,那么发声结果必然是自然的、优美的。歌唱空间因人而异,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并在整条练习中贯穿使用,必定有好听的音响效果与优美的声音。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正所谓有了歌唱空间,声音才能流畅,才有好听的混声效果。
2.角度
在做练声练习时,起音的动作为:用口鼻同时吸气,吸气声音、动作要小,吸气之后声带挡住气息,依附在挡气点上直接唱,整条练习力度虽小但一定要准确无误,然后气息绵延不断地支持,不断补充气息,气息的方向像水流一样是流动的、有计划的,演唱乐句始终保持声音在气息上歌唱,然后循环往复。歌者的身体从开始到结束始终保持相对的松弛感,面部表情放松不松懈,歌唱腔体宽松不松散,而气息的方向一直绵延向下、不断流动。在气息流动时发声部位搁住、胸去贴一下,使得头腔、胸腔以及腹腔在一条线上,感觉有一种“投掷”感,气息胸前贴上在起音过后气息向下,保持喉部稳定,与此同时注意头腔的共鸣(只有气息向下,发声位置保持时,声音的位置才感觉在头顶)[4]。
(二)歌曲演唱
在将整首歌曲进行系统的练声练习之后,在头腔、胸腔、腹腔都保持的状态下加入唱词。首先是润腔的使用,演唱者依据旋律中的音高与唱词加以润色和美化的一种表演形式,是一种既有表情性又有技术性的技法。通过加入滑音、颤音、加花等装饰音加以润色,使得乐句更加完整,刻画的人物性格更加形象,人物感情表达得更加完善,创造出声音独特的美感来表达歌曲本身的韵味,符合歌曲的味道与审美习惯。再者是歌词的演唱,中国歌曲的吐字要求字正腔圆,人在自然说话时的吐字要求为字头、字腹和字尾的准确性,演唱歌词与其在原理上大体是相通的。咬字指的是字头,即声母,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音,即:唇、齿、舌、牙、喉,其要求一般为短、轻、准;吐字指的是字腹与字尾,即韵母,字腹的要求要长时值;字尾应收住尾音,才算唱完整个字。在唱字头时应用唇部用力,上下嘴唇喷口应有力而清晰;字腹是字的主体部分,其歌唱响度最大;字尾在收音时要收的自然、分明。在发音时要充分运用‘咬’字的技巧来增强歌曲的感染力。在将声音都放入歌唱的通道后,进行咬字吐字。比如歌曲中出现最多的字:“想”,在唱时应该嘴皮用力咬住Xi,然后归韵到a-n-g;“唇”字相同:先咬住chi,归韵到w-u-n。第三,演唱时的情绪处理,全曲一开始在F大调上,这时候的对石柱哥的思念之情是内在的、含蓄的想念;在两段唱完后调性转为G大调,情绪转变为激动与兴奋;全曲的“想你”一直将整首曲目推向了高潮,在曲目结束部分又从G大调转到A大调,情绪比前两次更加猛烈,其对石柱哥的思念更加强烈,情感更加激昂。而在结束部分,由于都是山丹内心的情感活动,还没有等到她的石柱哥,在慢慢冷静之后表达出了内心的酸楚与无奈:石柱哥怎么还不回来。在整首歌曲的演唱中更能体现人物层层递进的思念之情,和中国女性大胆追求幸福的执着之情。
四、结语
陕北信天游是我国艺术领域中的瑰宝,它将陕北人民的喜怒哀乐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陕北地区作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其音乐艺术更是多姿多彩。本文选取的《想你哩》是陕北信天游歌舞音乐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这首音乐用平凡的故事内容、细腻的艺术表现、以及精巧的作曲编排,展现了陕北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朴实无华的黄土精神。词作家韩继新、曲作家张千一、以及编曲者姜哲新大胆运用创新的艺术创作手法及超高的艺术水准,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创造性地将传统作曲技术与现代作曲技术融合至《想你哩》中,使得陕北民歌中原有民歌的特色得到强化、作品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人物的文化意蕴得到表达。而整幕歌舞劇《山丹丹》将歌、舞、剧三者相结合的表演形式,更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和听觉的享受,使作品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更深层的提高,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美学层面上真善美的感受。在演唱作品前,应该做好对整首歌甚至整幕剧的案头工作,设立规定情境、确立人物形态、掌握表演尺度,使表演与演唱完美结合,做到收放自如、恰到好处。而歌者通过对歌曲的细致分析,不仅感受到陕北地区的文化内涵,也能体会作品美学意义上的真善美,对以后歌曲的演唱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志山.真善美的哲学与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秦国庆.陕北民歌的艺术特征浅析[J].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6):130+76.
[3]董雅男.对陕北信天游歌词、唱腔及艺术特征研究综述[J].北方音乐,2017(4):38-39.
[4]刘军.陕北民歌信天游的艺术形态分析[J].黄河之声,2015(8):35-36.
(责任编辑:李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