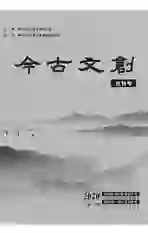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之一:儒家的理想人格
2020-09-10邱紫华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协同发展,各民族文化共同融合形成。这种文化有显著的多元化色彩,文化人格中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而其中,中国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圣贤人格”,求“仁”,讲“礼”,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为了塑造“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济世”抱负的伟大人格。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
关键词: 儒家理想人格;“圣贤人格”;“三不朽”
中图分类号: B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1-0004-07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协同发展、各民族文化共同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它非常丰富而复杂,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需要具体分析后继承、运用,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潮流,在几百年间,诸子百家都表达了各自的社会主张以及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
多元的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代中华民族多民族的共同的文化。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道家和佛教文化为主干;这三者各有特点,既相互竞争,又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应当说,儒家、道家、佛教禅家的思想特征和人格理想是鲜明的。但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精神,却主要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型人格精神。我们经常讲的“外儒内道”或“内儒外道”就是中国文人的复合型人格的表现。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表现为儒、释、道各家对他影响的深浅或侧重的不同。
一、儒家的理想人格
什么叫做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的部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和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的人格精神;人格则决定了一个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有它所追求的理想的人格精神。
中国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信奉“济世哲学”的思想流派。以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人为代表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圣贤人格”。什么是“圣贤人格”呢?“圣贤人格”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就是胸怀“三不朽”的济世之志。
第二,有着深厚的“仁爱”精神和善于进行道德自我修养的人。
第三,拥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超人智慧和能力。
拥有以上三种内涵的人就是儒家所憧憬的、所赞美的圣王、圣人、圣贤。
二、圣贤人格所追求的“三不朽”人生理想
何谓“三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鲁国大夫叔孫豹表述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所谓“立德”,根据唐代孔颖达在《孔颖达疏·五经正义·左传》中的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
“立德”就是为民族、人民创立美好的社会体制,如尧、舜、禹时代;或为民众创立了某方面的知识体系或确立了某些法规、法则,如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周公演绎《易》;或为本民族确立了崇高人格的道德标杆和行为范式,如确立礼仪原则。
历代以来,中国人就以黄帝、尧、舜、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为楷模。近代以来,人们则以孔子、王阳明、曾国藩为楷模。
“立功”,孔颖达解释为:“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其意思有两层:
第一是为民族、为国家创立了千古不灭的功勋的伟大人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把大禹、李冰、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朱元璋、努尔哈赤、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看作是历史上的功勋人物。
第二是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像屈原、岳飞、文天祥、林则徐,以及20世纪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艰苦拼搏的民族英雄等。
“立言”,孔颖达解释为:“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就是通过著书立说来阐明伟大的思想和重大的发明;这些思想和重大发明足以流传后世,影响后代的思想行为。例如,周公演《易》,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孟子、管仲、晏婴、杨朱、墨子、孙武、吴起、屈原、宋玉、贾逵、杨雄、司马迁、班固、祖冲之、僧一行、司马光、苏东坡等。他们的著述积累成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思想精华。再例如,直到20世纪,鲁迅仍然高度赞美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三、儒家追求的“内圣”人格精神
在生活实践中,儒家的“圣贤人格”精神表现为“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一词出自《庄子·天下》,后来却成为儒家理想人格所需要的实践精神。儒家一贯强调思想修养和行为实践紧密结合,重视“学以致用”。明代著明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将其总结为“知行合一”。
“内圣”指个人的思想与德性修养。它包括这些内容:
第一,有高远的人生理想。
儒家追求“三不朽”、“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民请命”的人格精神。在人生实践中应当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皆济天下”。一句话,就是一个人要胸怀大志,有理想、有抱负,反对沉溺于声色犬马的个人享乐,鄙视庸庸碌碌而无所作为的苟且的生活方式。
第二,有深厚的道德修养。
孔子在《周礼·儒行》中论述了儒家的人格修养。
鲁哀公问孔子:“先生的服装,是儒者的服装吧?”
孔子回答说:“我少年时期住在鲁国,穿袖子宽大的衣服。长大后住在宋国,因为宋国是殷人的后裔,所以,我戴的是殷人的帽子。我听说,君子的学问要广博,而衣着要入乡随俗。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儒服。”
孔子的意思是,儒者并不在于服装、外表,而是在于精神思想,学问修养。
孔子系统地向鲁哀公讲述了儒者的气质风貌。
首先,儒者博学,能够陈述历史上各种人物的善良之道;他们努力学习,随时能够回答别人的咨询;儒者总是心怀忠信之心,等待别人的推荐而发挥自己的才能。
其次,儒者穿着衣服要符合“礼”的规定,行为举止谨慎、恭敬、谦让。
再次,儒者“不以金玉为宝”,而以忠信为宝;不追求积聚土地和财物,而以道义为立足的根本,把才艺和学问看成自己最富有的东西。
最后,儒者不遇到政治清明的时候就隐居不出;对于那种不遵守道义的人就不同他合作;儒者要先建功劳而后才接受俸禄(先劳而后禄);儒者不能见利忘义;儒者不能屈从邪恶和暴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儒者敢于担当责任;儒者生活节俭,不追求奢侈享受……这些都是孔子阐述的儒者做人的原则。孔子论述的这些做人的原则,被后世的儒家总结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五常”被后来的儒家看作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此为伦理原则,用以处理社会和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儒者以“仁爱”为精神核心。
儒家的哲学和伦理学出于维护古代宗法制社会秩序的需要。孔子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多达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
什么是“仁”?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孟子说:“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
孔子讲的“仁”,一方面是指“人的内心中的仁爱”情愫;另一方面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儒家“仁”思想的要点在于“爱人”。过去,统治者把人民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主张。孔子是古代第一个把劳动民众看成是“人”的思想家。他提倡养民、利民、富民、教民、安民、博施于民。这是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
孔子提出:“唯人者能好人,能恶人。”这就是说,爱“仁”的是仁,能憎恨恶的、“不仁”之人也是仁。真正的仁者,就是既能“好仁者”,又能“恶不仁者”(《论语·里仁》)。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与“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忠恕”思想。
“忠恕”就是在人与人相处关系上所体现出来的“仁”。所谓“忠”,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说,个人自己想要立住脚,同时也要让别人立得住脚;自己要事事行得通,也要让别人事事行得通。
所谓“恕”,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所不愿意干的事,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去。可见,“忠恕”就是宣扬“宽恕”“宽容”“容人”的处事态度。这就是孔子提倡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品德(《公冶长》)。
这里的“直”就是“值”,指适量代价、相当的对等的代价。“以直报怨”就是坦诚地面对怨恨,正直、公平地对待怨恨。孔子认为,对于怨恨,要用正直的心去对待。因为,“正直”是不受外界影响。正直的原动力是真诚。
至于“以德报德”,就是说,对于别人的恩惠、恩德,需要抱有感激的心,用自己的恩德来回报他人。
可见,孔子所谓的“忠恕”就是做人要有诚恳为人之心,不要有丝毫损害别人之意。
孔子的“仁爱”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为“博爱”、“泛爱”。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拥有“仁爱”“忠恕”品德的人。
儒家在道德理想上,以塑造“仁、义、礼、智、信”的人格为目标。这里,特别谈一下儒家的仁爱精神中的“仁”“义”“礼”“智”“信”。
仁:指尊崇人性,以人为本,富于爱心和同情心。
义:指坚持正义,保持节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不为金钱、物质的诱惑丧失人格、原则和道义。
礼:指尊重他人,具有公民意识;注重等级礼仪和文明礼仪。
智:指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能力、思想水平。不断丰富自己的智慧和工作应对能力,以较高的思想水平和专业技能服务社会。
信:指诚信、守法、踏实、可靠。对人处事要有信用,一诺千金。
第四,儒者應当崇尚“礼”。
什么是“礼”呢?“礼”的观念起源很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形成。自夏、商、周以来,“礼”就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和这个制度所需要的道德规范。
“礼”就是区分“上下尊卑”的血缘关系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儒家尊崇“礼”的基本内容就是尊崇“德”与“孝”。
儒家的“德”就是“君令臣共”“君令不违”;“孝”就是“父慈子孝”;“德”与“孝”两者加在一起就是儒家所谓的“礼”。所以,儒家的“礼”就是尊崇血缘伦理关系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
对于儒家来说,“礼”不再是商、周时代的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强权。例如,商、周时期的“礼”强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统治者享有特权。举行“礼”的仪式时往往豪华奢糜。一句话,商、周之“礼”是奴隶主阶级享有特权的“礼”,而不是儒家主张的“个人道德修养”之“礼”。儒家崇尚的“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之上的,是维护和谐的社会等级秩序、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可见,商、周时代的“礼”与儒家崇尚之“礼”,其内容实质已有很大的差别。
儒家认为,遵循“礼”就是善;违犯了,就是“非礼”、就是恶。一个人要遵循“礼”就需要“克己”——时时约束自己、节制自己,要“每日三省吾身”。孔子主张约束、节制和“每日三省吾身”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即推崇个人的“反思”。黑格尔论“反思”:“反思”是思维主体对自身思维的思维。人人都能思维,但不是人人都能够反思。反思是智慧。
“克己”就是时时约束自己,就是节制自己。它要求做事、做人不过分;不偏激、不逾矩;这就是孔子提倡的“去其两端,执其中也”的“中庸”之道。一个人做事做人能够做到“中庸”,能够做到处人处事“不偏不倚”,就达到了“至德”的境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儒家推崇的“仁”和“礼”是什么关系呢?
“仁”和“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仁”(仁爱、德、孝)是“礼”的内容;“礼”是“仁”(仁爱)的表现形式。内容形式应当统一。一个人关心子女或父母的健康,却采取了粗暴的呵斥,这就是有“仁”而无“礼”。人们所谓的“刀子口豆腐心”就是有“仁”而无“礼”。
但是,当“仁爱”与“礼仪”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儒家则把“仁爱”放在了第一位。例如古代著名的君子柳下惠。柳下惠原名叫展获,字子禽(一字季),谥号惠。曾是鲁国主管刑狱的官员,后人尊其德行而称其为“柳下惠”。他的出生地是周朝诸侯国鲁国“柳下邑”。柳下惠比孔子早生一百多年,柳下惠曾在寒冷的雨夜,让一个陌生女子坐在自己怀中取暖,直至天明而“坐怀不乱”。
四、儒家“圣贤人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
“外王”指政治、社会的实践能力,即工作能力、统治驾驭能力和权术智慧,即“霸权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说,一个人有能力治理好一个大家庭、大家族,就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国家);如果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康富足,就能够平服天下之人心,使天下安定祥和!
生活安定、富足、祥和这就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大智慧。历史上,有的人可以打天下,却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儒家培养的就是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才和智者。
“外王”包括这些内容:
第一,要有博大的心胸和容纳精神。
这样才能做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融合和协调各种关系,采纳各种智慧;才能够做到多角度的思考、多层次地对待。
第二,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
作为统治者需要超常的、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这是“外王之道”的重要的内容。统治者决定着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统治者需要拥有超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来看待形势的发展和走向。
第三,要有坚定的意志力和决断力。
儒家推崇的“外王”之道,就是统治者的驾驭能力、统治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力。敢做敢为,敢于承担责任和后果,应该“山崩于前不变色,海啸于后不失声”。
五、儒家尽力打造“圣贤人格”的目的
儒家打造“圣贤人格”的目的是为了“济世安民”,创建和谐的美好社会。
儒家追求的“圣贤人格”精神,充分地说明了儒家原本就拥有的“积极入世之心”和“济世之志”。儒家的本性就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力欲。
姜尚(子牙)曾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姜尚:《六韬·武韬·顺启第十六》)
《吕氏春秋·贵公》中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这个意思是说,天下不是一人、一家的天下,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占有这个天下。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之志不可夺也!”(《论语·子罕》)
《礼记·儒行》说:“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陆游诗《病起书怀》:“位卑未敢忘忧国。”
《春杂兴》之一:“夜夜燃薪暖絮衾,禺中一饭直千金。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始》)
青年毛泽东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世界者,我们的世界。”
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精神的担当性、责任感、使命感。
儒家的济世之志及其责任感、使命感成为千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精神品格。
唐代大诗人杜甫“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抒发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儒家社会理想!
宋代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
明朝末年,中国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思想团體“东林党”。因其设在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而形成了一个儒家的思想潮流。“东林书院”的门楣上有一幅明代思想家顾宪成书写的对联,足以说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之志: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再如,20世纪初为民族解放,为振兴中华而牺牲的爱国女英雄秋瑾的事迹,就展现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人格。
秋瑾常感叹:“人生处世,应当匡救时局的艰危,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怎么能为柴米油盐等家庭琐事了此一生呢?”
她曾写下《感时》之一:
忍把光阴付逝波,这般身世奈愁何?
楚囚相对无聊极,樽酒悲歌泪涕多。
祖国河山频入梦,中原壮士孰挥戈?
雄心壮志销难尽,惹得旁人笑热魔。
她在发动反满的武装起义前,曾写下感天动地的一首《绝命词》,留给她的闺蜜徐小淑: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日暮穷途,徒洒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拜仑)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
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渝,
中原回首肠堪断!
20世纪初“五四”的爱国运动中,中国学生和平民百姓也表达出儒家济世的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性!
20世纪30年代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歌词也证明了这一点:(田汉词 聂耳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上面这些事例说明,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为了塑造“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济世”抱负的伟大人格。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圣贤人格”就是:拥有“三不朽”的济世之志;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与能力;有着深厚的“仁爱”精神和信奉“礼”的具有道德修养的人。
如果这三者都具备,就是儒家赞赏的“完美人格”。儒家倡导的“圣贤人格”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儒家憧憬的这种理想的人格精神,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做到了。
六、对儒家精神的反思和再评价
儒家学说是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脊梁。但是,儒家的思想精神在当下的社会中的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是否采取不加批判的全盘继承和发扬呢?
正确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就是其精华;而儒家尊崇的血缘伦理和等级秩序等思想观念,其很大部分则是糟粕。
由于儒家的“礼”的核心就是主张“仁爱”“德”与“孝”等伦理秩序。后来的汉儒董仲舒以及后代儒者就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和“孝悌”等血缘伦理秩序。还有“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种血缘伦理制度和社会等级秩序神圣不可侵犯,这给历代的统治阶级提供了可利用之处。这就是历代统治者都尊“孔”、崇“礼”的原因。例如,清代统治者把孔子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
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孔子、孔教,其实是被历代统治者精心装扮后的“孔子的偶像”;它同历史上真正的孔子及其思想有很大的差异。
应当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社会的血缘等级制度的本质,是“向后看”,是“尊崇过去”,是以先人为“神圣真理”的理念。这个“向后看”、“向过去的真理看齐”的制度,必然要求人们遵循先人之足迹,以先人为圣贤,以先人为智慧的顶峰,让后人加以学习和模仿。这就容易导致中国人思维的守旧和反对创新。几千年下来,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思想停滞不前。
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在中国人的一些思维方法中,有着一种……偏重依恋过去事实的思维倾向。①
“中国自古以来就已确定那些制定生活规范的典籍,它们称之为‘五经’:《易》《书》《诗》《礼》《春秋》。②
“‘五经’被确立为中国人生活的规范。它提供了先例中的先例,因而最终‘五经’本身被看作真理,被认为十全十美。所以不管人间生活发生多大变化,人生的一切道理都在这‘五经’中寻求……这表明‘五经’体现的真理的永久性。虽然中國王朝更替频繁,但每个王朝都把‘五经’尊为最高权威,把它们看作人间生活的规范……视‘经’为人生的规范的态度,在周朝时就已相当普遍。”③
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于“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概念给予了准确、深刻的区分。他指出:在古代早期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模仿的方式”。“在这两种社会里,模仿的方向却不同。”在古代社会里,“模仿的对象是老一辈,是已经死了的祖宗,虽然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可是他们的势力和特权地位却还是通过活着的长辈而加强了。在这种对过去进行模仿的社会里,传统习惯占着统治地位,社会就静止了。在另一方面,在文明社会里,模仿的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这些人拥有群众,因为他们是先锋。”④汤因比的这一观点对未来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日本]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②[日本]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③[日本]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④[英国]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参考文献:
[1]论语[M].中华书局,2006.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3.
[3]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M].林太,马小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名家简介
邱紫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20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上榜学者。1983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分配至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87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93年提升为教授。1997年起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方美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1997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东方和西方美学史及美学理论研究。
已出版的主要专著有:《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引论》《东方美学史》(上、下卷)、《西方美学史》(第二卷撰稿人之一)、《印度古典美学》《东方美学范畴论》《触摸印度的千手千眼——一个中国美学家的印度文化之旅》《东方艺术哲学》《禅宗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家族相似”》等。从1989年起,曾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多次荣获教育部及省、市级优秀学术著作奖。近年承担了两个“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图书”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