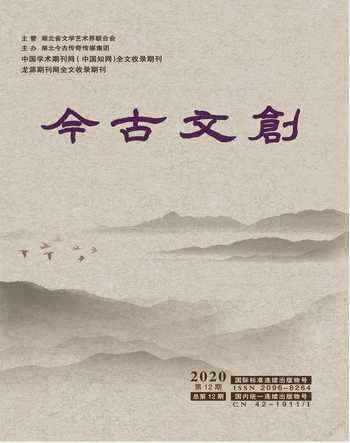苏雪林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
2020-09-10李文静
【摘要】 相比于沈雁冰、冯雪峰和沈从文等具有派别归属的文学评论家,苏雪林始终在以个人的名义进行文学批评。这种身份使她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可以自由发挥,又不可避免地打上极重的个人化色彩。政治倾向的一致和道德的洁净无瑕是她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尺度,这种尺度既揭示了苏雪林被主流文学所排斥的经历,也显示了“人生导师”胡适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 苏雪林;文学批评;价值尺度;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2-0033-02
苏雪林在五四时期以《绿天》《棘心》等代表作成名,作家是她在1920年代的基本身份,其文学批评始于她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期,内容主要是她在讲授新文学研究课程时所备的讲义,分为新诗、散文、小说、戏剧等五部分。这些讲义陆续在当时的《国闻周报》《现代》等刊物上发表,后来整理成《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在台湾出版。
尽管苏雪林一直试图以超越党派的个人身份进行文学批评,但纵观其批评文字和语调,意识形态对其价值判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政治倾向和道德尺度是突出的两点。五四时期的文学有众多的派别之分,如“文学研究会”“新月派”“创造社”“左联”等,这些派别有着各自的政治和功利性的追求。苏雪林是独立于这些派别之外的,但因为与胡适、凌淑华、陈源等人的交好,她的文学和政治立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友人的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时在文坛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一脉,他们对革命文学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已经引领了当时的社会潮流,这引起了苏雪林极大的反感。而另一方面,他的人生导师胡适和同事陈源等人,因和鲁迅的笔战而引来多方讨伐,他们为北洋政府辩护的言论也遭到猛烈抨击,学者形象几乎跌入谷底,而他们所代表的文学流派也面临着被左联掩埋的危险,作为追随者的苏雪林难免感到焦虑。所以在批评“创造社”“左联”的作家时,她的语言往往充斥着尖刻与矛盾,对鲁迅前后期态度的转变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在鲁迅成为左联“盟主”以前,苏雪林对他的小说是非常推崇的,1929年的《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她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而他的成功并不限于这一方面;1934年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中,她用了在文集中占据20多页的篇幅来解析,这在她的批评文章中是不多见的。她称鲁迅的作品“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具有简洁短小的优点”“像鲁迅这类文字,以旧式小说质朴有力的文字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变化,我觉得很和我理想的标准”,对于《呐喊》《彷徨》,她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当时的鲁迅和政党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未作出任何政治上的表率,所以苏雪林对他还是甚为敬重的。其实早在1928年,苏雪林就曾赠过鲁迅一本《绿天》,还题了“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流露出对鲁迅的追随之意。而1936年鲁迅刚去世不久,苏雪林就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两封信,在信中对鲁迅的态度发生惊人转变。她说鲁迅的心理“病态”,人格“矛盾”,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所传之奸恶小人”,“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攻击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她还称“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党羽,群而攻之,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撅而不复振……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鲁迅乃得巍坐文坛,成为盟主”。这一段很好地印证了她对鲁迅把持文学主流场域进而扩散到政治场域的反感,而在给胡适的信中吹捧国民党政府“是二十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万不可轻易说出反对的话”,其政治立场已经明显地发生倾斜。而且可以发现,在政治上反鲁以后,鲁迅的文学成就也被苏雪林一笔抹杀,她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几乎彻底否定了自己曾经给予鲁迅的评价,说“论创作,他不过写了《呐喊》《彷徨》两本短篇小说,只有《呐喊》里的《阿Q正传》,写的还算不错,但已有人指出有套襲日本作家谋篇作品的嫌疑”,“《故事新编》只能算是插科打诨的小丑口吻,谈不上文学价值”,只能“勉强称为小说”,而对于鲁迅为后来人所称道的杂文,苏雪林说“十几个杂感集,没有一篇不骂人,没有一篇不暴露他自己的劣根性,丑嘴脸”,“集绍兴师爷文学之大成”。而对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的贬低,也有力地佐证了政治取向对苏雪林的价值判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雪林衡量作品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尺度就是道德的洁净无瑕。有研究者指出,这种道德要求体现在作家是否具有高尚的人格和作品的内容是否洁净两方面,笔者比较赞同此种说法。苏雪林心中的道德模范首推胡适,这种偏爱更多的来源于胡适的人格魅力对苏的影响。胡适是苏雪林的同乡,老师,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动者,这些都使苏对胡适具有莫名的好感,将其奉为“现代圣人”。在《胡适的〈尝试集〉》一文中,她开篇就赞颂胡适“扭转三千年文学史的局面,推动新时代大轮,在五四后十年的思想界放出万丈光芒,”“将来自能在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上获得极崇高的地位”,仰慕之情满溢,在详尽分析其新诗后,最后又反驳“胡适的新诗是成功者的垫脚石”等观点,指出“胡适的诗不敢说是新诗最高的标准,但在五四后十年内他的诗还没有几个诗人可以比得上” ①,并用了大段排比来论述胡诗的有韵、有组织、有言外之旨,极力维护胡的地位,这些文字不免有拔高胡适、贬低同时代作家的嫌疑,也体现了人格标准对苏作批评时产生的负面影响。苏雪林对于她认为人格高洁的文人如胡适、周作人、陈源等人,不仅列专章详述,在评论其他作家、作品时,也常常见缝插针地把这些人拿来比较,甚至大段论述,并引用他们的观点来增强论据的权威性。在分析徐志摩、穆时英、周作人、几个超越别派的批评家和曾孟朴(东亚病夫)等人时,常常可以看见胡适、陈源的身影,而在涉及散文和“人性论”的章节中,周作人及其观点也会频繁地出现。苏雪林的道德洁癖延伸到作品的纯净、洁白上,就更加流露出她的感性了。苏雪林曾说,“自研究新文艺以来,即抱反鲁的宗旨,其次则反郁” ②。反鲁具有复杂的因素,反郁抛开政治的原因,另一点就是出于对其作品不加节制的“性描写”的反感。作为出生在封建末期、接受过传统教育而成熟于五四时期、又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女性,苏雪林的道德观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她敢于向束缚女性的旧道德宣战,以死争取读书上学的权利,发表崇尚自由的激烈文章;另一方面却恪守“忠、孝、节、义”的纲常伦理,甚至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孤独一生;她曾在法国学习文学和绘画,也充分领略了外国的大胆与开放,但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又使她恪守禁欲主义的教义,这些促成了她矛盾的道德观,对她在批评时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雪林对郁达夫的抨击由作品到人格再到批评者和读者,甚至最后连浪漫主义也一起打击,这种连坐批评法实属罕见,也显示了苏对郁的厌恶程度之深。《在郁达夫及其作品》一章中,她开篇即道“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谩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有夸大狂和领袖欲发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在句中苏还提及了张资平,可见把郁和郭降到了与张同等的地位。尽管之前有周作人“受戒的文学”为郁达夫正名,苏雪林还是用严苛的笔调一一列举郁所呈现的病态性欲和堕落行径,并批评了其艺术上的缺陷。这些都体现了苏雪林道德观保守的一面,然而有趣的是,从她对施蛰存的性描写赞赏性的评价中可以发现,事实不止如此。从苏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認为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把郁达夫的个人主义描写归结为具有普遍性的“时代苦闷”是不妥当的,她真正所反感的,是郁的以一己经验代表整个社会。施蛰存的作品中也不乏大胆甚至变态的性描写,但他所呈现的人物时小众的、不具有可归纳性的,所以苏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类似作品截然不同的反应上,既表现了苏雪林道德观的复杂,更透露出她对于文学话语权的一种内在焦虑。由上可见,苏雪林在评判作品的优劣时,道德的健全和高尚是重要标尺,我们知道有时候“文如其人”并不是十分准确的,但苏雪林往往把作品和作家等而论之,在激动处甚至由分析作品转为人身攻击,这种做法是有失批评家的水准的。更甚的是,正如对“道德模范”的崇拜时时溢于笔端一样,对“有违道德”的作家她也时时记得拿出来讽刺几句。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沈从文都是反面映衬的对象。如在称赞田汉戏剧的“情节安排之妥当与对话之紧凑”时,说“郭沫若、王独清等人之剧根本谈不上情节” ③,而在论述曾孟朴真善美杂志的用意时,指出“郁达夫正在上海大肆推销他的‘卖淫文学’”,“而所谓恋,所谓情,又都是极其下流猥亵,煽动兽欲……没有半点高尚情操存乎其间”,由对作家的厌恶又连坐到了其所在的城市,“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空气本不纯洁,让这群披着新文艺外衣的文人来闹一闹,更变成污浊万分的花柳病菌的世界了” ④可以看出,在道德的尺度上,苏雪林时常被个人情绪蒙蔽双眼,有时早已失去了史家态度和学者风范,不仅大胆假设,不加求证,而且常常忽略客观实际,用不同标准要求类似的作家。这种浓重的个人色彩也使得她的批评略显散漫,有时论述的重点不是很突出,而且随口而出的冷嘲热风也减弱了文章的严谨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文学批评的学术价值。
尽管在意识形态、道德和审美观所持的价值尺度影响了苏雪林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她以史家眼光关照现代文学,梳理出了文学发展的详细脉络,贯通古今中西的批评方法也对后来的文史书写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①苏雪林:《胡适的〈尝试集〉》,《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②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③苏雪林:《田汉的剧作》,《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页。
④苏雪林:《〈真善美〉杂志与曾氏父子的文化事业》,《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页。
作者简介:
李文静,女,汉族,江苏邳州人,硕士研究生,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