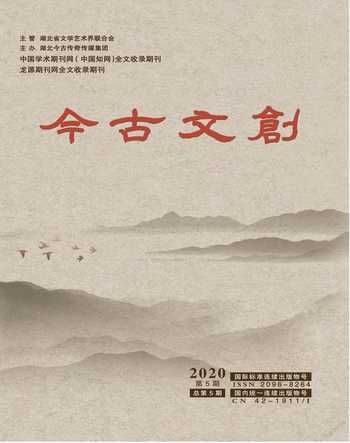从文学的叙事结构看《山河入梦》
2020-09-10赵敏
赵敏
【摘要】 《山河入梦》是作家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以双线并行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谭功达后半生的爱情和政治悲剧故事。小说叙事错综复杂,本文从叙事结构的六大方面叙述主体、叙述角度、叙述角色、叙述态度、时间结构、叙述语言看小说表达的精神意义和审美意义。
【关键词】 乌托邦;叙述主体;全知视角;现实态度;审美态度;时间结构;叙述语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27-03
《山河入梦》双线并举,以谭功达和姚佩佩的暧昧情感为一条主线,以谭功达的政治乌托邦幻想为另一条主线,讲述了谭功达这个怪诞庸凡人物后半生的爱情故事和从政理想,并最终迎来了他爱情消逝、理想破灭的悲剧结局。他向往的桃花源似的社会是永远无法抵达的乌托邦,他全部的政治热情与官场和现实不容。
他的爱情开始得木讷而压抑,不愿承认内心的情感让他在爱情面前始终心思复杂又软弱无力,认清自我情感时为时已晚,姚佩佩因防卫杀人被捕枪决,谭功达因包庇罪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病死狱中。故事体现了强烈的宿命感、人生的无力抗争之感,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加之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使人看罢不禁长吁短叹,产生深沉的思考。
文学叙事错综复杂,故事作为“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承上启下,完成了从传奇到平凡的过渡,小说双线叙事更显复杂。文学叙事涉及叙事要素、叙事结构、抒情方式等几大方面,本文仅从文学的叙事结构看《山河入梦》,并以叙事结构的六大主要方面分析谭功达的天方夜谭和他爱情、理想主义的开始和幻灭。
一、叙述主体、叙述角度和叙述角色
故事叙述主体有两重身份:现实主体和审美主体。现实主体即作家格非,作者根据自己的学识、经历等构思故事,设置背景、人物、情节等,将十七年的心血熔铸于“江南”三部曲中。但是作家本人在故事中没有出面,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读者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进入故事,走进主人公谭功达的世界,清晰感知到谭功达的内心和行为,以上帝视角审视这个从政和生活都软弱怪诞的县长的一生。谭功达是故事最主要的文学形象,审美主体也就是拟作者操纵着文学形象谭功达、姚佩佩、白小娴、白庭禹、钱大钧、汤碧云、小韶等人和普济、花家舍等地方与读者进行交流和对话,读者因此能在文本中感受到谭功达的人生悲剧并在此指引下拥有自己的思考。
显然,故事的审美主体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书中的某一个人物,而是书中人物群像组成的故事本身带来的力量和精神,它是书中那个苦闷压抑、阴郁怪诞、彷徨软弱、庸凡无力、爱情政治理想终会破灭的凄惨的灵魂。
故事的叙述角度是全知视角,即叙述者所知道和了解的要大于角色所知。叙述者是这个故事中以全知全能视角讲述故事的“人”,它以旁观而不参与的形式讲述故事,但又不是故事中的某个角色。这样,《山河入梦》全知全能的视角让故事的叙述者替代叙述角色出场,以第三人称讲述故事,观察人物举动、洞悉人物内心。
全知视角不仅可以看到人物行为,同样可以了解人物内心。小说中大量的人物内心独白被用字体不同的小字标示出来。读者可以轻易走进他们的内心,跟随他们的心理走向感知人物、推知故事发展。小说中同样包含大量字条和书信,以不同字体展现出来,其中的隐秘内容都被呈现到读者眼前,这些字条或是隐喻或是神秘的指引,曲折隐晦地暗示了人物的发展和结局;书信则清晰记录了人物的往来和情感的变化。无论是书中各个人物的意识流动、不同人写在字条上的诗词,还是最后谭功达和姚佩佩的书信来往,全知的叙述方式都以秘密“窥探”的角度展现了谭功达后半生的全部生活。
二、叙述态度
由于叙事态度是故事这个全知全能叙事者的态度,故事叙事的现实主体即作家格非并不参与故事,作家态度被刻意隐藏,这从根本上要求叙述态度冷静、客观。无论是表现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要求按照故事人物本来的性格和心理进行“如实”描绘,当人物性格等被固定,那么事件就按照人物本身的特点而发展。现实态度就被要求“真实记录”:谭功达办事的一板一眼、一丝不苟,强烈的政治热情,心理和行为不符的道貌岸然、苦闷压抑甚至是怪诞不经;姚佩佩的活泼富有活力,但内心敏感阴郁、脆弱逃避;政治社会中对人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和划清敌我阵营界限对人的戕害。同时故事所在的地点也被全景式地描绘出来:普济的风土人情,“桃花源”似的花家舍等。
现实态度的冷静、客观,体现在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全方位展现人物行为、心理等。谭功达对于姚佩佩,从开始相处的暧昧到欲望的压制、朦胧情思的不敢承认和反复思量,再到最終认清自我感情,都是秉持客观态度进行故事讲述;谭功达耗尽全部政治热情参与改变乡村,企图实现自己的乌托邦幻想——建造一个大同社会的“桃花源”。但是和爱情一样,这样的理想主义永远不可能实现。此时,叙述者的现实态度作为作品的表层倾向显而易见,但拟作者的审美态度作为深层倾向往往隐而不露。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又可以清晰感受到这其中有一个隐藏在叙述者背后的拟作者在不动声色地指引读者进行审美,拟作者的审美态度支配着读者进行审美观照,尽管叙述态度是冷静客观的,拟作者仍然可以以主次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施动者和受动者的关系和动作、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文学风格在背后对读者审美进行引导甚至是极大程度的操控。读者全身心投入故事中,尽管是旁观者,但是一旦走进文本,就带有强烈的个人体验。这种个人体验的前提是拟作者审美态度的指引。
对于谭功达,读者知道他行为和心理的偏差,了解他的政治热情和热切美好的期盼,但又清晰读出追求这种理想的艰难和不可到达彼岸的白日梦想;对于花家舍,读者看到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的美好,同时看到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宿命论等的不可捉摸、虚幻而脱离实际和难以为继。
叙述者只是拟作者的代言人,拟作者的审美态度可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改变而偏离原本的客观态度,这就造成了文学文本中带有情感引导的拟作者和客观叙事的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分离,同时达到叙述态度和审美态度偏离的效果,即叙述态度冷静客观,但审美态度在思考中怀疑批判又缺乏明确的答案,因此隐晦、含混又朦胧。
三、叙述的时间结构
众多故事时间节点的串联和统一,使时间作为一个构成要素不断推动故事发展,形成情节。和叙述态度一样,时间结构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现实时间,二是审美时间。现实时间是叙事中表现的自然时间,故事遵循自己的时间设定,在一定的背景中开始这个故事。小说从1956年4月开始讲述谭功达后半生20年间的种种。故事按照其独特的背景环境(其中包括自然环境和时代环境)推进演变,像是时间自然流逝中缓缓铺成的一段如烟往事。
1956年的中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各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谭功达来到普济出任县长,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谭功达改造的对象,这里的人都是他希望启发的百姓,谭功达想要在这片土地实施他的政治理想,构建桃花源社会,他多年的光阴都在这片土地上挥洒。小说的叙事时间就是在1956年开始,直至1976年结束。
小说的审美时间不同于生活中的时间消逝,故事中时间的定格或流逝是依据情节而改变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下时间可能平行,即在同一时间表现不同人物的行为或心理。例如,会议时领导在台上讲话,姚佩佩和汤碧云在台下传纸条交流;谭功达在花家舍生活收到姚佩佩的逃亡信件,可以看到两人的生命轨迹在同一个时间被表现出来。
同时,文学叙事中,时间会因情节的安排迅速消逝或者定格在某一瞬间。姚佩佩被捕之后的九个月直至死亡都一笔带过,命运的不可抗和虚幻在文本中以瞬间的方式完成。谭功达在狱中的生活同样涉笔简单,多年牢狱生活被凝缩成几句话语概括,弥留之际的谭功达再次看到了姚佩佩的身影,他所期盼的桃花源社会被宣告“实现”,他终于带着巨大的悲哀和欣慰离开这个世界。
四、叙述语言
叙述语言作为现实语言转化成文学语言的方式、手段,具有构建、转化作用。叙述语言的三种类型:概述、即时话语、场景描写都在《山河入梦》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小说通过叙述语言完成了文学文本的建构,并使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和审美意义。
(一)概述
在小说审美时间中,多年时光可以被一笔带过,数月数年光阴倏忽而过。姚佩佩和谭功达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都以概述的方式被简单呈现。二人在狱中的艰苦生涯被隐藏,只是结果的残酷就足以让人唏嘘。美梦的破碎只需要一瞬间,这样的叙述是对他们生命走向终点的一个总结。
除此之外,故事中有许多古诗词句。大量的古诗句,既丰富了故事内涵,让故事在古典中变得含混,同时作为故事的组成部分也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这些字句都作为概述的表现方式用以区别人物话语和心理,构成整个小说的叙述语言。
谭功达无意中翻阅到《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就像《红楼梦》中的判词一样暗示了姚佩佩的命运。谭功达居住的房屋是寡妇所留,寡妇自尽时桌上留下的小诗,似乎也预示着谭功达的一生:“花开若有思,花盛欲似燃。一夕风雨至,狼藉不可看。”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地狼藉失所有。谭功达的县长一生终究垮台,狼藉一地不忍再看。这一切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命运的神秘莫测加之古典诗词的多义表达造就了小说叙事语言的古典、神秘和朦胧。
(二)内心独白
小说常常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进入人物内心,表达人物意志。《山河入梦》中内心独白的频繁使用却恰到好处。充分表现了人物所思所想,给人物行动提供了心理支持。
谭功达不能说出口的话,不敢做出的行动都在他的意识当中暴露无遗。姚佩佩常常出现在谭功达的内心独白里。面对姚佩佩,谭功达的内心并不平静:“要是提拔她当个科长什么的,倒也合适。佩佩呀佩佩,只是你那一嘴吴侬软语,一身千娇百媚,自己还像个孩子似的,如何去约束下属?”这是谭功达第一次有关姚佩佩的内心独白。
面对姚佩佩的拉拉扯扯,谭功达作为一县之长多次严厉训斥,常常被弄得哭笑不得。可是当心中想起姚佩佩这个人,便立刻想到她的吴侬软语、千娇百媚。群众上前要打人时,姚佩佩害怕地缩在谭功达的怀里,文本清晰表现了谭功达此时意识的流动:“佩佩,我可不是故意的,她的汗味竟然都是香的,她的唇齿间水果糖橐橐有声,难道她在吃糖吗?都什么时候了,难道你还有心思吃糖?”
在谭功达尝试和这个下属保持距离无果后仍旧继续抱着她,内心独白再次出现,他不禁感叹她的身体竟然如此柔软,浓浓的糖果的芳香似乎不是来源于糖块本身,而是来源于她身体的各处。此时肢体碰触时谭功达对姚佩佩的暧昧情感呼之欲出,但行动上谭功达仍然保持着他的一贯作风,对于欲望始终压制,对情感也不敢承认。
谭功达对姚佩佩所有的情感和念想都被他的内心独白真实地反映出来。这样的独白不仅展现了人物的内心,同时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使主人公不仅拥有现实中的政治热情、乌托邦幻想,并且自我意识中有对姚佩佩的爱和性的冲动、渴望。内心独白中的谭功达是更为真实的他,比起表面的道貌岸然、一板一眼,自我意识中的他常常与现实相反。
许久,谭功达渐渐认清自己的情感,但是被张金芳设计与她结婚,悔恨时默念姚佩佩的名字后来又发现姚佩佩的邀约纸条,但已是一月之后,他心痛难耐,心中全是姚佩佩的模样,心中不断默念她的名字。
内心独白不仅在对爱情和性的渴望时出现,在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道路中同样常见。谭功达和母亲一样的寂寞忧伤,但是与母亲不同,他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他时常想起母亲,但是却对她并不了解,只能从戏文和书中看到一个固定的英雄形象。他在追求政治理想的路上无疑受到母亲的影响,但又总是受挫而不知所措,于是在他的意识中,母亲是他政治理想的希望、指引。在他彷徨困惑时,他总是想到母亲。
姚佩佩的内心世界,也通过内心独白展现出来。谭功达希望修大坝通电安路灯,可姚佩佩没有接话,她的内心是被忧郁包裹着的:“可我觉得黑暗挺好。只有在黑暗中,我才觉得自己是个人。”由于家庭的原因,寄人篱下的姚佩佩脆弱无依,阴郁寡欢。同时姚佩佩的内心独白清晰展现了他对谭功达情感的变化。起初谭功达在姚佩佩的印象中并不好,他老派木讷,做事一板一眼,一本正经,当姚佩佩得知自己被调到谭功达的办公室时,心事重重:“怎么偏偏把我調到他屋里去?怎么这么倒霉!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上的乌云不会移走……永远不会。”后姚佩佩邀请谭功达前来赴约,没有等到他来,姚佩佩此刻的独白竟是如此疯狂和急躁:“谭功达!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要杀人啦!他妈的我要杀人啦!”此时,姚佩佩已清晰知道自己对谭功达的情感依赖。
关于谭功达奋斗着想要实现的像花家舍一样的桃花源梦想,在谭功达的内心独白里,可以看到他的困惑: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显得郁郁不欢?他不得而知。谭功达的困惑和疑虑让这个乌托邦式新农村变得遥远而不可知。这里隐隐透露出,这样的政治理想,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读者不禁思考,这里超前的社会景象更像是表演出来的供人憧憬的假象,这是个讳莫如深的秘密,是不能到达的理想。
(三)场景描写
故事中包含大量的场景描写,甚至达到了繁多的地步。开篇即是对普济风水景色的描绘: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一片颜色多彩明丽的花海。一派人间胜地景象。至于花家舍,这片“净土”更是美好到有些许不实:柳树吐新枝,一排排白墙砖房错落有致,大片紫云英花地,水光潋滟的湖面,来来往往各司其职的人们,这里风景绮丽,阳光灿烂。
小说中大量的景物描写作为情感的抒发,既是故事的背景,又推动着故事发展。场景描写不仅体现在小说中的景物描写,还有环境气氛的营造,人物行为的刻画。钱大钧带领几个年轻职工给县长收拾屋子,各式人物粉墨登场,他们的一言一行,神态动作,犹如情景再现。
又如,姚佩佩被金玉侵犯时的内心独白以及她的紧张屈辱神态和一连串迅捷的动作都表现了气氛的紧张,文字叙述成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姚佩佩流亡时信中所写,皆是场景串联。诸多连续的场景描写构成了这个完整的故事,让读者在阅读故事时有画面感,流动感,并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体会到故事背后的精神和意义,引发深沉的思考。
《山河入梦》以生动叙事语言的描绘,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态度和审美态度的分离,时间结构的合理安排,讲述了谭功达后半生的人生旅程,并以谭功达的死亡悲剧作结。命运的难以捉摸,宿命的指引和操控,爱情的幻灭,桃花源梦想的破碎都连同谭功达一起埋葬在他深爱的山河。山河终入梦,只有在梦中,这个理想才能实现,他半生追寻的山河是迷雾中再也难寻的彼岸,永远不能到达。
参考文献:
[1]樊蕾.论格非创作转型后的“传统”书写[D].南昌大学,2019.
[2]柴微微.乌托邦幻灭史[D].沈阳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