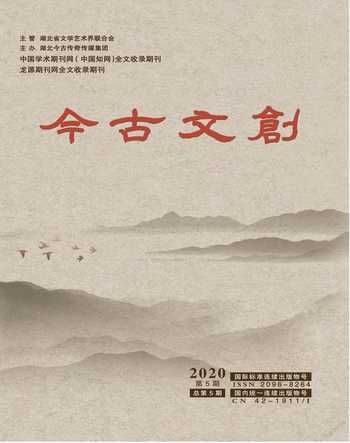论中国早期典籍中的记梦及其功用
2020-09-10曾小霞
【摘要】 中国古代典籍如《左传》《史记》中记载了大量的梦故事,探究中国梦文化心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梦与先民们的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密切相关,梦渗透到非梦中,与之一起构成历史。早期梦的主要功用有:阐发人生观、沟通鬼神、梦占军国大事。
【关键词】 梦文化心理;梦占;功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85-02
本论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晚清《史记》接受研究”(14YBA070)研究成果。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梦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王锺陵先生曾说:“如果说人类存在过梦文化的话,那主要应是在人类早期。”[1]354梦是一种牵涉甚广的文化心理现象,从梦出发探寻中国古代人的文化心理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商周时期对梦的卜筮是卜筮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种类。先秦诸子中孔子对梦发出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感慨,《韩非子》中侏儒梦灶以讽谏卫灵公等等,梦多方面地参与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中。先秦集中反映梦的典籍主要有《左传》和《庄子》。《左传》中比较重要的记梦材料大约有二十多条,《庄子》三十三篇中有十篇与梦有关。其他著作中也有不少梦的记载,如《史记》《晏子春秋》。《史记》或汇集前人史料,或采录各地见闻,书中梦事记载较多,如《殷本纪》中的武丁梦;《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梦与海神战以及秦二世梦见白虎;《高祖本纪》中刘媪梦与神遇;《封禅书》中的秦文公梦黄蛇、秦穆公梦上帝;《晋世家》中周武王梦天赐子名虞、骊姬以梦为手段杀太子申生、狐突梦申生;《郑世家》中燕姞梦兰;《赵世家》中赵简子梦钧天广乐、赵武灵王梦女鼓琴而歌、赵孝成王梦龙上天不至而坠;《孔子世家》中孔子梦楹;《外戚世家》中薄姬梦龙生代王、王美人梦日入怀生太子,等等。借梦以阐发人生哲理、以梦通鬼神以及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是早期梦文化的几个主要功能。
一、借梦阐发哲学观
唐陆德明曾说《庄子》:“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2]28庄子常借用梦的形式来阐释自己的哲学观,梦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庄子》文学风格的诡诞性。
庄子在《大宗师》中提出“真人无梦”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觉无忧”和“寝不梦”二者相辅相成,“觉无忧”方能“寝不梦”,“寝不梦”故“觉无忧”。“真人无梦”中的“真人”是庄子虚构出来的理想人物,实际上与后世的神仙无异,它要求完全摒弃人世的俗虑,万物不萦于心。
庄子还有“圣人大觉”说,《齐物论》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2]104-105 梦到“饮酒”,白天可能会哭泣,梦到哭泣,白天可能在“田猎”,说明梦是相反的。“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梦时为真,觉时方知梦为幻。庄子将人生比喻为一场大梦,“大觉”者为圣人,愚人是不能“觉”的。人生如梦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学。
庄子关于梦的最重要的论述当为梦蝶说,庄子借梦蝶事来说明他的齐物论,亦即说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蝴蝶与庄周,通过做梦,而互相转化,体现了梦的“物化”观。
《人间世》中通过匠石梦栎社树的形式揭示了树因不材而长寿,以阐发其无用即为大用的观点。《外物篇》神龟托梦宋元君,应在求生,但因其有知反遭刳肠之祸,庄子认为去智、去善方能免祸。《至乐篇》中庄子梦骷髅谈死之乐,阐发其以生为苦,以死为乐的人生观。
梦寓言清晰、全面地展示了庄子的人生观,梦中形象多变,托梦者有神龟、蝴蝶、骷髅、树等,在梦中,这些动物、植物甚至死人都富有灵性,能与人对话。庄子笔下的梦都是寓言,大部分是虚拟,以梦阐发其哲学观,寓意深刻,他对梦与觉、梦与人生、梦的本质有初步的探讨,这些探讨从侧面说明了梦在当时的重要性,同时开启了中国的梦文化思想。
二、以梦通鬼神
当人们发现梦境跟现实生活中的灾难和喜事有着某种联系时,由于解释不清,就将之与不可预知的鬼神之力联系在一起,把梦看成是鬼神对做梦者的预示,产生梦是梦者“与精灵、灵魂、神的交往”,做梦是“神为了把自己的意志通知人们而最常用的方法”。[3]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中都普遍信仰梦魂观念。我国云南景颇族和傈傈族的某些地区,解放前仍处于原始社会,他们认为人做梦就是灵魂外出遇到的事物和人,[4]“在高山族、黎族、彝族、壮族以及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那里,我们几乎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梦魂观念的表现或残余”。[5]
中国早期的梦文化也主要体现为梦魂观念,即认为梦是灵魂的外游。人在清醒时,灵魂寄居在人体中,当睡眠时,灵魂就会外出游荡。屈原《九章·惜诵》云:“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梦与魂并列以说明登天之梦。王充《论衡》:“人之梦也,占者谓之魂行。”
《左传》中有些梦体现出早期人们以梦通鬼神的观念,《左传·成公五年》记载:“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赵婴被赵同、赵括放逐后,梦到天使的神示,他试图通过祭祀免祸,但是由于他与侄媳赵庄姬私通,犯了淫罪,即使祭祀仍然得不到神的福佑。神福仁而祸淫,说明神对人的庇护也是看对象的,梦中的世界虽然有神的指示,但神的指示仍然遵循人世间的道德法则。
《左传》的梦大都被当作上天之命、鬼神之意,鬼神在梦中出现,将旨意或信息传达给做梦者,睡着时的梦境对清醒时的日常生活有着强烈的指示作用。对于《左传》将梦当做历史的一部分加以记载的现象,“当原始人把梦看作是真实的存在时,梦也就会介入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了……梦渗入到非梦之中,并和非梦一起构成历史。”[1]354梦与非梦,都是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早期文化中梦对非梦的渗透作用,更使得它具有不可随意摒弃的重要价值。
三、梦的政治作用
在中国前期文化中,上至君主,下至臣僚,都喜欢用占梦的形式决定军国大事。庄子《田子方篇》中周文王为了达到授政臧丈人的目的,不惜编造梦,群臣对此梦认可,周文王最终也顺利达到目的,这说明梦在当时具有合理性和权威性,梦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神示。周武王讨伐商纣时梦见三神告诉他“戍商必克”,也是以梦境来表明周朝是天命所归,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梦得贤臣是梦的政治功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武丁以梦得傅说,对于这段记载,王锺陵先生论断道:“无论这是当时的神道设教,还是事后的涂饰,要托以梦见,则梦之力可慑服‘群臣百吏’,为圣人增天命之光,亦伟矣夫!”[1]359
也有以梦作为政治进谏手段的。如《晏子春秋》记载景公梦见彗星后,“明日,召晏子而问焉:‘寡人闻之,有彗星则必有亡国。夜者寡人梦见彗星,吾欲召占梦者使占之。’晏子对曰:‘君居处无节,衣服无度,不听正谏,兴事无已,赋敛无厌,使民如将不胜,万民怼怨,茀星又将见梦,奚独彗星乎?’”[6]梦见彗星是不吉之兆,晏子一方面利用了彗星的不吉传说,另一方面进一步将着眼点从天灾转到政治上来,以阐释景公的梦,从而达到劝谏景公改变行政之道的目的。此外,《晏子春秋》中景公梦二丈夫、五丈夫、慧星以及梦与二日相斗而不胜等记梦情节都很好地体现了晏子的政见和敢于直谏的精神。
梦往往被有心人利用,尤其是帝王后妃。《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骊姬以梦为手段谋害太子。在帝王以天命自许的时代,梦往往是天命的媒介,帝王为了增强自己皇位的正统性而借助梦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以梦为手段为自己制造有利舆论:“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7]341
梦中之神即为龙,为了说明高祖的龙子身份,文中其他地方也有事实佐证,如借高祖斩蛇证明其为赤帝子,又说刘邦“醉卧,武媪、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7]343 刘媪之梦神,即为了证明刘邦乃天命之所归。《汉书·王莽传》刘京上书言梦:“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8]这个梦得到了王莽的欢心,为王莽的纂汉提供了舆论资助。
在早期占卜中,八卦、龟卜均需借助于工具和物理手段,其操作往往有不可控性,比较而言,梦更灵活,它具有自知性,个人的梦境与感知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来编造、描绘,这大概也是早期典籍中梦记载看起来较多的原因吧。总体上看来,《庄子》记梦多用以阐发庄子的哲学观,显示出初步对梦的哲学辨析,《史记》等史传作品中的梦则较多地体现出早期人们的梦魂观念以及梦的预兆作用与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王锺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8-49.
[4]中國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资料选辑[M].1982:9-10.
[5]刘文英,曹玉田.梦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
[6]卢守助.晏子春秋注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35-236.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4093.
作者简介:
曾小霞(1981-),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