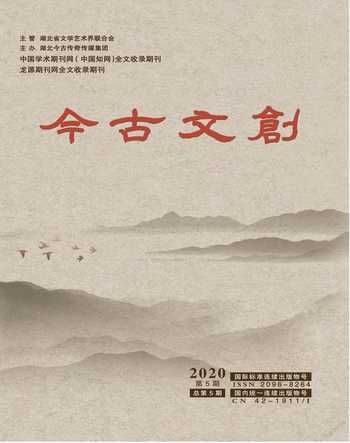从审美移情角度试析“江南三部曲”中的意象美
2020-09-10潘怡彤
【摘要】 审美移情是一种重要的审美体验范式,通过主客体之间相互交融,以达到由景及情、物我两忘的境界。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运用了许多意象,集中体现审美移情对意象美的塑造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本文将从个人情感注入的移情本质、景中含情的移情手法、审美对象激发读者共同与个人双重激情这三方面,试析“江南三部曲”中的意象美。
【关键词】 “江南三部曲”;审美移情;意象美;共同与个人双重激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24-03
项目名称:从审美移情角度试析“江南三部曲”中的意象美
作家格非于2011年完成“江南三部曲”的创作,并于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江南三部曲”中美学思想的体现是广泛而深刻的,颇具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江南三部曲”中的审美意象一直被学界广为研究,但多以意象解读、江南美学传统等方面的研究为主。本文旨在着眼于审美移情的角度,从移情本质、移情手法与移情作用三方面进行研究与论述。
一、个人情感注入的移情本质
立普斯说:“审美欣赏的‘对象’是一个问题,审美欣赏的原因却是另一个问题。美的事物的感性形状当然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但当然不是审美欣赏的原因。无宁说,审美欣赏的原因就在我自己,或自我,也就是‘看到’‘对立的’对象而感到欢乐或愉快的那个自我。” 其意思是说,在审美享受过程中,所令人感到愉快的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自我的情感。即欣赏审美对象时,人与物已相互交融,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界。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审美移情的本质即是个人情感的注入。眼中之物已不再是单纯的只有自然属性的景物了,而是一种主观情感的观照物,赋予了很强的个人情感。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融入了作者深厚情感的“物”,将会有更深邃的意蕴与更强的感染力,形成意象美,给读者带来审美想象与愉悦。
格非在“江南三部曲”的意象塑造上,便注入了自己浓厚的个人情感,达到“移情”的效果,体现出丰盈幽深的意象美。
书中有关“江南”的意象,与格非的个人情感是相交相融、物我合一的。格非出生在镇江丹徒丁岗镇,在这个江南乡下度过了16年。对于江南,他有着很深厚的情感,以及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他曾在随笔中写道:“读大学时,常有城里的同学问起‘桑中之约’,言下之意,‘偷情’何必桑中?要明白其中的奥妙,必须先了解桑园的规模和特点。我们家乡是丝绸产区,桑林通常宽阔无边,一对男女钻进去,往往便于隐蔽。此外,桑树的特点是上密下疏(桑叶繁茂,桑干稀疏),男女在桑中幽会,偶尔被人撞上,即便是在很近的地方,对方可以看见你的脚,却不太可能看见你的脸。” 又说:“密密的桑叶所筛出的清幽之光,既非一无遮拦的‘明’,亦非绝对的暗,妙在明暗之间,与外在世界隔又未隔,幽会的双方既在世界的中心,又在世界之外。”
由这里不难看出,格非对江南有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并在其中产生出了深刻的情感;而这种体验与情感又与江南的桑树林紧密相联。这便达到了一种审美移情的效果,桑林早已不单单只有自然属性了,而是被注入了格非本人的一种孤寂、游弋、奇奥隐秘的情感。
而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也将这种情感注入到了有关“江南”的种种意象的塑造之中。书中在许多地方都体现了这种“桑林之感”,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一处则是《山河入梦》中姚佩佩对紫云英与苦楝树的感怀。
姚佩佩在去普济水库的煤渣路上第一次看到紫云英时,便惊叹于它的美,并由此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伤感自怜,自觉自己是苦楝树阴影下的紫云英。紫云英明媚而清幽,就如丝丝缕缕的微光,在苦楝树巨大的阴影之下若隐若现。这是一种与“桑林之感”极为相似的情感,光影明暗交错,难以捉摸,情感则是孤寂的、游离的、飘渺无依的。
可以说,格非是将自己从生命体验中得到的独特而深厚的情感,注入到了书里的紫云英和苦楝树影上,产生了“移情”的效果,将其赋予了一种真挚而浓郁的感情,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有着凄愁、奇奥、漂泊、寂寥的特点的意象美。
在书中的其他许多意象中,这种特点也是一脉相承的。譬如《春尽江南》中那家名为“荼蘼花事”的会所,雨后檐廊下的睡莲、墙角的一丛蔷薇、过季迎春花的枝蔓,都呈现出一种“颓废的岑寂之美” ,在阴翳中闪动一点明亮;又如王元庆告诉谭端午的“雾岚”,阴沉的浓雾与略有微光的流岚交错,在暗影处微有光明。
种种这些意象,构成了“江南”这一大的意象。而正因格非这种深沉而独特的个人情感的注入,“江南”这一意象方呈现出一种深邃丰盈的美,这种美是明与暗的交杂,是隐晦、迷离、幽微的;颓丧寂寥,有一种“开到荼蘼花事了”的悲剧意味。
二、情景互生的移情手法
审美移情的情形主要包括偏重景、偏重情、情景互生三种。而“江南三部曲”则属于情景互生这一类。以书中人物的视角,去写人物眼中的景,而后再抒发情感。景与情相互交融,则形成了一个个富有美感的意象。
“不但由我及物,有时也由物及我” ,“江南三部曲”中深刻地体现出移情的双面性,其意象也呈现出更复杂、更深刻的美感。
譬如《人面桃花》中“金蝉”这一意象便是如此。张季元在遇难前将金蝉交给秀米,韩六分别时也将其给秀米;秀米革命失败,金蝉也仿若应了那句传言:“一遇到紧急情况就会发出夏蝉一样的鸣响” ,饥荒年间小驴子归还的金蝉连一袋米都换不来。
在秀米看到韩六给她的金蝉时,书中如是写道:“秀米轻轻地撫摸着光芒四射的蝉翼。现在,她已经没有当初凝视它的那种柔情蜜意,相反,她觉得这枚金蝉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仿佛是天地间风露精华所钟,宛然活物,说不定哪天真的会忽然发出叫声,或者鼓翼振翅而去。”
这便体现了移情的双面性。秀米由蝉展翅欲飞、活物般可怖的形态,引发出内心的恐惧感与不安感;又因为先前所经历的种种厄运,以及当下愁闷痛苦的个人情感,而在看金蝉时对其产生了这种感想。主客消融,物我两忘,金蝉与秀米在此时此刻是相互交融的,而也因此,金蝉被赋予了一层荒诞、悲情的色彩。金蝉本身所具有的蛰伏数年、一朝破土重生以及漂泊单弱交杂而成的寓意,与人物和金蝉发生勾连时,人物本身的命运凄苦、理想破灭、革命荒诞悲情的色彩相交相融,使金蝉这一意象被赋予了一种复杂、悲怆、理想破碎、人生荒唐的悲剧美。
而更令人称佩的是,作者采用这种移情手法,使构建出来的意象产生出独特而深刻的美感。这也令读者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将其当作重要的欣赏对象,并在阅读中进行二度创作,产生出独有的审美享受。
除了金蝉外,阁楼、冰花、睡莲、蒺藜、泡桐等意象,皆体现出这一特点。
譬如“冰花”这一意象。格非在谈“江南三部曲”的创作时说道:“我在写《人面桃花》时,无意中想到了冰。在瓦釜中迅速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和未来。这个比喻是我的守护神,它贯穿了写作的始终,决定了语言的节奏和格调,也给我带来了慰藉和信心。”
冰花在一般文学作品及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一般代表着脆弱、冰清玉洁、短暂。“江南三部曲”中的冰花意象诚然也体现出了这些特点,但其更独特的地方是有着一种命运的悲剧感,象征着理想被现实击碎的幽暗怆然。也正因其独特性与深刻性,才令读者在心中接受了这一意象,并从而阐发出自己独特的情感。
在塑造“冰花”这个意象时,作者同样采取了情景互生的移情手法。《人面桃花》的末尾处,瓦釜的冰花正在慢慢融化,这使秀米生发出桃源梦碎、理想消融的悲怆之感。而秀米在人生尽头所涌现的这种悲亡之情,又将冰花更赋予了一层厚重的宿命感。更兼有冰花织图中的那幅景象:陆侃微笑着与人下棋,谭功达正走下车来;亦真亦幻,宿命、沧桑、理想、颓唐,都给予了“冰花”这个意象独特而复杂的美。
而“江南三部曲”中独特的冰花意象,也将扎根在读者的心中,使读者在阅读这部书或是其他书时,基于此进行二度创作,从而获得独有的审美享受。
三、审美对象激发读者共同与个人双重激情
审美移情的功能是人的情感的自由解放。立普斯形容为“包含了心灵的丰富化,开扩和提高” 。
“江南三部曲”的一个不凡之处就在于,其塑造出的种种意象,作为审美对象,不仅激发了读者的共同激情,也激发了读者的个人激情,带给了读者更加彻底的情感解放。
共同激情指读者站在书中人物的角度,因人物所经历的事情,与人物同喜悲。个人激情则是读者跳脱到书外,以局外人的视角,对书中人物产生自己的个人情感。
而格非书中这些极富美感的意象,正激发了读者共同与个人的双重激情。
如“瓦釜”这一意象。秀米疯了的父亲陆侃在大火后安静了下来,对着瓦釜念念有词。这首先激发了读者的共同激情,读者站在陆侃的角度,产生移情作用,则瓦釜有了一种沧桑、悲怆之感。而又同时激发了读者的个人激情,即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一个疯子,终日对着瓦釜说话,这使瓦釜增添了神秘、诡谲的色彩,而结合后文瓦釜贯穿秀米的命运始终,则又有体会到了一种宿命感。
一次是站在人物的角度移情,一次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移情,如此两次移情,激发起读者共同和个人的双重激情,读者也得到了更多的体悟、思考,而“瓦釜”这个意象也更加深邃,更加富有内涵。
而更深一层的是,许多意象激起了书中人物“自媚”的情感,因这种“自媚”产生移情,则会使这些意象的美更加幽微,蒙上了一层绮丽魅惑的色彩。而读者当作为旁观者来看时,则又会产生出另一种更加复杂隐秘的审美感受。
“自媚”翻译自德语词“kitsch”,即讨好自己、迎合自己。学界一般将其直译为“刻奇”。昆德拉在解释“kitsch”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看见草坪上奔跑的孩子,由‘kitsch’引起了两行‘前后紧密相连’的热泪:第一行是说:看见了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多好啊;第二行是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此时,“草坪上奔跑的孩子”这一意象在观赏者的眼中就被蒙上了更加瑰丽幽邃的色彩,而旁观者,在将“观赏者看孩子奔跑并产生kitsch”视为一个整体来看时,则会生发更加复杂的审美感受。
可以从“江南三部曲”找到许多例子,其中《春尽江南》第四章中“墙角女孩”这一意象最为绝妙。
端午看到坐在墙角阴影处的女孩,因其愁态身形与绿珠相似,也因自己思念绿珠,故而产生移情。
笔者不揣冒昧的理解是:端午所感怀的,不仅是“墙角女孩”这一意象的绮靡之美,还有自己因她而引发的对绿珠的思怀,让端午在内心深处感受到自己仍然是一个有情意的人。这一点从后文中所写“晚宴的时候,绿珠给他发来两条短信,他还没顾得上回复” 可以得到佐证。这就可以称得上是昆德拉所说的“第一行泪”。
而之后,吉士也注意到了这个女孩,并与端午谈论。此时,端午的兴致很显然更浓了,这可以由他兴致勃勃地猜出“绿窗人似花” ,以及最后想说却被打断看出。笔者认为,这就是“第二行泪”:端午发觉,并不是只有他一人产生了这样的移情,这让他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肯定,也因此更加大胆地去进行审美享受,进而说出了“绿窗人似花”的话。
读者先是站在端午的视角,产生了共同激情,去感受阴影、浅蓝纱巾、墙角女孩与思念绿珠交杂一起的美感。
同时,又会跳出端午的视角,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把“女孩独坐墙角,端午移情墙角女孩,并发现吉士也与他相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产生个人激情。而这种个人激情,则主要是端午的“kitsch”给读者所带来的一种略有矫情又虚幻绮丽的感受。
故而,“墙角女孩”这一意象,在移情过程中也呈现出了晦暗、虚幻、缥缈幽婉,又带有“小布尔乔亚”色彩的美感。而这种复杂的意象美,也将给读者带来更为丰富而多层次的审美享受。
“kitsch”并不能算是一个褒义词,它代表着人物内心很强的自媚、自怜的思想,有一种虚幻的色彩。然而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几个主人公,秀米、功达、端午等,都并不是绝对的务实主义者,他们的身上本身就具备这样一种虚幻的特性;故而,因“kitsch”而产生的移情,与这些人物的气质是相吻合的。也正因如此,二者方才会碰撞出极富美感的火花。
四、结语
审美移情对“江南三部曲”中意象美的塑造十分重要。个人情感注入的移情本質使意象被赋予了深厚的感情,更加厚重动人;情景互生的移情手法使意象更为触动人心且意蕴深长;意象作为富有美感的审美对象,也激发了读者共同与个人的双重激情,为读者带来充盈丰沛的审美享受。
江南的淫雨霏霏,交织着人物的命途多舛,构建出了一个个深刻而隽永的意象,使读者沉浸其中,沉思感怀。
参考文献:
[1][德]迪奥多·立普斯著,朱光潜译.论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八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3.
[2]格非.乡村教育:人和事[J].百花洲,2011,(2):108-116.
[3]格非.江南三部曲·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63-64.
[4]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7.
[5]格非.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62.
[6]格非,木叶.衰世之书——格非访谈[J].上海文学,2012,(1):195-202.
[7][捷克]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99.
[8]李谊.韦庄词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8.
作者简介:
潘怡彤,1999年11月12日出生,女,汉族,籍贯安徽省六安市,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