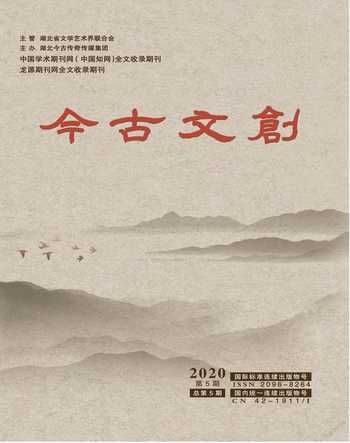论田耳小说的死亡书写
2020-09-10张创弘粹
张创弘粹
【摘要】 死亡是悬置在每个人头上不可忽视的问题,它开启了人类最丰盛的情感之门,同时也激发了每个人对生存价值的追寻。而田耳作为以书写人性本真为宗旨的作家,也试图从死亡中探寻生命的精髓。他借助文字搭建了一个叫“佴城”的世界,多篇小说共同讲述着佴城人们的死亡故事。花季少年自杀,校园意外身亡,复仇、自然死亡等等不同类型死亡的发生成为他小说的常态,死亡也在他的小说中起到了多重作用。本文将通过对田耳小说中的死亡描写及其相关意象的分析来探讨田耳的小说死亡书写背后的深沉意蕴,寻找佴城这一虚拟之城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田耳小说;死亡书写;佴城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19-02
死亡问题,作为横亘在每个人面前不可绕行的问题,这也是历来任何一位哲学家、文学家都无法忽略的问题。而在文学创作中,当庸俗平淡生活的书写已经无法满足作家们的情绪思想表达后,死亡则成为了文学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纵观田耳的小说,可以发现其中出现了许多的死亡描写。不同年龄身份的人物在一个叫佴城的地方完成着各式各样的生命终结仪式。
一、直面死亡:肉体或精神的消亡
田耳小说中频繁出现死亡这一话题。从死亡原因来看,将其分为自杀类、意外死亡類、自然死亡类、他杀类等。死亡不只是肉体的消亡,作为一个哲学话题,它更涉及到人的精神世界。
自杀一类的,比如新作《一天》讲述了“我”的农村堂哥双胞胎女儿纷纷离开人世的故事,全文围绕双胞胎姐姐单妮十六岁时在学校跳楼自杀身亡事件展开,并倒叙插入另一个悲惨的事件,即双胞胎妹妹双洁五岁在一次嬉闹中,被弟弟推落到五米多高的陡坎下,因家人的疏忽和愚昧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在抢救手术中被宣告死亡。《掰月亮砸人》桑女用铁钉撬马牙,引发败血病而死。叫花子小狗以复仇式的自杀表明了自己的控诉。意外死亡类《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以佴城中等师专一名女学生刘婉玲意外跌下楼梯死亡事件为源头。《在父亲的来信中》李忠林目睹父亲被撞死的那一刻。《韩先让的村庄》在小说最后也涉及到了意外死亡事件,一位来鹭庄旅游攀岩的大学生和一名当地居民小星不幸溺水身亡。《氮肥厂》氮肥厂的残疾门卫人老苏与寡妇洪照玉在氮肥厂的气柜上媾和,最后由于气柜异常发生爆炸,光溜溜的两人被冲上天空随即坠落而死。《衣钵》主人公李克的道士父亲在酒醉回家路上跌倒,头撞石头而意外身亡。自然死亡类有《金刚四拿》讲述了“我”大爹和罗四拿的大爹罗瞻先相继去世,“我”和四拿如愿当了一回金刚的故事。《坐摇椅的男人》中的老梁和小丁梦靥般死在摇椅上。《长寿碑》提到了两位乡村长辈“我”的舅舅和覃四姨相继离世。他杀类,《夏天的糖》小说结局江标加大油门开车从铃兰身上轧过去,夺走了铃兰的生命,也断送了年少记忆和念想。《一个人的张灯结彩》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痛心而惋惜的故事,哑巴小于的情人抢劫误杀了小于的亲哥哥。
死亡书写,尤其是非自然死亡书写在田耳的小说里成为了一种常态。生命活力的丧失,随之而来的精神困境也不断地在叩击着人们的内心。
二、“死”亦可欢:田耳小说死亡书写中的常与反常
接受主义美学认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召唤结构,存在着大量的未定性和意义空白,而将作者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接受意识连接起来的正是隐喻,隐喻是召唤结构存在的基础,是文学文本存在的中介,是读者在文本中获得意义的前提。在田耳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不一定与死亡直接关联,但是也无时无刻隐喻着死亡真相,比如望远镜、梦境。透过这些重复出现在多部不同小说中的意象,可以发现隐匿在小说背后的深刻意识。
(一)借“望远镜”窥探摇摆的人性
佴城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染缸,田耳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所接触太多面目全非的人,人性的‘摇摆’是我观察到最日常的现象”。①在佴城空间里,窥探成为了讲述故事的关键词,望远镜也成为了田耳小说的常见意象。望远镜又称“千里眼”,具有远距离放大的功能。田耳充分发挥其功能,深入地窥探隐藏在表象背后的人性的真实面目。在田耳小说中《坐摇椅的男人》中小丁把头一个月的工资拿来买了一只望远镜,在自家阁楼上偷窥晓雯的一举一动。小丁从小窥视晓雯父亲的一举一动,长大后变成晓雯父亲那样暴躁粗鲁的人。
将望远镜这一意象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是小说《天体悬浮》,小说前段望远镜在现实生活中用来观星。后半段小末和符启明分手后,望远镜从观星象的工具瞬间变为窥视的一种手段,这一转变源于符启明无意中透过望远镜看到了安志勇和他最爱的小末发生性关系。从此符启明不再抬头观察天体而是低下头去窥视小末和其他男人的生活。爱情的破碎让他的精神世界出现崩塌,复仇的欲望促使着他走上了死亡之路。正如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死”,死可以指一个过程,就好比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的边缘,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是走向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就是向死的过程。他一手成立的杞人忧天俱乐部,打着“观星象”的幌子继续着“卖肉”的非法勾当。他利用准备安乐死的绝症模特陷害安志勇。最后以故意伤害的罪名逮捕入狱。这种种举动他都成为了死亡之路的指路碑。
(二)释梦预示生命终结
《衣钵》《夏天糖》《坐轮椅的男人》以及《天体悬浮》都出现过梦这一元素。田耳把自己对“释梦”的爱好与本领,多次投射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
《夏天糖》中的顾崖,曾读过弗洛伊德,把《释梦》看了三遍。②顾崖不仅曾经训练自己把梦尽量详细地记录下来,还给涤青、铃兰都解过梦。顾崖以释梦为借口,试图寻找窥探铃兰内心的突破口。在各种细节的印证下,“我”(顾崖)确定了铃兰就是江标难以忘怀的女孩。后来他跟铃兰同居时做过一个梦,“在梦中,司机换成了我自己,车往前面开,路的中央有个小妹子躺着, 我想看却看不清楚……”③这个梦显示出顾崖在内心深处跟江标是相通的,江标在现实世界里用车轧死了铃兰,顾崖在梦中做出了类似的事情。释梦在这部小说既开导着人心,也迷惑着人心。涤青在顾崖的释梦后得到了解脱和释然,顾崖在给铃兰释梦后却做着江标的“梦”。
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传染病,江标记忆里有关童年铃兰的美好记忆在见到妓女铃兰后逐渐破灭,而江标内心那个困扰他数年的 “梦”却不停地在旁听者顾崖的脑海里上演。这是佴城的辐射效应,佴城里的每个人看似独立自由,却经历着同样的悲欢离合。
三、死而向生:田耳小说死亡书写中当代生命直寻
田耳小说里不存在一个绝对封闭,独守传统安逸的空间。就连佴城附近的小村庄 “鹭庄”也开始欺骗游客进村游玩赚取门票。《洞中人》隐藏在山洞里的耿多义也难以摆脱现实的干扰。《被猜死的人》将养老院也划入蔓延圈内,梁瞎子谎称能预测生死,并借此收取其他老人的礼金。《掰月亮砸人》里的叫花子小狗在吃人谣言的生发下的复仇心理导致他最后对田老稀的女儿桑女的尸体做出下流举动,这是变态心理也表明了对逼迫他的这一切的控诉。《氮肥厂》的两个底层人物只能靠性来互相安慰,最后的气柜爆炸让他们得到了解脱。不得不承认,透过田耳的小说几乎看不到乡村的宁静。
70年后的田耳目睹着物欲的追求占据着人生更多的空间,深刻感受到故乡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峡谷,每一个淳朴的乡民都躲不过城市风暴的席卷。这些所见所感挤掉了他对故乡一切的幻想。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何处是故乡?显然他再也无法重拾同乡前辈沈从文构建理想湘西的勇气了。既然找不到来时的路,归处又在何方呢?这也是田耳在内的70年代作家的思索。田耳就曾在《树我于无何有之乡》以樗树喻己,“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孤孤单单一株,无所依傍”。田耳在内的大部分70后作家也如同佴城中的人们那样有着漂泊之感。田耳选择死亡书写来抒发自我的孤独感。小说中多次提到的撰写悼词或碑文,或许也是一种自我影射。《洞中人》中才华横溢的耿多义以写悼词为生,《长寿碑》中热爱写作的戴占文谋生之计是给申请“长寿村”的岱城写长寿碑文。一些人的死亡给另一些人以生的希望。循环往复,死亡也便成为了一种新生。
田耳以平淡的日常化语言进行着死亡书写,不同的人们在他构建的佴城世界里上演着人生大戏。他从不加任何评论,只是拿着望远镜观察百态生活,侦探式地书写人们在变幻莫测环境下的困境。这样细致贴近的书写方式让人不由得心生害怕,佴城不就是人们正在生活的空间吗?大家何尝又不是佴城里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答案是肯定的,而作者将这样的感悟透过死亡传递给身处其中的人们。这也是对六十年前钱钟书著作《围城》的一种呼应。钱钟书也是在湘西完成了《围城》的布局和构思。时隔60年后,田耳重新捕捉到围城中人们的迷茫,甚至將其延伸到偏远的乡村里去。这是对理想故乡书写的一种冲击,也是一种直面生死的勇气。他借死亡书写指出了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精神世界的残败。
注释:
①田耳:《独证菩提》,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225页。
②田耳:《夏天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47页。
③田耳:《夏天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
参考文献:
[1]田耳.夏天糖[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2]田耳.洞中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
[3]田耳.长寿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4]田耳.蝉翼[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5]田耳.一个人的张灯结彩[M].北京:作家出版社.
[6]田耳.独证菩提[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7]田耳.衣钵[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8]田耳.金刚四拿[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9]田耳.姓田的树们[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
[10]海德格尔著,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社,2014.
[11]李敬泽.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田耳论[J],小说评论,2008,(05).
[12]徐则臣.“70后”作家的尴尬和优势[J].文学报,200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