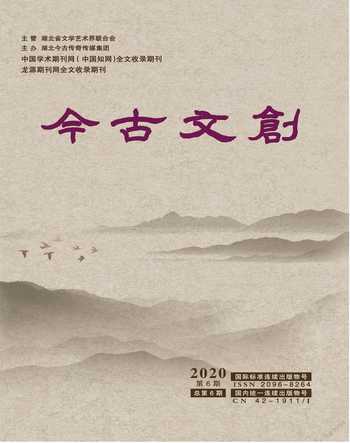试析春秋笔法在《桃花扇》中的体现
2020-09-10刘冰
刘冰
【摘要】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一个极具特色的显性话语,广泛存在于以伦理教化为旨归的古典戏曲、小说的创作及评点当中,历来颇受研究者瞩目。其“惩恶劝善”的褒贬大义与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选择、叙事策略及艺术构思等方面均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明清两代的文人戏曲当中,存在着大量借用春秋笔法进行创作的例子,孔尚任的《桃花扇》便是其中一个典型。春秋笔法在《桃花扇》中具体体现为笔削手段的灵活运用,冷峻客观的叙事态度以及篇章布局上的史家体例。
【关键词】《桃花扇》;春秋笔法;笔削手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6-0014-03
一、春秋笔法概念流变
春秋笔法经历了一个由经及史、由史及文的复杂流变过程,是一个经历代经学家、史学家不断开拓完善的概念范畴。由最初孔子开创的“一字定褒贬”的写作范例发展为左传、太史公之笔以及文学意义上的深文曲笔。春秋笔法的概念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观点一般写作《春秋》笔法,指孔子在编订《春秋》时所使用的那种“笔则笔”“削则削”,从中寄托“微言大义”的史家写作范例;广义的观点泛写作春秋笔法,指在一切叙事作品当中暗含褒贬,以一种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作者主观思想倾向的文学创作方法。既包括“直而不污”、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的一面。实际上,春秋笔法的流变过程,即是由狭义到广义的内涵扩大过程,如王基伦就在《〈春秋〉笔法的诠释与接受》一文中指出:“源自《春秋》经而来的‘《春秋》笔法’,原是我国自发性的经学名词,先后经由《左传》《孟子》《公羊传》《史记》乃至历代文学理论家的诠释之后,逐步迈入史书笔法及文学碑志传状写法的领域,成为很重要的文学观念。” 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及的《桃花扇》中的春秋笔法,主要是指广义上概念范畴。
二、春秋笔法在《桃花扇》中具体体现
(一)笔削手段的灵活运用
孔尚任虽然在《桃花扇·凡例》中标榜《桃花扇》对于史料处理的严谨:“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其地,全无假借。”但我们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比对可以发现,《桃花扇》中人事与史实之间出入之处颇多。梁启超在批注《桃花扇》的过程中,对其与史实相去甚远之处提出了批评,而我们认为,这些相去甚远之处正是春秋笔法中的一大特色——笔削手段造就的结果。正是有了笔削手段,作者才可以自由地对笔下人物进行腾挪转接,使得人物树立起来,更好地为褒贬大义而服务。所谓“笔削”手段,“笔”即指直录其事,秉笔直书;“削”即指“不录”,包括“隐而不书”“讳书其事”“改书其事”,指对写作材料进行有选择的删减。在《桃花扇》一剧中,孔尚任为了实现“惩恶劝善”的褒贬大义,运用笔削手段对重大历史关节事件以“书法不隐”的良史之笔进行了秉笔直书,并对部分历史人物进行了有选择的裁剪、嫁接。
1.对奸佞马士英人物形象的加工
为了收到惩创人心、使“乱臣贼子惧”的教化效果,孔尚任必须在剧本当中树立鲜明的忠奸对立派别,并且给忠臣一定的抬高褒奖,给奸臣必要的口诛笔伐。正所谓“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马士英便是作者精心结撰勾画的一个奸臣形象。《桃花扇》中的马士英祸国殃民、喜好奉承,跟阮大铖一道,构成了一对实打实的丑角形象。虽然历史上的奸臣马士英与《桃花扇》中所作所为大部分吻合,但为了加重马士英身上的奸臣色彩,孔尚任将原本诸多不属于马士英的劣迹加诸到了其身上。
马士英在《桃花扇》中为人诟病的一大过失为重用阉党余党阮大铖,两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加速了南明王朝的灭亡。而历史上马士英之所以在做了弘光朝首辅之后启用阮大铖,却是出于投桃报李的“报恩”目的。据史料记载,马士英在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正式开启了宦海生涯,在崇祯五年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但仅到任一个月便因挪用公款贿赂权贵事发被流放边疆,在赋闲期间,与因“魏忠贤逆案”被革职的阮大铖相交甚欢。后在东林党人、复社成员的活动周旋下,被罢相的周延儒得以复官,其中花费的银钱万两主要来自阮大铖的捐赠。阮大铖请求周延儒为己翻案不成转而举荐马士英,马士英得以成功复官。出于投桃报李的心态,马士英在弘光朝极力举荐了阮大铖,而上台后的阮大铖疯狂打击报复曾将自己打入“魏阉逆案”的东林士子,导致超纲混乱、民不聊生。《桃花扇》中将马、阮并成,共列阉党,而事实上,马士英并非阉党成员。阮大铖迫害清流的罪状,后人因“马、阮”并称而大多推到马士英身上,对于这一点,《明史》记载中也提道:“而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已居恶名,颇以为恨。”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记载,马士英对江南的一些复社成员,并没有抱有赶尽杀绝的敌对态度,反而启用了一些才干优渥之人。马士英曾言:“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尽管张溥为东林领袖,一手创办复社,但当时的东林诸子却大多忙着去周旋周延儒的官位,张溥的后事是由奸臣马士英一手操办、凭吊的。由此可知,历史上的马士英虽不能称得上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但也绝非十恶不赦之辈。关于其贿赂权贵一案,其中还颇有隐情。据《烈皇小识》记载:“宣府巡抚马士英,甫莅任,冒侵饷银六千两。镇守太监王坤疏发其事,士英逮问遣戍。例:巡抚到任,修候都门要津,侑以厚贿,赎缓不能猝至,則撮库中正额钱粮应用,而徐图偿补,此相沿陋习,各省各边皆然,不独一宣府也。士英莅任未几,一时不及抵偿,遂为王坤所纠。坤既以发奸为功,上亦心喜内臣之果能绝情面而剔积弊也,故凡言内臣者皆不听。”崇祯朝时期官场形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凡是巡抚到任都要给京城权贵送以丰厚的钱两,如果自己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钱,那就挪用公中钱两应用之款,之后再想办法慢慢偿还。结果内臣王坤出于邀功的目的告发了尚未来得及偿还钱两的马士英,导致上任仅一个月的马士英就这样被罢免了。
马士英在《桃花扇》中第二大罪状为与阮大铖一起迎立君德全亏、骄奢不堪的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桃花扇》第十四出《阻奸》当中写到马士英邀功心切,主动给史可法传书商议立福王之事,史可法原本犹豫不决,后听从侯方域“福王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论回绝了马士英的提议。但历史上的真实事实却是史可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与马士英一起迎立了福王。据侯方域《四忆堂诗集》卷五《哀辞九章·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扬诸军事史公可法》所写:“……福邸承大统,依次适允诺,应机争须臾,乃就马相度。坐失伦扉权,出建淮扬幕。进止频内请,秉钺威以消。”可知,在认为应当由福王继承大统这件事上,侯方域与史可法持有相同的看法,而史可法并没有争取时机第一时间拥立福王,而是主动去与马士英商议,导致马士英抢占先机夺得拥立之功。侯方域的友人贾开宗在注释中对该诗诗意做了阐释:“甲申燕京之变,公为南京兵部尚书,掌机务。时弘光以福邸当承大统,伦序无可易者。公以强藩在外,不即决,乃就凤阳总督马士英谋之,而拥立功尽归士英矣。”由此可知,迎立福王的罪责不应完全由马士英一人承担,孔尚任以“隐而不书”的春秋笔法抹去了忠臣史可法在迎立福王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此外,孔尚任对马士英言行改动较大的一处为其抗清而亡的结局。既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将马士英描绘得如此作恶多端死有余辜,那么就必须为其设计一个合适的结局以得到大快人心、惩恶劝善之目的,因而为马士英安排的结局是在台州山中被雷劈死,而事实上马士英却是在抗清失败之后英勇就义而亡。史学家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对此持公允论断:“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別。南京既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马、阮并称,诚士英之不幸。易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可为士英诵矣。”抗清名士黄伯端在临刑之前所说的“不降即贤”未免失之简单粗暴,但跟钱谦益等一众剃发易服投降清廷的前明大臣比起来,马士英毕竟没有失去一个明朝官员应有的节气。
2.对“有明三忠”之一左良玉的人物形象加工
左良玉是孔尚任精心刻画的一大忠臣,在《桃花扇》中一出场便是一位忠君爱国、威武英勇的将领形象:“七尺昂藏,虎头燕颌如画,莽男儿走遍天涯。活骑人,飞食肉,风云叱咤。报国恩,一腔热血挥洒。”但梁启超在《桃花扇》第九出《抚兵》的批注中,却以严厉的口吻指出《桃花扇》于左良玉袒护过甚。事实的确如此。历史上左良玉一大污点便是治军不严、军纪散乱,放纵部下烧杀抢掠,百姓深受其苦。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提到左良玉率军追击张献忠军队时“左兵二三万,一涌入城,城中无一家无兵者。淫污之状不可言。”普通百姓“不恨贼而恨兵”。对于这一点,清代著名文学家王士祯也有论断:“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做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爱及乌上之乌,爱及乌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携重宝贿左良玉时,甚至以“公所部多杀掠”来拉拢彼此的关系。由此可见左良玉军队军纪败坏可谓人所共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针对这些不利于左良玉形象塑造的史料非但采取“隐而不书”的方法,还对此多加讳饰。如在第十一出《投辕》中借柳敬亭之口为其辩白:“俺柳敬亭冲风冒雨,沿江行来,并不见乱兵抢粮,想是讹传了。”甚至在第三十一出《草檄》中营造左军军纪严明、无人敢喧哗的氛围,借唱曲艺人苏昆生之口说出:“今日江上大操,看他兵马过处,鸡犬无声,好不肃静。”苏昆省深夜唱曲还被店家打断:“客官安歇罢,万一元帅听得,连累小店,倒不是耍的。”
历史上左良玉另一大污点是引兵东下被认为有谋逆之心。对于这一点,《桃花扇》极力刻画左良玉就粮南京实属被饥兵胁迫,无可奈何之举。《桃花扇》第九出《抚兵》集中描绘了兵粮缺乏、人心浮躁的危机场面:“你听外面将士,益发鼓噪,好像要反的光景。”直到左良玉发出“就粮东去,安歇营马,驾楼船到燕子矶边耍”的承诺,这一危机才安全度过:“慰三军无别法,许就粮喧声才罢,谁知俺一片葵倾向日花。”紧接着孔尚任借两个士兵的对话暗示左良玉从此蒙上不白之冤,难免被人怀疑的无奈事实:“[副净向末]老哥,咱弟兄们商量,天下强兵勇将,就扯起黄旗,往北京进取,有何不可![末摇手介]我们左爷爷忠义之人,这样风话,且不要题。依着我说,还是移家就粮,且吃饱饭为秒。[副净]你还不知,一移南京,人心慌张,就不取北京,这个恶名也免不得了。”孔尚任对左良玉袒护之心可见一斑。
(二)篇章布局上的史家体例
孔尚任在《试一出 先声》里借老赞礼之口说出:“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直接把一部《桃花扇》传奇当作《春秋》来看待。事实上,《桃花扇》的确突破了传奇体制,没有按照常规的传奇框架进行结构,而是在篇章布局上借鉴了史家体例。
首先,是记事体例上对编年体的仿照。《春秋》为记史首先开创了编年体体例,叙事严格依从年、季、月、日的时间顺序。《桃花扇》在每一出开头均模仿《春秋》按照时间先后注明年月,如在第三出《哄丁》下标明癸未三月,第八出《闹榭》下标明癸未五月,使其整部书的结构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史书而非普通的传奇。每一出结尾处的四句七言诗跳出剧情进行总结,又极类似《史记》的“太史公曰”。
其次,是人物群像的宏观展现。史家记史永远是着色分明、均衡用力地,不可能集中所有笔墨浓墨重彩地去突出刻画某一个英雄人物,在人物形象展现上具有群像性特征。《桃花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同样具备史家的群像性特征。纵览全书,描写主人公侯方域、李香君离合之情的为第二出《传歌》、第五出《访翠》、第六出《眠香》、第七出《却奁》、第十七出《拒媒》、第二十二出《守楼》、第二十三出《寄扇》、第二十四出《骂筵》、第二十五出《选优》、第二十八出《题画》、第四十出《入道》,所占戏份与代表兴亡之感的史可法、左良玉等人戏份差之不远,诸多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呈现方式上具有接踵而来、设色均匀的史家群像特征。
(三)冷峻客观的叙事态度
虽然《桃花扇》一剧有着鲜明的忠奸对立,但作者对人物的呈现始终采取了一种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作者的主观好恶态度隐于文后,行文用笔做到了“不动声色”。作者只负责客观呈现不负责表达爱憎,觀众只能凭借剧中人物的言谈与行动对人物的道德品格做出个人判断。孔尚任对客观叙事有着极为强烈的自觉意识,早在开篇的《试一出 先声》里便将自己与叙述者进行了隔离。孔尚任先是借老赞礼之口说出:“昨在太平园中,看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营造出一种《桃花扇》已经先于叙事者存在的假象,紧接着又将叙事的权利赋予老赞礼:“今日冠裳雅会,就要演这本传奇,你老既是旧人,又且听过新曲,何不把传奇始末,预先铺叙一番,大家洗耳?”从而大大疏远了自己与叙事者的关系,使得故事的演绎更少作者感情的直接流露,而以一种更为冷静客观的旁观者视角缓缓铺展开来。
其次,《桃花扇》大量采用了限知视角进行叙事。譬如第十出《修札》 杨龙友惊慌失措地向侯方域传递消息:“兄还不知道吗?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抢南京,且有窥伺北京之意。本兵熊明遇束手无策,故此托弟前来,恳求妙计。”作为观众的我们因为看过左良玉“谁知俺一片葵倾向日花”的内心剖白,所以明白杨龙友之说为讹传,但身处故事当中的杨龙友根据自身见闻所得出的判断却是左良玉要谋反。作者就这样将自己深隐于文后,让人物自己讲话自己判断,完全淡化了作者的存在感,从而使叙事态度达到真正的冷静客观。
三、结语
《桃花扇》作为中国戏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跟情致浪漫、一往而深的《牡丹亭》《长生殿》相比,呈现出了迥异的艺术特色。其较少虚幻色彩,叙事视角聚焦于发生不久的现实人生,有着其他同样优秀的戏曲作品所不具备的深广的思想与察补时弊的救世情怀。而这一切,跟作者对春秋笔法的娴熟使用多少脱不开干系。厘清春秋笔法在《桃花扇》中的具体体现,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桃花扇》主题思想、透视孔尚任写作壸奥,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王基伦:《“〈春秋〉笔法”的诠释与接受》,孔学研究,2005年,第00期。
参考文献:
[1][清]孔尚任著,李保民校点.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陈才训.“春秋笔法”对古典小说审美接受的影响[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