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义人:一个日本婴儿的乳名及其隐喻
2020-08-20
日本四国岛松山地区的大濑村是个不大的小山村,位于内子町之东,石锤山西南,为重峦叠嶂所围拥。这个峡谷中的小山村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与穿村而过的小田川大致平行。由于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为群山所遮掩,盆地里的小村庄看似被山峦和森林完全封闭,呈口小腹大的瓮形。1935年1月31日,一个小生命就在这个村子里的大江家呱呱坠地,其曾外祖父随即为襁褓中的婴儿取了“古义人”这个含有深意的乳名。
所谓“古义人”之“古义”,缘起于日本江户中期古学派大儒伊藤仁斋(1627—1705)的居所兼授学之所“古义堂”。在位于京都堀川岸边的那所小院里,伊藤仁斋写出了其后成为伊藤仁斋学系重要典籍的《论语古义》《孟子古义》和《语孟字义》等论著,继而与其子伊藤东涯共同创建了名震后世的堀川学派,拥有弟子达3000 余人。这位古学派大儒(或曰堀川派创始人)肯定不会想到,《孟子古义》等典籍及其奥义,将经由自己学系的后人,传给一个乳名为“古义人”的那个婴儿——59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并被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观和伦理观,成为静静流淌于其文学作品里的一股强韧底流。而“古义人”这个儿时的乳名,则不时以“义”“义兄”“古义”以及“古义人”等人物命名,不断出现在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信》(1987)、《燃烧的绿树》(三部曲)(1993-1995)和“奇怪的二人组合”六部曲(2000-2013)等诸多小说作品中。譬如在长篇小说《别了,我的书!》开篇第一句里,大江健三郎开门见山地表示:“虽说已经步入老年,可长江古义人还是因暴力原因身负重伤后第一次住进了医院。”[1]为了更好地暗示读者,大江特意在日文原版第一行为“長江古義人”这几个日语汉字加了旁注“ちょうこうこぎと”。这里的“ちょうこう”是固有名词,指涉中国的“长江”,而“こぎと”,则是“古義人”的音读,在日语中与“古義堂”谐音,这就清晰地告诉读者,自己经由曾外祖父和古义堂所接受的民本思想,其源头在于长江所象征的中国。关于“古义人”这个名字的缘起,大江本人曾在《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里如此回忆:
古义人的名字中,就融汇了这个学派的宗师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我从阿婆那里只听说,曾外祖父曾在下游的大藩洲教过学问。他处于汉学者的最基层,值得一提的是,他好像属于伊藤仁斋的谱系,因为父亲也很珍惜《论语古义》以及《孟子古义》等书,我也不由得喜欢上了“古义”这个词语,此后便有了“奇怪的二人组合”这三部曲[2]中的Kogi[3],也就是古义这么一个与身为作者的我多有重复的人物的名字。[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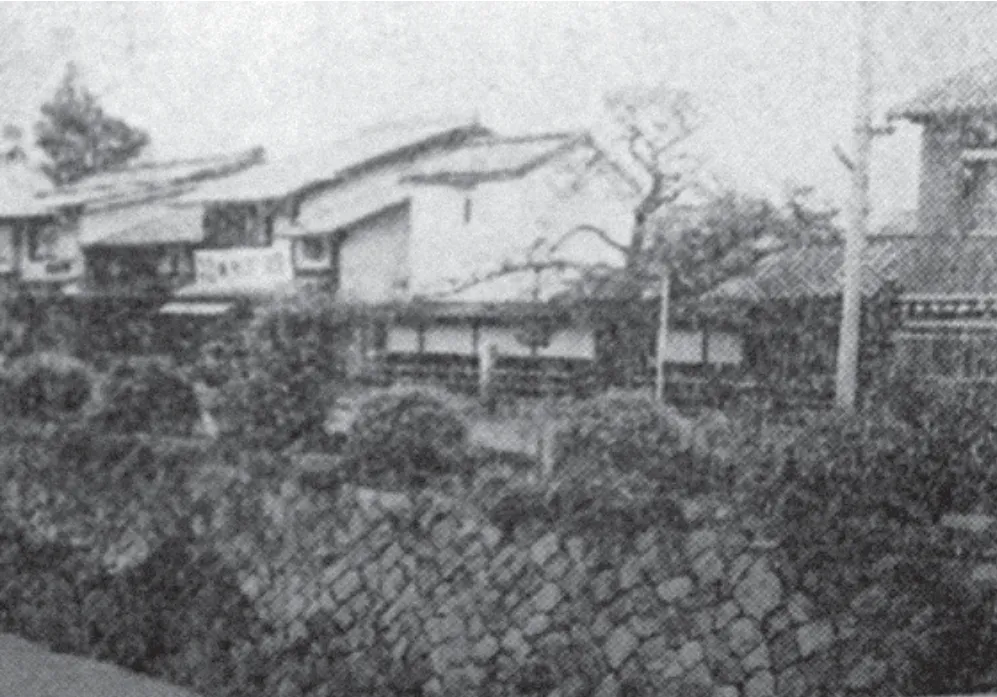
古义堂旧照(堀川岸上右侧低矮房屋)

古义堂石碑
“古义”这个词所承载的民本思想,连同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思想以及经大江本人丰富和完善过后的人文主义思想一道,浑然形成大江健三郎之宏大博深且独具特色的文艺思想。
由莫言引发的思考和回溯
大江的曾外祖父与孟子学说结下的不解之缘,要从其家族所从事的造纸业说起。大江的故乡大濑村所在地区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和林业支撑,历史上曾是全国木蜡的主要产地,这里还生产利用树林中的黄瑞香树皮制作的纸浆,用以生产优质和纸。日本学者黑古一夫曾多次前往此地作田野调查,他认为:“江户时代的大江家以武士身份采购山中特产,到了明治仍然继承祖业从事造纸业。”[5]其实,大江家作为批发商除了收购山中的柿干等山货外,从江户时代传承下来的造纸业才是其主业,从山民手中收集黄瑞香树皮并在河水中浸泡过后,将从中撕下的真皮加工为特殊纸浆,再向内阁造币局提供这种特殊纸浆以供其制造纸币。当时,日本全国仅有几家作坊能够生产这种特殊纸浆原料。战后,由于货币用纸发生了变化,便不再使用这种纸浆原料。
为了更好地经营祖传产业,大江的曾外祖父年轻时曾前往大阪,在古学派大儒伊藤仁斋学系开办的学堂里研习儒学,更准确地说,是研习孟子的相关学说,尤其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和易姓革命思想。2008年2月21日午后,在东京都郊外小田急沿线的成城宅邸里,大江健三郎对来自中国的作家莫言这样解释曾外祖父专程学习儒学的原委:

伊藤仁斋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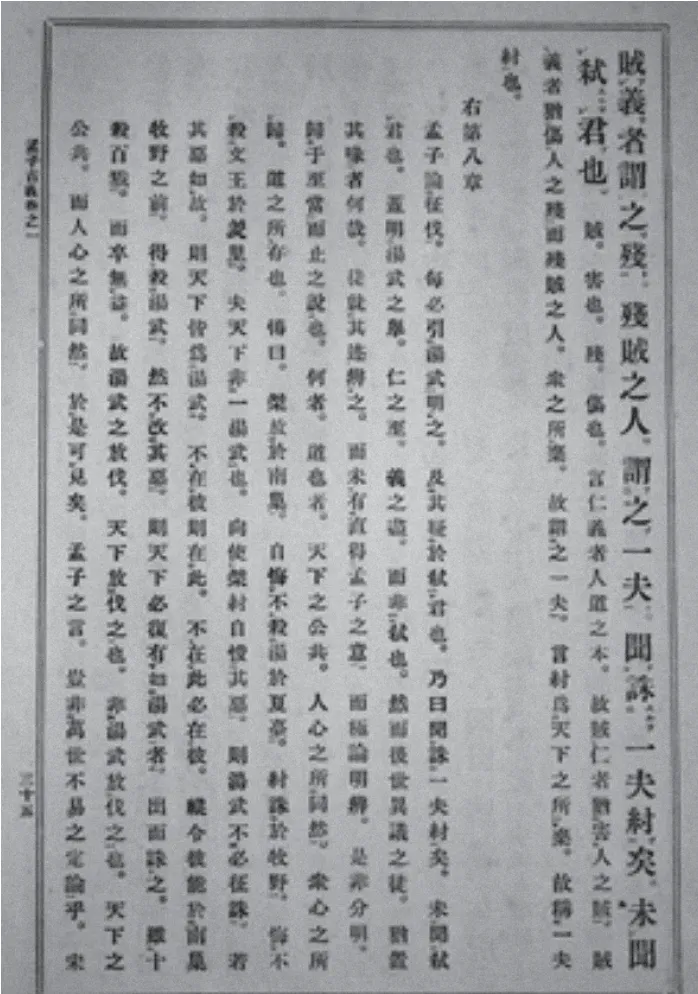
伊藤仁斋著《孟子古义》
曾外祖父年轻时曾在大阪的新兴商人间开办的私塾里学习孟子的相关学说。在当时的日本,普遍认为孔子的《论语》有利于天皇制,因而比较欢迎《论语》,同时认为孟子学说中含有反天皇制的因素,便对孟子及其学说持反对态度。不过也有个例外,那就是江户时期的儒学家伊藤仁斋对孟子持肯定态度,认为后世诸家大多根据当时的统治阶层利益来阐释儒学,比如朱子学也是如此,这就越来越背离了儒学的真义,所以需要回到原典中去寻找古义,想要以此为据,用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还写了一本题为《孟子古义》的研究类专著。相较于宣扬孔子及其《论语》的私塾古义堂所授教材《论语古义》,曾外祖父选择了《孟子古义》的学术观点,并将这些观点传给了儿时的我。早在孩童时代,我就觉得《孟子古义》中的“古义”是个好词,就接受了“古义”这个词语。[6]

2008年2月21日午后,大江健三郎与莫言(许金龙摄)
在被问及“你的曾外祖父是个商人,为什么要去学习儒学”时,大江则这样对他的老朋友莫言解释道:
当时的日本商人都认为,经商是为得利,而若想得利,首先便要有义。若是不能义字当头,即便获利,也不会长久。本着这个义利观,曾外祖父就专程前去学习儒学中的“义”,却不料被儒学的博大精深所深深震撼,更是与《孟子古义》中有关易姓革命的理论产生共鸣,在学习结束后,就带着据说是伊藤仁斋手书的“義”字挂轴回到家乡,却不再经商,而是在村里挂上那个“義”字挂轴,就在那挂轴下教授村里人学习儒学。再后来,就去邻近的大洲藩教授儒学去了。
莫言的提问引发出大江对自身家学渊源的长期关注,那次访谈结束后,或许是认为自己未能向莫言透彻地解释古学派的义利观,两年后的2010年3月,大江在刊于《朝日新闻》的文章里,引用了三宅石庵[7]在怀德堂发表的讲义:
所谓利,是人的合理之判断,无外乎“正义”——义——的认识论之延长。实际上,商人绝不应考虑利用彼等职业追求利益,而应考虑从“义”这种道德原理出发之伦理性活动。义在客观世界中被转为行动之际,利无须努力追求亦不为欲望所乱便会“自然”呈现。“利者,纵然不使刻意相求,利亦将如影随形也。”[8]
这显然是日本近世儒学教育家对《易经》中“利者,义之和也”的解读,典出于《易经》“乾之四德”中“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亦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我们也可以将孟子向梁惠王所作谏言,理解为孟子学说在《易经》义利观的基础上所作的寓言式诠释。
大江对“古义”的再阐释
时隔大约一年半后的2009年10月6日,在第二届“国际视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大江对莫言、朱天文、陈众议、小森阳一、彭小妍等中日两国作家和学者更为详尽地讲述了曾外祖父学习儒学的背景:
……我在孩童时代有个名为“古义人”的乳名。我的曾外祖父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伊藤仁斋作为研究日本近世的中国哲学的学者而广为人知,他运用中国古典的正统解读法,写了“古义”(系列)的论著,准确地说,是《论语古义》和《孟子古义》等论著。
江户时代,有着基于近世的领导人和政治家的中国哲学意识形态。日本一直存在来自中国朱子的朱子学传统,及至日本近世,就出现了两个不同于朱子学的、对于古典的理解。其一,是作为学者而出现的、著名的荻生徂徕这个人物,他主张把中国哲学真正视作古老的文本,遵循文本的本义进行解读。他的这种解读就成了武士和知识阶层的哲学,当德川幕府封建体制崩溃、发生明治维新的革命之际,就成了赋予日本知识分子力量的思想来源之一。……不过在这同一时期,另有一个对民众传授中国哲学的人,传授与政府的、权力方的解读相悖的中国哲学的人,此人就是伊藤仁斋。我的曾外祖父学习了这种中国哲学,便在自己的房间里挂起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字幅,那上面有了不起的大人物手书的“義”字。曾外祖父将其悬挂起来,就在那下面教授我们那里的人学习中国哲学。曾外祖父说,这么大的字幅,是伊藤仁斋亲手所书。于是,临去东京之际,我便将其偷了出来,存放在我的房间里。曾外祖父就说了:“大江,给你二百日元,我赎回来吧……”[9]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大江所说的、在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之下,孔子与孟子学说在日本社会受容与传承的际遇迥然相异——“普遍认为孔子的《论语》有利于天皇制,因而比较欢迎《论语》,同时认为孟子学说中含有反天皇制的因素,便对孟子及其学说持反对态度。”以此观照孔孟学说东传日本的历史,孔子学说在圣德太子时期便奠定了儒家正统的地位,演变为天皇制伦理的法理基础。而孟子学说,则由于民贵君轻的基本政治伦理天然违背了天皇制自上而下的尊卑观,从而成为东传日本之儒教的异端。这种尊孔抑孟的主流意识形态,直至伊藤仁斋的出现,才得到反思和受到批判。

荻生徂徕肖像
不受历代天皇待见的孟子及其学说
《论语》早在3世纪后半叶就开始传往日本。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由于阿直歧的推荐,率治工、酿酒人、吴服师赴日,并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就是汉文字流入日本之始。其后继体天皇时,百济五经[10]博士段杨尔(513)、高丽五经博士高安茂(516)、南梁人司马达(522)相继赴日。又钦明天皇时(554),五经博士王柳贵、易经博士王道良等赴日,这可以说是以儒教为中心之学术文化流入日本之始”[11]。如果说,这大约300年间的儒学传入是时断时续涓涓细流的话,那么,到了7世纪,即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的推古天皇时期,这涓涓细流就成了奔腾于日本本土文化这个河床中的汹涌洪流,广泛而持久地滋润着干涸的本土文化。在这个时期,有史可考的日本第一位女天皇炊屋姬,也就是推古天皇,为了抗衡把持朝政的权臣苏我马子,故而册封自己的侄子、已故用明天皇的儿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便是后世盛传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对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则不断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借以如饥似渴地吸收和消化来自中国的先进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从中国大量引入的儒学和佛教文化。圣德太子更是学以致用,很快便基于儒佛文化亲自拟就并于604年颁布了旨在对官吏进行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该《宪法》除第二条之“笃信三宝”和第十条之“绝忿弃嗔”取自佛教经典外,其余各条尽皆出自儒学经典和子史典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朱谦之老先生曾对此做过清晰的梳理:
第一条“以和为贵”本《礼记·儒行》及《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上和下睦”本《左传》成公十六年“上下和睦”与《孝经》“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第三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本《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与《管子》;“天覆地载”本《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四时顺行”本《易·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上行下靡”本《说苑》。第四条“上不礼而下非齐”本《韩诗外传》及《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第五条“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本《文选》李萧远《运命论》“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第六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本《礼记·礼运》“君仁臣忠”;“惩恶劝善”本《左传》成公十四年。第七条“人各有任,掌宜不滥,其贤哲任官”,本《尚书·咸有一德》之“任官惟贤材”;“克念作圣”本《尚书·多方》。第八条“公事靡监”本《诗经唐风鸨羽》,《鹿鸣四牡》之“王事靡监”。第九条“信是义本”本《论语》“信近于义”。第十条“彼是则我非”本《庄子》;“如环之无端”本《史记·田单列传》。第十二条“国靡二君,民无两主”,本《礼记·坊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及《孟子》。第十五条“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本《韩非子·五蠹篇》“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与《左传》文公六年“以私害公非忠也”;“千载以难待一圣”本《文选·三国名臣传序》。第十六条“使民以时,古之良典”本《论语·学而篇》“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2]
由此可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论语》和五经都对《十七条宪法》带来巨大影响,从而为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做了前期准备。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部宪法引入《论语》者有四,而引入《孟子》者则为一。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引入中国儒学的初期阶段,或许是对于孟子有关易姓革命的民本思想不甚了解,在《宪法》中的参考和引用大大少于孔子的《论语》,但圣德太子还是对孟子表示出了敬意。
圣德太子去世后,孝德天皇在大化二年(646)颁布《改新之诏》,史称大化改新,提出“公地公民制”,将皇族和大贵族的土地收归天皇所有,“确立天皇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及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儒学的天命观及与之相联的符瑞思想成为革新的重要理论基点”[13],由此正式成立中央集权国家,并将大和之国名更改为日本国。
随着神话传说故事《古事记》(712)和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720)的问世,日本历代天皇越发强调皇权天授、万世一系,及至明治维新后由伊藤博文起草并实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更是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尊崇,以法律形式确认天皇秉承皇祖皇宗“天壤无穷之宏谟”的神意,继承“国家统治大权”的上谕,其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被赋予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之地位[14],集统治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于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主权在民、人民福祉才是政治活动之最大目的等孟子的政治主张,便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历代统治阶层的利益发生了猛烈碰撞。至于孟子所提“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易姓革命的政治主张,更是为日本历代统治阶层所不容,不但代表皇室利益的“公家”不容,即便是代表幕府利益的武家也绝不能接受。于是,在孔子自被奈良朝奉为“文宣王”(768)并享有王者至尊的一千余年间,孟子非但不能享受亚圣的荣光,就连其著述《孟子》也不得输入日本,致使坊间四处流传,不可将《孟子》由唐土带回日本,否则将会在回航途中遭遇海难……这大概就是大江健三郎对莫言所说的“普遍认为孔子的《论语》有利于天皇制,因而比较欢迎《论语》,同时认为孟子学说中含有反天皇制的因素,便对孟子及其学说持反对态度”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了吧。
以民意代天意的民本思想
这种尊孔抑孟的现象到了幕府时代也没有任何改变。进入幕府时代之后,“作为军事独裁政权的幕府政权一直提倡武士道及尚武精神,而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武士道形成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利用儒学阐释武士道,汲取了儒学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依其统治利益所需改造儒学,冀以充实武士道”[15]。尤其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出于加强思想统治、维护并发展幕府政治、经济制度的需要,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由佛儒并用转向独尊儒家思想学说,把儒学定为官学,同时强行禁止‘异学’。……倡‘大义名分’,把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16]。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依其统治利益所需改造儒学,翼以充实武士道”;二是“把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前者是说幕府根据其统治利益所需而任意“改造”儒学,用以“充实武士道”;后者则表明被幕府选中的、可供其“改造”的儒学或曰官学,便是“把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了。由此可见,经过种种“改造”的这种所谓儒学,就只能是遭到严重篡改的“儒学”,为统治阶层的伦理纲常保驾护航的“儒学”了。这种“儒学”,便是大江口中的“来自中国朱子的朱子学”,也就是被权力中心所指定的官学。为了对抗这种官学,“及至日本近世,就出现了两个不同于朱子学的、对于古典的理解。……有一个对民众教授中国哲学的人,教授与政府的、权力方的解读相悖的中国哲学的人,此人就是伊藤仁斋”[17]。
大江在这里提及的伊藤仁斋是江户时期古学派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学者,而伊藤仁斋所在的“古学派是日本儒学的重要派别,也是官学朱子学的反对派。古学派学者认为只有古代儒学才具有真义,汉唐以后的儒学全是伪说。他们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以古典经典为依据,冀从古典中寻找作用于社会的智慧源泉,重新构建不同于朱子学、阳明学的思想体系,实际是希望以复古的名义打破当时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古学派的先导者是山鹿素行,另外两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分别为堀川学派的伊藤仁斋、园学派的荻生徂徕。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具有共同的特点,政治上代表被闲置的贵族及中小地主阶级等在野的民间势力”[18]。这里说的是在德川时代中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民附属于大小藩主,而这大大小小的藩主又附属于大名,各大名则附属于“大将军”德川幕府。随着幕藩体制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开始出现危机,其封建体制开始瓦解,近代思想也从中逐渐萌发并发展起来,就这个意义而言,与朱子学对抗的古义学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尤其在享保年间,当时日本全国的农村经济因商业高利资本的侵入而衰落,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震撼着德川幕府封建统治基础,这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的朱子学带来沉重打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初奉宋儒,……及年三十七八始出己见”的伊藤仁斋叛出朱子学,转而在《论语》和《孟子》等古典中寻找真义,认同孟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以民代天、以民意代天意的民本思想,主张以仁义为王道,所以仁者之上位,虽说是天授,其实更是人归。对于失去民心民意、引发天怒人怨的残暴之君,则认为其已被以民意为象征的天道所抛弃,从而可以对其放伐。

古学派的先导者山鹿素行
以革命颠覆不义的理想主义呼声
在详细阐释孟子的放伐理论时,伊藤仁斋更是在《孟子古义》里缜密地为孟子如此辩护道:
孟子论征伐,每必引汤、武明之。及其疑于弑君者,乃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盖明汤、武之举,仁之至,义之尽,而非弑也。……何者?道也者,天下之公共,人心之所同然,众心之所归,道之所存也。传曰:桀放于南巢。自悔不杀汤于夏台;纣诛于牧野,悔不杀文王于羑里。夫天下非一汤、武也,向使桀、纣日悛其恶,则汤、武不必征诛,若其恶如故,则天下皆为汤、武,不在彼则在此,不在此必在彼。纵令彼能于南巢牧野之前,得杀汤、武,然不改其恶,则天下复必有如汤、武者,出而诛之,虽十杀百戮,而卒无益。故汤、武之放伐,天下放伐之也,非汤、武放伐之也。天下之公共,人心之所同然,于是可见矣。孟子之言,岂非万世不变之定论乎?宋儒以汤、武放伐为权,亦非也。天下之同然之谓道,一时之从宜之谓权。汤、武放伐,即道也,不可谓之权也。[19]
在当时看来,伊藤的宣言是何等的大胆。如果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易姓革命早已屡见不鲜,素有改朝换代之说的话,那么在日本这个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的国度里,伊藤仁斋的以上话语可谓大逆不道了。所谓弑君,用日语表述便是“下克上”,明显包括“犯上作乱”和“以下犯上”等道德和伦理层面的指责,但是伊藤仁斋在纣王被杀这件事上,却全然不作这种语义上的认可,倒是完全依孟子所言,认为武王伐纣是诛杀贼仁贼义之独夫而非弑君,可作为正义行为予以认可和鼓励,因为“夫天下非一汤、武也,向使桀、纣日悛其恶,则汤、武不必征诛,若其恶如故,则天下皆为汤、武”,更是强调汤、武放伐是天下之同然的“道也”,而不是宋儒(或曰维护幕府等级制度的朱子学)所批评的从宜之“权变”。
伊藤仁斋笔下的“道”,其后被暴动之乡的年轻商人所接受、所宣传、所传承,并取其宗师伊藤仁斋居所兼私塾的古义堂之“古义”二字,为自己的曾外孙命名为“古义人”。这个乳名为“古义人”的孩子多年后在作品里借小说人物之口讲述了这个乳名的背景:“宴会即将结束时,大黄突然说起古义人这个名字的由来。当然,这是以笛卡尔的西欧思想为原点的,然而并不仅仅如此。在与大阪——当时的大阪——有着贸易往来关系的这块土地上,不少人曾前往商人们学习儒学的学校怀德堂。古义人的名字中,就融汇了这个学派的宗师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20]至于伊藤仁斋在上文中提及汤、武放伐时所认定并高度评价的“道”,时隔大约400年之后,大江在另一部小说里作出了这样的回应:
关于武装暴动的原因,那位与我有书信往来的老教员乡土史家,既未否定亦未积极肯定我母亲的意见。他具有科学态度,强调在万延元年前后,不仅本领地内,即使整个爱媛县内也发生了各类武装暴动,这些力量和方向综合在一起的矢量指向维新。他认为本藩唯一的特殊之处,就是万延元年前十余年,藩主担任寺院和神社的临时执行官,使本藩的经济发生了倾斜。此后,本藩向领地城镇人口征收所谓“万人讲”日钱,向农民征收预付米,接着是“追加预付米”。乡土史家在信末引用了一节他收集的资料:“夫阴穷则阳复,阳穷则阴生,天地循环,万物流转。人乃万物之灵长,若治政失宜,民穷之时,岂不生变乎!”这革命启蒙主义中有一股力量。[21]
在这里,大江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人乃万物之灵长,若治政失宜,民穷之时,岂不生变乎”,其以革命颠覆不义的理想主义呼声,显然来自《孟子·梁惠王下》的相关内容及其受日本的传承者伊藤仁斋的影响。不仅如此,大江还把以上经其改写的话语定义为“革命的启蒙主义”,而且特意指出其中蕴藏着“一股力量”。更具体地说,这既是对孟子“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2]等易姓革命主张的认同,也是借伊藤仁斋对此所作的解读而赋予故乡暴动历史以正当性和合理性,让所有暴动者及其同情者据此获得伦理上的支撑——“夫天下非一汤、武也,向使桀、纣日悛其恶,则汤、武不必征诛,若其恶如故,则天下皆为汤、武。”显然,故乡的历史暴动史实与先祖传播的孟子有关“民本”和“革命”思想融汇在了一起,森林中的农民暴动叙事所体现的朴素村落政治观和斗争史,恰恰是“民本”古义和“革命”的现代左翼思潮相结合的表现,更是大江健三郎在未来的人生中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
注释:
[1]【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奇怪的二人配(下)别了,我的书!》,译林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页。
[2]在写作《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时,已发表同以长江古义人为主人公的《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这三部长篇小说,后三部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水死》和《晚年样式集》尚未创作和发表,故有“三部曲”之说。
[3]Kogi 为“古义”的日语读音。
[4]【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第10页。
[5]【日】黑古一夫著,翁家慧译:《大江健三郎传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2页。
[6]根据2008年2月21日下午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对谈现场所录文字整理而成。
[7]【日】三宅石庵(1665—1730),日本江户中期的儒学家,曾任怀德堂第一任堂主。
[8]【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定义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第280页。
[9][17]根据会议录音整理而成的资料。
[10]五经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这五部典籍,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为古老的文献,也是我国古代儒家的主要经典。
[11][12]朱谦之著:《日本的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页、5—6页。
[13][15][16][18]刘宗贤、蔡德贵主编:《当代东方儒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5页、156页、157页、164页。
[14]参阅收录于《日本国宪法》之《大日本帝国宪法》,讲谈社学术文库2201,第61—77页。
[19【]日】伊藤仁斋著:《孟子古义》卷一,第35页。
[20]【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奇怪的二人配(上)被偷换的孩子》,译林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09页。
[21]【日】大江健三郎著,邱雅芬译:《万延元年的Football》,作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84页。
[22]《孟子·梁惠王下·2》引自【日】伊藤仁斋著:《孟子古义》第34-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