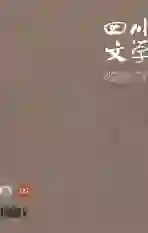“是真佛只说家常”
2020-08-10邵丽
邵丽
第一次读到托宾,是在王安忆老师编选的世界短篇小说精选《短经典》里。读过之后我就给忘记了,平淡,甚至可以说有点太淡。如果不在一字一句间目不转睛地细细品味,你简直不知道他在作品里想表达什么。
后来我在写作与父亲的一段旧事的时候,托宾《一减一》里结尾的一段话突然蹦到我的脑海里:“我明白这些年来我拖延太过。我在黑暗的城市中簇新的床铺上沉入睡眠时,知道现在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我得跟你说,我醒来后一段时间里,这几乎令我感到宽慰。”
从六七岁起我与父亲有了隔阂,几十年里我们都不曾化解,甚至从来没有拉过一下手。他快去世的时候,我匆匆忙忙赶回家。他已经咽气了。当时我确实很痛苦,但咀嚼痛苦的结果却是感到了某种轻松——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已死,我们之间的冷战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他的死,反而化解了很多宿怨,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是真佛只说家常”,世间的人情物理莫不如此。托宾好似随口说出的异常平淡的东西,我们也都司空见惯,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咀嚼的。他总是用淡淡的一句话,便能说出蕴藏在我们思想深处、总想表达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的那种亲人、朋友之间的疏离和隔膜。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和弟弟卡瑟尔寄居在阿姨家里,“阿姨用她自己漫不经心的方式对待我们”,“没人听我们说话,看见我们也不笑,无论是我们中的哪个”,好像他们不存在似的。作为他们的母亲,“一次都没联系过我们,一次都没有。没有来信、电话,也没来探视。我们不知道要被扔在那里多久。后来那些年里,母亲从未解释过她为何没来消息,我们也从未问过她在那几个月里是否曾想过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感受。”因而,这种手足之间因为大意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疏离,终于成为一种习惯,毕竟“这应该不算什么,因为毫无含义,恰如一减一等于零。”
对亲人的疏离和防备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终于还是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以至于在他们的思想上包裹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弟弟和我学会不要相信任何人。我们那时候学会不要谈论对我们重要的事情,我们执泥于此,终身怀抱这份坚定顽固的骄傲,仿佛这是一项技艺。”
这是心平气和的叙述,也是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在大人的忽视里,孩子默不作声地长大了。而童年结在心头孤独的痂,永远都不会痊愈,改变它们的只有死亡:“我们又陪她待了一会儿,然后他们请我们离开,我们逐一抚摸她的额头,走出房间,关上门。我们走过走廊,在我们的余生,呼吸仿佛都会带着她最后的痕迹、最终的挣扎,仿佛我们自身在世上的存在已被我们看到的事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四。”
成长如蜕。对亲人情感的咀嚼和反思,最终会反映为对故乡的眷恋,也许那是我们最后从肉体到精神的归集之地。曾几何时,“我不信上帝……我连爱尔兰都不信,”但当他在机场遇到故人,得到额外帮助的时候,过去的一切终于又回来了:“我想到了上帝和爱尔兰。”
很多时候,托宾的小说读起来很像没头没尾,中间也不涉及所谓传统小说的“起承转合”。但只要沉浸到他在小说中营造的那种氛围里去之后,你才会发现在平静的生活表面之下,其实波涛汹涌,千头万绪。他的作品有一种生发的力量,只要你反复阅读,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体验。所以也有评论者认为,托宾的小说要读到十遍以上才能入其堂奥——我在写这篇评论之前,确确实实读了十几遍之多,然而还是有意境纷披、言犹未尽之感。
如果不知道托宾是个同性恋者这么一个前提,你很可能不能明白文中的“你”到底是谁。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一直迷惑,以为是打错字了。通过查阅资料才知道,他年轻时就公开过自己的同性恋取向,所以他说自己不相信上帝是其来有自的,毕竟爱尔兰曾经是最为保守的天主教国家之一,直到2015年同性婚姻才合法化,较其他欧洲国家晚很多。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我们才会知道“你”到底是谁,也会明白在这部不足万字的作品里,蕴含了多大的信息量。它不仅关乎亲情、乡情,也关乎爱情。这种爱情是不能完全公开的,在他本已疏离的亲情之外,还有一份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守护的爱情,他心里的隐忍和孤独,需要怎样的克制和挣扎?“我知道快吃完时,我母亲有位全都看在眼里的朋友,走过来看了看你,小声对我说我朋友来了,这可真好。她加重了‘朋友这个词的语调,口气温和暧昧。我没告诉她,她看到的已经结束,已成往事。我只说是啊,你来了真好。你知道,当我不停说笑闲聊,不把话直说时,你是唯一恼怒摇头的人。从来没人像你这样在意这事。只有你总是要我说真话。此刻我正朝我的租房走去,我知道,如果我打电话对你说,在今晚这陌生的街头,痛苦的过去带着猛烈的力量又回到我身边,你会说你并不惊讶。你只会奇怪为何六年后才来。”
读到这里的六年,你也才开始明白开头所说的“我母亲已逝世六周年,爱尔兰距此时差六小时”的“六”是什么意思。
托宾的表达方式十分隐忍和节俭,很多时候,甚至吝啬到了几乎多一个字都不愿意说的地步。这种大幅度的留白,只能靠读者的想象去填补,这也恰恰是他的写作魅力之所在。比如这一段:“星期五早晨,护士问我是否觉得她很痛苦,我说是的。如果我此刻坚持的话,我肯定她能得到吗啡和一间私人病房。我没有征询他人意见,觉得他们会同意的。我没有对护士提到吗啡,但我知道她很聪明,从她瞧我的眼神,我看出说话间她知道我明白吗啡的功效,这能让我母亲舒舒坦坦地睡过去,舒舒坦坦地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呼吸会一来一回,一浅一深,脉搏会弱下去,呼吸会停一下,然后再次一来一回。”
紧接着,小说便写道:“在私人病房中,那天夜里,呼吸一直一来一回,然后好像一起停了。”
这场事先预谋的“安乐死”,简直说得风轻云淡,不着痕迹。如果不是反复看多遍,很难知道其中曾经发生了什么。
浓缩在八千多字里的短篇小说《一减一》,讲述的本是“我”回愛尔兰参加母亲葬礼的普通故事,但这个故事却是对“你”说的。因此,在交错的时空和看似简单却一言难尽的人际关系里,展现了复杂的个人、社会、家庭、亲情、爱情和乡情的各种面相。我与“你”虽然已经分手,答应不给“你”打电话,但每当“有些夜晚,当那些悲伤的回音和晦暗的感触潜到我身旁,却比旧日更为强烈。像是细声低语,又如声声呜咽。我希望你在这里,我希望之前那些电话我都没打过,那些时候都不如此刻这样需要打电话。”我虽然害怕回到母亲身边,遭受她的漠视,所以远远躲开了她,但“那晚在飞机上飞越西半球时,我悄悄哭了起来,希望没被人发现。在遇见琼·凯芮之前,我回到了简单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有个人的心跳曾是我的心跳,有个人的血液成为我的血液,我曾蜷缩在此人体内,而她本人正病卧在医院中。要失去她的这个念头让我心如刀割。”
与亲人和爱人的隔阂、疏离与冷漠虽然蔓延到了整个人生,但在最后终究会被打开一个缺口,让蓄积已久的情绪找到自己的归路。而通过文字和语言来铺陈这一切,虽然会再遭遇一次痛苦,但却是调和和抚慰疼痛最恰当的方式。
托宾的小说能够穿越文化的藩篱,直达我们心间。我们读托宾,也是在读自己。当我们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绝望于愈来愈粗糙麻木的感情时,我们遇到了托宾。他替我们说出了那种无以言喻的心情,也因此让我们完成了某种救赎。
责任编辑 杨易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