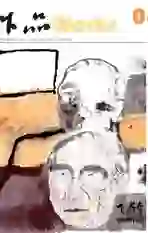苏轼: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2020-08-06宗城
宗城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定州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向南行驶。车内,中年人头戴乌角巾,手捧诗书,深情地回望着斜阳柳树。他叹了口气,缩回车中,城门口,许多百姓自发来为他送行。
他这一行,要流落到千里之外帝国边缘的岭南。曾经,他是名满天下的京城学士,如今,皇帝一封语气严厉的圣旨,几乎宣判了他政治命运的死刑。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那一年,他五十七岁,已不再是昔日汴京声名鹊起的少年,在定州,他甚至已经贫困到没钱买马、雇人(苏轼把自己的窘迫,写在了《赴英州乞舟状》中)。为了凑足盘缠,他不得不绕道汝州,向弟弟苏辙寻求资助。好在,苏辙送给兄长七千缗(相当于七百万文钱),缓解了他的经济危机。
苏轼一生的热望是匡扶社稷,实现大宋中兴,但他性格刚直,秉笔直言,不被朋党领袖喜爱,因此无论新旧两党,谁人主政,他最后都逃不开被贬的命运。
对于贬官,苏轼习以为常。治平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被外派离京;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说了新法的弊病,再次触怒王安石,他自知不容于朝野,主动请求出京任职;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那是苏轼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他几乎是去地狱边走了一遭,在监狱里待了103天,每天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宣判。好在上天垂怜,他被打发去了黄州,说是外放,实为软禁。
神宗年间,苏轼与新党不合。神宗去世后,高太后重用司马光,旧党一度把持了朝政,苏轼还朝,做到了礼部尚书,他若是顺从旧党,便是官运亨通,但他认死理,新党有问题,他冒死进谏,旧党专横,他也直言不讳。苏轼两头不讨好,再次走上贬官之路。
从定州到惠州,苏轼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了大宋帝国最偏远的角落。
和乌台诗案时相比,他又老了一截。乌台诗案那一年,他四十三岁,已经是官场的老人。而现在,当他千里迢迢赶赴惠州,已是近六十岁的高龄。儒家说,苏轼不知自己是否参透了命数,他回望人生,看到的是告别与轮回。
遥想当年,他与王安石朝堂论争,哪怕政见不合,私下里也能互相尊重。王安石从不想杀苏轼,这是他和小人不同的地方,乌台诗案,苏轼下狱,是王安石一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把他捞了出来。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下野,隐退金陵,正巧苏轼赴任汝州,路过此地,王安石特地在渡口驻足几天,只为见苏轼一面。二人浮舟江上,惺惺相惜,沉默中长揖而笑,胜过千言万语。
王安石评价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则感佩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他们在金陵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围炉夜话,通宵达旦,往日朝堂纷争,江湖夜雨青灯。而如今,安石归去,朝堂上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苏轼独行在古道,感受到的不只是失意,还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凉薄。纵然如此,他也能豁达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从盛名到贬谪,苏轼这一路走来,体会最深的是人情冷暖。昔日高中进士,风云朝会,自己的府邸那是每天都有拜访的人,多少商贾名士,争着抢着要他苏东坡的笔墨。如今得罪权贵,仕途黯淡,附庸风流者走的走,散的散,就连那些红粉佳人,一听说要去岭南,也怯生生地打了退堂鼓。只有他的至亲,还有红颜知己王朝云愿陪他,赴那千里迢迢的不归路。(苏轼自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相传,这个王朝云不但是苏轼的红粉知己,还是苏门弟子秦观的暗恋对象。秦观的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据说就是为王朝云所写。苏轼是个明白人,看出来秦观的心意,就示意王朝云,要求秦观为其填词。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记载:“东坡曾令朝云乞诗于秦观,秦观作《南歌子》词以赠,秦观词题作《赠东坡侍妾朝云》。”这首《南歌子》如此写道: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
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住,还因暮雨忙。
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林语堂写苏轼时,最动情的就是写到他和王朝云的忘年恋。林语堂说:“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轼是如何赞美王朝云的呢?有词为证: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著点,更夏文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態。闲跑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殢人娇·赠朝云》
这个“维摩”就是苏轼对王朝云的雅称。据林语堂记载,相传:“释迦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间。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朵硬是沾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克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王朝云是苏轼流落时的慰藉,温存他那被雾霾笼罩的沮丧内心。他们在惠州如同神仙眷侣,修小屋,种树苗。苏轼那屋子取名为“白鹤居”,他在旁边的空地上,先后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桧树和栀子树。他和知己云雨恩爱,甚至琢磨起长生之术。只是,人在造化面前,毕竟过于渺小了,当苏轼好不容易得到安慰的时候,上天又给他重重一击。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五日,王朝云染上瘟疫而死,时年三十四岁,此时,苏轼到惠州不过两年。
时人记载:朝云一生向佛,临终前,她执着苏轼的手诵《金刚经》四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和闪电,一瞬即逝,不必太在意”。
八月三日,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南畔的栖禅寺的松林里,亲笔为她写下《朝云墓志铭》,铭文道: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
如汝宿心,唯佛是归。
惠州民间传说:“王朝云葬后第三天,惠州突起暴风骤雨。次日早晨,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前去探墓,发现墓的东南侧有五个巨人脚印,于是再设道场,为之祭奠,并因此写下《惠州荐朝云疏》。”其中说道:
“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掩微躯。方负浼渎精蓝之愆,又虞惊触神祇之罪。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显,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世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
王朝云死后,苏轼又先后写下了《朝云墓志铭》《惠州荐朝云疏》《西江月·梅花》《雨中花慢》和《题栖禅院》,悼念这位他后半生最刻骨铭心的女人。不仅如此,他还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并亲手写下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生活在岭南,苏轼不能像以前一样上疏皇帝,关心国家大事,但他闲不住,他那一腔忧国忧民的抱负不允许他怠惰。他知道广州、惠州等地常有瘟疫,与水质有关,就写信给当时的广州太守王古,商量筹措一笔资金,建立官府认可的医院。
然后,他从水质入手,提议建设水管,引城外优质山泉入城,缓解平民的用水问题。这个水管怎么修呢?苏轼想到了岭南丰富的竹子,他用竹管为水管,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再涂上厚漆,防止漏水。为了避免竹管堵塞,官府必须按时派人检查,更换竹管。苏轼的这个计划因地制宜,解决了广州城内一个大麻烦。
同时,苏轼叮嘱太守,别让他人知道这是他的主意,因为他当时正是“反面典型”,苏轼担心,这事被上面知道,会卷入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可讽刺的是,后来太守王古被革职,理由是“妄赈灾民”。
苏轼在惠州,大大小小的事,只要是关于民生的,他都要过问两句。有一年惠州谷价下跌,官府拒绝直接收取农民缴纳赋税的谷子,而是要他们把谷子换成现钱,再交给官府。但这样一来,农民实际上等同于被勒索,因为当年的谷价远低于市场合理水平。苏轼知道后立即给相关官员写信,他言辞恳切,据理力争,终于说动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减轻了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这还不够。苏轼下到田地,看见农民们顶着暴晒,赤脚前行,每天都付出大量时间在插秧中。他想起了自己在黄州见到的“浮马”,是一个可以有效节省插秧农民体力的工具,他就再次写信。这一次不但给惠州的官员,还寄给了广州太守,像一个推销员似的,热情地介绍“浮马”的好处。
苏轼在惠州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在惠州湖上修建桥梁、给无名死者重建坟墓、写祭文、在城西修建一座用于买鱼放生的放生池(日后名为“苏东坡放生池”),还有鼓励当地教育等。就是这一件件实事累积起来,让惠州百姓感激这位远道而来的东坡先生,他不只会吟诗作词,更是一位体恤百姓的好官。
在古代,岭南穷山窮水,是烟瘴之地,达官贵人至此,总是一身的牢骚。但苏轼不同,他到了岭南后享受生活,他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老朋友陈糙想来探望,他回信说: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多百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路尺,此未易遗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就,莫作儿女态也……”
苏轼在惠州最大的惊喜是吃的,尤其是那些在北方很难吃到的岭南瓜果,其中就有他最喜欢的荔枝,于是有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爱吃荔枝,也酷爱喝酒。岭南不禁酒,给了他沉浸酒肆的机会。他在惠州学习了一种酿酒法,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酿成,据说酿好后,清香可比王孙甘露。
曾有人统计,《东坡全集》共出现“酒”字九百多次,苏轼喝过的酒,可以铺满他的府邸。他不但喝酒,还自己造酒。作为苏轼的忠实读者,林语堂就说他是“造酒试验家”,传说蜜酒、真一酒、天门冬酒、桂酒、万家春酒、酴酸酒、罗浮春酒等,都与苏轼有关。而苏轼留给后世的绝美诗词,很多都是酒劲上头,即兴而成,比如有一首《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写得颇为雅致: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襄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显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楼残红。
苏轼被荔枝和酒勾了魂,不但自己吃,还教别人怎么吃。如今惠州有名的烤羊蝎子,就是苏轼的心头好。那时候,惠州的肉铺宰羊,别人都爱吃羊肉,但苏轼嘱咐屠户,每天把“大梁骨”留给他。这个大梁骨,就是我们说的羊蝎子。
据说,苏轼烹羊蝎子会先煮熟,然后轻洒酒和盐,在火上烤至微焦,待酥脆焦嫩,便是食用的最佳时机。他不但爱吃羊蝎子,烧蚝、盐焗鸡也都是他的桌上料理。如此吃好喝好,以至于他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又说:“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诗背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且说苏轼的好友王巩,因乌台诗案而被贬岭南宾州,他南下时,只有歌妓柔奴愿意随行。后来,王巩等到了北归的机会,他在临走前与苏轼重逢,唤柔奴为好友敬酒。故友重逢,不胜唏嘘,苏轼问及岭南风土,柔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知道苏轼的境况后,当朝宰相章惇大为不快,惊呼:“苏子瞻尚尔快活耶!”
其实,苏轼这种乐观,王安石早就领教过了。在那些贬官黄州、杭州的岁月里,苏轼郁闷归郁闷,但依然寄情山水,保持他那至死方休的乐观主义。所以,他在那里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文字。
冬至时吃羊肉,他说:“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某一天吃猪肉,他说:“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又有一天,他品尝了一位老妇人做的环饼,兴奋道:“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就连野菜,苏轼也吃得津津有味:“秋来霜露满园东,芦菔生儿芥生孙。我与何憎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那些年,苏轼留下许多舌尖上的传奇,比如“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玉糁”“东坡腿”“东坡脍”“东坡墨鲤”“东坡饼”“东坡酥”“东坡豆花”“东坡肉”等,成百上千的店铺,都说自己和苏东坡有关系。
如果北宋有《舌尖上的中国》,苏轼绝对是座上宾,他对吃食的态度,正应了周作人的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無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知堂谈吃》)
绍圣四年(1097年),在章惇的授意下,苏轼被贬为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这一年,他刚好六十岁。
为了让苏轼受尽苦头,章惇还借朝廷诏令,对被贬的苏轼下了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
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章惇之所以把苏轼贬到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而与此同时,苏辙被贬雷州,则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轼是朝廷命官,只能乖乖领命。有几人知道,他在岭南哪是快活,分明是苦中作乐,跋涉千里,忍受痔疮之痛,仕途失意,更无几人言说,苏子瞻心中郁结,只好托付诗文,自我疗愈罢了。
所以他在惠州曾写道:“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春天里的病容,才是苏轼的无奈。
其实,章惇和苏轼本是旧时好友,年轻时,他们一同出游。有一次,二人要过独木桥,桥下是万丈深渊,章惇怂恿苏轼一起过去,在石壁上题字,苏轼不敢,章惇就一个人大笑而过,在石壁上写下大字:“章惇苏轼来游。”苏轼看到后,断定章惇以后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何,苏轼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高斋漫录》)
还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山寺边饮水,听说附近有老虎,章惇借着酒劲兴奋地想看,在距离老虎数十步的地方,马儿都吓得不敢继续走了,章惇偏偏取出铜锣,在石头上碰响,没想到,老虎被他吓跑了。(《耆旧续闻》)
后来,少年知己成为官场对手,一个旧党,一个新党,夕阳下渐行渐远,但彼此依然敬重,有一次,章惇还救了苏轼一命。
邹金灿先生在《苏轼和章惇》中写道:“新派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以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4个多月,受尽屈辱,在狱中写下‘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悲愤诗句。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章惇站了出来。章惇在神宗面前与新党同僚据理力争,说诸葛亮号‘卧龙,但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所言,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方势力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伤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可惜,随着党争激烈,北宋政坛的报复越来越残酷。绍圣年间,章惇成为宰相,为了报复旧党对蔡确等新党老臣的冤杀,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罗织罪名,大兴牢狱,把一大批和旧党有关的人抄家流放,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自然难逃厄运。
绍圣四年五月,苏轼动身前往儋州,在路途中与弟弟苏辙重逢。他对弟弟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大意是:琼州、雷州虽然被大海阻隔,但我们兄弟二人仍可隔海相望,这不正是皇恩浩荡的眷顾吗?
苏轼总能把叹息化作玩笑,咽下人世间的苦与痛,寄情一壶温热的酒。他和苏辙是在藤州相遇的,在去雷州的路上,兄弟二人故意走得很慢,他们知道,此去一别,再见不知何时,从藤州到雷州不过五六百里,他们足足走了二十五天,其间同床共枕,秉烛夜话,吃最粗糙的粮食,忍受岭南的燥热和无常。
真正要离开雷州的那天晚上,苏轼痔病发作,如若将死之人。雷州不像汴京,有一流的大夫立刻给他开药。苏轼只能忍着痛苦度过整夜,苏辙也彻夜不眠,陪在哥哥身边,那个晚上,他为苏轼诵读陶渊明的《止酒》诗,苏轼作了一首《和陶止酒》,作为回应:
萧然两别驾,
各携一稚子。
子室有孟光,
我室惟法喜。
当苏轼真的要坐船去往海南时,苏辙眉头紧锁。在北宋,被贬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海南比广东更加偏僻,毒蛇猛兽遍地皆是,更恐怖的是,北宋时期,那里是瘴疠和疟疾的高发期,而两年前,王朝云正是死于由此引发的瘟疫。
据《琼州府志》记载:“此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
《儋州志》则写道:“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在水,莫不有毒。”“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
乐观如苏轼,这一次也做了最坏打算。他给朋友写信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又对弟弟苏辙慨叹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他在儋州过得清苦,方言不熟,地理不通,身上的疾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帮助他的人也会被他牵连。昌化军使张中是他的仰慕者,知道他来海南后,安排他和小儿子苏过“住官房,吃官粮”。结果,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至雷州时,听说苏东坡住在昌化官舍,派使者渡海,把苏轼一家逐出官舍,并且狠狠地处分了张中。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得到北上的一天,所以在听说好友佛印要来看他时,他写信回绝,自述道:“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唯有一幸,无甚瘴尔。”
好在蘇轼懂得苦中作乐,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在一些百姓的帮助下,他在城南的桄榔林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又劝课农桑,勘察水利,指导当地人打井取水。稍微融入当地生活后,苏轼的嘴又馋了,他和儿子自创了一道美食,取名叫“玉糁羹”:“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不仅如此,他连蝙蝠都吃得下。在《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一诗中,他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苏轼吃东西不挑食,自然不会错过海南的美味烧蚝。有一次,当地百姓送给他一些生蚝,苏轼就把生蚝剖开,取出肉放进热汤里,随后灵机一动,倒酒入锅,待煮熟之后,取之入口,味道出人意料。美食家苏轼兴奋地告诉儿子,这个烧蚝的做法,一般人你别告诉他:“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翻阅东坡文集,我们看到苏轼的这一段海南时光极尽凄凉,又被写得充满了生活的小欢喜。他为了排忧解闷,甚至钻研起养生的门道,晚年自创养生三法——晨起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写入文章《谪居三适》。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却悠然自得道:“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
海南历史千百年,左迁至此的官员不计其数,但儋州人最喜爱和憧憬的一位,百年来都是苏轼。因为苏轼热爱海南,并没有只把海南当作蛮夷之地,他来到海南后没有消极怠工,也毫无高门读书人的架子,反而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修了座“载酒堂”,找当地的读书人一起喝酒。这座“载酒堂”就是后来的东坡书院。
苏轼是考试能手,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他来到儋州,最得心应手的一是喝酒,二就是教别人考试。他在儋州点拨了很多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其中最得意的弟子是来自琼山府的姜唐佐。他本来就是当地教师,听说苏轼要来儋州,当即启程,不求回报侍奉在苏轼左右。几年后,姜唐佐去广州应考,临行前苏轼为他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往后,姜唐佐学成返乡,开办乡学。他继承老师的遗志,帮助更多海南人走上读书之路,所以《琼台纪事录》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如今来到海南儋州,我们还能看见东坡书院,在一片绿树繁花的掩映下,东坡居士头戴圆帽,手捧古籍,一身正气行走于浩然天地。
或许在独自面对大海时,苏轼会想起汴京的闹市。去年灯市,花好月圆,一切都是极好极好的,但那些都过去了,都已经随着仁宗朝那个“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神话,一起扫入了历史的坟茔。
对一个士人来说,抱负无从施展,他热爱的国家只想放逐他,许是午夜梦回最心酸的事,但苏轼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即便在帝国最边缘,他所表现的,依然是一个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苏轼。只是这种“释然”背后,终究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晚年,苏轼的诗词更加沉郁顿挫。他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仿佛是对自己这辈子的回望: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初读之下,是阅尽千帆的老人,在执着之后的放下与坦荡,但细细品味,未尝不是对人生的自嘲。所谓“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苏轼何等志向,最后一生功业,也不过几个外派州府,眼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自己却如已灰之木、不系之舟,个中滋味,又有谁人知。
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同样隐匿了自己的无奈。那是他在儋州写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
总角黎家三四童,
口吹葱叶迎送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
溪边自有舞雩风。
此诗作于元符二年(1099年),苏轼时年六十四岁,被贬儋州,一生已是陌途。这个年纪,前唐宰相李德裕在感慨“鸟飞犹是半年程”,而苏轼呢,他借着酒劲,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一个说官话的四川眉州人,和三四个黎族小伙把酒言欢。苏轼有趣的地方,正在于此,但他嬉笑之间,却又隐约流露出了对人生的感慨。
所谓“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这两句致敬《论语》的诗,其实是苏轼对自我的开导,就是说,没有必要执着于自己被贬谪千里的事实,也不必沉沦于政坛失意的绝望,即便在偏远之地,你一样可以快乐地随风起舞。这种开导,看似豁然,可我们想,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开导自己?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我想,这不可救药的乐天背后,实是东坡自饮的悲凉底色。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六十五岁的苏轼终于等到了朝廷的大赦。三年海南光阴,如今物是人非,苏轼北眺茫茫大海,内心百感交集。临行前,他留下了自己在海南的最后两首诗,其中一首道: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据林语堂考证:苏轼本想搭福建一艘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友人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齐渡海。渡海后,他们先到雷州去探望了秦观,然后一家人再缓缓北上。
北上期间,苏轼收到了章惇被贬的消息。讽刺的是,章惇这个昔日权倾朝野,对他一贬再贬的人,如今却成了被罢黜的对象。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谏官任伯雨八次上章弹劾章惇,陈瓘、陈次升等人跟进,不但称章惇有谋反之心,轻视徽宗,还重提当年他想追废宣仁太后的事情。宋徽宗一怒之下,把章惇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章惇的一个儿子章援,恰好是苏轼的门生(昔日科举,苏轼为主考官时,亲自以第一名录取了章援),他听说此事后,担心苏轼念及旧仇,会报复自己的父亲,于是诚惶诚恐地写信给老师,恳请苏轼宽宥章惇以前的行为。
可叹章援不懂,苏轼根本没有报复之心,他在收到信后大喜,不但对身边人夸起了章援,还写信答复他: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想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在信中,苏轼宽慰章援,坦陈自己重病在身,对章惇毫无加害之心。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自己与章惇的共同朋友黄实说:“子厚(章惇)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雖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大夫人也。”
苏轼被赦免了,但他的身体也愈发虚弱。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让他痛苦难熬。苏轼谢绝了大部分拜访的友人,卧榻病床一个月。他没有胃口,也无力起身,自知离油尽灯枯之日不远,他嘱咐友人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林语堂《苏东坡传》)
七月十五日,苏轼的病情继续恶化。高烧、牙根出血、饭菜难咽,实在太饿了,就喝人参、麦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或者少许清水。他身体暴瘦,面色如枯骨,又过数日,他的呼吸都困难了,两只眼无神地望向窗外。昔日故人,仿佛一个个向他走来,又离他远去。而他面对着哭哭啼啼的亲人,仍强装着乐观的神色,气息微弱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在常州(今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半月之前,他曾写信给维琳方丈道:“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苏轼一生坎坷,不折其节,他的政治成就虽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章惇等同期友人出色,却凭借不朽的诗文、豁达的品性,在历史的长河中造就更加深远的影响。北宋是一个才人辈出的时代,而苏轼苏东坡,是闪耀群星中最夺目的那一颗。
求仁得仁,死生无憾,对苏轼这一生的评价,他自己已经写出来了。那是在去潮州纪念韩愈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苏轼这一生,当得起“浩然”二字,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君子对世界最谦卑的爱。
参考资料:
[1] 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
[2] 林语堂:《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
[3]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
[4] 陆游:《老学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5] 王安石著,李壁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6] 李廌、朱弁、陈鹄:《师友谈记·曲洧旧闻 西塘集耆旧续闻》,中华书局,2002年8月。
[7]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3月。
[8]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
[9] 搜狐网:《兹游奇绝冠平生——苏东坡在儋州》,http://m.sohu.com/a/161048669_669776/.
[10]朱飞镝: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第28卷第3期,第5-9页。
[11]卢捷.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记苏轼惠州到儋州行程.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第七期,第70-71页。
[12]王启鹏:苏东坡在惠州的三重突围. 惠州学院学报, 2010, 30(1):27-30.
[13]杨再西:《谪居三年,惊鸿一瞥——苏轼给海南留下了什么?》,海南温度,http://club.hainan.net/wendu/0018/index.shtml.
[14]邹金灿. 苏轼和章惇.学习博览, 2014年第9期,第22-22页。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