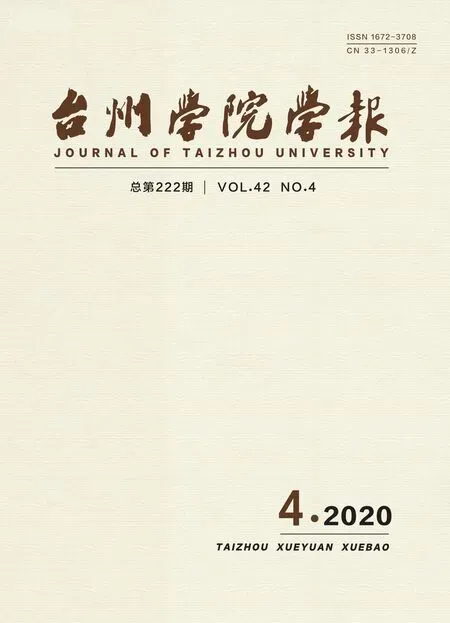汉语新词语英译的八大关键问题
2020-08-05任开兴
任开兴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一、引言
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理查兹(Richards I.A.)曾说过:“翻译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活动。”[1]在这一活动中,词语的翻译是第一道门槛。词语是翻译中最小单位,其翻译错综复杂,译者时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感,即使是译界大咖也颇有感慨。严复先生在翻译《天演论》时频频为新译名的确立而绞尽脑汁,不禁喟然长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2]
相比既有词语,新词语翻译的难度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全红教授认为:汉英新词翻译具有创造性、时效性、不易求证等特征,而这一切叠加一起,大大地增加了汉英新词翻译的难度;有些新词不说一次性翻译不好,就是假以更多时日并配以精兵强将也未必能拿出理想的译文。他因此发出这样感叹:汉英新词翻译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活儿[3]。
网络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加速了新词语的诞生和嬗变。新词语的翻译,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译界绕不过去的话题。本文就新词语英译几大关键问题略陈管见,伫候明教。
二、内涵一致问题
文字只是新词语的外壳,而内涵才是核心。内涵,即概念的内容,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概念义,它系词义的核心部分,具有概括性、特征性和普遍性。新词语的翻译不能以文字外壳为依据,而应以内涵为准绳。也就是说,以内涵等值为主线,将理解新词后分析出的内涵内容由原语世界对等地移植到译语世界。尽管两者的外壳可以迥然不同,但是其内涵应该是一致的。
例如,在翻译“植入式广告”这一新词语时,不应该按照汉语思维将其翻译成implanted advertisement。首先要弄清“植入式”与“广告”这两个独立概念形成的组合关系,析出其内涵,形成“把产品及其服务具有代表性的视听品牌符号融入影视或舞台作品中的一种广告方式”这样的概念义,然后按照这一概念义在英语中寻找对应词。当然,能否找到对应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英语词汇掌握情况。如果对应词的词形、词义及语音表征在译者大脑词库中存储不够清晰或没有存储,语言转换就有可能中道而止。写作中遭遇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4]之力不从心现象,在翻译中也会同样出现。不过在网络检索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可以把“植入式广告”分解成英语关键词,再通过谷歌搜索引擎,就能轻而易举地检索到其对应词(product placement),并能在相关描述中找到其同义词(embedded marketing)。同时,一旦断定汉语新词语的英译必定包含某个英语关键词,也可以输入“汉语新词语+英语关键词”,或许能直接找到译文。例如,不知道“方舱医院”如何表达,可以在谷歌搜索框中输入:“方舱医院”hospital(必须有双引号),便能找到 fangcang hospital、mobile cabin hospital、module hospital、makeshift hospital、pop-up hospital、temporary hospital等译文。考虑到内涵对等及英美媒体的使用现状,选用pop-up hospital更符合英美人“口味”。
当然,这种检索方法只能适用于部分新词语的翻译,译者要想翻译时驾轻就熟,就必须对相关的英语文本了如指掌。恰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出现的新词语,只有多阅读相关的英语报刊,对特定的英语表达方式了然于胸,做到知己又知彼,才能在翻译诸如“吹哨人”(whistle-blower)、“封城”(place a city on lockdown/impose lockdown on a city)、“居家令”(stay-at-home order)、“零号病人”(patient zero)、“甩锅”(pass the buck)等词语时,可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三、语境顺应问题
“形单影只”的词语,其词义往往是稳定、概括和抽象的。一旦置入特定的语境,其境况语义就被激活,意思变得明朗。正如弗思(Firth)所说,“每一个词语在新的语境下都是一个新词。”[5]词语的翻译不强求字面意思上对等,但要求其含义与境况信息契合。
“语境对语言理解的作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top-down),即根据大的语境来理解具体的话语;另一种是‘自下而上’(bottom-up),即从话语的字面意义出发来理解语境中的话语。”[6]15就新词语翻译而言,“自上而下”方式更加突出。当新词语进入具体的言语活动时,其表达的实际词义往往因境而异,这既有本身的意义,又有话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所赋予的词义。只有将它们与这些语境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正确地解读潜在的含义,为准确英译打好坚实的基础。
例如,“碰瓷”原来是古玩业的行话,意指一种故意让人损坏瓷器,借机讹诈的行为。原本译作broken porcelain scam便能等值转换,但随着其伎俩不断更新、道具不断翻样,“以不变应万变”之策显然独木难支,只能依据“砸碎的道具”来应变,如broken bottle(glass/eyeglass/vase/watch/phone/computer)scam,甚至是 melon drop scam。当下,“碰瓷”已悄然转变为交通事故中讹诈名词,可以统称为staged crash scam,也可以根据具体特征译为swoop and squat scam/panic stop scam/side swipe scam/crash-for-cash scam等。同样,“充电”本来是“补充电能”的意思,但是不同语境可以赋予它新的喻义,翻译时应根据所充的“电”来应变。充的是体力,译成 recharge one’s batteries;是知识,可译为brush up/brush up on/update/upgrade one’s knowledge;是技能,应译成 upskill onself/upgrade one’s skills;是学历,可用 pursue further studies/education。
真可谓是“意随境迁,译从境变”,“没有语境的明示,翻译犹如在岸上游泳。”[7]
四、修辞和谐问题
修辞,作为一种可以有效运用语言的技巧或艺术,能“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8]1474。新词或旧词新义的修辞理据突出表现为隐喻、借代、拟人、仿词、别解、委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探讨隐喻和委婉语。
隐喻是一种基于物理和心理上的相似性隐藏比较的修辞手段。“物理的相似性可以是在形状上、外表上或功能上的一种相似,心理相似性是指由于文化、传说或其他心理因素使得说话者或听话者认为某些事物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6]172隐喻是一种从源域向目标域映射的认知过程。这种映射是基于不同概念域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关系,从一个具体概念域射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用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陌生。当不同域之间的新旧事物存在主客观上的相似性时,人们就会用旧的能指指代新的所指,一词多义便诞生了。但由于中西文化观念不同,隐喻义可能会出现分离或此有彼无的现象。因此,“隐喻的翻译是翻译的‘高难动作’,是考验译者汉语母语水平和英语外语水平及检验译者汉英文化认知能力的‘舞台’。”[9]49
首先要注意汉英不同映射导致隐喻义出现分离的现象。例如,有些汉英词典将“银弹外交”翻译为silver bullet diplomacy。其实,汉语中“银弹”喻为“腐蚀、拉拢人的钱财”[8]1563,而英语 silver bullet是一种用银子做成的子弹,是神话故事中用于消灭狼人的特效武器,被喻为“杀手锏”。不同映射导致二者貌合神离。因此,“银弹外交”翻译为silver bullet diplomacy系乱点隐喻“鸳鸯谱”,应更正为dollar diplomacy。
其次要留意此有彼无或错位对应的现象。例如,“暗箱”原来指照相机中镜头至底片间不漏光的空间,由此隐喻为“暗地里”,而camera obscura或black case没有这种喻体共知性,故不能将汉语喻体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英语中,必须要求英语中的喻体和本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否则会增加对本体的理解难度,导致跨文化交流失败。英语中能与“暗地里”产生联系的词语有back-room、under the table、under the rose、pull strings等,故“暗箱操作”的翻译必须按照英语民族的思维,是名词的话可以译为back-room control/under-the-table operation/under-the-rose manipulation等;是动词的话可以译成control...in the back room/operate under the table/pull strings等。
“委婉语是一种有动因的、美好的语言形式。”[10]16从古至今,委婉语一直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具有较高的能产性。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文化程度的提升,国人更加注重文明礼仪,使用新词语称谓某种现象时也更加注重使用含蓄、委婉、高雅的措辞方式。因此在翻译时要精准识别委婉语,采用淡化、美化策略,为跨语言交际助添润滑剂。如果委婉语借译自英语,应还原其原貌,如“出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直男”(straight man)、“ 疲 软 市 场 ”(soft market)、“负 增长 ”(negative growth)等;若英语中存在类似汉语中的委婉表达现象,翻译时可尽量保留汉语的含蓄和婉转,必要时可以舍形求义,如:“车震”(parking)、“基友”(confirmed bachelor)、“咸猪手”(wandering hand)、“一夜情”(one night stand)、“走光”(wardrobe malfunction)等。
五、语义韵和合问题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词语搭配亦会气味相投。具有相似语义特点的词项往往会成群结队,构成一个更大的语言单位,并弥漫出特定的意义氛围,即“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语义韵”由辛克莱(Sinclair)借鉴语音韵律的理念构拟,由洛(Louw)公开提出,最初定义为“由其搭配词激发出的、与搭配词相匹配的意义氛围”[11]157,后来又补充了“呈现出消极或积极的语义,表达说话者或作者对某个语用场合的态度”[12]57。斯塔布斯(Stubbs)将语义韵分为积极韵、消极韵和中性韵[13]。鉴于“语义韵是隐藏于字里行间的语言现象”[14],译者要熟知这种隐性语言知识,明辨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例如,“香蕉人”被《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指在思想、文化上已经完全西化的海外华人及其后代。因他们像香蕉那样黄皮(黄皮肤)白心(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叫香蕉人。”[8]1430可见,该词语在汉语中如同“鸡蛋人”一样没有呈现出消极语义韵,否则不会被该词典收录了。但是英译时不得不顾及语义韵问题,不能想当然译为banana,因为依据维基词典(Wiktionary),它像jook-sing、Twinkies一样系种族蔑称(ethnic slur)词,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因此,我们翻译时力避此类用词,改为American-born Chinese(ABC)、British-born Chinese(BBC)等。
同时,也存在汉语中贬义暂无对应英译的现象。“窜访”就是其中一例,它是由“流窜访问”简化而成,几乎成了评述达赖的专用语。有学者认为,作为贬义词的“窜访”译成中性词visit,未能有效传递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政治立场与感情色彩,主张新造toutvisit一词作为“窜访”的一个规范译法,以便在翻译层面向西方媒体表明中国政府旗帜鲜明的原则立场[15]。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值得称道,但人为创造别国文字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不如在visit后面加上in exile(即visit...in exile),既可清楚地表明达赖所处的窘境,又能同样有效地传递上述意义。
六、借词回译问题
从广义上说,借词可以采用借音、借形、借义的形式。不管它采用何种形式,回译时最好遵循命名理据,尽可能将其推位至原语的轨道。就汉英翻译而言,主要涉及借音和借义。
借音回译是依据发音,将从英语借来的词语回归成英语。要进行这种回译,语音溯源必不可少。过去由于疏于溯源,导致有些音译词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派力司”就是其中之一。所有收录“派力司”的词典都提到它源自英语palace,但英语palace根本没有“毛织物”之类的含义。其回译因此成为译界一大难题,值得回译新词语时引以为戒。
溯源固然有助于回译,但也不能固步自封,一方面应与时俱进。有些原语的商标名已时过境迁,或没有泛化成普通名词,现在再拘泥于原始商标名进行回译,未免有点刻舟求剑之嫌。如今,与其将“席梦思”“蔻丹”“莱卡”译成 Simmons、Cutex、Lycra,倒不如译成mattress、nail polish、spandex来得通俗易懂。另一方面,还要因搭配而异。部分音译词进入汉语之后有了新搭档,回译时不能回归原词。例如,“秀”虽然源自show,但“秀肌肉”不宜译 为 show one’smuscles,应 译 成 flexone’s muscles。
借义回译是依据字面意思将从英语借来的词语回归成英语。这种见字识义的回译方法能屏蔽活译的主观因素干扰而造成的译名杂乱,保证新词语跨语际的高保真性。如“窗口期”(window period)、“大脑风暴”(brainstorming)、“湿租”(wet lease)等。这种回译透明度较高,一般不易出错,但也不能麻痹,要认真溯源,以确保回译后不会变形。例如,“蓝牙”回译成英语有这样几个版本:Bluetooth、bluetooth、blue tooth、blue-tooth、Blue Tooth、Blue Teeth等,其中不乏源自权威词典的版本。这些回译,孰是孰非,只有深究其命名的理据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原来,英特公司技术人员是依据丹麦国王的名字(Harald Bluetooth Gormsson)来命名这套允许移动电话与计算机通讯的系统,寄望该系统能像丹麦国王一样将通讯协议统一为全球标准,故Bluetooth才是正确的书写形式。
由于汉英语序不同,回译时必须与英语的顺序保持一致,切勿随意颠倒。如:“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泡沫经济”(economic bubble)、“融媒体”(media convergence)、“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一 篮 子 货 币 ”(currency basket)等。同时,个别借词是由英语不同词语借译而成,回译时必须对号入座,如“底线”表达“最低的限度”之意时应回译成bottom line,作“运动场地两端的界线”解释时可以回译为baseline。
当然,借义回译也是一把双刃剑。借义翻译可让译者省事,但回译时过分拘泥于原词也会致使同义词受到冷落,不利于措辞多样化。例如,翻译“群体免疫”只会想到herd immunity,不会想到community immunity、population immunity或 herd effect;翻译“同情用药”只会使用compassionate use,不会用expanded access;翻译“权力真空”只会考虑power vacuum,不会考虑power void。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
七、经济原则问题
经济原则,亦称“省力原则”,是指导人类行为的一条根本性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16]87。具体到语言层面,即“一句话中应该不含多余的信息,句中的每一成分都必须有存在的理由,并且在传输的信息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应该让文本越简捷越好,以便减少读者在解码语言信息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17]52019年末爆发的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由最初定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简化成“新冠肺炎”,再压缩到“新冠”,这种不断删繁就简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经济原则使然。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应遵循经济原则,在确保正确、达意的前提下,剔除冗余的信息,进而达到言简而意丰的效果。
任何汉语新词语都可以抽象到概念层,再使用英语将其概念义表达出来。因此有些汉英词典的编者在找不到对应词的情况下,往往采用冗长的解释性译文。如:
“变形金刚”(anamorphic plastic or metal toy based on a“Star Wars” figures and such like figures with movable parts which can be repositioned to transform it into likenesses of planes,tanks,animals,etc)[18]
“代币券”(a ticket with a specified value to be used for making payment as a money substitute)[19]
上述解释性翻译固然有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汉语新词语的内涵,但就经济原则而言过于冗长,浪费较高的时间成本。好翻译贵在精准,既精简又准确,这两个译名显然没有达到这一点,可删繁就简,分别译为transformer和token。
出于表达需要,有些传统词汇被重新挖掘出来使用,翻译时要观察英语是否生成了类似的表达方式。如果有,也不宜续用解释性译文。如:
“开脸”[(of a girl at the time of getting married) change the hair style,clear off the fine hair on the face and neck and trim the hair on the temples][20]
“告地状”(to write one’s troubles in chalk on the sidewalk as a means of begging)[21]
“开脸”是中国古代一种美容方法,早已传到西方,被归化翻译为threading;“告地状”在英语中也有类似表达,即screeve。
八、中看不中用问题
近几十年,译界推出不少新词语译名,其中不乏经典之作。然而,新词语的翻译不是译者自娱自乐的行为,产品最终要接受英美读者的检验。有些译名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也存在着曲高和寡或“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现象。乍看之下,有些译名确属上乘之作,但通过语料库检测,有可能是“叫好不叫座”。仅以“拳头产品”和“豆腐渣工程”的译名为例。陆谷孙先生认为,将“拳头产品”硬译为fist product自然乖谬,煞费苦心想出的blockbuster product仍不尽人意,观看拳击比赛时突发灵感冒出的 knockout product才意形兼备,至为妥帖[22]46;张健教授认为,“豆腐渣工程”译成jerrybuilt project“能起到异曲同工之效”[23]41。这些译名能否博得英美读者的认同,只要查询语料库就能见分晓。
通过Global Web-Based English(GloWbE)、News on the Web(NOW)、The Intelligent Webbased Corpus(iWeb)三个在线语料库对这两个译名和其他几个并不被看好的译名进行检索,得出的使用频次见表1。

表1 “拳头产品”和“豆腐渣工程”译名的词频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knockout product的词频屈指可数,并没有比fist product占优势,而jerry-built project在偌大的语料库中居然没有容身之地。究其原因,前者可能是借用了拳击术语而显得过于残酷或夸大其词,后者中的project具有褒义,不愿与带有消极的jerry-built“同流合污”,否则有损语义韵和谐,但能与中性的shoddy“委曲求全”。因此,“拳头产品”不妨采用blockbuster product,“豆腐渣工程”可以译为shoddy project。这里的shoddy系“回纺织物”,由破布打烂、重新纺织而成,易撕裂,与无粘性、易粉碎的豆腐渣具有相似之处,可以殊途同归。鉴于“豆腐渣工程”基本上属于完成品,译成shoddy/jerry-built construction也是不错的选择。
九、话语权争夺问题
话语(discourse)本为语言学术语,原意是“交谈、讲话”,后经巴赫金、福柯、费尔克拉夫等人的阐发,成为与思想信仰、价值追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相交织的术语。谁拥有话语权即意味着谁就可以制定规则、维护权威、决定真理、书写历史甚而压制他者[24]75-76。“话语权背后隐含了国家之间地位和实力的角逐,同时记录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竞技”[25]89,“权力之下,翻译赫然成了服务国家利益、对外国文化进行强取豪夺的工具”[26]41,“在现、当代,翻译仍然是不同语言的话语力量的博弈,是原语与目的语争夺话语权的斗争。”[27]95
但对于话语权的博弈,国内译界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赵彦春教授认为,跨越两种语言的翻译行为是超越词汇的理据,翻译消弭人对语言的干扰。他不提倡为“宇航员”创造出taikonaut一词,其理由可以概括为:1)这样造词超出两套语言系统之间的语码转换规律,等于给英语造了一个单词,就翻译的本质而言属于“不译”;2)此词系汉英两种语言的奇怪混合,英语民族不明白其构词理据;3)对于造词的执着,可以誉之为爱国主义,也可以贬之为民族主义或心胸狭隘的小肚鸡肠;4)各个国家都造出一个“宇航员”的英文名,会造成名称混乱。[28]由此可见,他对使用汉语拼音造出英语单词的翻译方式基本上持反对态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学者打着“争夺话语权”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广拼音化外译,极力主张要将“不折腾”“大妈”“屌丝”“房奴”“碰瓷”“山寨”“土豪”等词语以汉语拼音的形式融入英语,并理直气壮地将它们写入论文或收入词典中。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失偏颇。音译既有“适应症”,也有“禁忌症”,不能一概而论。要正确把握“话语价值”的尺度,量“值”而行,努力把中国的文化精髓、重大科技成果推广出去。Taikonaut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自豪感的词语,理应大力宣传推广。它一诞生就被Oxford、Random House、Collins等词典收录,而法国人创造的spationaut仍被排挤在这些词典门外,这种收词的偏袒性也正是我国航空实力有力的证明。它的创造不是为了与astronaut一争高低,也不会造成用词混乱,它专指Chinese astronaut,使得指称更加明确、用词更加经济。
同时,考虑到美国新闻报刊中“很多有关中国的报道都将中国妖魔化、丑陋化、荒谬化”[29]60,对于消极现象要谨慎处置,尽量找到英语对应词进行化解,不留一丝源自本土的痕迹。必须清楚认识到,一旦拼音化定型了,就会烙上中国印,背上“中国源头”之罪名。最近,美国高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别有用心地妄称“新冠病毒”是Wuhan virus或Chinese virus,企图将病毒标签化、污名化,让中国背上制造疫情灾害的黑锅。对此,我们要坚决反对、积极反驳,并在翻译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十、结语
以上只涉及新词语翻译的部分关键问题,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不一一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翻译时需通盘考虑。
事实上,第一个吃到“新词语翻译”这只螃蟹的译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加以创新或完善。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同步提升“搜商”和“译商”,通过充分利用物质性工具进行搜索,进而站在整个人类智慧的基础上去解决日新月异的新词语翻译之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