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升庵簪花图》与狂士身份形塑
2020-07-25故宫博物院书画部蒋彤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 蒋彤
故宫博物院藏陈洪绶(1598-1650)《升庵簪花图》轴(图1)绘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①谪戍云南时的放浪生活情形。画心右上有陈洪绶自题及落款,但未注纪年与受画人,钤“章侯氏”“洪绶私印”,另钤“清群簃鉴赏”②“身世沧桑”两方鉴藏印。关于此画的创作年代:许文美在《论陈洪绶版画< 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中的仕女形象》[1]文中认为《升庵簪花图》成画年代与《水浒叶子》(约1633-1634 年)相差不远。翁万戈认为画中款题似陈洪绶1635 年所作的《冰壶秋色图》(伦敦英国博物馆藏)字体,但更趋向后来化为长方形的结构,定此约作于崇祯九年(1636 年)[2];李维琨、陈传席二人分别从线条与风格上判断此为陈洪绶中年成熟后所作③;张晨《陈洪绶的< 杨慎簪花图>》[3]文中将杨慎的怪诞行径与画家个人身世相联系,认为是陈洪绶晚年所作。

图1 《升庵簪花图》轴 明 陈洪绶 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升庵簪花图》的创作年代,本文同意翁万戈、李维琨等先生所判断的属于陈洪绶中期所作。与陈洪绶所绘来自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不同(这里不包含陈洪绶为同时代人所绘的肖像写照),升庵是距其生活时代不远的前朝大臣,陈洪绶为何要画杨升庵,以及在缺乏已有的人物形象及图式作参照的情况下,陈洪绶如何表现升庵形象?以往学者主要集中对画面中升庵簪花的形象与意涵进行探讨,如邱稚亘《< 升庵簪花图> 在陈洪绶簪花人物画中的定位》[1]39-74一文认为,《升庵簪花图》熔铸了陈洪绶对青春的倾慕、对功名的失望以及对政治的担心,同时作为陈洪绶绘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终止了其描绘青春、希望与活力的所有寄托;丁培利《杨慎“傅粉簪花”的文化内涵——以陈洪绶< 升庵簪花图> 为例》[4]认为,陈洪绶根据晚明文学家、史学家及杂剧对升庵形象的“塑造”实为其自画像,以借此表达其怀才不遇、青春已逝但壮志未酬的心迹。“簪花”是陈洪绶对晚明文本记录中升庵狂士形象进行的图像转化,仅对画中“簪花”的细节进行强调而忽略图像的整体形式,不能全面阐释陈洪绶对杨升庵产生的情感共鸣。
本文通过对《升庵簪花图》的构图、人物形象及细节等的分析,认为陈洪绶借用了唐宋以来表现高士形象的图式与技法风格将本为狂士形象的杨升庵进行了“高士化”的塑造,并结合陈洪绶的人生经历试图从其对狂士身份的认识角度解释其中原因。
一、升庵狂士形象之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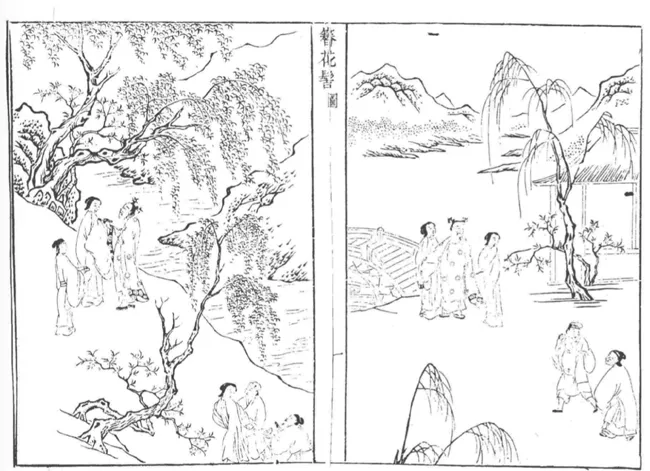
图2《盛明杂剧》中《滇中妓龙蛇竞练裙•杨升庵诗酒簪花髻》插图 明 沈泰辑编
根据画心右上陈洪绶自题“杨升庵先生放滇南时,双结簪花,数女子持尊,踏歌行道中。偶为小景识之,洪绶”,可知画中高髻簪花的男子即为杨升庵,他面部因醉酒而略泛微红,两名女子一捧酒尊一持羽扇随行其后。所绘为时人熟知之典故:嘉靖年间状元杨升庵因朝廷“大礼议”事件获罪,谪戍云南期间表现出的“纵酒、傅粉簪花、携妓游市”等一系列癫行放举。
然考察史料,升庵在其谪戍滇南的半生中“好学穷理,老而不倦”,可谓旷达自适。其友人刘绘《与升庵杨太史书》中云:“仆观足下自蒙难以来,呕心苦志,摹文续经,延搜百氏,穷探古迹,凿石辨剥勒,破冢出遗忘。”[5]他结社,讲学,潜心学术,与滇中文人及门生探古访幽,著述达百余种。《明史·杨慎传》云:“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6]即使升庵曾有诸如“不须更奏琵琶曲,司马青衫泪满巾”④类“歌筵妓席”[7]之作以及“戴花归路似东坡”[8]等的旷怀之作,也仅仅是其谪戍生涯中的自我遣怀。自谓对升庵“窃附景仰之私”[9]的思想家李贽在《焚书》中谓:“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 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9]并在其《续藏书》中将升庵列入“忠节名臣”与“文学名臣”[10]中,由此可见李贽对升庵人品、道德、才望的景仰。
有关升庵脱略礼法,放浪形骸之形象最早见于王世贞(1526-1590)的《艺苑卮言》:
用修谪滇中,有东山之癖。诸夷酋欲得其诗翰,不可,乃以精白绫作裓,遗诸伎服之,使酒间乞书。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赏伎女,购归装潢成卷。杨后亦知之,便以为快。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㫒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人谓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11]
王世贞点明杨慎有“东山⑤之癖”,是引用东晋名相谢安隐居会稽东山,纵情诗酒,出游必携歌妓同行的典故来引出升庵谪滇后的狂诞行为:拒绝富人的高价求字,醉酒后在歌妓衣衫上挥毫泼墨,胡粉傅面,双丫簪花及携妓游行等。结尾处王世贞不赞同时人认为升庵此举是自污以避祸⑥,他以“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作结,以其同为文人的身份分析了升庵外在狂态下的真实心态。由于这种心态与明代中晚期士人普遍的怀才不遇感相符,引起了他们的情感共鸣;再加之王世贞作为明代后期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之一,其《艺苑卮言》深刻影响了后来近百年的文坛,以至于其所记升庵之事被明代中晚期流行的人物品鉴书籍⑦所引用传抄,并将升庵的行为归于“豪爽”、“任诞”⑧、“佻达”⑨等类别下以凸显其狂士形象,且均认同王世贞对升庵心态的分析:“王中丞元美曰:‘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真知言哉。”
崇祯年间,升庵的“狂士”形象还成了杂剧创作的灵感来源,杂剧家沈自徵⑩(1591-1641)曾言读到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所记杨升庵后“每拊膺欲绝,当浮白一斗,呕血数升,愦而后止”⑩。其杂剧《簪花髻》(或称《杨升庵诗酒簪花髻》)即在前述杨慎的癫行放举基础上进行夸张,极尽表现其无赖与痴绝。剧中展现了杨升庵的痛饮狂醉,以妓女装扮外出游春,对沿途指责其不合礼法者及高价求字者均漠然置之,兴之所至便在歌妓衣衫上挥毫泼墨,见风雨连天、春色将归,便掩面痛哭……这些都更加张扬了升庵放浪不羁的狂士形象(图2)。
表面放诞不羁,内心沉沦痛苦的杨升庵是晚明江南失意文士们的情感投射,对升庵纵酒、簪花、携妓等种种狂行的书写,更是晚明失意士人崇尚率性之真以及抒发苦闷的出口。故杨升庵这个本为“好学穷理,老而不倦”且“追求自我回归之适意”的旷达之士被晚明不遇文士们共同塑造成了任气使才、放浪形骸的狂士形象。而本文所讨论的画家陈洪绶正是晚明失意士人中的一员,其《升庵簪花图》亦可看作是除上述人物品鉴类史传、戏剧之外以绘画来塑造升庵狂士形象的另一种方式。
二、狂士的“高士化”
与陈洪绶所绘来自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不同,杨升庵是一位距其生活时代不远的前朝大臣(这里不包含陈洪绶为同时代人所绘的肖像写照),在没有传统的人物形象及图式做参照的情况下,如何表现升庵的狂士形象是陈洪绶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画中人物身份来看,《升庵簪花图》属于表现“士妓交往”题材的作品。明代中晚期士人狎妓风气兴盛,故这类题材在明代并不鲜见,较为典型的有明代中期唐寅所绘《陶榖赠词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3)以及吴伟《歌舞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等。唐寅侧重于向观者传达出一种暧昧的意涵,无论是士与妓所身处的私密空间的营造、人物间的互动以及诸多细节的安排上均可见出;吴伟虽用单纯的白描画法,但也注重表现文士对女妓活动的关注及歌舞场景内的放纵浪漫气息。[12]若将《升庵簪花图》置于此类“士妓交往”题材的作品中来看,观者可明显感受到陈洪绶对此题材作出的不同处理:首先,画面中升庵与女妓所身处的不再是画家刻意营造的封闭而私密的空间,画面中除中景比例较大的人物外,仅有前景的山石和远景的古树,这种开放式构图使观者可对画中的人物活动一览无余。其次,画面中杨慎虽因醉酒而面色泛红,但他表情肃穆,踽踽前行,身后二女妓一捧酒尊一执羽扇随行,杨慎与其二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没有任何互动交流,但在唐寅与吴伟的作品中士人多暧昧地注视着女妓。

图3 《陶榖赠词图》轴 明 唐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有“东山之癖”,那么此幅表现“升庵携妓游行”的图画不难让人联想到明代流行的“谢安携妓游东山”题材的作品。收藏在日本彦根城博物馆的《谢安东山图》轴(图4-1),画面中谢安回头与身后两位打扮华丽的女妓交谈,互动亲昵。郭诩的《东山携妓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4-2),画中谢安昂首前行,胡须随风飘动,女妓紧靠在谢安身后,且女妓之间仿佛在相互谈笑交流,使整个画面凸显一种纵情不拘之感。沈周(款)《临戴进<谢安东山图>》(上海博物馆藏,图4-3)中策杖而行的谢安面露微笑,随行女妓们衣着华丽,左顾右盼,谈笑风生,亦表现出一种闲适自在的气氛。虽然同为游行中的士人与女妓,但两名女妓只作普通侍女一般的安排,陈洪绶并无意强调升庵与女妓之间的亲昵互动,以及由此所展现的升庵放浪不拘的狂士形象,反而着重强调了其有节制的苦闷形象。

图4-1《四季山水图之东山携妓图》轴 明 滋贺县 彦根城博物馆藏

图4-2《东山携妓图》轴 明 郭诩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3《临戴进<谢安东山图>》 明 沈周(款) 上海博物馆藏
画面中升庵前行至树下驻足,其姿态与背景之树及前景山石所呈现的位置关系,从图式溯源,可以连结至画史中塑造高士形象的“树下人物”图。此类图式较为早期的如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中七贤与荣启期就分别坐于银杏、松、柳、槐等树下,表现出不拘礼教的各种姿态。后来的唐墓壁画中出现了树下站立或行走的高士,如唐韩休夫妇墓中的高士壁画(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图5)以及山西地区的唐代墓室屏风画,画中老人(或男子)均褒衣博带,侧立于树前。宋代,“树下人物”组合成为一个更为熟悉的绘画样式:树的位置被置于画面一侧,通常由画面右下角向上延伸至整个画幅中间,画面前景通常安排山石与溪流,人物被安排在画幅中间,或立、或坐、或卧,如传为北宋许道宁的《松下曳杖图》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表现一位衣带飘举的高士于松树下持杖驻足,这种图式还多见于表现东晋隐逸诗人陶潜的作品中,如传为南宋梁楷的《东篱高士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6)绘凝神品花的陶潜于松荫之下飘然徐行,明初取法南宋院画风格的杜堇,其《陶潜像》[13](图7)亦受此图式的影响。梁楷与杜堇画中陶潜面向画幅左前方以四分之三侧面面对观者前行,与《升庵簪花图》中杨慎前行角度较为相合。在《升庵簪花图》中,由于陈洪绶要安排随行的两名女妓,故他将树的位置挪至画幅左后方,使其自左向右上延伸,以保持画面的稳定性。这种构图与杜堇所绘同为表现“树下高士”题材的《陪月闲行图》轴(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图8)中对背景之古树安排极为相似,《陪月闲行图》主要表现了宋代诗人林逋月下策杖行吟之情景,巧合的是《升庵簪花图》中前景的山石布置也与杜堇此画相似(图9)。以“树下人物”图式来塑造高士形象在陈洪绶作品中并非孤例,如晚期作品《摘梅高士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图10)及《为豫和尚画》册之《高士临流》页(美国檀香山美术学院藏)等。

图5 韩休夫妇墓高士壁画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6 《东篱高士图》轴 宋 梁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7《陶潜像》明 杜堇 藏地不明

图8 《陪月闲行图》轴 明 杜堇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9 《升庵簪花图》轴(局部)明 陈洪绶

图10《摘梅高士图》轴 明 陈洪绶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在表现陶潜形象时,梁楷与杜堇画中都以松树作陪,这是一种程式化搭配, 以便让观者借由图像便想起他《闲情赋》中所写“翳青松之余荫”[14]的诗句。而杜堇在表现诗人林逋时,则将背景树木换成了与林逋“梅妻鹤子”传说相符的古朴的梅树,观者便不难想起林逋《山园小梅》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与《艺苑卮言》所记不同的地方是,《升庵簪花图》中陈洪绶刻意不作升庵“游行城市”的安排,仅以一棵苍劲的黄叶树(或为枫树)作背景,黄叶一般代表了对季节信息的传达,升庵头上所簪之花有菊花,也与秋季相合,与杂剧中升庵“游春”、“伤春”的季节设置不同,陈洪绶作秋天的渲染是否有特殊的隐喻?与陶潜、林逋同为诗人的杨升庵是明代复古文学思潮的先导李东阳(1447-1516)的门生,李贽《续焚书·修撰杨公》记杨慎十二岁时曾作《霜叶赋》,且“一日偶作黄叶诗,李文正公(笔者注:李东阳)见之曰:‘此吾小友也!’乃进之门下”[15]。对比陶渊明与松及林逋与梅的搭配,陈洪绶刻意安排了这棵秋天枯老的黄叶树以衬托升庵年少时的才情与中年遭遇的无奈。
除图式外,从人物形象与技法风格上也能看出陈洪绶对升庵所做出的“高士化”处理。陈洪绶自题中写道升庵是“双丫髻簪花”,根据古代的礼仪,未成年男女,头发多作小丫角,称为“总角”或“丱角”,且杂剧《簪花髻》中升庵因男扮女装游春提出“我将秃莺儿挽一个双丫髻”[16],所以“双丫髻”应是表现杨慎放浪形骸的狂士形象的重要情节,但陈洪绶似乎有意在弱化这个情节,画面中杨慎的双丫髻并不明显,观者仅能根据杨慎头上盘在一侧的单髻以及所簪之花来想像他的双髻,而这与陈洪绶对“胡粉傅面”情节的舍弃一样,似都在淡化表现升庵的放浪形骸与癫行放诞。
画中升庵高大壮硕,身着传统魏晋高士滚以黑边的宽袍,前襟两侧的带子在胸前结扣,这种服饰是根据唐宋高士图题材作品中人物所着外衣变化而来,与梁楷《东篱高士图》轴中陶渊明外衣相似。与以上塑造陶潜、林逋等人衣袂飘举、意出尘表的潇洒之态不同,升庵所着袍袖下垂不受风,衣纹轮廓线及褶皱处以流畅、秀劲且粗细均匀的铁线描勾勒,这与张庚《国朝画徵录》中“洪绶画人物,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兼有公麟、子昂之妙”[17]的说法相符。以铁线描绘衣纹,风格整体圆转,但升庵衣袖下端有一些方折的用线,这种如铁丝般紧劲连绵的线条使人物显得肃穆凝重,将升庵赋予了极为高古的精神气质。为与升庵的高古气质保持一致,陈洪绶亦以“晋唐古意”的风格来表现随行的两名女妓:此二人身材瘦削,高腰长裙曳地,脚着高履,腰缀饰品,长弧线的运用展现了女妓优雅娴静的气质,整体风格古朴素雅(图11);且一人捧尊另一人手执鹅毛扇抄手侧立,目光随微微上扬的头部呈仰视,这与出土的一些唐代墓室壁画(图12),以及棺椁石刻线画中以“铁线描”所表现的侍女形象[18]极为相近(图13),古朴素雅的女妓形象衬托了升庵的高古气质。

图11 《升庵簪花图》轴(局部)明 陈洪绶

图12 唐 《宫女图》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前室东壁

图13 唐 《仕女图》章怀太子墓石椁内部线刻画
三、高士的“狂士化”与陈洪绶的“狂士”身份
从图式与技法风格来看,《升庵簪花图》中陈洪绶是以传统高士的形象来表现晚明失意文士群体认知的风流、狂诞的杨升庵,将升庵的狂士形象“高士化”了。那么陈洪绶此举为何?单纯的高士形象是否是同为失意文士的陈洪绶个人对杨升庵的认识?

图14 《史实人物图》卷(局部) 明 陈洪绶 藏地不明

图15 《渊明故事图》卷 (局部) 明 陈洪绶 美国檀香山美术学院藏
陈洪绶绘画生涯中不只一次的以“升庵簪花携妓”之题材作画,其后期作品《史实人物图》卷中第四段(图14)所绘亦是。与《升庵簪花图》轴中“高士化”的升庵形象不同,陈洪绶有意还原了晚明失意文士群体所认知的升庵的狂士形象。观者可通过双丫髻及簪花行为毫不费力地辨识出所绘人物即为升庵,且所簪之菊花下垂至背部,更加突出了升庵“双丫髻簪花”的情节。升庵身前飘起的衣带在整体下垂的衣袍的对比下显得格外明显,不似《升庵簪花图》轴中升庵形象的肃穆。人物位置亦不再是升庵踽踽独行,女妓作普通随行侍女那样安排,画面中两名女妓在前,一捧托盘,内置瓶插菊花及酒壶,另一女妓则正在弹奏琵琶,升庵与一名手持黄叶树枝的女妓随行其后。画面中升庵一手握空酒觚,另一手则伸向前方似在索要壶中之酒,升庵与女妓之间的亲昵互动展现了其在礼节法度之外的狂放不羁。因此,陈洪绶个人对杨升庵的认知并非仅是单纯的高士形象,他亦有从其所属群体的视角上对升庵狂士形象的认识。

图16-1《人物故事图》册之“升庵簪花”页 清 陈字 故宫博物院藏

图16-2 同上,“渊明饮酒”页

图16-3 同上,“孟浩然寻梅”页
陈洪绶似乎有意在其人物画中对狂士与高士形象进行相互借用,在一些描写隐逸高士形象的作品中可见其在人物形象上做出的“狂士化”改变,使之减弱了画面本身原所营造的高人逸士的风采。如表现传统高士陶渊明的《渊明故事图》(美国檀香山美术学院藏)中“采菊”“种秫”“无酒”“解印”“却馈”“行乞”等段,皆可见渊明形象的高古奇骇却又狂放不羁。“无酒”段(图15-1),被其子与门生以篮舆[19]抬行的陶渊明头上簪菊。“种秫”段(图15-2)乃陈洪绶自创[20],旁题“狂药中人,何须得食!”以及渊明夸张的手势及身姿动态都给观者带来一种狂傲的视觉体验。那么,陈洪绶在其作品中对狂士与高士形象进行相互借用的原因是什么?
明代中晚期,阳明学派及其后学[21]所推崇的“狂者胸次”[22]理论在李贽、屠隆、袁宏道等的推动下继续发展,在“世俗生活中,在市民社会与自我边缘化的士人中”[23],率性所行,纯任自然的“狂士”被标举至崇高地位。而这与晚明士人着重凸显升庵谪戍云南后的颠行放举互为表里。陈洪绶生活在这个时代,亦追求适性疏放,不受拘束的生命形态。陈洪绶好女色,喜纵酒、狎妓,早年曾以“狂夫”自称,曾谓:“不守牖下而老死,得行歌山泽、沉湎声色……放浪辄庆其幸也。”[24]又曾言:“少壮太平时,身为酒色制。”[24]67在《五日观妓》诗中陈洪绶自己写到“佳人索我赏花诗,偏我吟诗醉酒时。放宕不拘吟数绝,座中笑得傍花枝”。[24]344后人有以“畸士”为称,周亮工记其“性诞僻,好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25]。张岱《陶庵梦忆》中载,陈洪绶曾于西湖断桥边挑戏女郎之风流韵事[26];周亮工与毛奇龄皆记陈洪绶多“为贫不得志人作画,周其乏”[25]672,且“豪家索之千缗,勿得也。尝为诸生,督学使索之,亦勿得”[25]663。朱彝尊记其尤好为女妓作画“客有求画者,虽罄折至恭,勿与。至酒间召妓,辄自索笔墨,小夫稚子无勿应也”[25]665。巧合的是,朱彝尊所记陈洪绶“酒间召妓作画”与晚明士人所记升庵“醉墨淋漓女妓裙袖”一事极为相似。即使是甲申之变后,陈洪绶依然“纵酒狎妓如故”[25]665,晚年“栖迟吴越,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绶亦自以为狂士焉”[25]659。这些都反映了陈洪绶赋性狂散,怀才自放的一面。陈洪绶的狂放行为与晚明失意士人赋予升庵“纵酒、簪花、携妓游行”的狂士形象是相似的,而陈洪绶亦在杨升庵的狂士形象中找到了自我投射,故而其绘画生涯中不止一次的以“升庵纵酒、簪花、携妓游行”之题材作画。
但另一方面,陈洪绶还是一个出身于仕宦之家,习八股、举子业的儒生。他跟随着父辈的传统,以功名为志,不断追逐传统读书人“仕进用世”的理想,具有对文人士大夫崇高身份的企慕以及“显亲而继祖,致君而泽民”[24]74的期望。当陈洪绶以画艺被召为内廷供奉后,他自感用世理想的破灭,而后其师黄道周、刘宗周等人相继遭到贬黜、革职,直至经历甲申之变的亡国之痛,使得陈洪绶“伤家室之飘摇,愤国步之艰危”[25]660,故而绝意仕进,托诸诗文书画抒发其胸中磊落之概,纵酒使气,佯狂避世。他的颓然自放,是如同传统高士那般仕进不得则隐逸山林,杖履琴书,悠然自适的自我谴怀。在陈洪绶看来,狂士与高士有着相同的情感及精神特质,二者皆怀有仕进之抱负却无法在其所处之现实施展,继而追求一种自我回归的适意,一为隐居避世一为佯狂避世。故宫博物院藏陈洪绶之子陈字所绘一套人物故事册页中,亦有一页表现了升庵簪花携妓游行之事(图16-1),同套册页中还绘有陶渊明(图16-2)、王羲之、刘伶、孟浩然(图16-3)、米芾、苏东坡等或为高士或为狂士之轶事。陈字之画艺深受其父影响,其将升庵的形象与传统高士与狂士并置,亦可反映其父陈洪绶在高士与狂士身份认识问题上的影响。正如晚明袁中道所示:“狂者,是资质洒脱,若严密得去,可以作圣。既至于圣,则狂之迹化矣。”[27]这也就不难解释杨升庵作为引起陈洪绶情感共鸣的理想化文人,在塑造其狂士形象时融入的高士化特征,以及在塑造陶渊明等传统高士形象时引入的狂士化特征了。
四、结语
《升庵簪花图》是明代中晚期除人物品鉴类史传、戏剧传奇等文本之外,以图像来塑造杨升庵狂士形象的一种方式。而陈洪绶作为标举狂狷人格,追求适性疏放的晚明失意士人,却并未按照其所属群体集体认知的那样强化升庵谪戍后的颠行放举,将其塑造成任气使才、放浪形骸的狂士形象。这是因为在陈洪绶看来,狂士与高士有着相同的情感及精神特质,二者皆怀有仕进之抱负却无法在现实中施展,继而追求一种自我回归的适意,一为隐居避世一为佯狂避世,二者殊途同归。因此陈洪绶借用了唐宋以来表现高士的“树下人物”图式并结合其人物画善用的高古游丝描,将升庵进行了“高士化”的塑造,使其具有了如高士一般的精神特质。后人常见其笔下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却不易见出隐藏在高古奇骇外表下的内在精神特质,正如其所言:“老迟幸而不享世俗富贵之褔,庶几与画家游,见古人文,发古人品,示现于笔楮间者,师其意思,自辟乾坤。”[24]26在晚明狂士形象的塑造上,陈洪绶确实是自辟乾坤的,这也是陈洪绶作为晚明人物画家最值得称赏的地方。
注释:
①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 年)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后任经筵展书官、殿试掌卷官等职,参与《武宗实录》的修撰。其父杨廷和曾任明武宗、世宗两朝首辅。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 年),因“大礼议”事件,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终身不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卒于永昌。
②笔者暂未找到两方鉴藏印的所属者,2007 年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秋季艺术品拍卖中清代允禧(1711-1758)《山庄清晓图》外签有“慎靖王山庄清晓图,清羣簃鉴藏”,且画心钤有“清羣簃鉴藏”印,可知印主人与陈洪绶并非同时代人。参见:倪葭:《沈周<仿倪云林山水图>的流传与影响》,全文刊于《中国书画》,2017 年第5 期,14 页。
③李维琨认为此画约为陈洪绶崇祯十六年(1643 年)所作。参见李维琨:《中国巨匠美术丛书之陈洪绶》,文物出版社,1998 年,6 页。陈传席:《清圆细劲·润洁高旷——陈洪绶的人物画》,《陈洪绶研究:朵云》(第68 集),19 页。
④《毕节见滇老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白首话青春。不须更奏琵琶曲,司马青衫泪满巾。”《升庵遗集》卷17,《杨升庵丛书》,第三册,天地出版社,979 页。
⑤谢安(320-385),东晋人,字安石,号东山,浙江绍兴人。后出仕为宰相,因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败前秦而名垂青史。
⑥时人对升庵纵酒、簪花、携妓游市等诸狂行的另一种看法是“自污以避祸”,明简绍芳撰《赠光录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中“至若陶情乎艳辞,寄意于声妓,落魄不羁,又慎所以用晦行权。匪恒情所易测者也”。《明史·杨慎传》中云:“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第四册),中华书局,2000 年,3385 页。
⑦主要有:焦竑《玉堂丛语》“任达”类,张萱《西园闻见录》、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梁维枢《玉剑尊闻》“任诞”类以及尹守衡《皇明史窃》等。有学者对此曾作系统的整理,参见林宜蓉:《中晚明文艺场域“狂士”身分之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 年,78 页。
⑧任性放诞,语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
⑨戏谑、放荡、轻浮。
⑩沈自徵,字君庸,江苏吴江人。沈璟之侄,国子监生。所作《簪花髻》与《霸亭秋》《鞭歌妓》合称《渔阳三弄》,皆为以失意文人遭遇为题材的短剧,收入(明)沈泰辑编:《盛明杂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