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周春《西夏书》的著者、义例与卷次
——兼与胡玉冰教授商榷
2020-07-23崔壮
崔 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自元廷为前代修史,成辽、宋、金三部而未及西夏,后世遂多有存补阙之念而私修西夏国史之人。仅以《西夏书》为名者,所见便有王昙、秦恩复、徐松以及周春等数种。不过,这些史籍大多已经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周春之手抄残稿约十一卷。据笔者查知,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万州区图书馆均有藏本,而以国家图书馆所藏为最佳。《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曾影印此本行世,胡玉冰教授亦以之为底本著成《西夏书校补》,由中华书局出版,不啻为西夏学界之盛事。然而,目前学界对周氏此书的一些认识,尤其胡教授的相关讨论,依然有进一步研商的余地。
1 关于著者
《西夏书》是否周春所独著,这本不成为一个问题,却偏有学者强起纷争。第一个是邓衍林,他在《中国边疆图籍录》一书中著录有《西夏书》十五卷,题为周莲撰,其下注道:“吴骞序云:松霭先生尝著《西夏列传》,以史氏之阙,顷复续成《世纪》二卷、《载记》五卷、《年谱》一卷、《考》三卷、合萌《列传》四卷,裒然为定书云。”[1]邓氏似乎是将“松霭”当作了周莲。第二个便是胡玉冰,他著《〈西夏书〉考略》一文,作出“编著者不只是周春一个人”的判断,且受邓书题名及注文的启发,创造出“吴骞还认为《西夏书》除《列传》是由周春编写之外,其余部分是周春之兄周莲续作”的观点,并力证“此说可信度很大”。[2]日后,胡教授著《西夏书校补》,在前言中全盘推翻旧日结论,指出邓衍林著录时将“周春”误题作“周莲”,并作出论断“其编修者只可能是周春一个人”。[3]4同一个研究者,面对同一部史籍,前后结论的巨大反差,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邓衍林所引吴骞的《西夏书序》,颇多讹脱之处,正确引文当为:“松霭先生……往尝著《西夏列传》以补史氏之阙,顷复续成《世记》二卷、《载记》五卷、《年谱》一卷、《考》三卷,合前《列传》四卷,裒然为完书。”[4]松霭,为周春之号。民国《海宁州志稿·周春传》载:“周春,字芚兮,号松霭……乾隆甲戌进士。需次里居十余年,笺经注史,旁及百家,刻所著书六种行世。乙酉兄莲举乡试,偕行入都。明年选广西岑溪知县。……丁亥,以父忧去官。……春既归,潜心著述,淡于宦情……遂不谒选。”[5]3337所著书除《西夏书》外,尚有《十三经音略》《小学余论》《代北姓谱》《辽金元姓谱》《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辽诗话》《阅〈红楼梦〉随笔》等。王鸣盛称周氏“博学嗜古,默而好深湛之思,著书等身,名重东南”,[6]当非尽虚誉。据吴骞序文,周春从事《西夏书》之撰述,先成《列传》四卷,后续撰《世记》二卷、《载记》五卷、《年谱》一卷、《考》三卷,遂为完书,共计十五卷。周氏的《西夏书列传自序》云:
“嘉庆甲子仲夏既望,见诂经精舍课题,思欲撰《西夏书》,五旬而藁粗具。正效橐悲巴之蛰,俄求龙树之方。未暇讨论,因之中辍。窃念他史莫难于志,而《夏书》惟传最难,列传既完,全书易就。但乞钞胥两手,何需藩溷十年?乘炳烛之余光,先成四卷;备西朝之霸史,愧乏三长。缀集旧闻,搜罗逸典。访壬戌无名之记,烬简罕传;吊中兴李夏之都,荒墟安在。聊比崔鸿、萧方等之作,且补孙巽、刘温润之亡。所冀博雅通儒,摘暇纠缪云尔。”[7]
嘉庆甲子即嘉庆九年(1804),是周春受阮元之聘、任海宁安澜书院院长的次年,[8]这年仲夏,周氏见到诂经精舍课题,因有此著。其道“五旬而藁粗具”,当指全书之稿而言,由此足见周氏对于历史文献的熟知程度。周氏辑稿时恰值仲夏,因寻求释家的修行之道而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致使史稿“未暇讨论”。①周氏又说:“窃念他史莫难于志,而《夏书》惟传最难,列传既完,全书易就。”凸显出其在史学方面的卓越识见。于是他先撰成《列传》四卷,《世记》等十一卷则为日后续成。
考之国图藏本《西夏书》抄本,先为四卷《列传》,前录《自序》即为列传之序而非全书之序,《自序》题名下有小字注云:“先欲单行,故有此序。”[7]由此可知,所据以抄录之《列传》文,为周氏预备单行之本。续抄之《载记》与《考》部分,题名为“《西夏书》卷之X”,则显然所据以抄录者必为预备编制成完书之本。那么为什么抄者不全据完书抄录呢?当是周春生前未能及时通订全书所致。胡玉冰教授所发现的题名不一、卷次抵牾现象就是由此而来,《西夏书》撰者非一人之论纯属子虚乌有。作为周春著《西夏书》的唯一见证人,吴骞不仅为之撰《西夏书序》,而且在《西夏书列传》初成时即曾寓目,有《松霭大令以西夏书列传见示率题三体》之作,其三云:“果庄缚后肃西邮,史笔霜寒廿二州。若比崔鸿方等例,不妨追配号阳秋。”[9]可见吴氏确对周春著史一事深悉无遗,其言必可信。
关于周莲作《西夏书》一说之伪,在此还需补充两点。其一,将周莲与周春混淆,并非个例,《清稗类钞·鉴赏类》“周玉井藏书于著书斋”条载:“周莲,字予同,又字芚兮,号玉井,又号松霭,晚号黍谷居士。”[10]这是将周春的字号全部混入周莲名下,邓衍林见吴骞序称“松霭”便以为周莲,或许就与此有关。其二,民国《海州志稿》卷十四《艺文志·典籍十二》载:“周莲,文在子,字予同,号玉井,乾隆乙酉举人,授中书科中书,早卒。”[5]1575周春初撰《西夏书列传》时在嘉庆九年(1804),时年已七十五岁,吴骞序更谓其“虽寿登耄耋,神明不异少壮,望之若仙”。[4]周莲为周春之兄,既“早卒”,其时必已久殁,安有与撰、续撰《西夏书》之可能?是故周春独撰《西夏书》当无可置疑。
2 关于义例
《清史稿》卷四八四《吴任臣传》:“吴任臣,字志伊。志行端悫,强记博闻,为顾炎武所推。……《十国春秋》百余卷尤称淹贯。其后如谢启昆之《西魏书》,周春之《西夏书》,陈鳣之《续唐书》,义例皆精审,非徒矜书法、类史钞也。”[11]是以周氏所著足与吴、谢、陈诸书相提并论,皆“义例精审”之作,未可以史钞目之。“义例”指著书的宗旨与体例,二者虽各有其内容,却紧密相关,“例”以“义”起,“义”由“例”显。就周春著《西夏书》而言,最大的“义”大概就是他在《西夏列传自序》中所说的“备西朝之霸史”。何谓“霸史”?《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史部均设有“霸史”类,《隋书·经籍志》释之曰:“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12]《旧唐书·经籍志》述四部分类之详,更为简明地解释道:“霸史,以纪伪朝国史。”[13]是以其志经籍,径改“霸史类”为“伪史类”,《新唐书·艺文志》亦同。可见,周春并未打算将正统王朝的地位赋予西夏。基于此“义”,周氏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纪传体之“例”来安排西夏历史的内容。
胡玉冰教授曾指出:“自宋迄清,西夏一直被‘正统'封建政权视为偏霸政权,史家也多持这样的观点,故在史书尤其官修史书中述及西夏历史时不采用和其他‘正统'王朝历史一样的‘正史'体裁即纪传体形式,以示区别。周春显然想对此有所突破,要用纪传体来编修西夏历史。”[3]12胡氏认识到《西夏书》外在的纪传体体裁,却未能深察其内在的体例设置的“霸史”用意,致使所论显然失之妥当。今存周书的抄本仅存三体,即列传、载记与考,其中最能凸显其用意的便是这“载记”一体。我们知道,一般纪传体史书纪皇帝之事多称“本纪”或“纪”,而周书却以“载记”之名编西夏历代君主之年,这种名称上的差异所展示的正是僭伪与正统的区别。胡教授认为周春撰“载记”参考的是《晋书》的编纂体例,而殊不知“载记”一体首创于《东观汉记》。实际上,探寻周氏撰史体例之渊源不论是上溯至《东观汉记》抑或《晋书》,都不太准确,因为二史所记之对象都是九州之全史,除“载记”外又各有帝纪存在。
周春真正的效法对象很可能是北宋时期胡恢所著的《南唐书》。该书亡佚已久,虽内中详情不可尽知,但其以“载记”之名纪南唐三主的编撰特色早为世人所明悉。苏颂曾有《与胡恢推官论〈南唐史〉书》一文畅论此事:
“仲尼曰:‘必也正名。’……今足下题三主事迹,曰《南唐书》某主载记者,得非以李氏割据江表,列于伪闰,非有天下者,故以‘载记’代‘纪’之名乎?夫所谓‘纪’者,盖摘其事之纲要,而系于岁月,而属于时君,乃《春秋》编年之例也。史迁始变编年为本纪。秦庄襄王而上与项羽未尝有天下,而著于本纪。……以是质之,言‘纪’者不足以别正闰也。……所谓‘载记’者,别载列国之事兼其国君臣而言,有正史则可用为例,故《东观记》著公孙述等事迹,谓之‘载记’。而《晋书》又有《十六国载记》,盖用其法也。足下必以南唐为闰位,自当著《五代书》后,列云‘李某载记’可矣。今曰《南唐书载记》,似非所安也。”[14]
苏颂一语道破胡恢撰“《南唐书》某主载记”之用意:“得非以李氏割据江表,列于伪闰,非有天下者,故以‘载记'代‘纪'之名乎?”可谓目光锐利。然而,他对胡氏的做法并不以为然,称“似非所安”。其理由有二:第一,范晔《后汉书》不仅有“帝纪”,而且为皇后撰“纪”,因此“言‘纪'者不足以别正闰”;第二,所谓“载记”是“别载列国之事,兼其国君臣而言”,其例当用于“正史”之中而不可单用,如《东观汉记》《晋书》之法。苏氏之论颇为通达,故至陆游再撰《南唐书》时,谓:“苏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为本纪。”[15]
至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馆臣对陆游的解释并不买账,连同苏颂之论也一并驳斥。陆氏《南唐书》之提要云:
“胡恢从《晋书》之例,题曰‘载记’,不为无理。游乃于烈祖、元宗、后主皆称‘本纪’。且于烈祖论中引苏颂之言,以《史记》‘秦庄襄王’、‘项羽本纪’为例,深斥胡恢之非。考刘知幾《史通·本纪篇》尝谓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各隶本纪。又称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诸侯而称本纪,循名责实,再三乖谬。则司马迁之失,前人已深排之。而游乃引以借口,谬矣。得非以南渡偏安,事势相近,有所左袒于其间乎?”[16]588
《总目》支持了胡恢的做法,称其“不为无理”,又以刘知幾在《史通》中的言论为依据否定了苏颂的观点,并揣度陆游撰述之意道:“得非以南渡偏安,事势相近,有所左袒于其间乎?”平心来看,对作者之意的揣度,苏氏正中其的,而《总目》颇嫌过当;对本纪之撰否与正闰之判别的看法,苏氏多探本之论,而《总目》则难免堕入后世之俗见。章学诚曾称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17]887谓其论史常“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17]21《总目》引刘氏之言以辨胡、陆之是非,则正与刘氏同堕入不知其意而轻诘古人之境。对于周春而言,官方修撰之《四库总目》的史学批评无疑更加具有权威性,于是以“载记”为名辑君主之事实成为其撰述西夏霸史的最佳选择。与周氏约略同时的史学名家赵翼亦以为:“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18]
载记之外,周春还设有“世记”。胡玉冰认为《西夏书》此例是对《金史》“世纪”的效法,[3]13当不误。不过,若追根溯源,先秦之《世本》,《史记》之《世表》《世家》,及魏晋时期之《帝王世纪》《袁氏世纪》当为“世纪”命名之源;魏收《魏书》之《序纪》,李延寿《北史》之《魏先世纪》为追封之前世设篇立纪的做法则发《金史》创设“世纪”体例之先声。②略早于周春,乾隆间学者郭伦曾撰《晋记》有“世系”一卷,记未入晋之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史事,《四库全书总目》称“司马懿父子改为《世系》是已”。[16]460至于“年谱”与“考”二例,当即正史中之“表”与“志”也,其名盖仿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司天考》《职方考》以及《十国世家年谱》。《考》三卷,亡其一,并名目亦不可知。《年谱》亦亡,据笔者揣测,有可能是辽、宋、金、夏四国纪年之对照表。
3 关于卷次
今存《西夏书》残钞本,仅存三体,依次为《列传》《载记》《考》。就卷次而言,前文已述,钞本实为两种编次体系即《西夏书列传》本与《西夏书》完书本的拼接。研究者不察,遂以为这就是原书的编次方式,李蔚《周春〈西夏书〉评介》称:“将列传放在本纪之前,这不能不算是该书在体例上的一大特点。”[19]胡玉冰校补《西夏书》将钞本之卷次重新梳理,依然将《列传》置前,其后为《载记》《考》,仅仅改原“西夏书列传卷之X”与“西夏书卷之X”的混合状态为一律,即全部依照后者编次。我们知道,《西夏书》之“载记”实为“本纪”的更名,自《史记》创设纪传体以来,安有述一国之事,以臣传居君纪之前者?此外,“本纪”与“列传”非但是君臣、尊卑的关系,更是一种经纬编纂原则的体现,如章学诚认为“纪之与传”,“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17]948-949本纪是全书的纲领 (即“经”),世家、列传、志、表均为本纪之“纬”,“经纬相宣以显其义”,[17]428纪传体的最大妙处便在于此。周春的《自序》称“《夏书》惟传最难,列传既完,全书易就”,所言只是撰述的先后,而非全书编排的次序。
前引吴骞《西夏书序》云:“松霭先生……往尝著《西夏列传》以补史氏之阙,顷复续成《世记》二卷、《载记》五卷、《年谱》一卷、《考》三卷,合前《列传》四卷,裒然为完书。”这段话除《列传》所言为撰述次序外,“《世记》二卷、《载记》五卷、《年谱》一卷、《考》三卷”已然暗示着部分编次的情况。考国家图书馆藏本《西夏书》,残存之《载记》与《考》的卷次如下。
西夏书卷之四 载记二
西夏书卷之五 载记三
西夏书卷之六 载记四
西夏书卷之七 载记五
西夏书卷之九 地理考
西夏书卷之十 官氏考
《世记》所载为西夏君主之先世,依照常例必在《载记》之前,《年谱》为“表”例,《考》为“志”例,依照《史记》《汉书》之先例,“表”在“纪”之后、“志”之前,如是则恰与吴骞之序相同。“列传”则当殿末。那么,《西夏书》全书之卷次可补足为(加粗字体为补目)如下。

西夏书卷之四 载记二
西夏书卷之五 载记三
西夏书卷之六 载记四
西夏书卷之七 载记五

西夏书卷之九 地理考
西夏书卷之十 官氏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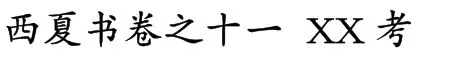
西夏书卷之十二 列传一
西夏书卷之十三 列传二
西夏书卷之十四 列传三
西夏书卷之十五 列传四
显而易见,这种对于《西夏书》卷次的补订与抄本残存之完书编次并无冲突龃龉之处,且符合传统历史编纂之常例。
4 余语
胡玉冰教授的《西夏书校补》虽然在体例上尚有欠缺,但其广泛钩稽西夏史料,补苴阙卷佚篇(残缺之《载记》、亡佚之《世记》)之功实不可没。今人聂鸿音先生又成《补〈西夏艺文志〉》一文,“据古今中外撰述补出《西夏艺文志》子部释教类的汉文书目,以及其他各部的夏人译撰,包括经部二十二种、史部九种、子部三十七种、集部六种,共计七十四种”,[20]方使该志稍具形状。傅增湘先生尝谓:“傥有褚少孙、班昭其人者,因而足成之,以备霸史之一,庶无负松霭露钞雪纂之苦心乎?”[21]笔者于今谓:若有贤学者能深探周春撰述之意,本清人补阙求全之精神,立足胡氏《西夏书校补》、张氏《年表》及王、聂二先生之《艺文志》,以《年表》补《年谱》之阙,以《艺文考》足原《考》三卷之数,完其十五卷规模,使《西夏书》破镜重圆,将非但故作者周春之幸,更乃西夏学界之幸、中国史学之幸。
[注释]
① 周春对于释家之学颇有钻研,曾“遍观藏经六百余函”,著《佛尔雅》八卷。(参见梁晓虹的《周春的〈佛尔雅〉》,《辞书研究》1991年第1期,第97页。)② 赵翼认为《金史》“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乃“仿《尚书世纪》之名”。(参见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页。)实际上,上古并无是书。(参见王玉德的《先秦〈世纪〉献疑》,载《文史》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