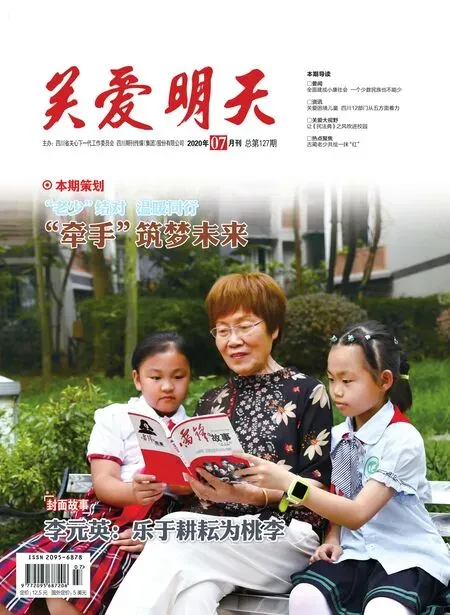常开明:追忆岁月话巨变
2020-07-22莫尔佳
文/图 本刊记者 莫尔佳

常开明向记者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8年前,在自己退休时撰写的回忆录《足迹》里,常开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6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个人的经历,却是漫长而艰辛。
常开明现任崇州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尚在职时,他便加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战线中来,迄今已有17个年头了。在他看来,人生宛若一本书,有时精彩,有时平淡,有时耀眼,有时平凡。几十年时光过去,常开明从一名吃饭都要数着米粒的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战场上镇定自若的优秀指挥员,再从纷纷战火硝烟中走到地方,踏上平凡的工作岗位,退休后,又发挥余热,投身到关爱事业中。
这名年近古稀的老人,回忆往昔,点点滴滴,物是人非而不悲叹,逝水流年而不沮丧,他坦然面对生活和时光,也感恩祖国发展带来的幸福晚年。
贫苦童年 艰辛求学路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适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候,才7岁的常开明,总爱沿着田埂,去拾捡那些播种撒谷子时散落的谷粒。“我把谷子捡回来,一颗一颗剥开。我专门去称过,1两米呀,大概有1100粒。”回忆起这段往事,常开明在好笑之余,又露出几许唏嘘。
常开明出身于梁平县(现重庆市梁平区)一个穷苦的农村家庭。家中虽穷,但自小热爱读书的他却很争气。小学考初中时,他以县内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了梁平中学。“在当时那可不容易。”常开明说。
尽管考上了初中,但学费却让常家犯了难。“我们一学期的费用是6元钱,”常开明回忆道,家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虽然学校给常开明评了助学金,每学期有两元五毛钱的补助。“可剩下的三元五毛钱我还是交不起呀。”于是,学校就把像常开明这样交不起费用的孩子集中起来,“在另一个屋子吃饭。”学校给这些孩子提供的伙食,只有米饭没有菜。“一块豆腐乳就是三天的菜了。”常开明记得很清楚,自己用三分钱买一块豆腐乳,每顿饭“就刮一点点”,他笑着说,“有点味道就行,这样饭就吃下去了。”
那时候,每周上课六天。平日里,常开明在学校住校,周日则赶回家里,“帮着做一天家务。”常开明的家距离学校有13里路,为了能赶上周一早上的早读课,每周一,他总是凌晨3点起床,匆匆往学校里赶。“要走一截跑一截,走两个半小时才能赶到学校。”当时没鞋穿,冬天也需要打赤脚,“脚上都长冻疮了。”
艰苦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没有影响常开明学习的热情。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却因“文革”而中断,这让常开明终身遗憾。“前不久我都还在给我家属(常开明的妻子)说,要不是‘文革’,我可能就一路高中、本科、研究生甚至出国留学都有可能呢!”他半开玩笑地说。
这遗憾,终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从1984年开始,常开明在部队文化学校,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从初中课程学起,最终取得了大专学历。“可以说是‘五年寒窗无人问’。”常开明说,自己当时“挑起两副担子,进行三个告别,”所谓“两副担子”,是指工作担子和学习担子一肩挑,“三个告别,”则是指“和节假日告别,和电影电视告别,和妻子儿女告别”。“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都在学习。”1998年,常开明又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后来,他在学校和单位宣讲时,总爱开玩笑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小学生,徒有虚名的中学生,自学成才的大学生”。
军旅岁月 血染的风采
1972年12月,刚满20岁的常开明参了军。他自陈“工作40年没离开一个‘部’字”,即“部队”和“组织部”。在1999年转业到崇州市委组织部之前,常开明在部队呆了27年,先后荣立7次三等功。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
1979年1月,常开明所在师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执行紧急作战任务的命令后,立即转入战备状态。2月,常开明与战友们一起,从甘洛县出发,经西昌抵达昆明,之后转乘汽车一路兼程赶至中越边境线。
越过边境线那个晚上,部队在外露宿。常开明躺在铺在地上的方块雨布上,身上盖着毛毯,仰望着星空,久久不能入睡。“我想自己作为连队政治指导员,党组织把100多人交给自己,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思考着如何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去赢得最大的胜利……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在接下来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常开明跟随所在连队先后遭遇了多起战斗。一次,连队战士顺着战壕往山顶上爬时,敌人一颗炮弹在离常开明十多米远的地方爆炸了。一块小弹片从他的嘴角边划过去,鲜血直流。常开明轻伤不下火线,依然指挥部队战斗,占领阵地后,所在连队给予了敌人狠狠的打击。
时隔41年,再次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常开明说:“从1979年1月6日接受扩编命令,到4月20日凯旋回传,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在这段时间的日日夜夜里,我和我的战友们,可以说是经受了苦与乐的生活体验、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和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日新月异“过时的计划”
谈及这些年来新中国的变化时,常开明忍不住笑了起来,“计划赶不上变化。”——他口中的“计划”,是指自己1980年新婚时,和妻子商议的“到2000年存2000元”计划。
那时候,常开明每个月的工资是52元,妻子的工资是30元。“我俩算了算,除开各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存下20元。”常开明一边说一边笑,“一年存200元,10年就是2000元,20年能存4000元,在此期间家里多少还得置办些东西。我俩一合计,觉得到了2000年,有个2000元的存款还是可以的。”为了证明那时候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常开明补充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不少红军老八路,“攒一辈子才攒一二百元钱呢。”
但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快得超出了常开明夫妇的想象。1993年调任团政委时,常开明每月工资300多元;1999年转业时,常开明每月工资1400多元。“二十年前那个存钱计划,早就成了没人提的老黄历了。”2012年退休时,常开明的退休金是每月3700多元,现在也已涨到了7000多元。与节节攀升的收入一同到来的,还有愈发丰富的物资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现在的日子,是真的好啊!”常开明慨叹道。
如今的常开明,过着“充实和惬意”的生活。“我现在每天主要做三件事:一是坚持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二是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体魄;三是做关工委工作,继续发挥余热,关心关爱好下一代。”常开明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