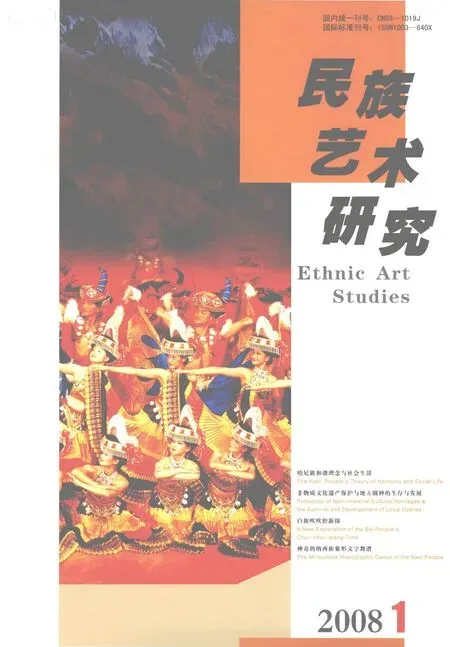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舞思潮巡礼
2020-07-12茅慧
茅 慧
对于舞蹈艺术来说,观念思潮与现实中业态的发展往往扭结、渗透于一体,比较难于剥离、分解,舞蹈的群体性运作方式以及这门艺术独特的人类肢体语言特点,使其思潮的呈现带有鲜明、强烈的实践性、群体性、交互性的特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间舞①本文论及的 “中国民间舞”的概念涵盖民间自然存续的传统舞蹈、都市文化生活领域的群众舞蹈、广场舞蹈以及舞台化的创作加工型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艺术观念、实践理念,总体而言带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印记和特征。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寻根热及 “风情歌舞”创作的喷涌
1984年12月,在杭州召开了 “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文学界的一些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如韩少功、阿城等,共同商讨“文学与当代性”的话题。他们有感于当时文坛出现的盲目模仿西方文艺流派而缺乏自身民族文化根基的现象,认识到这是由于民族文化根基的断裂使然,从而率先提出了 “寻根”的口号,并申明此一 “寻根”不是肤浅的恋古怀旧,而是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和发展层级上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深刻解读,并以建设民族的新文化为宗旨。随之,文学界出现了一批以 “寻根”内涵为主旨的作品。
正是受这一时期文坛 “文化寻根热”思潮的影响,触发了中国舞蹈界的文化意识觉醒,激发了舞蹈界各舞蹈种类的创作演出激情。在一系列对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优秀作品的恢复性演出时,出现了寻根问祖的仿古乐舞、土风熏热的民间舞新作。在舞蹈界的主流媒体上,“舞蹈寻根热”“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生命力”等重大问题也成为中国民间舞理论探讨的热门话题。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和强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覆盖广泛的文化寻根热潮。在文化领域由政府主导行为的一个重大举措,便是 “中国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程在1981年的启动。1981年9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在北京成立。主编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担任,副主编为孙景琛、陈冲。此项工程由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统领,由原文化部系统层层下达文件成立各省、市、县级集成编辑部,建立队伍,每年从财政下拨专款。从田野调查到志书撰写,全国数千人参与了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由于此项工程在全国的全面开展和推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受益于集成工作的成果,许多散存潜藏于民间、从未被官方重视和规模化整理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得以显山露水,走到时代大舞台的前沿。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便陆续在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民间歌舞大会、调演性质的活动。如:1980年的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农民业余艺术调演,1980年9月由原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1982年2月举行的河北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83年的北京市民间花会,1983年的江苏省民间舞蹈会演,1984年的云南省首届民族舞蹈会演,1984年的河南省第五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85年的四川省民族民间舞蹈会演,1985年的广西壮族歌舞节,1987年的首届北京龙潭花会大赛……可以说,一时间民族民间舞蹈之花开遍四方。
随之,以这些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初步挖掘整理成果为基础,全国范围内,以各级文化馆、群艺馆和专业歌舞团体为表现主体的、各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舞—— “风情歌舞”大量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掀起了民间歌舞风起云涌之势。这其中成为全国较有影响力的佼佼者有:1986年由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中涌现了双人舞《元宵夜》,三人舞 《担鲜藕》,群舞 《安塞腰鼓》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民间舞。这些舞蹈皆取材于民间原生形态的舞蹈资源,由于添加了积极乐观、豁达奔放的民族气质,民族风味十足,情感亲切强烈。这些节目凭借电视直播的平台,一夜之间享誉全国。1987年,由山西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风情歌舞 《黄河儿女情》在第五届华北音乐舞蹈节上引起轰动,旋即全国热传。其中的舞蹈《看秧歌》《难活不过人想人》以其特有的西北浓烈的乡土风情,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审美神经,给观众带来一种别开生面、大土大美的艺术享受。舞蹈艺术舞台上从此开始出现一种被专家解读为 “俗美” “丑美” “怪美”的民间样式。这样的舞蹈审美潮流的出现,植根于中国广大民众的根深蒂固的民俗情怀,“俗、丑、怪”为特征的舞蹈美的展示,带着浓烈的土地芬芳以及粗犷豪迈的黄土气息,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这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艺术样式,所以极易引起广大观众的情感共鸣,并得到审美上的认可。
延续着这一依恋于乡舞乡情的民族民间舞奔腾潮流,至20世纪90年代后,在传统民族民间舞的沃野中被养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民间舞蹈创作杰出人才开始出现。张继钢的民间组舞专场 《献给俺爹娘》 (1991年)一炮打响,其中的 《黄土黄》 《一个扭秧歌的人》,将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民生、民情、民风生动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舞动着的肢体中所流淌出的爱爹娘、爱土地、爱国族的深厚情感,感人肺腑。《献给俺爹娘》舞蹈晚会和他随后创作的一系列 “乡舞乡情”类作品,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文艺思潮中寻根动向在舞蹈中的典型体现。
在文化寻根热潮中,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中面临新的时代课题,舞蹈创编者们面对丰富多彩的、千百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56个民族的民间舞蹈,如何去保护、创新?这一问题是中国舞蹈长期探索而仍在破解中的难题,持守民间舞蹈的民间原貌,往往因缺少时代气息和现实要素而显得落后陈旧;而对民间舞蹈的民间原貌加以改动,则极易因断裂了民间舞蹈原貌的根系而变得面目全非,失去民族舞蹈的语言辨识度和历史厚重感,其中的尺度分寸很难把握。
云南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大省,具有丰富的民族舞蹈创作实践经验和卓越的成绩,相对于其他省份的民族民间舞蹈,云南的创作具有代表性。1992年,为迎接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云南举行,云南省组织创作了一台以舞蹈为主的云南民族民间歌舞晚会 (后更名为 《跳云南》)。《跳云南》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期间推出,产生了极为热烈的反响,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彝族舞蹈节目 《跳菜》,其原型是彝族婚礼上的一种喜庆歌舞,由一群男性表演者肩托菜盘,自跳自唱,充满了粗野、狂放的舞蹈风格,令观众交口称赞。据这台民族民间歌舞集锦的创作者之一钱康宁总结,这台歌舞遵循的是 “土、新、美”的原则,“土,即是尽量保持民族民间歌舞的原始形态和基本风格;新,即指节目尽量以1988年以后新挖掘整理的为主;美,就是在保持民间歌舞基本风格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其艺术性和审美价值。”①钱康宁:《云南民族音乐散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71页。尽管 “土、新、美”的创作原则是针对 《跳云南》这一具体作品的,但是其基本结构和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随后的一段时期,都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共同 “默认”的追求,只是在不同的地区,其具体呈现出来的程度有所差别。这一时期还先后涌现了表现东北黑土地风情的舞蹈专场 《黑土地》(1991年),表现东北乡民风情的 《月牙五更》(1991年);表现西北黄土高原风情的 《黄河水长流》 (1995年);表现闽南风情的 《悠悠闽水情》(1995年)、《惠安女》(1996年);表现云南傈僳族风情的 《啊,傈僳》 (1998年)等诗化风情类展示的作品。
应该说,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前所未有地走上了历史的大舞台,走到了亿万人民的眼前,让中国广大观众领略和享受到五彩斑斓、奇珍异卉般的传统舞蹈、民间风情。这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给中国艺术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瞭望世界、胸怀祖国、思想活跃开放、思考客观公正的历史高台,使得中国的舞蹈艺术工作者能够在世界视野、国际框架中深思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生存问题、发展方向和运作机制,在与世界先进的舞蹈文化交流交互中寻找立足之根本、生发之契机。
二、“课堂元素教学法”为学院派民族民间舞创作提供孵化器
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以北京舞蹈学院为核心的中国高等舞蹈教育领域,以培养中国高精尖各类舞蹈专业表演和创作人才的园地里,对各民族原本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民间舞蹈样式,采取的是一种叫作 “课堂元素教学法”的民族民间舞蹈课程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方法首先由北京舞蹈学院许淑英、潘志涛等开拓,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成型,形成了基本的元素提炼方法后,运用于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为主的民族民间舞蹈的提炼整理,并在随后的时间里被不断更新细化,又以北京舞蹈学院在全国舞蹈高等教育中的强大引领作用,波及全国舞蹈院校民间舞教学中。“元素教学”基于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条分缕析的解构进而重构的动机,其思想体系的最终目的,是为原本形态分散凌乱、风格千变万化、表演千人千面等不易系统把握的纯民间舞蹈 (即:原生形态民间舞),归纳提炼出一套能够易于课堂教学传授、有助于为创作者提供形态典型准确的舞蹈基础语汇。具体而言,即 “从纯民间的风格、动态中提取大量可以单独使用的动作素材,使其 ‘元素化’,成为能够遣词、造句的语素。这样,学院派就可以将这些元素作为他们文化理想与文化诉求的载体,在此基础上进行舞蹈剧目的编创。”②金浩:《新世纪中国舞蹈文化的流变》,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52页。
对于这一 “课堂元素教学”方法,曾任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主任的赵铁春有详细的理论阐释:“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创作必须以中国56个民族 (不同区域)的民间舞蹈动作、动律为载体,突出民族性、地域性、民俗性。这是区别种类、净化舞种、族群认同,更是对创作和表演的最起码的评价标准。一、‘扎进去’吃透。必须知道梨子的滋味。1.一个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编导,在其创作之前首先要 ‘扎进’生活或叫作 ‘深入’生活,到某个民族地域中去了解、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2.要真正了解并懂得尊重民族地域的价值取向及宗教 (禁忌)习俗。3.要了解熟知某个民族的心态及追求,要寻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情感、思想和传达方式。4.要掌握 (也包括准确的判断)某个民族地域的风格化的舞蹈动态,要研究它的舞蹈风格、动律特点及动作衔接规律。二、‘浮出来’创新。必须具有思辨联想的头脑。1.一个民族民间舞的编导,首先要对某个民族地域风格动作有较准确的把握,而后应有清醒的头脑使自己跳出来成为旁观者,并冷静地思考,在捕捉、判断、思辨联想中循环往复,在否定和肯定的过程中决定取舍。2.在把握某个民族地域风格动作后,如何将动作、动律因作品需要而变化、发展,重新构筑作品中的动作、动律、衔接、过渡等,但前提是不能破坏主体审美风格,从而形成既属于某个民族风格的动态又符合作品自身独特的动态审美规律的创作。3.编导要具备一定的功力将作品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并运用思辨联想使之创新,创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舞台民族民间舞作品。”①赵铁春:《“DNA”的确认,是与不是之间——我对创作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四点体会》,《舞蹈信息》2005年8月1日。在此所言的 “扎进去”和 “浮出来”的舞蹈创作思想和路线,基本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所倡导的文艺创作要 “深入生活”“高于生活”的路数,核心价值与中心任务是创造代表时代的,即脱胎于传统又高于传统的新的艺术样式,可以说这样的认识和思想在中国舞蹈界是非常强大和普遍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提出了与之明显有别的其他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理论观念。但随着“课堂元素教学”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措施和方法得以实施运行并随之在创作实践中的不断加以应用后,浮现出的问题却也相当明显。首先,当今的舞蹈创作人员由于各种社会、个人、环境种种原因,绝大部分或者无暇、或者无意真正做到 “深入生活”,上述赵铁春的理论建构带有很大的理想色彩;其次,学院教育要为舞台创作服务和提供孵化器的目的,决定了它的思想意识趋于主流和正统,审美指归趋向高雅和精致。而高雅和精致又隐藏着趋同甚至雷同的隐患,以学院审美的单一、统一替换了民间审美、民族审美的自由和多元,进而使得一些创作出来的舞台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充满了提纯过的精致 “香水味”,而流失了丰厚质朴的 “乡土气”。虽然在新时期以来,由 “课堂元素教学法”孵化或者延伸创作出来的学院派民族民间舞也有相当数量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如塔吉克族女子独舞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朝鲜族女子独舞 《扇骨》、苗族女子群舞 《水姑娘》、朝鲜族男子独舞 《残春》、汉族男子群舞 《鼓舞声声》等,但整个中国学院派舞蹈对传统民间舞蹈自然生命体的 “解构”与 “再构”的大一统思路和能动做法,与国际社会对此问题所持有的主流观念和行动原则不尽相同,它是否经得起历史文化和时间长河的荡涤磨砺,的确不得不令人在乐观中审慎。
三、“非遗”观念自上而下的营造与引领下的中国民间舞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各个族群的民族文化遗产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自进入21世纪后,跟我国民族民间舞蹈密切相关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首先在知识界、文化界受到关注,并置于国家软实力的思考建设中推广宣传,进而在全社会产生切实的影响和引领。这一思潮由国际社会和国家上层发起、引领和设计,通过宣传、教育迅速将 “非物质遗产保护”观念普及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其思潮的源头起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确立了国际社会保护人类物质遗产的义务。但人类文化遗产中另一种重要形态,即用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类文化遗产不能概括的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更为严峻地被破坏和快速消亡的现象,日益引起 《公约》各缔约国的关注,最终被提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议事日程。该组织开始对文化遗产做出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区分。并于1982年,在教科文组织内部特别设置了一个管理部门,叫作 “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部门。(后来因受到日本的 “无形文化财”术语的影响,于1992年将其部门改称为 “无形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部门。)
为了弥补 《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11月在巴黎通过了 《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正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中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只是这个建议案中是以“民间创作”来指代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谓。其对民间创作内容的界定,与后来教科文组织和有关文件中对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基本一致。如1997年,教科文组织第2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言》中,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界定,就基本沿用了上述建议案。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了世界各民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全部文化遗产对于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呼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言中提道: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并在宣言中提到文化多样性与人权、文化多样性与创作、文化多样性与国际团结几方面的内容。
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迄今为止教科文组织有关非遗保护最重要的文件。2005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上的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共同构成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国际法体系的骨干公约,体现着当今人类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和对策框架。上述一切,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于21世纪开始在中国兴起的国际思潮背景。
在这一国际文化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2004年8月2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中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随后,2006年9月14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挂牌成立。该机构是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 (中央编办复字 [2006]03号)成立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机构,承担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具体工作,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政策咨询;组织全国范围普查工作的开展;指导保护计划的实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举办学术、展览 (演)及公益活动,交流、推介、宣传保护工作的成果和经验;组织实施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人才培训等工作职能。2007年,原文化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其主要职责为:拟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起草有关法规草案;拟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保护规划;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承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工作;组织实施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承担清史纂修工作。200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大会审议通过在中国建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的申请报告。亚太非遗国际培训中心的成立,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我国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自身贡献之愿望的充分认可,为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对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开展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维护亚太地区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心致力于宣传和推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组织地区性和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活动,提高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会员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能力。
自2006年起,包含着音乐、舞蹈、戏曲、说唱等众多门类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部分项目,年年在国家 “非遗日”前后在各地登台上演,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宣传效果。这些演出中舞蹈类的节目有朝鲜族农乐舞、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基诺族的 《基诺大鼓舞》、蒙古族的 《少女萨吾尔登》、苗族芦笙舞 《滚山珠》、羌族的《尔玛吉》、达斡尔族的 《鲁日格勒舞》、藏族的卓舞 《雅砻春潮》等。还有一些非遗调演,选调非遗表演项目比较集中的省份来进行整台演出的呈现。如2010年2月27日至3月30日在北京举办的 “全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演”,一共调集了 “高原奇葩——青海省专场” “羌魂——四川省专场”“侗歌声声——贵州省专场”“草原欢歌——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专场”“八桂风谣——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场”“多彩哈达——西藏藏族自治区专场”等九台演出,共上演近120个节目。
可以说迄今,由政府为主导、以社会文化主流机构为承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从媒体宣传到剧场呈现而得到空前实践,也成为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舞蹈创作界不断被学术思考和实操面对的热点。而对于中国舞蹈创作领域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与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理念形成了一对同时冲击创作者思想的并头潮。随着一批又一批国家级、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类名录的公布,原本早已是民族民间舞创作者长期关注并熟稔的舞种纷纷上榜,使得创作者在作品中开始既想寻求 “传承保护”的表现样式,又要遵循舞蹈创新的基本规律,处于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要求对民族民间舞蹈原汁原味地保护;另一方面,舞台艺术的规定性、国家文艺方针的创新性要求,现实又要求拿出成果。因此,在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支撑下,出现了一些不成熟的舞台表现:有一些作品中,开始加入老者、长辈的角色,并有其对晚辈、儿孙、后代进行教育和引导的表演桥段,或者穿插一段模拟民间祭祀仪程的表演;有的作品直接在作品的某个段落上生硬地插入一段不经任何处理打磨的原生形态民间舞蹈,将传统民间艺人请上台表演……这些艺术处理手段都尚处于粗放、图解和描摹的低级水平。原生形态舞蹈的当代剧场呈现样式、规律、要义等都还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命题。
经过十余年的 “非遗”文化思潮的浸润和淘涤,“非遗舞蹈”到底应该如何保护和发展,仍然是从理论到实践持续纠缠于舞蹈界思想的命题。近年,“活态保护”“生产性保护”观念又成为 “非遗”语境中的热词,但具体如何在文化工作和艺术实践中实行,秉持怎样的文化观念,将直接影响创作呈现的面貌、文化含量和艺术成色。
从2014年开始,北京舞蹈学院开艺术创作风气之先,推出由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承演的 《沉香》系列,至今已经推出了5部。此系列创意理念最初源于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邓佑玲。她关于传承民族舞蹈文化的倡议,激发起了专业舞蹈院校师生对传承与保护各民族传统乐舞的热情与责任感。在北京舞蹈学院下设的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掌门高度教授的直接指导把关下,《沉香》系列以中国民族民间舞系表演班学生为承载主体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将传统民间舞蹈持有者——民间艺人请进教室言传身教,完成了15个省份、涉及15个民族的40余支舞蹈的集成,其中既有国家级、省市级以及区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包括尚未入选 “非遗”名录但仍然在民间生活中葆有生命活力的传统乐舞种类。《沉香》系列的开展有助于稳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学科根基,是一项依据学科特点,践行当代高等教育文化传承职能、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在 《沉香》第五部公演的开场视频短片中,清晰地阐明了其艺术理念和主张:“《沉香5》依然借助专业性的身体,来呈现不同族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积淀的独特生命体验与精神追求,我们借助当代年轻人的气质,来演绎他们未曾去过的古代与远方,将中国千年舞蹈的气质和美学显示出来,体现我们在这个大时代中的作为与担当。”显然这是一种占尽身体与创想工具优势的 “非遗”保护与传承方式,它的出现直接呈现出舞台上放大化、精微化、提纯化、增强化的视听效果和艺术性的感染力。比如江西南丰石邮村的傩舞 《开山》,20世纪50年代曾经在吴晓邦先生的慧眼识珠下进行过舞台表演,当年吴晓邦先生在表演中加持给这个民间舞怎样的艺术含量,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在《沉香4》中,北京舞蹈学院青年学生金佳文的表演,真可谓灵动飞扬,传神毕至。在民间样式中那些珍贵的、独特的一招一式,被入木三分地继承了下来,并且更强化了其原本不够亮泽的点点闪光。
思潮如水,不是流归此处,便是流向他方。很显然, 《沉香》系列的思路与观念与20世纪前半叶戴爱莲先生的 “边疆舞蹈大会”之观念和创举是遥相呼应的,皆以舞蹈文化持有者身份替换的方式达到对一种新型民间舞样态的建造,此举建造了当代舞蹈文化,以其高超的技艺含量和精美包装名留史册,占据着时代文艺舞台的 “C位”。在如此理念指导下的举措,还包括近年来多次由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牵头主办的 “非遗舞蹈进校园”的系列实践活动等。如今,这一潮流的流向和终局尚无法判断,更难以历史地评价其功过。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许更重要的是思想中的人本精神、多元观念、持守信念的引领。
回望放眼,中国民间舞如滔滔江河,从亘古奔向未来。它传颂着从未间断的中华民族的身体语言,诉说着精彩、神秘、绚烂的历史密语;裹挟着无数代中华儿女的思想观念和创造才情,几度辉煌、几番沉浮,也许不停地讲述它,也是一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