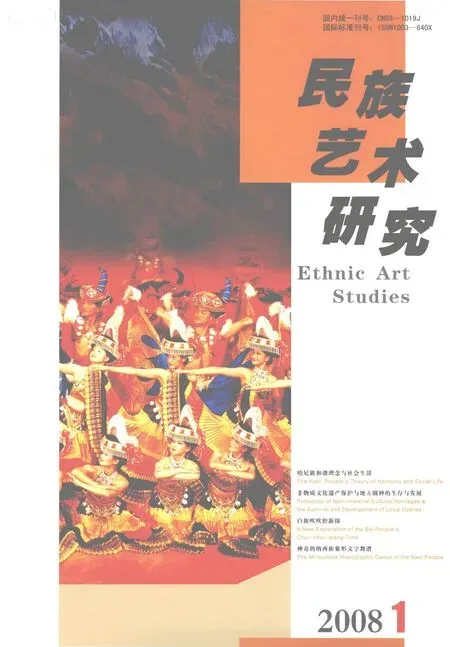国家剧院:当时与当下
2020-07-12马文卡尔森桂菡译
[美]马文·卡尔森,桂菡译
作为全球通用术语,“国家剧院”一词的概念似乎已相当明确,但正如其他被广泛使用的跨民族、跨文化类术语一样,一旦我们对它的具体用法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其所指的数量简直跟存在于世界上的国家剧院实体一样多。当然,对于 “国家剧院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无疑已达成了共识。但事实在于,即便是最为著名的国家剧院也不一定能与其概念完全契合:国家剧院通常是设立在国家首都/首府的纪念性建筑,由政府批准、授权与扶持,其全部或绝大多数作品均为国家民族戏剧。一些国家剧院的创办与运行,严格遵循了这种理想模式;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家剧院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之偏离。分析这些现象的产生原因,可以为我们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国家理念与剧院运营情况提供有趣的见解。本文主要聚焦于欧洲国家剧院,但对基于欧洲理念而发展形成的非欧洲地区的国家剧院情况也予以简单介绍,因为后者对 “国家剧院”这一概念的界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一
“国家剧院”的概念与它所依赖的 “现代国家”的概念一样都起源于欧洲,两者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几年中共同发展。正如洛伦·克鲁格 (Loren Kruger)证实的那样,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和国家剧院的概念与浪漫主义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 (尤其受到18世纪末法国卢梭和德国作家们的影响)。德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剧院的诞生要早于德意志民族一个世纪,由于这一时期人们的重心在于创建德意志民族、形成德国意识,所以这一情形的发生倒也并非匪夷所思。就像莱辛 (Lessing)在 《汉堡剧评》里清晰描绘的那样,这个时期的德国舞台与大部分欧洲舞台一样被法国剧作与法国样式所统领。即便试图上演德国本土化的剧作以取代法国戏剧,但对戏剧感兴趣的德国原民族主义者事实上是在延续一种不为人知的普遍法国模式即法兰西喜剧院的传统。尽管从名字上看不出,但法兰西喜剧院实际上是法国国家剧院的雏形,它由中央政府建立维护,致力于呈现法国主流剧作家作品。18世纪的法国在世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使得许多国家在成立剧院时往往以法兰西喜剧院为原型,尽管这些国家尚处于君主制时期,而剧院的成立初衷也是为了满足君主需求,而非出于国家立法机构要求。其中最为典型的有1741年成立于维也纳的城堡剧院 (Burgtheater)、1748年成立于丹麦的皇家剧院 (Royal Theatre)、1788年成立于瑞典的皇家戏剧剧院 (Dramaten),它们至今仍然是国家剧院的典范。早在1776年,城堡剧院更名为国家剧院 (Hof und Nationaltheater),这一举动无疑是新意识诞生的体现(也不是整个18世纪都会如此,想想今天的英国皇家国家剧院)。
法兰西喜剧院在革命一开始就对新局势做出回应,1789年它将自己更名为国家剧院,不过这一名称仅仅沿用了4年光景——剧院被认为同宫廷走得太近而与 “国家”过于疏远,1793年它被迫关闭、演员们被逮捕。在拿破仑的领导下该剧院进行了重组,在短暂的帝国剧院时期之后恢复了 “喜剧院”这一名字,依旧是欧洲剧院的主要典范。
在19世纪,“国家剧院”的概念在中欧与东欧广为流传。在那里,国家剧院常常扮演着挑战法语、德语、俄语政治美学霸权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的重要角色。在波兰,戏剧始终同争取民族和语言独立息息相关,波兰国家剧院的命运便反映出了这种斗争的兴衰。早在1756年,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都大帝 (King Stanislaw Augustus)像18世纪的许多君主一样建立了一个波兰版 “法兰西喜剧院”,模仿后者将其命名为 “波兰喜剧院”,在18世纪70年代波兰第一次被瓜分期间该剧院关闭。1779年,剧院重新开放并被沃依切赫·博古斯·奥夫斯基 (Wojciech Bogusławsk)称为史上第一家波兰国家剧院。1782年与1814年博古斯·奥夫斯基担任剧院主管,1820年他主持出版了 《国家剧院历史》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Theatre)一书。19世纪大部分时期,由于再次受到外国势力入侵,“国家剧院”之名被禁止使用,华沙话剧的大本营是一家名为 “综艺剧院”(Variety Theatre)的剧院。1924年即波兰政治复苏后的第六年,“国家剧院”这个名字终得重见天日。
1840年,在匈牙利正式宣布将马扎尔语作为官方语言后不久,佩斯马扎尔剧院 (The Magyar Theatre of Pest)被指定为匈牙利国家剧院。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新国家的兴起,新一代人目睹了一系列类似事件的发生:1952年的罗马尼亚、1860年的克罗地亚、1861年的塞尔维亚以及1867年的斯洛文尼亚纷纷建立起国家剧院。这些新成立的机构,是人们的艺术愿景、社会关怀以及深厚的民族自豪感的体现,这一点在诺维萨德的塞尔维亚国家剧院 (Serbian National Theatre)组织者发表的目标声明中得到清晰表述:“为了提高戏剧艺术在我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为了加强并永远支持她的存在与发展,为了给民族戏剧文学注入新的动力,为了给我们渴望献身于这项崇高技艺的子孙们创办一所学校、一座托儿所,为了通过我们民族中有技能、有文化、有热情的人们的努力和经验来提高戏剧实践水平,为了使戏剧达到一定高度或达到完美的程度,从而使其成为道德的学校、成为高尚情操的榜样与形式典范,成为教育和学习的载体,成为民族意识的警钟,成为民族精神、民族语言的守护者,成为我们辉煌与悲伤过去的一面镜子,也成为我们命运的使者。”
葡萄牙国家剧院 (National Theatre of Portugal)是这一时期在中欧与东欧以外唯一存在的国家剧院,它于1864年由改革者阿尔梅达·加勒特 (Almeida Garrett)创立,在革命后的十年间他被授予 “提高该国戏剧艺术水平”的任务。民族主义、语言自豪感以及民族戏剧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得到普遍加强并于70年代在北欧蔓延。1872年,芬兰国家剧院 (Finnish National Theatre)成立,其职责在于从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抵御前期的瑞典霸权;1876年,为捍卫挪威、对抗丹麦的主导地位,挪威国家剧院在卑尔根成立。这家挪威国家剧院是由1850年成立的第一家挪威剧院发展而来,如今人们在提起它的时候想到的总会是它的首任导演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他为挪威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基础。
爱尔兰国家剧院可谓是19世纪最后将这一国家剧院 “传统”得以体现的剧院。像在挪威、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的前辈们一样,盖尔联盟 (Gaelic League)的成员们将剧院视为树立新文化、新语言、新政治的重要场所,在这里爱尔兰语站在英语的对立面。这一认知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发展并最终促使爱尔兰国家戏剧协会 (Irish National Theatre Society)于1903年成立并在第二年开设了艾比剧院 (Abbey Theatre)。1924年6月,叶芝(Yeats)作为戏剧界领袖与格里高利夫人(Lady Gregory)一同致信给新成立的自由邦政府主席,宣称艾比剧院因其 “传统与成就”已然成为 “爱尔兰国家剧院,它不应当由个体管控而应当直接属国家所有”。当局对此表示认可,为艾比剧院提供国家资助,这让它成为英语国家第一家由国家资助的剧院①伦诺克斯罗宾逊: 《爱尔兰艾比剧院:一段历史,1899—1951年》,伦敦:西奇威克和杰克逊出版社,1951年版,第125—26页。。
暹罗国王在1935年开始着手创建国家剧院,从而首次对 “国家剧院”概念范畴进行了扩展,但由于20世纪早期政治动荡、战争频频加之被占领,剧院的创建被迫中断。在20世纪,许多非欧洲尤其是亚洲与非洲的国家将建立国家剧院的首要目的定位为对欧洲文化进行模仿学习。18世纪中叶的君主们纷纷效仿法兰西喜剧院来创建自己的国家剧院以追随法国文化,20世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纷纷将创建国家剧院作为效仿欧洲文明的重要途径。这一情形同样出现在土耳其,1947年阿塔图尔克建立了土耳其国家剧院,这是其有意识将土耳其文化西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的希腊、20世纪40年代末的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纷纷开设国家剧院,这使得巴尔干半岛在20世纪中叶成为欧洲此类剧院最为密集的地区。1946年韩国开始讨论国家剧院相关事宜,但随着1948年的独立该项目获得了推进,新国民议会早期法案要求在1950年建立韩国国家剧院。
毫不奇怪,具有强烈欧洲倾向的澳大利亚此时也开始考虑建立国家剧院。这无疑是受到了1948—1949年冬季英国议会通过 《国家剧院法案》(National Theatre Bill)的刺激,这是在漫长立法之路上迈出的首要一步。毫不奇怪,澳大利亚政府要求蒂龙·古思里(Tyrone Guthrie)出任这一工作的顾问。古思里刚刚在老维克剧院 (Old Vic)结束了为期8年辉煌的导演生涯,在他的努力下,这座位于伦敦的剧院被人们默认为将会成为未来的新国家剧院。事实上,这一猜测在1963年被证实,只不过在接下来的15年内并没有实现。1949年,古思里花了两周时间参观了澳大利亚的各个剧院,最后他报告说澳大利亚尚未进入能够创建国家剧院的阶段。在他看来,澳大利亚既没有独特的戏剧作品,也没有训练有素的戏剧艺术家群体。他建议澳大利亚将戏剧艺术家们派往欧洲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技能,等到他们回国后再通过引进欧洲剧团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这一建议对澳大利亚民族戏剧运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古思里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自然引起了澳大利亚当局极大的不满,所以直到1968年澳大利亚政府才决定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他们当时决定不再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剧院,而是要组建一个伞状组织以支持创建在每个省会的官方国家剧院。1953年,古思里在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德创建了莎士比亚剧院(Shakespeare Theatre)并希望这座剧院最终会被公认为加拿大国家剧院;但在这里,剧院在创建期却遵循了他向澳大利亚提出的建议——主要依靠引进的英国人才来维持自身的运转。
二
欧洲戏剧出现在殖民时期的非洲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不过由于 “国家剧院”的概念首先暗示了它不应当受外部权力控制,所以这一实体显然不适合作为殖民主义的工具拿来使用,这无疑使得 “国家剧院”在非洲处在一种鲜为人知的境地。不过在人们意料之中的是,一些非洲国家随着独立的到来纷纷建立了国家剧院,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呼应了20世纪欧洲不少国家使用戏剧来鼓励表达新型民族文化的愿望。然而, “国家剧院”在20世纪后的殖民国家是一个比在20世纪欧洲语境中更为模糊的符号。这些机构作为表达新民族国家意志所想起到的作用现在已被以下事实所限制:国家剧院往往是与欧洲文化相联系的戏剧概念,所以它同欧洲殖民主义密切相关。所谓的肯尼亚国家剧院(Kenyan National Theatre),实际上便是由殖民当局在肯尼亚独立前十年即1952年创建的,它的本质正是致力于完成殖民主义计划。即便在肯尼亚独立后,该国家剧院的定位和剧目仍旧几乎完全从属于欧洲文化,直到今天它仍处于为实现真正民族性而奋斗的阶段。
非洲国家剧院多是在独立后建立的,因此难免与之前的欧洲文化藕断丝连。在这里,欧洲的文化经验就如同幽灵般困扰着它们并且经常在殖民与后殖民议程之间造成紧张局势。塞内加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于1960年从法国独立出来,新国家的第一任总统利奥波德·森格尔 (Léopold Senghar)认为,艺术对于建立国家的自我形象至关重要,他实施的一个重要文化项目便是在1965年于达喀尔建造一座国家剧院。丹尼尔·索雷诺国家剧院 (Daniel Soreno National Theatre)是为数不多的以人名命名的国家剧院之一,它是为了纪念该国最著名的殖民主义艺术家——索雷诺 (Soreno)。索雷诺出生在达克,但在图卢兹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加入了地区剧院并最终在法国加入了让·维拉 (Jean Vilar)在法国的国家人民剧院 (French Théâtre National Populaire),该剧院当时是法国戏剧界的主力,是法兰西喜剧院的竞争对手。就像洛伦·克鲁杰 (Loren Kruger)指出的那样,TNP在法国的地位就如柏林人民剧院 (Volksbühnen)在德国的地位,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它可以以国家剧院的身份发表正式声明。因此,索雷诺国家剧院将同名的索雷诺作为教父可谓是法国殖民主义与国家剧院运动民粹主义分支的完美结合。有趣的是,随着20世纪后期法国开始下放对戏剧的控制权,巴黎郊区与主要省会城市纷纷得到政府支持建立起了官方剧院。丹尼尔·索雷诺在各地都很受尊敬,所以在图卢兹主要演出场所与如今位于巴黎郊区万森纳的国家剧院都以其名字命名。
直到1950年以后,国家剧院才出现在阿拉伯世界,在那里它们满足了与以往任何具有此名称的组织看似有关实则明显不同的文化需要。作为20世纪阿拉伯世界特色文化的代表,埃及在这个方面同样是领军者——在纳赛尔 (Nasser)的领导下,埃及国家剧院于1953年建成。同大多数早期国家剧院相反,埃及国家剧院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对立)需求。同许多19世纪欧洲国家剧院一样,埃及国家剧院是在民族主义热潮中建立起来的,此时长期侵略势力 (此处指英国)正在衰减。国家剧院从那时起便被视为是这个国家的中心文化象征,是一流剧作家和戏剧艺术家的展示舞台。与此同时,它还具有暹罗和土耳其国家剧院以及许多后殖民国家剧院的一些特点。即,作品即便出自当地艺术家之手,但依旧呈现着欧洲戏剧的气质,即便是在它支持者的队伍中创作出的作品,依旧缺少民族性表达,更多是对欧洲戏剧模式的模仿。
在这个方面,埃及国家剧院不像19世纪寻求民族文化独特表达的国家剧院,而更符合18世纪君主试图通过模仿法兰西喜剧院来证明本国文化能力时所走的道路。时至今日,语言选择始终是国家剧院的核心问题,这种选择在埃及同样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绝大多数新兴的国家剧院会支持一种地方语言,这种语言在文化表达方面常常被控制或遭到占领国的压制与忽视,例如捷克语、匈牙利语、芬兰语、挪威语和盖尔语。然而,埃及国家剧院选择的语言实际上并不是埃及人民使用的语言——剧院采用的是 “标准阿拉伯语” (Fusha)或 “古典阿拉伯语”,即 《古兰经》中的语言,其形式已经在整个阿拉伯文学世界中建立起来。在阿拉伯世界中,标准阿拉伯语与地方方言始终维系在一种紧张状态里,尽管成立之初阿拉伯国家剧院便严格要求以标准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但随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埃及成立的国家剧院,并没将这一要求严格延续下去。如在1958年的突尼斯、1960年的叙利亚另成立的现代阿拉伯国家剧院,1963年的阿尔及利亚以及1968年的伊拉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突尼斯成为第一个正式授予阿拉伯口语与标准阿拉伯语一样具有正式法律地位的阿拉伯国家,1979年文化部颁布了一项指令,正式批准标准阿拉伯语、阿拉伯口语与贝都因语为国家戏剧作品创作语言。
以色列的情况与阿拉伯剧院的紧张气氛形成了有趣对比。建国十年后,以色列将早些年创建的哈比马剧院 (Habima Theatre)命名为国家剧院。和标准阿拉伯语一样,希伯来语是当地人民的经典语言,也是 《托拉犹太律法》(Torah)所使用的语言,可实际上它几乎只在仪式上使用。创造了 “犹太复国主义”一词并作为该运动奠基人之一的内森·伯恩鲍姆 (Nathan Birnbaum),主张将意第绪语作为官方犹太语言。但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意第绪语逐渐被视为是散居海外者所使用的语言,而希伯来语则被认为更为纯净、合宜。因此,与浪漫主义时期的东欧民族主义运动相比,语言和民族主义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被赋予了一种近乎神秘的关系,而戏剧像先前一样成为向公众印证这种关系的实际证明。
随着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希伯来语戏剧在16世纪到18世纪鲜为人知,只是零星以文学作品形式出现,而此时中欧和东欧则发展出了强大的意第绪戏剧文化。1907年后,波兰与俄罗斯出现了以希伯来语戏剧来 “替代”意第绪语戏剧的状况,其中最重要的当属1917年成立于莫斯科的哈比马剧院,其特殊使命在于强调希伯来语在犹太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该剧院最终迁往巴勒斯坦,后在1931年于特拉维夫建成,最终被指定为以色列国家剧院。
三
19世纪后期的国家剧院概念继续流传于世界各地,尽管在后殖民时代,这种作为民族自豪感、国家独立重要象征的 “文化纪念碑”的传统功能受到了极大损害 (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因为它与欧洲文化的传输密切相关)。许多创建于20世纪的所谓国家剧院其实很少参与到文化整合中,它们更多可被视为当地政府想要达成符合欧洲标准文化成就这一期望的映射。这些国家剧院与创建于19世纪初期的欧洲国家剧院的模式不同,它们更像是20世纪欧洲君主们建立的剧院——后者创建剧院的目的同建造小型凡尔赛宫模型的目的相仿,不过就是为了效仿法国文化潮流。如今,这些剧院在其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非常边缘的角色。本人曾于1985年参观了所谓的危地马拉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 of Guatemala),这座位于危地马拉市中心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欧式建筑已关闭了数月之久,在临终之前它所举办的显然是一场农业展览。而在1989年,本人在摩洛哥的国家剧院观看了一场演出,但那是一场美国喜剧 《哈维》 (Harvey)的业余演出,主要由欧洲外交使团成员出演。
因此,虽然 “国家剧院”一词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与欧洲传统保持着密切关系,它在那里诞生、在那里产生了著名实例。不过奇怪的是,几个拥有重要戏剧传统的欧洲国家却从未创建过正式的国家剧院,即便创建也已经到了20世纪后期,那时距离他们的国家达成民族统一已时隔甚久,甚至要远远晚于那些全球偏远的地区。在后期创建的国家剧院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英国剧院。早在19世纪中期,英国文化界同政界便开始讨论是否要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然而直到一个多世纪后也就是1976年,这座剧院才真正被建立起来。本人不打算涉足此话题所涉及的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方面的问题,在此仅简要引用劳伦·克鲁格 (Loren Kruger)在其关于国家舞台与文化表达书籍里的观点。克鲁格认为,1913年英国议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清楚地表明了这样做的动机。克鲁格指出:“这场辩论的重点在于指出了国家剧院是英国作为世界调和力量 (大英帝国强权之下)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模范影响力的代表,而不是讨论资金和运作中将会涉及的实际问题。”①劳伦·克鲁格:《国家舞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尽管大英盛世和英国戏剧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文化使英国成为一个特例,但欧洲国家剧院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在功能上的转型非常典型,它不再作为新兴国家的集结点出现,而是成为了一个纪念碑,以此来见证一个已经在政治上确立起来的国家的文化成就。
西班牙国家剧院几乎与英国国家剧院同时建立,但其重点和创建方式同后者截然不同,这多归结于它将当代法国剧院视为自己学习的典范,而英国国家剧院则恰恰相反。佛朗哥 (Franco)去世后,西班牙在1976年至1981年担任总理的阿道夫·苏亚雷斯(Adolfo Suárez)领导下,依照西欧常规模式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并在1977年效仿法国建立了文化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国家剧院已经与一个半世纪前作为第一批欧洲国家剧院楷模时的状况截然不同了。在早些时候,法国的民族戏剧舞台仍在拿破仑建立的制度下运作,这与大革命前的做法可谓遥相呼应。位于巴黎的两座官方戏剧机构——法兰西喜剧院与奥迪翁剧院 (Odéon)是法国戏剧的代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日益感到,国家不应仅仅支持设立在首都的单一剧院机构,大家认为全国上下只要是公众可进入的剧院,都可以作为国家剧院的代表。
20世纪剩下的几年岁月中,一些欧洲国家旧中央集权在国家剧院问题上所持的观念与新型的去中心化观点相冲突,这在法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简而言之,这种直到今天依旧持续的冲突既涉及到巴黎两座由政府支持创建的剧院,也关乎到外省甚至郊区的剧院。在这些新的剧院中只有极为少数几座被指定为 “国家剧院”,它们多使用其他名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 “国家戏剧中心” (National Dramatic Centers),该术语在1960年中首次使用,这一运动在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AndréMalraux)领导下达到顶峰。尽管法国各地仍旧可以找到国家戏剧中心(CDN)和其他各种国家资助的剧院机构,但政府迟迟不愿增加所谓国家剧院的数量。截止到今天法国只有六所国家剧院:传统歌剧院 (Opéra),歌 剧 喜 剧 院 (Opéra-Comique),奥德翁剧院 (Odéon),法兰西喜剧院 (Comédie-Française),一栋分散的巴黎式剧院即国家丘陵剧院 (Théâtre National de la Colline),以及一个分散的地区性剧院即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 (Théâtre National de Strasbourg)。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许多欧洲国家都感受到在首都建立中央国家剧院同试图为全国观众服务从而下放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许最令人瞩目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那里国家剧院需要担当起巡回演的责任从而扩大其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这成为剧院关切的重大问题。在1978年,芬兰建立了八个主要的地区剧院,具体负责其所在地区的巡回演出,尽管如此,芬兰几乎每一个人口超过25000的城市都会有由国家资助的常设剧院。1967年瑞典建立了第一个地区剧院——诺博滕斯泰恩剧院 (Norbottensteatern)。它所巡演的范围几乎覆盖了瑞典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在北极圈以北。1974年,瑞典的国家文化政策要求在瑞典各地设立同性质的国家区域剧院以承担类似的责任。挪威的第一个地区性剧院是特罗姆瑟的霍达兰剧院 (Hålogaland Teater),它于 1971年成立,与瑞典诺博滕斯泰恩剧院相同,也要在挪威北部约国土面积1/3的地方进行巡演。十年内,五个地区剧院纷纷成立,其中一个设在松恩-菲尤拉讷 (Sogn og Fjordane)县,该县最大的城市中心人口不到8000人。
在西班牙,苏亚雷斯 (Suárez)依照马尔罗 (Malraux)国家戏剧中心的概念在1978年于马德里创立了国家戏剧中心 (Centro Dramático Nacional)。国家戏剧中心的工作分成两个部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剧院建设潮流过后,萨拉·奥林匹亚 (Sala Olimpia)创作新的或实验性质的作品;而马丽亚·格雷罗 (María Guerrero)则遵循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戏剧传统。此处明显缺乏的 (特别是考虑到CDN传统尚未形成,所以重点在于国家剧院传统)是对于国家传统尤其是国家经典的重视。针对这种顾虑,1985年,一座名为 CNTC (Compañía Nacional de Teatro Clásico)的剧院创立,以用来展示西班牙戏剧的黄金时代 (也特别用来寻找类似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公司和法国喜剧传统的模式)。马德里CND的首任院长阿道夫·马尔希拉克(Adolfo Marsillach)担任新CNTC剧院首任院长。
20世纪70年代末,西班牙政府在重组时的重点之一是承认加泰罗尼亚人民的民族独立性,并在1979年颁布了 《自治法》 (Statute of Autonomy),对其予以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尽管同一时期加拉西亚与巴斯克人的民族身份也得到了承认,但这种认可在加泰罗尼亚文化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巴塞罗那长期以来一直是马德里的主要文化竞争对手,也是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它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自治法》呼吁建立加泰罗尼亚电视台、广播电台,拥有自己的新闻界以及其他 “社会交往”手段。巴塞罗那活跃的戏剧环境使得它在这一新纪元很快便拥有了一座加泰罗尼亚国家剧院。加泰罗尼亚国家剧院(Teatre Nacional de Catalunya,即 TNC)于1997年9月开幕,它作为例子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国家剧院的理念是如何在世纪末这一特殊时期政治局势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从建筑上来看,它几乎是对这一理念的直接呈现:TNC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巨大独立纪念碑,坐落在城市一条主要的林荫大道上,其建筑风格仿造希腊神庙。批评者们将其比作陵墓,称它是一座加泰罗尼亚堕落山谷。
四
如果说TNC在建筑上与19世纪早期多数国家剧院相似,那么它所上演的剧目则反映了时代的紧张局势。20世纪60年代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依旧是法国经典剧目,它几乎不会呈现任何来自于其他文化的剧作 (最多是勉强向尤内斯库这种剧坛新贵开放)。而这一切在当今都发生了变化,像欧洲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剧院一样,加泰罗尼亚国家剧院开始大量上演古典与现当代欧洲剧目。当下的戏剧季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舞台上不仅有高乃依、莫里哀和拉封丹 (由美国导演罗伯特·威尔逊执导),也有莎士比亚、科尔德隆、托马斯·伯恩哈特、欧里庇得斯、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契诃夫。长久以来,巴塞罗那不仅以作为加泰罗尼亚首府而自豪,而且以自己远比与世隔绝的马德里更加欧洲化为傲。加泰罗尼亚国家剧院的创建初衷自然需要有加泰罗尼亚语创作的剧目来辅助实现,但巴塞罗那的文化状况与20世纪末国家剧院的形象促使它需要选择更为国际化的剧目。当巴塞罗那最著名、最受尊重的演员/导演之一约瑟夫·玛丽亚·弗洛塔茨 (Josep Maria Flotats)被选为新国家剧院负责人时,他在这个方面做出了非常明确的选择——他长期以来都被批评在波利欧拉玛剧院 (Poliorama)时期忽视了加泰罗尼亚戏剧。尽管如此,在1996年9月新成立的国家剧院开幕季上弗洛塔茨所选择的作品——托尼·库什纳 (Tony Kushner)的 《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无疑是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一种冒犯,因为这是他与加泰罗尼亚文化竞争对手马德里的一家剧院合作完成的作品。弗洛塔茨对于剧目的选择 (他的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是契诃夫的 《海鸥》),以及他在制作上花费的巨额费用导致自己在剧院创建一个月后便因管理不善为由被解雇。努里亚·埃斯珀特 (Nuria Espert)预言说 “没有弗洛塔茨,TNC将成为一座博物馆”①引用自玛丽亚·M·德尔加多:《“其他”西班牙剧院》,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不过这并没有得到证实——在接下来几位院长的努力下,TNC依旧维持着自己的声誉并努力在民族戏剧与欧洲戏剧之间找寻着中间位置。
在某些方面,类似情况也存在于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这是唯一一座不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剧院。在那里,院长史蒂芬·布伦瑞克 (Stéphane Braunschweig)一直没有留心阿尔萨斯的本土剧目,相反却利用阿尔萨斯—洛林这种模棱两可的民族身份,将斯特拉斯堡剧院既作为法国官方属性的国家剧院,也作为一个建立在欧洲基础上的区域性独立民族剧院 (就像巴塞罗纳长期以来都在古老的欧洲单一民族国家地图上占据着一席之地)。斯特拉斯堡剧院的演出使用多种语言,主要为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其作品取材于多个国家。除了位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边界位置,斯特拉斯堡现在还是欧洲议会的所在地。很显然,布拉什威格也将这个法国国家剧院视为新欧洲的国际剧院组织。尽管它的资金来源与名称显示它理应归属于法国,但其演出方式却表明了它从属于1990年乔治·斯特雷勒 (Giorgio Strehler)组织的欧洲剧院联盟,该联盟目前涵盖了许多泛欧洲化的国家剧院。
直至20世纪末,意大利在总理罗马诺·普罗迪 (Romano Prodi)和文化部长沃尔特·韦尔特罗尼 (Walter Veltroni)的支持下建成了意大利国家剧院。尽管意大利在1861年即已统一,但在剧院方面而言呈现高度分散的局面。意大利的剧院由各个地区、省、市出资管理,并不受到联盟政府的支持。然而在1998年,意大利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国家剧院立法,首次确立了两座国家剧院,即米兰短笛剧院 (Piccolo di Milano)与罗马剧院(The Teatro di Roma),两者都是历史悠久的市政组织。
选择它们作为国家剧院的理由很清楚:国家剧院应当设在国家首都这一理念,可谓是一系列创建活动的基础,只是在20世纪后期,由于权力下放,该情况才有所转变。罗马最为著名的罗马剧院显然是最佳选项。不过几十年来,意大利最为著名的是米兰短笛剧院,该剧院由20世纪后期最受人尊敬的欧洲导演之一乔治·斯特雷勒 (Giorgio Strehler)领导。斯特雷勒多年来一直梦想着将米兰短笛剧院变为意大利官方国家剧院,因为米兰短笛剧院被人广泛默认为是意大利的国家剧院。他生前最后几年致力为该剧院创建一座纪念性质剧院,希望它能够在世界诸多国家剧院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斯特雷勒在1997年的圣诞节去世,他没能看到这个梦想实现。值得一提的是,斯特雷勒作为首任主席所创建的欧洲剧院联盟可以被视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超越了欧洲过去国家剧院范畴并直指劳伦·克鲁格 (Loren Kruger)提出的 “跨民族剧院”概念。
尽管 “国家剧院”这个概念是在德国发展起来并由它做出了最早的尝试,但随着20世纪的结束,德国却成为了西欧、中欧主要戏剧国家中唯一没有官方国家剧院的国家。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一样,直至19世纪后期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那时各地的地方剧院已经建立了起来,并像意大利地区剧院一样得到了来自自治区、地区与当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其次随着普鲁士政权在德国各地的建立,各地的文化尤其是戏剧依旧保持着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层面上来看,今天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剧院(Bavarian State Theatre)也许比柏林任何一家剧院都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剧院。尽管德国的戏剧生涯存在着这种 “离心力”,内部历史压力与外部模式,似乎也会促使柏林在20世纪初创立一家国家剧院,尤其是当效仿法兰西喜剧院而成立的德意志剧院(Deutsches Theater)由麦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接手掌管的时候。随着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德国的分裂以及如今看来负面消极的老旧民族观念,都不利于德国战后复兴国家剧院计划的实施。即便是在两德统一之后,这一设想似乎依旧遥不可及。德意志剧院仍被公认为是柏林甚至整个德国的官方国家剧院机构,但在20世纪末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就像斯特雷勒的米兰短笛剧院使罗马剧院黯然失色那般,德意志剧院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被布莱希特 (Brecht)领导的柏林剧团 (Berliner Ensemble)所取代。到20世纪末,随着柏林剧团影响力的减退,弗兰克·卡斯托福 (Frank Castorf)领导的人民剧院 (Volksbühne)从侧面取代了德意志剧院。尽管目前欧洲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有所消减,但人们不能排除德国还会有建立国家剧院的可能性,毕竟西班牙同意大利近期已然完成了这项工作。不过,作者认为,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竞争,使这种可能性的概率接近为零。无论是德国剧院还是柏林剧团都是欧洲剧院联盟的成员,而这个组织如今似乎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