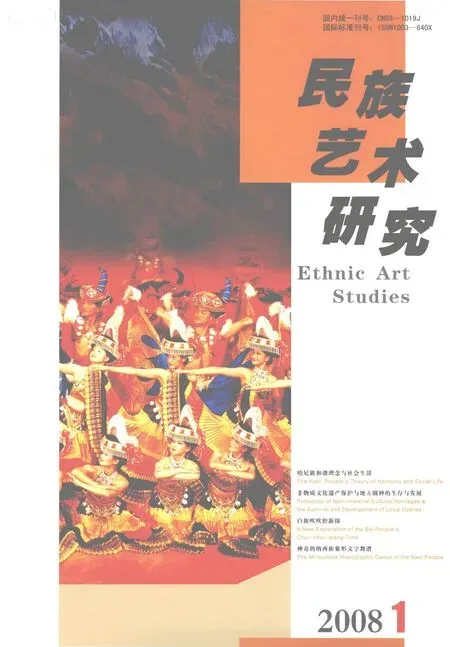正似我们借来的人生:在皮尔森的舞台上
——第26届国际戏剧节的东欧戏剧
2020-07-12卡莉娜斯蒂芬诺娃桂菡译
[保]卡莉娜·斯蒂芬诺娃,桂菡译
倘若将皮尔森国际戏剧节比喻为人,那他/她定是位虽衣着质朴却举止优雅、品位脱俗的人士,他/她也必定是个持久且低调地专注于个人创作的勤奋之人。这类人天生便熟谙生活本质,他们从不浪费时间,同他们交流能让你更明智、更从容。
我已经多次参加过皮尔森戏剧节——自1997年开始,那时候它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但我每次都会带着因新发现而油然升出的喜悦回到家:一位新导演、一部新剧、一支新团队……然而,第26届皮尔森国际戏剧节馈赠于我的比之前还要多。时间纵然已过去了数月,我却依旧沉浸在对它的回味之中。对于戏剧节的思考并不只局限于讲座或是专业性质的谈话,而是同样存在于平日生活中——这有助于我对其做出新思考并探寻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实质。我与之于无形之中保持着交流。这种关系让我想到一些人——平日里你并不会与其频繁相见,但无论在时空层面如何相隔,他们良好的品性,他们那种在当下尤为难得的宁静、平和的内心,却始终激励着甚至鞭策着你。
一
当下绝大多数戏剧节很难抵挡住各式各样的诱惑与相应而来的错觉——似乎只要保持项目不断运行,我们就能够做到/看到/拥有一切。从某种层面来讲,这些戏剧节成了我们混乱生活的延续——匆匆忙忙的生活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苦涩挫败感——这是一种属于失败者的滋味。
我们自然是没有能力去应对一切的,退一步说,至少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所希冀的全部实现。而事与愿违的是我们不但在网络上持漫游的态度,甚至对于生活也如同蜻蜓点水般一掠而过。简言之,大多数艺术节跟我们人类甚是相仿——经常会做出错误抉择,并且惯于用数字作为衡量质量的指标。即便是专题性的戏剧节也执着于 “求大”而非“求精”。
以上描述显然与皮尔森戏剧节大相径庭。若是用一句话概括皮尔森戏剧节,那便是“分寸得当,毫无废话,诚实正直”。
正因如此,皮尔森戏剧节不仅像我们身边某种人,也像是一部高质量的文学经典。它在剧目的选择与编排上把握精准,遵循了统一性,下一个剧目就像是对上一个剧目的延伸。这些剧目由一个共同点联合在一起:借用扬·科特 (Jan Kott)对莎士比亚的著名评价来说,便是它们都在关注 “生与死之间短暂片刻的最终目的”。在探寻生与死之意义的基础之上,在生死之间的进程中做选择即为本次戏剧节的中心主题。
“我们将要死去/今天或是明天/生活才是我们所需。” 《伊利亚特》 (Iliad)中的一首歌开启了本届戏剧节的演出。该剧由斯洛文尼亚导演杰尔内杰·洛伦奇 (Jernej Lorenci)执导,这部戏宛若一把调音叉定下了戏剧节的整体基调。
《伊利亚特》这部剧的第一个手势动作就表明了整部戏的姿态:一个典型的巴尔干半岛人将酒倒在地上,以此向死者表示敬意。这个动作在整场演出中反复出现:故事的叙述者——舞台上的荷马——剧中主角——人和神都在做着这个动作。所有人都面朝观众(这是典型的洛伦奇式舞台手段)坐在椅子上,他们面前放着麦克风。这些麦克风不单单是为了放大演员讲话或歌咏著名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声音,对于演出音效它们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它们的作用下,战争的隆隆鼓声、马蹄声、十年无意义的逃亡都被营造了出来……这些效果只需要在现场用手指轻敲一下即可实现——根据场景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节奏被制造出来。这一惊人的简单“伎俩”伴随着荷马六弦琴强劲的节奏与一些简短音乐的 “介入”,通过竖琴、钢琴和雷贝克被活灵活现地演奏出来,带给受众一种非凡的史诗般感受。由于演出并没有特殊的视觉效果——换句话说,没有什么会约束抑制观众的想象力——所以这种史诗性的效果反而更加显著。
不过,《伊利亚特》的创作目的并不是要让观众想象出史诗般的画面场景,但史诗已然贯穿在这部作品之中。这部剧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大原因在于其声音的频率,就像音乐一般,这些声音将观众推进某种特殊的浪潮之中并将其传送至另外一个维度、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中。
这种由此而生的近乎形而上的转变是立陶宛已故导演艾蒙塔斯·内克罗斯 (Eimuntas Nekrosius)的创作特色之一——尽管在他的作品中,舞台上充斥着大量的纯物质性元素。波兰导演格尔泽尔兹·布拉尔 (Grzerorz Bral)在这方面也是位大师。布拉尔与其山羊之歌剧团 (Song of the Goat Company)的风格与洛伦奇较为相似,即舞台取消布景甚至使用的道具也屈指可数。像洛伦奇的作品一样,山羊之歌剧团的作品也能够带领观众进入肉眼所看不见的领域。我称这种戏剧为“垂直戏剧”。它强烈抵制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唯物质主义与肤浅即我们那种水平的生活;它就像一条生命带,让我们的灵魂保持在一个较好的频率上;戏剧把我们推到灵魂的高处或深处 (取决于视角),在那里我们得以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本能地看到何为高贵何为卑劣。这种垂直戏剧的最终成就便是它切切实实地让我们记起我们天生便具备可分辨出这些重要区别的能力。
洛伦奇和他的同胞托米·詹尼奇 (Tomi-Janezic)的戏剧舞台上通常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舞台元素,比如 “一小堆肉” (主要是为了加强作品效果)。如在 《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歇斯底里地殴打着一支军团,尽管这不过是因帕特洛克勒斯之死而被惩罚的人类留下的 “一堆肉”——就像是从屠宰场直接拿出来的一样。这一幕让人感觉像是典型的复仇式恶性循环——人们不知不觉在疯狂与激怒状态中相互残杀着。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点: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阿基里斯的母亲以幻象形式出现,在她儿子面前勾勒出了两条道路——短暂的生命和不朽的死亡或者是漫长的生命与悄无声息地逝去。这种选择完全符合现代意义,我们也知道他会选择哪一条道路。阿基里斯此刻坐在一个灯泡镜面的镜子前,就像是坐在一个现代更衣室里一样。在母亲消失之后,阿基里斯仍然独自一人保持着沉默,静静的呆在那儿。叙述者通过麦克风制造出有节奏的背景声——仿佛是逐渐消失的母亲悲伤声音的回声,在她脸庞上似乎隐隐出现了一个无形的合唱队,它试图指引人们盲目地在过去的日子里寻找正确的道路。
二
声音在戏剧节另外一部剧目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剧由柏林的里米尼·普罗托科尔 (Rimini Protocoll)与瑞士维迪剧院(Swiss Theatre de Vidy)合作完成,名为 《人走后的房间》(Rooms after People)。这部剧的声音只有人声 (讲话人并不在场)。当人们了解自己即将死去 (无论是主动选择死亡还是被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他们会记录下自己的声音,通过这种形式他们可以在死后继续与人交流——告诉人们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宣布遗产获得者及其原因,或者仅仅是分享一些回忆、自己是多么地想要被记住、是否相信死亡后会有什么等待着自己。
声音、文字、故事——德国记录剧场大师用声音录制编辑出了100%真实的故事。声音在八个房间里回荡,这些房间分别放置着归属于不同人的私人物品,它们曾经就围绕在其主人身旁。观众五人一组从一个小门厅进入。在所有视觉信息中,只有一个人的脸可以被看见——就是所录制的视频里最乐观的一位土耳其加斯塔巴特人,尽管他的身体还很好,但他已经为未来的自己安排了一个伊斯坦布尔式葬礼。其他人呢?一位病重患者选择了安乐死;一位前外交官将她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她曾经工作过的非洲的艺术家们;一对年迈的夫妇,除了他们的钱之外,还想把在漫长的一生中从许多教训中汲取的智慧留给别人;一个依旧年轻的人发现自己患有遗传性致命疾病,可这已经太晚了,他想告诉他的儿子这件事情;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希望每次从岩石上跳下来都是最后一次(也许是这部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还活着的英雄之一);一位年迈的妇女,在度过自己漫长而有意义的人生后,她将一堆巨大的家庭照片放在她老式舒适的房间的圆桌上;此外还有一位教授,毫无疑问他死后将一无所有。
经过这场 “葬礼”,世界看起来、感觉起来都与以往有所不同,至少在短时间内我们都变得明智了些。在经历了这一独特的戏剧体验后,你会觉得自己很长时间身处于一种哲学的浪潮中。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个人化的痛苦因素,或者仅仅是因为人们在 《人走后的房间》中不单与死亡邂逅更是接触到了之前很少思索的事情即 “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边界区域”,于是我们对于生命的看法有所改变。难道人类的声音不从属于它所寄居的肉体,甚至不是可见与不可见两个世界之间的媒介?人类的声音,虽然是从身体里发出的,但有时却有另一种世界性的属性,难道那就是来自精神世界的不可改变的声音?无独有偶,其实中国传统音乐家在用自己的身体或乐器发声之前,首先要达到内心的平静与绝对的和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神圣和谐的媒介。
里米尼·普罗托科尔的作品唤起了我对于声音的另外一个回忆:我的丈夫在离开这个世界的前10天发出的声音。那是在一个重要的百年庆典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虚弱到需要在两个人的帮助下才能在台上站稳,然而他的声音就像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听到的那样。这声音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他的身体可以永恒存在,以便看到整个庆典是如何进行的。
当然,尽管 《人走后的房间》让人得以一窥惊人的深刻哲学与无限的精神境界,但在此之后,它向众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清醒的问题:对于其他人而言,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是不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奢侈?如果这部作品存在缺陷的话,那便是它只是向人们展示了能够承受这种奢侈平静的那部分人的状态。
三
戏剧节最后一个作品是 《摹仿生活》(Imitation of Life),它的关注点则放在了另外一群人身上——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辛,生存在借贷与偿还之中。该剧由匈牙利人科内·蒙德鲁佐 (Kornél Mundruczó)执导,由来自布达佩斯的普瑞通剧院 (Proton Theatre)上演。这部剧也是 “不可见的”。
戏一开场,舞台前面的大屏幕上显示出一个疲惫中年妇女脸庞的特写镜头,她在与画面外我们看不到的人激烈争吵着什么,绝望地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渐渐地,她被赶出了自己所住的公寓,这显然并不是她第一次被逼进绝境。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是吉普赛人!她讲述着零碎混乱的故事,似乎想要用这些故事把自己遮盖起来,剧中她的生活也的确更像是 “对生活的模仿”。整部戏只有一个细节:一次例行的强制性 “杀虫”沐浴清洁……大屏幕升起,观众看到的是一套带有古老高天花板的公寓,其中有一间宽敞双人房,房间里有高高的拱门形落地窗,还有一个厨房、客厅以及卧室。中年妇女坐在桌旁,旁边是一个来驱赶她离开的清算人。谈话还没有持续多久,这位妇女便晕了过去。
接下来的一幕可谓 “封锁住”了这场演出。《摹仿生活》这个戏采用了非常大胆的蒙太奇技巧,它由很多巨大且风格截然不同的片段/情节组成,段落与段落之间没有任何缓冲过渡。就好像是一封电报,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图像和声音组成,简洁且切中要害。清算人叫来一辆救护车,歧视的故事还在继续:他们不想来这个街区派送。房间又 “消失”了——现在它在一层雾幕的后面,雾幕从天花板的顶端向下流动,形成一堵墙——而在旁边的屏幕上,观众可以看到急诊室接线员的台词。接着,雾气上显现出投影:这是一组酒店的镜头,公寓房客的儿子在这里做男妓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从投影镜头看见他,那感觉他就好像是鬼魂似的。雾幕就像一个瀑布在不断地流动,时而浓密时而稀疏,有时就像是在波浪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浮动、生动的 “屏幕”,它给人带来一种惊人的效果:男孩儿具有一种欺骗性的立体感,就好像是海市蜃楼或是幻觉——像他选择过的虚幻生活那般。
不仅在这个场景,在整场演出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对蒙太奇的运用贯穿始终。潜台词不仅生发在台词之间,更是生发在这种惊人的舞台语言的隐喻中。这就是为什么 《摹仿人生》这部戏在没有任何说教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保持一种高尚的道德水准,它不失良知且被赋予了很强的社会信息。
下一个场景是该剧目的精髓,也是孟德鲁佐独特的舞台语言——没有任何语言,也没有演员,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我相信这一情况是第一次在戏剧中出现。雾消失了,房间又回到了舞台上,这次没有人在里面。一阵吱嘎声响起,这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物件的房间开始慢慢逆时针倒转。首先,房间里的小物体开始下落,它们不均匀地碰撞,当大的物件也参与到分崩离析的队列中时,嘎嘎作响的声音逐渐变得震耳欲聋。而且,当地板变成天花板时,一些大型的厨房电器也掉落下来。其效果令人震惊:就好像我们目睹了一场大地震或飓风,甚至更甚——简直是一场地壳运动般的大灾难。
等到房间转回到它的初始位置,清算人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一位新来的年轻女房客。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摹仿生活》还在继续上演。即使房间里一片混乱,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清算人,也没有对新来的房客产生任何影响。清算人前脚一走,新房客后脚立马给她躲在门外的儿子打电话让他进来 (合同规定她应当一个人居住),他们收拾了一下唯一幸存下来的床铺,等到孩子睡着后她穿上一件低俗的超短裙,发了几条短信准备开始 “工作”,随即离开房间。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场面:前房客的孩子进来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接下来舞台台口又出现了屏幕,上面浮现出一条新闻:当事男妓在公交车上杀人;这一事件激起了一阵抗议浪潮。全剧结束。
直到最后一刻,人们才发现原来 《摹仿生活》的创作原型来自于一部纪录片。2004年,导演阿帕德·席林 (Arpad Schilling)和他的克雷塔科剧院 (Kretacor Theatre)受新闻节目启发,创作了 《黑土地》 (Black Land)。该剧在世界各地巡演,并震惊了观众——这是另一部在舞台上为人类当下状态爆发出痛苦呐喊并试图让我们从沉睡中惊醒的匈牙利作品。与席林不同,蒙德鲁佐在演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政治综艺节目中的故事与带有煽动色彩的语言,但是他在舞台上创造的不同寻常的形象与丰富的感官体验,同样让作品成为正在发出求救信号的电报;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封电报的收件人。顺便提一句,当他的作品在2009年荣获新戏剧现实奖 (New Theatre Realities Award)时,人们感觉这就像是对席林感染力十足的演讲的回应。“……我们经常讨论言论的自由,席林说,就像是它比人类尊严的自由更为重要似的。这就导致了一种情境——所有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会带来什么后果。它们可谓暴力、残暴、种族主义的丰沃之地。”
四
当然了,并非皮尔森戏剧节的所有作品都像这三部戏一样令人震惊 (我敢说它们简直是当代戏剧的杰作)。还有另外两部作品也非常好,不过它们因过于风格化而让人略感疏远。它们是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捷克导演之一——间·米库尔丘克 (Jan Mikulššek)的作品——它同样聚焦于死亡,但在生命价值与道德尺度的判断上持有特殊观点。毫无疑问,戏剧节上还有一些喜剧作品,不过它们不是那种让我们荒废几个小时以忘却现实处境的作品。相反,由沃吉特·什特帕内克(VojtěchŠtěpanek)执导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 《备忘录》(The Memorandum)、由吉伊·哈维尔卡 (Jirˇi Havelka)执导的 《业主联谊会》 (The Fellowship of Owners)正是喜剧类作品的典范,它不会让我们与我们所笑的东西脱节,而是让我们既能从笑声中获得活力,又可以通过它来武装自己,这就使得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选择面对而非选择逃避。
《业主联谊会》也以纪录片为基础,采用吉伊·哈维尔卡所专长的沉浸式戏剧形式。该戏上演于市政厅的地下室,观众们倚四面墙而坐,演员们围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旁扮演着公寓业主聚集在住宅楼入口处举行例会。他们需要讨论一些常见问题 (比如建造电梯的必要性,若施行需获得多数选票),不同的业主对此有不同的反应。典型化的人物,喜闻乐见的语言梗、演员的行为动作以及角色相互之间的关系引发观众阵阵笑声。这部剧无论是看上去还是感受起来都像是真实生活的写照。直到有那么一刻其中一对夫妇中的孕妇开始分娩,人物动作切换成慢动作模式,才立刻将观众带回到了剧场现实中,接下来的演出又突然回到了之前完全模仿现实的模式上来。这两种戏剧模式之间的美妙转换,让我想起了在几年前的皮尔森戏剧节上,我看到的另外一部哈维尔卡的作品:《铜管乐队》 (Brass Band)。在那场演出中,观众可以直接加入表演的行列,他们可以扮演乐队演奏所在的酒吧中的乡村老百姓,既作为观看者,也作为参与者,参与到这一行动中。
最后,这里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看似与戏剧无关的细节,也可以说它是本文不予置评的结尾。在皮尔森戏剧节期间,在每晚以及所有周末演出中观众都能够看到该市副市长兼捷克议会文化委员会主席马丁·巴克萨(Martin Baxa)的身影——没有大张旗鼓地现身,身边也不配备任何保镖,就像是其他热爱戏剧的人一样,从他身上你看不到一点儿“正式”的派头。就像是前几年他担任城市市长的时候;顺便一提,当时皮尔森正在为成为欧洲文化之都做准备,一座崭新的剧院就在那里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