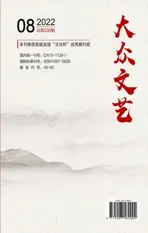非遗保护背景下的乡民艺术传承与创新研究
——以山东莱芜传统舞蹈花鼓锣子为例
2020-07-12莱芜职业技术学院271100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271100)
村落与城市相比较而言是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空间,在长期的乡土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村落文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乡民艺术也适时地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发生了改变。花鼓锣子作为当地乡民艺术也有着属于它的起起伏伏,当然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离不开乡土社会整体语境的,它甚至对乡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民间艺术活跃的村落
颜庄位于莱(芜)、新(泰)路之要冲,莱芜的母亲河——汶河穿村而过,颜庄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据相关志书记载,颜庄建村历史悠久并且一度作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后因战乱,村落衰败,人口骤减。明朝洪武年间,多户人家由外地迁来曾名李子园村。后来人口扩张,村落就沿着汶河一直向北延伸,名为延庄。后因谐音,逐渐演化为颜庄。颜庄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既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重要集镇,又是焚香祭祀、迎神赛会的主要场所。村落的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激发了乡民对艺术生活的追求。颜庄的9个自然村就是在这样的乡土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演特色,每到过年,不论大村还是小村都会有风格各异的乡民艺术表演,踩高跷,舞狮子,舞龙等等,样式繁多复杂,场面非常的壮观。
经济的繁荣昌盛,村落文化的活跃,是花鼓锣子形成的重要基础。花鼓锣子作为一种村民集体娱乐项目,既是颜庄村的标志性文化又是该村落的传统艺术。花鼓锣子在村际关系、区域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颜庄村人民精神意志的依赖和寄托。
二、记忆里的花鼓锣子
花鼓锣子传承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清末民初时期,许多人流离失所,靠乞讨卖艺谋生。为了吸引顾客或获取怜悯,这些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或唱或说并加以表演。乞丐敲着花鼓,艺人打着铜锣,卖鼠药的耍着旱伞,磨刀人打着夹板,还有旁人伴随这些韵律和节奏高低起伏的哼唱。这些被当地酷爱民间艺术的村民张凤旨、刘俊田、杨春庆、苗传美、吴庆乾等人见到十分喜欢,于是5人将这些技艺学过来,经过多年的钻研打磨,逐步将它们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演变成一种独特的歌舞说唱表演形式。因为主要演出的道具与伴奏乐器是花鼓与铜锣,所以当地人们称这种表演形式为“花鼓锣子”。
过去的村民生活窘迫,衣食无助,但是他们不甘于贫穷和寂寞,他们或通过去庙寺烧香跪拜向神明来祈求平安顺遂,或聚在一起唱唱跳跳,以一种穷乐的方式寻求心灵上的沟通与精神上的满足。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时间久了便形成了花鼓锣子这一独特的乡民艺术形式。可以说,花鼓锣子的兴起与发展与当地的民俗民情、乡土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花鼓锣子最初的演出形式由5人组成,演出时以锣鼓、唢呐演奏开场,第一个登台的领舞者(戏曲中小武生装扮)腰带腰鼓边跑边敲,打小镲与打锣者(花旦扮相,男扮女装),打夹板与打伞者(丑角扮相)在领舞者的带领下按照既定的顺序依次登场,演员上场即开始说唱表演。花鼓锣子的艺术特色比较鲜明。首先,语言风格恢谐幽默,生动有趣。花鼓锣子的主要演员和观众都是村落民众,顺口溜式的方言土语更容易在村落里产生和传播。艺人们借助这些方言土语编汇成朗朗上口的语句,于嬉笑怒骂之间诉说着村民们内心不善外露的心声。花鼓锣子有不少唱词是即兴而出的,穿插在舞蹈当中,即景生情,见物说物,见人说人,这样的唱词在保留和传承上面会遇到困难。其次,花鼓锣子的舞蹈动作讲究的是欢快热闹,再加上翘胡子、调情等滑稽可笑的动作,形成了欢快喜乐、恢谐幽默的唱跳形式与风格。过去花鼓锣子的演出队形多种多样,有“龙摆尾”“跑圆场”“八字形串花”“转灯式”等等。不同的队形样式向我们展现了当地标志性文化的魅力与个性,增添了表演色彩。再次,节奏旋律轻松活泼。花鼓锣子的曲调为鲁中民间小调,它们由乡土社会而来,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经过民间艺人们精心的挑选与改造,又重新反馈给了乡土社会。这些曲调速度多以中慢为主,表演基调多欢庆喜乐,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最后,颜色鲜艳喜庆的服装造型。花鼓锣子演员的服装造型虽然夸张艳丽但却突显了其塑造的艺术形象,对现场气氛具有良好的烘托作用,大大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鲜明的艺术特色,花鼓锣子这一乡民艺术才得以在乡土社会广为流传和发展。
三、起起伏伏的乡民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原先的乡土社会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跟着产生了剧烈变化,蕴含其中的乡民艺术同样承受着一系列现代化因素的冲击,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乡土社会的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致富。过去空闲时用来打发时间聊以自慰的乡民艺术不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还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改变了村落原来相对封闭的环境,新的文化渗透进来,改变着当地年轻人对原本乡土生活观念的认知和态度。例如花鼓锣子这样的乡民艺术已经不再被年轻一代所热衷,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更谈不上传承与发扬。就这样,人员不足,人员老化,以及经济压力等因素使花鼓锣子渐渐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土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乡民艺术发展十分缓慢,很多艺人继续坚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不让老一辈的东西丢了,然而在对民间艺术的发展和改造上面却几乎很少涉及。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话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术、乡民艺术在非遗保护运动中得到了国家、政府等各方的关注和支持。颜庄村的标志性村落文化——花鼓锣子在各方的扶持下也渐渐得到恢复。“回归”后的花鼓锣子在舞蹈动作,唱词、曲调等方面都有着新的构思与编排,这些创新与发展无疑进一步增强了村民对集体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对乡土社会的生活产生了新的影响。人们玩花鼓锣子主要目的不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希望自己引以为傲的乡土传统文化能够得到传承与发展。2006年,花鼓锣子成功申请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代表地区参加的全省性民间艺术表演活动中获得众多好评,人们记忆当中的花鼓锣子又重新“热闹”起来。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有其双面性。花鼓锣子的重新“回归”有着些许的“无奈”。为了迎合当今社会文化对民间的需求,花鼓锣子进行了调整,很多内容发生了变化,新的审美情趣被注入到原有的表演形式当中。比如演出服装,据花鼓锣子的第四代传承人李沛庆讲,过去演出时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乞丐装,这样一是能够得到观众的同情,还能够增强诙谐可笑的艺术效果。但是这些与申遗的初衷不符,于是就都换成了与龙灯队统一的服装。还有花鼓锣子的唱词,本来大都是来源于乡土生活的即景生情式的方言土语,亲切俏皮,朗朗上口。然而为了更好的与政府精神文明相切合,开始由“即兴”转为“既定”。这些“既定”让艺人们念着拗口,演的费力。总而言之,在非遗保护背景下,乡民艺术重新“回归”并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在新的发展进程当中,乡民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根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势必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矛盾。
四、结语
花鼓锣子至今已有四代传人,作为村落集体性文化的它已经与村落融为一体。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城镇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时代背景下,花鼓锣子原来所依赖的乡土社会秩序和环境正在改变,人们对它的认知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受经济、城市化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花鼓锣子曾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幸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为其带来了新的“春天”,使花鼓锣子又重新回到乡土生活之中。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花鼓锣子在经历非遗保护的运动中出现了新的苦恼,它希望得到发展,但是不得不做出改变,有些改变是无奈的、迷茫的。而出现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乡民艺术与非遗保护活动的需求和目标不一致,乡民艺术是自下而上的生长而保护活动却是自上而下的渗透。这些矛盾还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和多方的努力才能慢慢解决。我相信,发展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乡民艺术终会冲破迷茫绽放出更美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