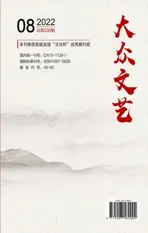《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中“梦”的探析
2020-07-12华东交通大学330000
(华东交通大学 330000)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戏剧史上同时期的杰出剧作家,他们的作品历久弥新。其中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皆属写梦佳作,本文拟将二者平行比较,试图分析二者梦的异同。
一、故事层面
(一)“游园惊梦”到“寻梦殉梦”的情感追寻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的深闺小姐。深受礼教束缚、苦闷无处诉说的她首次走进后花园,看见生机勃勃的满园春色,由衷生发对自由的强烈渴望,爱情的萌动与年华易逝的感伤也涌上心头。原始欲望本能促使杜丽娘展开爱欲追寻,无奈为枷锁捆绑的深闺小姐只能做梦,去往另一个时空寻求出路。因此故事情节上,梦中与柳梦梅如胶似漆的杜丽娘醒后大胆做出寻梦的痴狂举动,寻梦的失败也将她引向殉梦这一为情而死因情复生的道路。因情致死已实属难得,死后为与爱人长相厮守又努力重回人间更是“至情”所就。伤春、幽怨、惊梦、寻梦、殉梦、圆梦环环相扣,杜丽娘在梦起梦圆中也成功地从缺乏主体意识的千金转变成敢于献身的深情女郎、捍卫真情的勇敢战士。梦是情节发展的推力,也是主角实现思想升华的依托。
(二)仲夏一梦,个性解放下的冷静反思
不同于杜丽娘的梦境,《仲夏夜之梦》中的“梦”并非剧中人物的生理现象,而是一种梦幻。仲夏的森林中,故事里的人物对个人情感、自由平等的追求与超自然的魔力共同营造出了超时空的奇幻世界。文艺复兴的浪潮下,以追求爱情、向往自由为主题的作品不在少数,但狂热的解放追逐也会使人盲目、疯狂、丧失理智,走向另一个极端。故事中,赫米娅与拉山德为摆脱父权包办婚姻逃入森林,在魔法花汁作用下,拉山德竟阴差阳错爱上赫米娅的朋友海伦娜,能与仙王叫板的仙后提泰妮娅更是不可思议地爱上一头驴。较之杜丽娘梦醒后的疯狂追梦行为,莎翁笔下的人物在梦幻复原后并无过多动作,当魔法解除,森林中的所有就如从未发生,但森林中的荒诞行为却呼唤人们对理智与情感展开深思。
二、作者层面
(一)对梦方式的选择
梦既是创作对象,也是创作手法。16世纪末,不论是东方的《牡丹亭》抑或西方的《仲夏夜之梦》,都试图在梦的奇幻情境中委婉完成自然人性的无意识展示。郑传寅在《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中谈到:“以梦幻喻人生,将剧作家观察生活的视点由传统的人伦政治方位,扭转或提升到哲理层次,从而深化了剧作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采用梦的叙述摆脱了传统写作手法的束缚,有助于作者更好地体会人生的虚幻无常,挖掘生命更深刻的意义。
1.以情反理的委婉方式
汤显祖身处晚明时期,在明王朝内忧外患的同时,市民阶层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有了萌芽迹象,思想上,以张扬人的主体精神为指归的陆王心学盛行于大江南北。汤显祖的启蒙老师便是陆王心学泰州学派的弟子——罗汝芳。汤显祖自称“为情作使”者,主张以情反理。在他笔下,一方面,梦是欲望的表达,“情之至”便会进入梦境作死生游转,另一方面梦又生于情缘于情,有情才会有梦,二者不可分割。汤显祖也曾在《复甘义麓》中明确指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创作原则。
创作《牡丹亭》时,汤显祖敏锐地看到了理学的危害与假道的虚伪,借梦境张扬人性。作者首先设定背景:杜丽娘自小熟背《四诫》等封建读物,父母又请老古板陈最良给她上课,教导她《关雎》讲的是后妃之德,从萌芽上消灭丽娘心中的青春萌动。此外,作者还从行为上限制杜丽娘:自家的花园都未曾游逛。在此基础上,作者开始安排杜丽娘游园、入梦,当杜丽娘看到如此美景,内心便不由生出怅惘。于是现实中无法摆脱的禁锢在梦境中实现。这第一次入梦,正是汤显祖借梦来传达对礼教压迫之深的反抗。杜丽娘自惊梦之后,抑郁成疾最终离世,此时汤显祖巧妙地安排杜丽娘和柳梦梅的人鬼之情,并精心设计还魂情结,向封建礼教和没有温度的理学提出挑战,礼教也许可以束缚人的躯壳,却困不住人追求自由的思想与追逐真情的精神。
2.宣扬人文主义的重要手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戏剧家。该时期,人文主义的崛起对封建传统势力形成了挑战。因此,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包含了情感解放,鼓励个性,和谐仁爱等积极思想。在仲夏的梦幻中,我们看到日月星辰、森林平原、山谷河湾、鸟语花香……与剧中人呼应,展现了似梦似幻、若真若虚、和谐完美、愉悦欢乐的基调。
《仲夏夜之梦》中,莎士比亚特意安排忒修斯听完人们叙述仲夏夜经历后,以所谓的理性口吻评论“我从不相信这些离奇的故事和神鬼的玩意儿。”看似有理,但他也曾像这两对情侣一样因为爱情而迷失于林里,因此让他做出客观评判,正如中了花汁却以“理性”自诩的拉山德一样荒唐。莎翁借助错乱颠倒的梦幻之境传达出对理性的讽刺与批判,此外,莎翁也表达出人文主义精神浪潮下对理性与情感和谐统一的反思。
3.舞台表现的增色方法
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戏剧的魅力不仅取决于剧本语言的优美,结构的完整,能否体现出舞台的独特张力,别出心裁吸引到观众更为重要。黄士吉曾提出:“梦境独有的这种生动醒目的直感性、形象性、生动性,极适合舞台艺术的表演要求,恰恰补足了戏剧表现手法的局限。”因此不管是中国的《牡丹亭》还是西方的《仲夏夜之梦》,运用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均可达到增加戏剧的趣味性、可观性,为剧作增添神秘浪漫色彩的作用,而且梦境的构造也为受限于固定空间的戏剧拓宽了表现空间,营造出了多重层次感。
(二)对梦发生场所的营造
从梦发生的场所来看,《牡丹亭》杜丽娘“游园惊梦”以后花园为背景;《仲夏夜之梦》则是在森林中。在中国,园林一般乃私家归属,而莎士比亚笔下的森林则是自然的森林,蕴涵的意义不尽相同。
1.代表“家中之野”的花园
与雅典自然界森林不同,花园是人为产物,虽可以超越以“家”为空间载体的社会伦理秩序,但却无法彻底脱离,于是后花园只能称得上家中之野。它既是人们超越世俗的情感寄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牡丹亭》中的花园,以自身的美引发了杜丽娘对春的伤逝,对生命、青春和爱情的热爱与憧憬,她的情欲在这个花园萌芽,又在花园得到了释放,但是她的肉体却始终逃脱不了家的牢笼。死后被埋在花园之中虽然可以看作是她本人对爱情的执着以及对旧梦的怀念,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恰恰说明了作为自然人的杜丽娘至死都未曾摆脱家的牢笼,一生囚禁其间,为故事增添了一丝凄凉。
2.代表自由世界的森林
《仲夏夜之梦》中的森林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也是乌托邦式的象征。对比之下,戒备森严的雅典城代表着崇尚父权、专横残酷的现实世界:赫米娅和拉山德彼此相恋却被父亲要求嫁给狄米特律斯,依据法律,如若违反父亲意志就要被处死或永远独身。在雅典的宫廷中,作者展现了青年人婚姻自主的要求与家长包办婚姻、非人道的雅典法规的尖锐冲突。雅典城外,精灵居住的森林充满生机,宛若一片桃花源。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把森林设置为自由恋爱场所的故事。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必须遵循严格的等级礼制,而森林中的仙女精灵却能自由嬉戏玩耍。所以森林便为爱情的发生提供了场所,如爱神阿弗洛狄忒与美少年阿多尼斯的浪漫故事就发生其中。而与莎翁悲剧代表作《麦克白》《李尔王》中阴冷恐怖、悲凉压抑的荒原相比,仲夏夜的森林月色如水,花朵芬芳,生机勃勃,是个不染世俗的天堂,没有禁锢没有压制,只有美丽的景色和自由自在的灵魂。通过对场景的布置也表达了作者对个性解放的推崇和对美好和谐的向往。
三、结语
通过对《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故事情节的分析以及对作者梦境话语的选择和梦境发生场所的营造方式——花园、森林的比较,可以认识到受社会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这两部作品在梦的描写和梦境方式运用上有同有异,而二者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内涵也值得我们不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