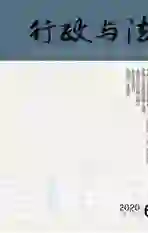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研究
2020-07-04刘凯
摘 要:《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等一系列行为。随着该《决定》的出台,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保护也应作出回应。目前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存在保护对象不统一、制裁范围有疏漏、罪名适用区分困难、罪数判定存在差异以及违法与犯罪标准重合等问题。对此,应当以《决定》的出台为契机,结合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新的立法需求,在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前提下,基于违法一元论的立场,完善现行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保护立法并作适度的前瞻性规定。具体而言,应当协调《刑法》及相关行政立法的规定,完善现有罪名的规定,将食用等行为独立成罪,并完善司法解释。
关 键 词:刑事保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刑法谦抑性;野生动物资源
2020年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野味产业”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1]多种证据证明,常见的诸多野生动物都携带了可致病的细菌、病毒、寄生虫,[2]食用野生动物对公共卫生健康安全具有极大的风险。事实上,我国食用野生动物的风俗由来已久。宋代便有记载:“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文人苏轼也曾作诗:“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时至今日,由于少数地方部分民众社会公共卫生健康意识落后及立法疏漏等原因,部分地区仍存在食用“野味”的现象。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2月24日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客观地说,《决定》在强调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之外,增加了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公共安全的全新内涵,对于治理食用野生动物现象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决定》出台为节点,对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立法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当前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行探讨。
一、野生动物资源立法保护的现状梳理
我国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采取了行政与刑事相结合的二元保护模式。毫无疑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属于法定犯的范畴。这类犯罪并不违反伦理道德,只是由于法律规定才成为犯罪,[3]也即“由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成立的犯罪”。[4]最初将法定犯理论化的犯罪学家加羅法洛在其经典著作《犯罪学》中提出了诸多法定犯的类型,其中之一为“与某个国家中地方性或特别立法相抵触的行为。如违反……狩猎、捕鱼……以及其他各种地方法规的行为”。[5]通常在治理这类犯罪时采取的是“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定罪机制,[6]“前置法”即相关的行政立法。下文将分别基于行政和刑事角度,同时结合《决定》内容,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立法进行梳理。
野生动物资源行政保护的立法现状可总结为“一个核心,多维补充”:“一个核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其最初制定于1988年,并于2004年、2009年、2016年以及2018年进行了修改①。《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及相关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非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以及非法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多维补充”则是指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而制定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在刑事保护方面,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罪名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下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之中,主要为第341条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以及非法狩猎罪。分则第151条规定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虽然也涉及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其指向的犯罪客体为海关制度,破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危害的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犯罪客体不同,笔者不做过多关注。此外,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的内容,明知或应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有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决定》主要涉及野生动物资源的行政保护,相关内容可归纳为三点:第一,重申现行立法规定,禁止所有非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并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这一内容涉及到猎捕、交易、运输以及食用等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由《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5条、第46条、第48条、第49条等规定。加重处罚意味着在没收涉案非法物品的基础上,处更为高昂的罚款、吊销从业证照等。第二,全面禁止食用行为。《决定》中禁止食用的对象既包括受法律保护的、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包括人工饲养繁殖的相关陆生野生动物物种,对此将参照现行法律规定处罚。该内容扩大了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给现行立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将野生动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三有”野生动物),且在第28条规定了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采取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体现出了将人工繁育的物种与传统意义上的野生动物做不同对待的立法精神。与之相对应,立法(第30条)绝对禁止生产、经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以及为了食用而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但单纯的“食用”行为并未禁止;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野生动物以及不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立法仅禁止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并不禁止食用、购买等行为。《决定》不再区分野生动物的保护等级,也不再区分是否为人工饲养繁殖,一概禁止食用行为。笔者认为,《决定》主要参照的法律条文应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9条。该条为违反第30条对应的责任,对于非法生产、经营、为食用非法购买等行为,将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在此,可将其处罚范围扩张至食用环节,将其保护对象扩大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之外的其他野生动物,以协调《决定》的适用。第三,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等行为。对于《决定》作出的该规定,应当从四方面进行理解:一是该款内容应为前述规定的补充,以保障禁止范围的完整性,不留死角;二是应当对该规定涉及的野生动物做扩大解释,将“野生动物制品”纳入禁止范围;三是“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是其限定条件,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不应在禁止之列;四是“食用”是受禁止行为目的的限定词,出于科研等其他合法目的而依法实施相关行为者不应受处罚。《决定》第4条对出于科研、药用、展示等目的而对野生动物进行非食用性利用的情形作出了例外规定。当存在这些违法情形时,笔者认为可参照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6条、第48条的内容。第46条规定了非法狩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时的法律责任,可将之扩大至为食用目的而狩猎的情形;第48条规定了非法出售、购买、利用、运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出售、利用、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可扩大其适用范围,将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交易、运输行为纳入其中,以解决《决定》的适用问题。
二、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存在的问题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属法定犯的范畴,在适用相关罪名时需要考察相关行政立法的内容,以准确认定行为的性质。如前所述,《决定》扩大了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和禁止行为类型,对现有行政保护的内容产生了冲击,间接地对《刑法》相关罪名的适用产生了影响。笔者结合《决定》对刑事保护产生的影响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对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⒈保护对象存在差异。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无论是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还是其他野生动物,均在保护之列。从该法条的体系定位——《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及文义解释的角度观之,此处的“野生动物”应为“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在此前提下适用不同罪名。但是,《解释》中却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的范围作了扩大解释,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反观《野生动物保护法》,其保护的是“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且在2016年修法时删去了有关国际条约适用的规定,这意味着如何适用CITES有待进一步明确。该法还规定,对于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要采取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从立法内容来看,严格贯彻了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的理念,同时还隐含了限缩保护范围的精神。但司法实践并未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影响,如2016年引发热议的“深圳鹦鹉案”①,被告人因出售个人饲养繁殖的6只鹦鹉而被认定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是以“狩猎”为中心,非法捕杀的野生动物是否为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三有”野生动物并不影响定罪。就此来看,《刑法》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大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此次出台的《决定》则体现了扩张保护范围的理念,禁止食用将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而食用通常是猎捕、杀害行为的终端行为,对于捕杀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罪是否能够通过扩大解释的法律方法进行规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明确。
⒉禁止范围尚有疏漏。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相关的非法猎捕、杀害、运输、买卖等行为均受到禁止,而对于其他野生动物,则禁止非法捕猎行为。换言之,根据犯罪对象的不同,《刑法》的禁止范围存在很大差异,留下了一定的疏漏。一是食用等利用行为未被彻底禁止。早在2001年便有学者发起了《珍爱自然:拒烹濒危动植物宣言》的倡议,提出拒烹、拒售、拒食野生动的“三拒”主张。[7]2003年SARS疫情后,部分地区制定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定,如《深圳经济特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若干规定》,[8]但《刑法》至今未作修正。虽然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部分特殊情况对《刑法》分则第341条和第312条作出了解释,行为人明知或应知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但这实际上并未扩张该罪名的适用范围——立法本就禁止收购行为,犯罪目的并不影响定罪。同样,明知或应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解释,对于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现象没有实质的助益。此次《决定》完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刑法》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将食用行为纳入制裁范围。再者,无论是食用还是经营,都可看做是“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方式之一,《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对非法经营、利用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作出了提示性规定。如果立法意在实现对野生动物的全面保护,那么应考虑禁止所有的非法利用行为。二是与捕猎相关的下游行为未被完全禁止。追根溯源,破坏野生动物犯罪的起点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进而发生杀害、运输、出售、购买、食用等行为。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立法仅禁止捕杀和购买行为,运输及出售行为未作规制。出售与购买行为可看做是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从一方主体转移至另一方主体的过程,是一种“流转”现象。如果立法意在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非法“流转”,那么仅禁止买卖行为并不能保证治理范围的周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的被告人在非法捕获野生动物之后赠与给其亲朋好友既有可能是活体,也有可能是死体,还有可能是部分残骸,如肉、骨骼、皮毛等等。对于这类行为,《刑法》也未作出規定。如宋某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①,被告人宋某和使用猎捕网非法猎捕“三有”动物班翅山鹑31只,掐死带回家后送给其侄子宋某某3只(死体),法院并未追究其侄子的责任。再如李某平、肖某元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②,被告人肖某元非法购买5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后将其中3只赠送给其两名友人,法院也未追究受赠者的责任。综上来看,如果立法意欲完全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现象,那么赠送及非法获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以及非法运输、出售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也应受到禁止。
⒊罪名区分存在困难。根据立法表述,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的犯罪构成看似明确,但实际上却难以区分。根据通说,[9]二者的区别在于三方面:第一,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侵害的对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后者则是一般野生动物。第二,犯罪成立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犯罪时间、地点、工具、方法等要求。前者没有限制条件,后者则有禁猎期、禁猎区、禁用的方法和工具的要求。第三,犯罪成立是否要求一定的情节。前者属行为犯,后者则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但结合具体的犯罪形态来看,这些区分标准缺乏实际意义:首先,如果基于事后的视角对犯罪过程进行评价,那么自然能够对犯罪对象是否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与日本刑法理论中判断是否成立不能犯时采取的事后判断立场相似。[10]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社会公众并不能对诸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与一般野生动物作出区分,更遑论是否能认识到野生动物的具体保护级别与名称。[11]其次,捕杀野生动物的时间、地点、工具、方法由犯罪对象的体型、生活习性等因素确定,而非其保护级别、名称,这就导致两罪的犯罪过程在多数情况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差别仅在于结果不同。换言之,区分两罪无法通过行为时留下的客观证据来间接证明行为人意欲实施何种犯罪,只能通过获取其直接供述的方式发现真相,[12]但问题不止于此。根据《解释》对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规定,非法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构成犯罪,这就导致非法狩猎罪实际上成为了“行为犯”,更难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进行区分。
(二)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⒈罪名适用存在疑义。如前所述,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难以区分,这直接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罪名适用的争议。如果行为人沒有明确的捕猎对象且使用的工具、方法也不具有特殊性,那么无论根据立法还是概括故意理论都将面临对行为准确定性的难题。根据理论分类,[13]概括故意包括对行为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对行为对象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以及对危害结果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具体而言,行为人会认识到犯罪对象是野生动物,但对其保护级别和物种缺乏认识,也即对行为对象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此时,如果犯罪未能顺利进行,未造成任何结果,那么应如何认定行为构成何种罪名。如实践中发生的胡某福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非法狩猎案①:2016年5月12日,被告人胡某福持枪支上山打猎过程中被群众发现,枪支被群众夺走并上交派出所。法院认定其同时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狩猎罪,数罪并罚执行管制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就此来看,司法实践贯彻了谦抑思想,在未造成结果时认定为非法狩猎罪。但这反而给理论提出了难题:既然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行为犯”,在未造成结果时,如何认定行为人构成该罪。
⒉罪数判定存在差异。在行为人造成双重结果时则面临是否应认定其构成想象竞合犯还是数罪并罚的争议。换言之,应以何种标准去界定猎捕野生动物犯罪行为从着手到犯罪结束的全部过程进而确定准确的罪数。对此,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存在差异。罗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②:2019年4月22日20时许,被告人罗某在当地农田、水沟等地,通过照明、电捕的方法非法捕获9只野生蛙类。经鉴定,9只蛙类中有3只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另6只为“三有”野生动物。法院认为,被告人一行为触犯二罪名,属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罚,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免予刑事处罚。与此案相似,在罗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③中,被告人罗某与罗某贵(另案)在当地山中采用夜间照明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4只。其中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只、国家“三有”野生动物3只。法院未论证是否属想象竞合犯,直接认定其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在石某真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④中,被告人石某真于2017年5月25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4时许,在当地山坳以灯光照明诱惑方法非法狩猎和猎捕候鸟22只,其中有囯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只,其他为“三有”野生动物或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法院认定其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犯非法狩猎罪,判处罚金2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4000元。与此类似,在余某文、李某、马某龙等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⑤中,四名被告人于2019年4月30日上午6时一同去打鸟。被告人余某文准备了气枪、汽车等作案工具并射杀鸟,另三人找鸟、捡鸟,偶尔开枪。四人猎杀野生鸟类共有11只,其中2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它为江西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法院认为其中三被告人的行为分别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应数罪并罚,分别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从这四起案例来看,如果将行为人的整个捕杀过程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捕杀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一般野生动物都是“一个行为”造成的结果,适用想象竞合犯理论自然没有异议。但是,前述被告人均为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就此来看对罪数的认定更适合基于连续犯的理论展开。[14]而由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不同,涉及两个不同的罪名,这就使得连续犯的理论不能完全解决罪数认定问题,需要借助数罪并罚理论进行考量。相比之下,似乎数罪并罚的做法更为适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告人的捕猎行为具有可分割性和相对独立性,如果使用电网、粘网等犯罪行为具有“一次性”特征的捕猎工具,那么将之认定为连续犯便存在不妥。所以,对于捕猎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司法实践认定罪数的做法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想象竞合犯或数罪并罚处理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
⒊犯罪与违法标准重合。根据修订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将直接追究刑事责任。2016年修法时增加了行政处罚的内容,即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以及罚款等。就此来看,立法意图通过增加捕杀行为的责任类型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做无罪化处理,以在入罪之前留出一段行政处罚的“缓冲地带”,形成梯度化的责任区间。但这次修法对司法实践没有产生影响,如颜某友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①,行为人用制作绳套陷阱的方法猎捕了1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后被法院认定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这显然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相矛盾——二者对该行为都可适用,犯罪门槛与违法门槛发生了重合。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如张某甲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②:2015年3月,被告人张某甲、李某甲在网上相识。李某甲得知张某甲手中有犀牛角,便欲购买。同年7月某天,被告人张某甲携带自家祖传的“犀牛角”及印章、手串、项链等角制品,从山东来到盘锦,在盘锦火车站附近的宾馆内,以人民币35000元将上述物品卖给被告人李某甲。2015年10月15日,被告人张某甲再次携带角雕件等物品来到盘锦,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张某甲出售给李某甲的印章为岩羊制品、张某甲携带的雕件为北山羊制品。后法院认定张某甲犯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笔者认为,该案无论从情节还是危害性来说,都适合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而非刑事责任。
非法狩猎罪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刑法》处罚的是非法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情形。《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包括两种具体标准:一是数量,即“非法狩猎猎野生动物二十只以上”;二是情节,即“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15]两种标准存在本质差别,前者要求一定的犯罪结果,而后者则使得非法狩猎罪成为了“行为犯”。“情节严重”应当意味着大量野生动物被捕杀甚至灭绝的危险,[16]仅仅因为满足“四禁”要求便构成犯罪,未免有背离立法原意之嫌。因此笔者认为,上文提及的胡某福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非法狩猎案,被告人尚未造成捕杀野生动物的犯罪结果,符合行政处罚的条件,也没有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⒋定罪量刑标准有待完善。除个别罪名外,《刑法》分则通常不会规定具体的量刑标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也不例外。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规定的法定刑有三个幅度,上文论及了尚不构成情节严重时与行政处罚衔接不畅外的问题。而对于情节严重以及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则存在量刑标准与定罪标准重合且缺乏梯度性的问题。我国《刑法》中的“加重犯”包含结果加重犯、数额加重犯及情节加重犯三种类型,[17]但该罪涉及的“情节严重”以及“情节特别严重”与传统的情节加重犯又有所不同。根据《解释》,两罪名的加重情节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手段、方式、身份等具有特殊性而加重的情节,但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与基本犯相同①。另一类则是以犯罪对象种类、数量或涉案金额为标准的加重情节。这两类情节又存在一定的交叉,当构成基本犯罪但尚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时,若具有特定情节则认定为“情节严重”;若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时,则因存在特定情节而构成“情节特别严重”。但就犯罪对象的种类和数量标准而言,该加重情节本身有其不合理性。通常来说,加重处罚的规定意味着存在基本犯形态。但在两罪所涉的部分犯罪对象中,加重情节与定罪情节相重合,行为人往往面临两种情况——或无罪,或构成“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不存在构成基本犯的可能,行为人极有可能直接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如叶猴、河狸等野生动物,一旦捕杀1只即达到“情节严重”的条件,而金丝猴、野马、高鼻羚羊、雪豹等野生动物,捕杀1只即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起刑点就是十年有期徒刑。
非法狩猎罪虽然不存在加重情节,但其定罪标准也存在一定问题。有研究认为,司法解释规定的“二十只”入罪标准太低,有扩大刑事追究范围的嫌疑。[18]但笔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野生动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一方面会导致入罪标准过低,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入罪标准过高。对于以兔、鸟、蛙类为代表的小型野生动物,具有群体数量大、生存区域与人类生活区域交叉、容易捕捉等特点,并且受保护的种类极为较广泛,“二十只”的数量标准有入罪门槛过低的风险。相反,对于野猪等大中型野生动物,其种群数量往往很少,生存区域往往远离人类生活区域,必须使用一定工具或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并且这些工具和方法往往对人类也有威胁,可能造成人体伤害或死亡等更为严重的后果。[19]此时,“二十只”的入罪标准似乎又有些过高了。
三、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的价值取向
(一)野生动物保护应增添新内涵
在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0]在2月24日出台的《决定》中更加强调了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这些都为今后野生动物保护指明了方向。
生物安全是进入21世纪以来颇受关注的领域,其内涵丰富广泛,涉及到转基因技术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从广义上看,生物安全指一切生物处于不受损害的状态,包含转基因技术安全、外来物种入侵、濒危物种保护等内容;[21]狭义的生物安全则指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免受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害和损害的状态。[22]2019年10月,我国的生物安全立法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草案规范、调整的范围包括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等八个方面。就此来看,我国立法采取的是狭义的生物安全理念。生态安全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泛指人类健康、生活保障、生活资源、生存环境、所处社会和生存权利等处于不受侵害的安全状态,[23]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三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后者则专指自然生态系统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24]我国《环境保护法》是治理生态安全问题的基本法律,侧重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但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的生态安全单行法律。
基于对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理论及立法实践的考察,野生动物保护是两者交叉的节点。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野生动物自身有诸多未知的不安全因素,其食物来源、生长过程、病毒传播、再到屠宰过程等都不具有可控性,[25]早年发生的SARS疫情,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致病率极高的甲型流感病毒,以及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与野生动物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从生态安全的角度来看,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会直接导致生物链缺失进而引发生态失衡,[26]对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换言之,保护野生动物不仅仅能够维护生物多样性,还可以避免因不当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导致各种有害生物危害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生物风险。现有立法虽涉及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检疫问题,但未完全确立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目标。相关刑事罪名则更重视对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的维护,未能发挥维护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应当增添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新内涵,强调对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保障。
(二)贯彻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保护固然重要,但应当正确认识到刑法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换言之,应当在强调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同时贯彻刑法的谦抑性,摒弃传统刑法观念中的刑法万能主义观和重刑主义,[27]遏制当下野生动物保护泛刑法化的趋势,把握合理的刑事保护边界与尺度。
最初提出刑法谦抑性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其明确了“谦抑性”的三个核心理念,即刑法应当具有补充性、不完整性以及宽容性。而这三个核心理念都可通过刑法的“补充性”来概括。[28]之后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完善了其含义,即刑法应当作为社会抗制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29]事实上,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中确实存在部分足以伤害公众法感情的案件。如“闫啸天掏鸟案”①和前文提及的“深圳鹦鹉案”等都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质疑。还有部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以及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件,犯罪的起因是社会公众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如农田、林地、鱼塘、虾池、牲畜等而采取了有失妥当的方法导致野生动物死亡的结果,进而构成犯罪。对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处严厉的刑罚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损刑法的权威与公正。换言之,野生动物应当得到保护,但刑法在部分案件中的适用过于刻板、僵硬,反而动摇了公众内心的法律确信,对实现法治产生了负面影响。[30]
(一)统一各法律部门的规定
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需要,应完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首先,协调不同法律部门的规定。基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行政法的保护范围应当大于或等于刑法的保护范围。如前文所述,《刑法》《决定》《野生动物保护法》《解释》等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存在差异。基于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司法实践情况,结合此次出台的《决定》内容,同时出于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应当对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对象范围做统一规定。具体而言,《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明确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人工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提供同等保护,为适用相关罪名奠定行政立法的基础。其次,对于之前未被立法所重视的人工饲养繁殖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应对其保护问题作出规定。但应注意的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人类以及整个自然界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具有种群数量稀少、甚至面临灭绝的危险,[40]与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动物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即使对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提供全面的保护,也应当贯彻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设置合理的入罪门槛及科学的量刑规则。
(二)完善相关罪名规定
针对《刑法》中现有的三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名,可考虑对其作出一定的改进,以解决罪名间区分困难、司法适用不确定、犯罪与违法标准存在重合等实际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应明确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的“结果犯”属性。根据当前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鲜见未造成任何犯罪结果而被认定构成前述两罪名的情形。而且根据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既然造成一定犯罪结果的行为构成行政违法,那么仅有行为时更不应认定为犯罪。如果明确两罪必须造成一定结果才能构成犯罪,那么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违法与犯罪标准重合的问题也具有了立法层面的基础,也能够避免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对此,可考虑将刑法表述改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致使野生动物资源受到破坏,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此,可以提高两罪名的入罪门槛,实现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而且,如果以犯罪结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便于与非法狩猎罪作出区分。二是可考虑取消非法狩猎罪,设置调整范围更为广泛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以规制非法猎捕、杀害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狩猎”的内涵显然小于“捕杀”,是其下位概念。从立法层面來看,非法狩猎罪的核心在于禁止有目的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非法狩猎罪早已“名不副实”,“狩猎”基本等同于“捕杀”。如果追求对野生动物进行全面保护的目标,那么将该罪改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并不存在实践上的障碍。如此还能确保《刑法》保护范围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决定》之间的协调统一,避免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可考虑在前述罪名之外增设减轻刑事责任的条款,对出于合法目的而造成犯罪结果的情形,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如前所述,如果取消非法狩猎罪,设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那么将侧重对犯罪客观方面的考察,突出犯罪结果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如此将会扩大入罪的范围。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买卖、运输祖传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案件,以及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而造成野生动物死伤的案件,因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对行为人处严厉的刑罚并不利于实现立法目的,所以应设置减轻刑事责任的条款,以对相关罪名进行限制,实现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以及刑事立法科学化的目标。
(三)食用等行为独立成罪
《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以及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其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并且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食用行为作出了限制,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刑法》则禁止非法捕杀及买卖、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非法捕杀其他野生动物的行为。《刑法》禁止的范围明显小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决定》,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8条、第49条对经营、利用行为作出了具有刑事违法性的提示性规定,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并无直接对应的罪名。对于非法经营、利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通常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而对于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因这些野生动物属于《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在涉案数额较大时,司法机关多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但这也引发了争议,即《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效力级别不够,在缺少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等明确规定时,不应将之认定为非法经营罪。[41]
需注意的是,在2020年2月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及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明确将“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开办交易场所、进行网络销售、加工食品出售等),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解决了前述争议,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修订《刑法》新增设的罪名,脱胎于“投机倒把罪”,[42]被学界普遍称之为“口袋罪”,主张限缩其适用范围的呼声占据了主流。虽然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在形式上符合该罪的构成,也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危害,但却忽视了行为对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及公共卫生安全等更为重要的法益,指向性不够精准,且该罪并不能杜绝社会公众个人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也不能治理赠送等非法提供、获取野生动物的行为,更不能禁止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所以,从长远利益出发,应考虑将食用、非法经营等非法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独立成罪,设置“非法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同时,可设立“非法提供、运输、获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用以治理赠送、无偿获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非法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这些行为目前尚未受到刑法的禁止,但其危害性不应被忽视。此两罪名的法定刑不应过重,与现行非法狩猎罪的法定刑相当即可。
此外,基于立法前瞻性的考量,可考虑作出保护非野生动物的刑事规定。鉴于当前并无非野生动物保护的专门行政立法,所以刑事立法应当相对保守。对于非野生动物的保护可借鉴境外立法的经验,从犬、猫等“伴侣动物”着手,有限范围内禁止非法食用行为。一是由于当下相关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如来源不明等,食用犬、猫等动物存在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二是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公众呼吁保护伴侣动物,有限度地保护犬、猫等伴侣动物具有社会文化基础,社会公众易于接受。借此,可逐渐培养社会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塑造保护动物的文明理念,待形成自发、主动保护动物的文化氛围之后,可考虑建立涵盖野生动物以及非野生动物保护的完整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深圳市在2020年4月1日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中,通过“白名单”与“黑名单”相结合的方式,明确列举了猪、牛、羊等可以食用的动物范围,间接禁止了食用犬、猫等动物,这为今后制定相关法律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
(四)完善司法解释
笔者认为,针对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对现有司法解释予以完善:首先,在定罪方面应当明确犯罪工具及方法对罪数判定的重要作用。对于同时造成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一般野生动物死伤的情形,如果行为人采用陷阱类捕猎工具、方法,如设置电网、粘网等情形,由于犯罪行为不具有可分性,实际上是一行为造成了多结果,不应对行为人数罪并罚。应根据想象竞合犯的理论择一重罪处,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采用枪支射杀等行为具有可分性的犯罪工具、方法捕杀野生动物,可结合连续犯的理论对其数罪并罚。其次,适当提高犯罪门槛,准确划定与行政违法之间的分界线。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应当设置完善基本犯形态的入罪标准,留出行政法发挥作用的空间。就非法狩猎罪而言,一方面,应当取消“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入罪情形,使其回归“结果犯”的起点;另一方面,应当借鉴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相关犯罪的入罪条件,根据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个体体型、捕杀难度等因素设置科学的入罪数量标准。最后,应完善量刑标准。针对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有关的犯罪,应当以数量标准为主,设置三个梯度的量刑幅度,避免出现当前“或无罪,或五年(十年)有期徒刑起”的不合理现象。同时,结合现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特定情节,设置加重处罚的条件,以打击情节恶劣但犯罪结果轻微的犯罪情形。同样,非法狩猎罪的量刑标准也应当精确化、科学化,区别不同野生动物种群分别设置量刑标准,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此外,鉴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基本属性,行为人先前所受相关行政处罚的情况应得到重视,可将因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作为量刑的参考因素。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2]黎天德,吴玲.SARS与嗜食野生动物所致的人类疾病[J].中国热带医学,2003,(6):878.
[3][10]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5,330-332.
[4]陈兴良.违法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A].贾宇主编.刑事违法性理论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1.
[5](意)加罗法洛.犯罪学[M].耿伟,王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5.
[6]田宏杰.行政犯的法律属性及其责任——兼及定罪机制的重构[J].法学家,2013,(3):55.
[7]赵荣光.拒烹、拒售、拒食野生动——我是怎样提出“三拒”倡议的[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9.
[8]龙山剑.禁食“野味”有法可依——深圳出台《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若干规定》纪事[J].人民之声,2003,(11):32.
[9]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87.
[11]苏雄华,冯思柳.生态法益视域下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5):89.
[12]晋海,吴柯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实证研究——基于496个判例的研究分析[J].行政与法,2017,(2):89.
[13]张永红.概括故意研究[J].法律科学,2008,(1):86.
[14]蔡桂生.论连续犯與同种数罪的区分及刑事处罚[J].福建法学,2007,(2):7.
[15]刘凯.非法狩猎罪的司法实践困境分析——基于421起案例的实证研究[J].行政与法,2019,(7):71.
[16][18]蒋兰香.规范刑法学视野下非法狩猎罪司法解释的基本逻辑[J].法学论坛,2019,(6):153-154.
[17]陈兴良.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J].法学研究,1985,(4):31.
[19]刘凯.论非法狩猎罪之异化与纠偏[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9,(3):109.
[20]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4/content_5478896.htm.
[21]王子灿.论生物安全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J].法学评论,2006,(2):147.
[22]陈颖健.生物安全: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新领域[J].求是,2004,(6):53;于文轩.生物安全立法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7.
[23]翟新明,余广俊.生态安全法框架体系完善构想[J].人民论坛,2016,(5):139.
[24]吴柏海,余琦殷,林浩然.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J].林业经济,2016,(7):21.
[25]郑风田,孙瑾.我国部分地区嗜食野生动物的成因探析[J].消费经济,2005,(5):86.
[26]孙杭生.食野习俗与生物链缺失问题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06,(1):81.
[27]杨鸿雁.和谐社会视野下对传统刑法观念历史局限的考量[J].法学杂志,2008,(2):64-65.
[28]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J].法商研究,1995,(4):55.
[29]梁根林.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J].现代法学,2000,(6):47.
[30]罗钢.动物刑法保护的公众意识与规范反思[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9,(6):58.
[31]张文,杜宇.自然犯、法定犯分类的理论反思——以正当性为基点的展开[J].法学评论,2002,(6):33.
[32]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J].中国法学,2017,(4):47.
[33](日)团藤重光.法学的基础[M].1998:82.转引自(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12.
[34](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14-215.
[35]王昭武. 法秩序統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J].中外法学,2015,(1):173.
[36](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M].曾文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5.
[37]田宏杰.行政优于刑事:行刑衔接的机制构建[J].人民司法,2010,(1):86.
[38]赖登赞,林庆坚.司法解释与法律的稳定性[J].人民检察,1998,(3):12.
[39]高永明.刑法修正案修正规则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91.
[40]张桂新,徐君.关于野生动物的主要法律规定[J].野生动物,1991,(5):37-39.
[41]孙飞.浅析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定性[J].森林公安,2015,(3):32.
[42]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2000,(2):22.
(责任编辑:王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