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闻专业是尴尬的?
2020-07-02许知远
文 许知远


彭刚
2020年5月14日,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在一场校内会议中指出,经学校反复研究、慎重决策,决定大幅度扩大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规模,今后学院的人才培养主要在研究生层次进行。次日,该学院一位教师向媒体证实:从今年开始,清华新传学院将暂停招收本科生,但将扩大研究生招生。这一消息被解读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取消本科”。
撇开媒体和大众对这一消息可能存在的揣测和误读,关于“新闻本科专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这一话题在网络上被持续热议。有网友表示“新闻是非常讲究实践和人脉的专业,根本不是教出来的”,还有新闻专业毕业的本科生表示,自己在应聘记者时完全没有优势。这些议论让人们重新审视“教育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记者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等问题。
本文从许知远的《新闻业的怀乡病》一书中摘编了一些章节,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作为记者出身的许知远,早在2005年,似乎就认识到了新闻专业的尴尬。同时,他认为优秀的记者应当是一名“准知识分子”。
新闻专业为什么尴尬?
两项最负盛名的职业教育正遭遇质疑。《管理学习与教育学刊》在对MBA毕业生经过一番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花费10万美元、2年时间的MBA教育对毕业生未来的薪酬及职业前途并无明显作用。加拿大的管理学权威亨利·明兹伯格最近也说,管理课程只对那些已具有管理经验的人才适用。
比起商学院,新闻学院更为尴尬。哈佛大学在1908年创办了第一所商学院,不管怎样, MBA在全美最大100家公司中的40家是由MBA(不一定来自哈佛)领导的。创办于1912年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现今必须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尽管它的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是那么著名,尽管它在新闻领域享受着甚至比哈佛商学院之于商界更高的声誉,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校长李·伯令格却不这么认为。他最近表示,新闻学院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因为它的课程实在太技术化、简单化了。学生们在这里经过10个月的“如何采访、报道”的简单培训后,就拿到了硕士学位。但这些技能在任何报社内都可以学到,他看不出这种教育有何意义。伯令格认为,新闻学院应该更广泛地教授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期也该延长,它有理由像法学院与医学院一样既在实践上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在学术本身上也有更高的追求。

哥伦比亚大学
笔者之所以转述这两则例证,是因为笔者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不久前,笔者所在的公司组织了一次时髦的管理训练。你知道,有关“团队精神”“管理能力”的培训项目在最近两年如此流行,以至于所有勇于争先的公司领导者都愿意让自己的员工去感受一下“目标管理”与“有效沟通”。对笔者个人而言,为期两天的培训是个沮丧的经历。在种种考验人的项目面前,尽管笔者所在的团队中不乏聪明人,但在积分表现上却令人苦恼。
恰巧,笔者所在的公司又是一家报社,它吸引了一些来自各所著名与非著名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但却最终发现某些熟记“5W”原则的“新生力量们”不会正常写作,除了熟知的采访要素外根本不知道该问采访对象什么问题。对于商学院,笔者缺乏发言权。但是,笔者相信管理的短期培训除了像少年时的夏令营一样有一点可玩性外,不具有任何管理意义上的价值。你可以学些财会、心理学、流程上的基本常识,用英语熟练地说出“core value”(核心价值)、“strategy management”(战略管理)。但是,一个管理者的核心职责是做决策,他需要宽阔的知识背景与至关重要的直觉,这一点在企业的危机时刻尤其重要。
在新闻领域内,笔者的话可能稍微多一点可信度。今日英国最著名的记者克里斯托夫·赫钦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院说,当今的新闻丢失了文学能力,早期的新闻记者从查尔斯·狄更斯等作家那里吸取养分,新闻报道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的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新闻业影响巨大的常常是非正规的新闻人:亨利·鲁斯是一个知识分子与准传教士;吉普林与海明威的记者经历鼓舞了后来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彼得·德鲁克年轻时是个社论作家,并终身保持着与媒体的热切联系。新闻缺乏独立成为一个行业的能力,它必须不断地借鉴其他领域。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只懂物理的物理学家成为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却不可能看到一个只懂新闻知识的记者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事实上,记者需要成为一名准知识分子。
困扰我们中国同行的最主要问题,并非是他们采访技能的贫乏,而是他们还没学会严肃地看待自己的职业。他们首先要成为一名有尊严、有趣味、有眼光的个体,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记者。当然,这个要求适用于所有职业。
回到开头,哈佛商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面临的指责,并非是全然否认它们在技术培训上的非凡贡献,而是对技术环节的深层基础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显得更加珍贵。那些总是沉迷于技术性改革的行业是不会具备长久的生命力的。而对于正在建立自己的商业传统与新闻传统的中国同行来说,及早打下更深厚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
通才需求VS专业分工
有感于美国人对于世界的无知,24岁的亨利·鲁斯与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布瑞顿·哈登于1923年创办了《时代》杂志。关于发起缘起,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他们对十新观念的浓厚兴趣。在1923年之前,也就是在《时代》创办之前,当人们提到“新闻”时,政治与犯罪是唯一的反应。但鲁斯对于一切社会现象几乎都抱有强烈的兴趣与好奇 ——医学、法律、科学、技术、宗教甚至新闻业本身,这也使得《时代》几乎重新定义了“新闻学”的概念。1929年,鲁斯创办了《财富》杂志,因为他想更深入地了解仍为公众陌生的工商界。而到了1936年,他又试图利用镜头来展现如此广阔与奇妙的世界,于是在美国街头出现了《生活》杂志……
亨利·鲁斯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末的改革者传人。200年前,以富兰克林、亚当·斯密、狄德罗为代表的改革者们对于世界的强烈好奇心,驱动着他们不断进行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于是,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现代社会的法制、技术、民主、经济等基本观念也由此建立。产生于世纪和世纪的变革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伽利略对物理学基础的贡献等,同样是被一群对知识强烈饥渴的好奇者所驱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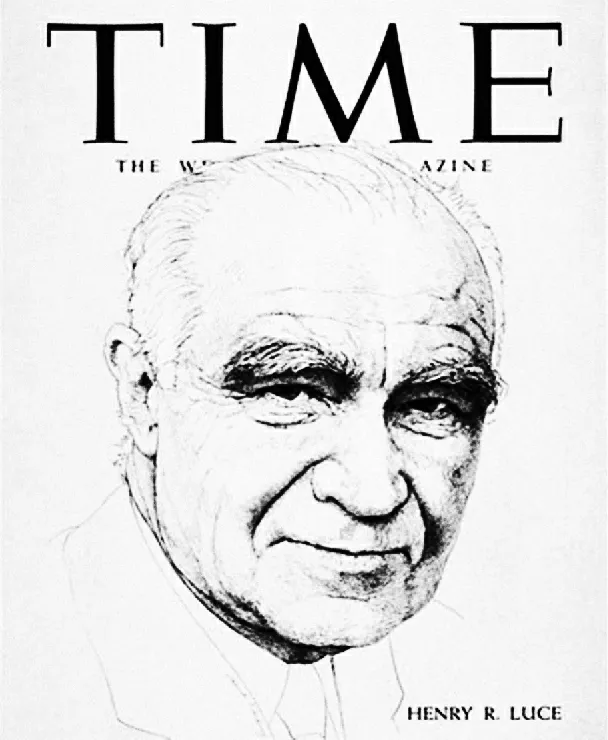
《时代》《财富》《生活》等杂志正是鲁斯这种好奇心与思想的产物与执行者。罗伯特·赫钦斯所谓的“鲁斯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性格的影响要大于所有教育制度的总和”的评价,正彰显出鲁斯的好奇心与充满理想主义的努力对于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因为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媒体所营造的影像与文字是公众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它们的确有可能比正规的学校教育更有效。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出现过杂志热。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梁实秋、林语堂,从日本归来的周氏兄弟,当然还有本土的陈独秀等等,他们渴望为僵死的中国文化注入生气,于是他们利用《新青年》《语丝》,还有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拼命地从西方国家引入制度、文化、思想的讨论。这一切努力的确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人中掀起了一股狂热,他们对于“恋爱自由”“科学与民主”这样的话题倍感兴趣,并激发了诸如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青年学生的高远志向。今天的学者喜欢将“启蒙运动”加之于20世纪20年代,并将其推至一个神圣的地位;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正是那些在20年代不断涌现的各类杂志与书籍,激发起了一代青年沉睡的好奇心,他们开始渴望了解生活的更多种可能性。
尽管今天的中国青年处于前所未有的多样选择的时代,但笔者仍有些遗憾地发现,互联网、电视、书籍并未激发起他们的热情与好奇。资讯的充足甚至伤害了他们的思维,当他们面对丰富的世界时,似乎仍在用单调的目光打量,他们多少有一点与马尔库塞所描绘的“单面人”相类似。
留心,这触及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命题——通才教育。亚当·斯密早在200年前就提醒我们,过细的专业分工正在让人变得工具化。今天,亚当·斯密的忧虑早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弊病。我们发现自己是如此乏味,除了工作之外,对于其他领域所知甚少。我们是医生,是律师,是程序员,是股票交易者,却不是一个丰富而有趣味的独立个人。在这本杂志的编辑看来,好奇心是对抗这种专业化与乏味化的最有效手段。当你让莫奈的画、柏辽兹的音乐、非洲的考古发现、微软试验室的科技发明、《纽约书评》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时,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充满了趣味,它湿润柔软而非干燥坚硬。好奇心让你摆脱与强悍的社会、狭隘的内心碰撞的机率,它让你学会与自己对话,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的教育理想,是《大西洋月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时代》的理想,如今,它也是我们这群年轻而好奇的编辑的理想。
从事新闻业需要的品质
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影响着现今大多数的中国记者。他们将自己的职业想象成一个转型社会的先知,试图在价值失衡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他们迷恋于揭露黑暗,追寻真相,就像20世纪80年代前的美国电影中的记者形象: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今天的中国除去面临19世纪末美国的转型以外,还同样面临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互联网开创的新传播年代,在这种语境中,新闻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呈现更多的信息,而是信息泛滥。在这双重夹击下,新闻业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就更明显地放大出来。
首先,新闻很难客观。新闻对正常的世界不感兴趣,它只喜欢异常。所以当战争、灾难到来时,新闻记者的神经也开始活跃起来。与过去年代不同的是,媒体在我们时代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媒体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依靠它来了解世界。所以新闻业的习性,将直接塑造大多数人对于世界的感知。2001年9月11日8点42分之后,美国人几乎相信,这世界上只有恐怖主义;就像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国人只关心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一样。不得不说的是,灾难的显著性,除去国际压力的影响外,媒体的渲染同样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电视网使中国大部分并非疫区的人民亦有了强烈的参与感。
其次,媒体具有天生的取悦市场的倾向,市场的诱惑可能比政府压力更可怕。保罗·克鲁格曼发现,英国的国有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在报道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常常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而美国私有的福克斯等电视网,却仿佛是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因为后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他们需要迎合公众的态度。
当然,笔者承认,从来就没有笼统的新闻业之称。电视与纸质媒介(报纸、杂志)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因为它的反馈更为迅速。所以,中国新闻业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必须拥有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媒体行业。电视天生适合于提供更多的信息;而报纸与杂志却并未提供更多的分析与观点,这种分析与观点本应在混乱期给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其次,理解力在我们时代的新闻业中将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甚至比勇敢这种品质更为重要。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着太多的牵扯,杰出的记者越来越注重为读者提供这种线索的梳理,而非简单的呈现。
不管新闻业多么受制于外界环境,笔者却越来越相信,与它的品质最直接相关的仍是新闻人本身。希望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平平的中国新闻人能够意识到,束缚他们前行的是他们自身能力的缺陷,他们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