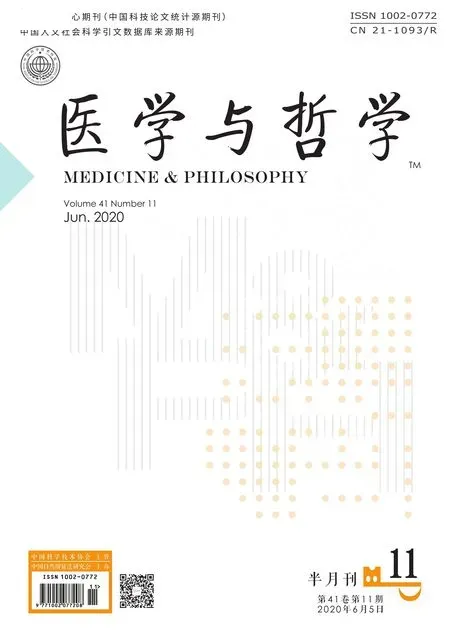从印鉴考察徽宗敕撰《圣济总录》国内外版本传藏情况*
2020-06-23杨金萍刘更生王振国
杨金萍 刘更生 孟 玺 王振国
《圣济总录》,200卷,是宋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方书,成书于北宋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年~1125年)。此书镂版未及印行即罹靖康之难,书版随内府图籍被掳劫至金。金大定年间(1161年~1189年)国子监和元大德四年(1300年)江浙行中书省曾用原版刊印2次。元大德本曾因明嘉靖帝赐赠而流传至日本。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年)江户医学馆有聚珍本刊行。目前,金刻本已不存,元大德本国内外尚存残帙,日本聚珍本国内外存有完本,另外还有明抄本、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刻本、日本抄本等多种版本。由于《圣济总录》是宋徽宗敕撰的大型方书,卷帙浩繁,影响深远,故几经刊刻及海内外传藏,特别是经由名家过眼,钤盖的官私印章较多,而此书各种版本流传情况复杂,故借助于名家印鉴及书目题跋进行考察,以期理清国内外众多版本传藏脉络。
1 元大德本
元大德本实为北宋政和版挖版重印,除每卷首行“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第某”为元人挖版外,其他绝大部分内容包括字体、栏框、刻工姓名等皆为宋版之旧。其版式白口,四周双边,每半页8行,每行17字,字大行疏,版心下部有刻工姓名。目前国内及日本存有元大德刻本的残卷,除去重复者,共计93卷[1]。
1.1 中国中医科学院2卷藏本(卷183、184):范行准藏书印
此2卷本有著名藏书家范行准的藏书印。卷183首页右侧有三枚印鉴,见图1。首行“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第一百八十三”卷题下有“范氏栖/芬室所/用图书”白文方印(盖倒);次行小标题后从上向下依次为“汤溪范/氏栖芬/室图籍”朱文方印、“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善本”朱文长方印。卷184首页次行小标题下有“范氏栖/芬室所/用图书”白文方印;卷末左下有3枚方印,分别作“善本”朱文方印、“范行准”白文方印、“善本”朱文方印。

图1范行准藏元大德本
从以上钤盖的印鉴可知,此2卷曾由范行准收藏。范行准,名适,浙江省汤溪县(今属金华县)人,致力于医史学研究及中医古籍整理,尤嗜搜求古籍善本,室名栖芬室,意指书暂时栖止之地,钤印未敢用“藏书”而名“用”、“备用”、“图籍”等,说明“藏书为用”之本心。
《栖芬室架书目录·子部医家类》载其收录情况:“《圣济总录》二百卷。存卷第一百八十三至一百八十四,一册,并属‘乳石发动门’。予同时曾得此书两本,以一册贻之闲好,记似妇科者,今其书久已散去,无可取检。”[2]从书目可证其曾收藏过2卷元刻本(属“乳石发动门”)。另一册妇科卷因贻他人而散佚。《中国医籍通考》云:“北宋刊元大德印《圣济总录》,藏北京范氏栖芬室,洵海内之珍本也。此书《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录》俱有阙佚。”[3]1984年范行准将栖芬室图籍全部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其中包括2卷元刻本《圣济总录》,故现今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来自范行准捐赠。
1.2 国家图书馆28卷藏本
国家图书馆藏《圣济总录》元大德本共4种28卷[2下、3、4、12(1页)、23、35、36、44、54、55、56、65、66、71、79、93、96、128、129、130、138、150、156、169、173、174、175、183],包括补抄本(128、129、138)。其中有多枚印鉴。
1.2.1 徐晓霞藏书印
徐晓霞藏书印见于卷23。此卷是国家图书馆4种藏本中的一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简目(初稿)》载:“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存一卷。二十三。元大德三年至四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三册。”[4]该卷右侧首行“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二十三”卷题下钤有“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次行从上向下依次钤有“晓霞/收藏”朱文方印及“爱日馆收藏印”朱文长方印,见图2。“爱日馆”是清末至民国年间徐钧的藏书室,徐钧,字晓霞,浙江桐乡人,喜收藏金石及图书,长于诗词。其父徐焕谟,擅诗文,著《风月庐诗稿》《风月庐剩稿》。《风月庐剩稿》民国二年刻本扉页牌记作“桐乡徐氏爱日馆藏板”,该刻本“桐乡劳乃宣序”称“同邑徐钧晓霞刊”云云,说明由徐钧刊刻,且爱日馆为徐钧藏书刻书之室。徐钧为南浔张均衡(字石铭)的妻(徐咸安)弟,徐钧的藏书可能与张均衡有一定关系;徐钧又与南浔著名藏书家刘承干、缪荃孙互有往来,另从他人书目题跋推察徐钧藏书有可能来自宁波范钦天一阁者。但此卷藏本未能查知由何处转藏徐氏。徐钧藏书印有“晓霞藏本”、“晓霞”、“爱日馆收藏印”、“长林爱日”,另有吴昌硕篆刻“爱日馆金石书画印”。

图2徐晓霞藏元大德本
1.2.2 “京师图书馆”藏书印(4册:卷65、66、71、93、150)
卷71首页卷题及卷末卷题后皆钤有“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朱文长方印,见图3,他卷亦见此印。京师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前身,宣统元年(1909)由清学部奏请筹建,至1912年成立并开放,《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归安姚氏书。宋徽宗敕编。元刊本。存。六十五六、七十一、九十三、一百五十。四册。”[5]从京师图书馆著录“归安姚氏书”推断,此5卷最初来自归安姚氏藏书,即浙江吴兴姚觐元,其藏书楼为咫进斋。京师图书馆藏书早期主要来自内阁大库,内阁大库曾从江南采进图书,其中就有归安姚氏藏书。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序:“顾草创之初,所恃以充架者,惟内阁大库旧藏。其中宋元秘籍殆数百种,惜其年湮代远,阙失弘多。其后端忠敏自江南奏进,有归安姚氏、南陵徐氏、海虞瞿氏诸家之书,旧椠精钞,往往而在。”[6]
总之,此四册本大体传藏过程为:归安姚氏→内阁大库采进→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图3京师图书馆藏元大德本
1.3 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6卷藏本(卷50、52、53、131、191、194)
卷50首页右侧天头处有“藩祖荫/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右侧次行从上向下依次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见图4。

图4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元大德本
1.3.1 怡亲王府安乐堂藏书印
安乐堂是怡贤亲王允祥的藏书室,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谥号“贤”,其第七子弘晓袭怡亲王。怡亲王府藏书始于允祥,至弘晓甚盛。弘晓藏书室名“明善堂”,藏书印为“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清代陆心源等将乾隆“乐善堂”当作怡府室号,今人已证其误[7]。此卷只有安乐堂藏书印,并无明善堂的印记,可能是允祥在雍正时期收藏。
陆心源《仪顾堂续跋》云:“怡贤亲王,为圣祖仁皇帝之子,其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二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8]说明怡府藏书的来源,系由毛晋、钱遵王归于徐乾学、季沧苇,而后归于怡府。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圣济总录》:《铁围山丛谈》中言政和间编,诏天下凡药之治病彰彰有声者,悉索其方书上之。此录盖汇聚诸方而成书也。”[9]说明钱谦益曾藏《圣济总录》。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宋元杂板书》载“《圣济总录》一百卷”,季氏之书多出于常熟钱氏之藏。由怡府藏书的来源结合钱、季的著录,或可推断《圣济总录》经由钱氏归转季氏,而后归入怡府,即:钱谦益→季沧苇→怡府。
1.3.2 潘祖荫藏书印
“潘祖荫/藏书记”的印记说明此书曾由潘祖荫经眼。《滂喜斋藏书记》证实怡府藏书并详记卷数,曰:“元《大德重校圣济总录》残本六卷。一函八册。宋政和中奉敕撰。原本二百卷,重刻于金大定,再刻于元大德,此即大德本也……此本仅存六卷(五十、五十二、五十三、一百三十一、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四)。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疏行大字。怡府藏书。附藏印:安乐堂藏书记。”[10]可见潘氏所得《圣济总录》来自怡府藏书。自载垣被慈禧太后赐死后,怡府藏书逐渐流散,其中一部分归于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为著名藏书家及金石收藏家,藏书楼名滂喜斋、功顺堂等。滂喜斋一部分藏书来自怡亲王府,潘景郑(祖荫族侄孙)《著砚楼书跋·怡府书目》:“《怡府书目》一册,余廿年前所得晒印抄本。目中著录,多宋元秘籍……盖怡府之书,藏之百余年,至端华(笔者注:应为载垣)以狂悖诛,而其书始散落人间。聊城杨氏、常熟翁氏、钱唐朱氏及先从祖,皆得其遗箧。吾家《滂喜斋书目》著录有怡府藏印者,不下二三十种,皆其精本也。其藏印可证者,有‘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诸印,皆精劲悦目。”[11]可见怡府藏书归潘祖荫者多。
1.3.3 “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
“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潘祖荫滂喜斋所藏6卷元刻本转归国立中央图书馆,后疏迁至中国台湾,现藏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学研究中心”。《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民国四十六,1957年)卷三“甲编”著录:“《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存)六卷八册。宋徽宗敕编,元太医院重修,元大德四年太医院刊本。存卷五十、卷五十二、卷五十三、卷一百三十一、卷一百九十一、卷一百九十四。”[12]32卷数与潘祖荫所藏吻合。其著录藏印亦与所见同。
综上所述,6卷元大德本的传藏过程大体为:钱谦益→季沧苇→怡亲王府(安乐堂)→潘祖荫(滂喜斋)→国立中央图书馆(民国)→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1.4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35卷藏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35卷元大德本《圣济总录》,一般每卷首页钤有印章,如卷六十七首页右侧自天头向下依次有“医学/图书”朱文方印、“跻寿殿/书籍记”朱文长方印、“帝国/博物馆/图书”朱文方印;右下卷题后钤“多纪氏/藏书印”朱文长方印,他卷类同,见图5。另一印模糊不清,郑金生指出是“宫内省图书印”,犬卷太一认为是“宫内厅图书印”,依稀可辨为“宫内省图书印”,此印并非每卷皆有。另外,在每册封面有二个书签,分别为“东京帝室博物馆”、“图书寮”。

图5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大德本
1.4.1 多纪氏藏书印
“多纪氏藏书印”、“跻寿殿书籍记”、“医学图书”诸印鉴,皆为日本著名医学世家及藏书世家丹波氏家族藏书印记。多纪氏即丹波氏,世代为医。1765年丹波元孝首创私人医学馆——跻寿馆,宽政三年(1791年)由丹波元德提议而归于幕府管理,改名医学馆(或称“江户医学馆”)。丹波氏藏书室名“聿修堂”,藏有较多的善本图籍。“跻寿馆记”、“跻寿殿书籍记”、“医学图书”图书印为丹波氏创立的医学学校印章,医学馆印章还有“江户医学藏书之印”。
从钤盖的印章推断此35卷元刻本是丹波氏家藏本。日本杉本良《聚珍版圣济总录序》指出江户医学馆在校定聚珍本《圣济总录》时,曾参考了二种元刻本,一是吉田宗桂被嘉靖帝赐赠的元大德本,另一种是丹波氏家藏本,曰:“我邦天文丁未之岁,吉田宗桂意安从僧策彦入明留居四年,其归也,赍《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来……癸酉春,与山本锡侯、丹波绍翁谋借之于吉田氏十世孙子颖,以为原本,以丹波氏家藏本及古写本校讐,活字刷印于医学。”可知丹波氏有二种《圣济总录》版本,家藏本与古写本对提,说明家藏本不是抄本,可能是刻本。《医賸》曰:“今吉医官及予家所藏大德重校本,亦大版大字,然无‘耶律楚材’五字(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无“五”)。原文书法端雅,盖为宋版之旧。但每卷首页‘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第某’数字,书刻并劣,系于元人改刊无疑矣。”[13]从丹波元简所述可推知吉田氏家藏本与丹波氏家藏本皆为元刻本,与上“丹波氏家藏本”之说相吻合。《聿修堂藏书目录》载录大德本:“残本《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存自六十二卷至九十四卷。二十二册。大德原本。”
总之,日本至少有二种元刻本及一种古写本《圣济总录》,吉田氏所藏元刻本为足本,而丹波氏所藏为残本。丹波氏家藏本目前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吉田氏家藏本原藏于吉田氏称意馆,《经籍访古志补遗·医部》:“《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目录一卷。元大德四年刊本。吉田氏称意馆藏。”[14]吉田意庵的藏书印有“吉田悌所曾阅”、“称意馆藏书记”、“吉氏家藏”,但目前所见的元大德本中未见有吉田氏藏书印,而吉田氏所藏元大德本,由于条件所限,未能查到现在藏于何处。
1.4.2 帝国博物馆图书印
“帝国/博物馆/图书”藏书印说明丹波氏所藏元大德本曾藏于日本帝国博物馆,后归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帝国博物馆始建于1872年,名为文部省博物馆,后经扩建,1889年改名帝国博物馆,1900年更名东京帝室博物馆,1947年改国立博物馆,1952年复更名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宫内厅前身依次是宫内省、宫内府,1949年改名宫内厅。宫内厅书陵部属于皇宫内藏书所,其前身是图书寮,1884年名为宫内省图书寮,1949年6月图书寮图书移交宫内厅书陵部。
综上可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35卷元大德本的传藏过程为:丹波氏家藏(聿修堂)→跻寿馆、江户医学馆→帝国博物馆→东京帝室博物馆→宫内省图书寮→宫内厅书陵部。
2 日本聚珍本
2.1 北京大学两部藏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2部日本聚珍本《圣济总录》,其中一部只钤有“北京大/学藏”朱文方印;另一部除“北京大/学藏”朱文方印外,还在序及每卷开首钤有“麐(麟)嘉/馆印”朱文方印,见图6。日本聚珍本是江户医学馆在元大德本基础上重新整理校刊,由医官子弟捐资刊行的活字本,丹波元胤参与整理刊行,是目前《圣济总录》版本中内容最完整且校刻质量精佳的本子,在国内外皆有流传,北京大学所藏2部聚珍本是由日本流传过来的。

图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聚珍本
“麐(麟)嘉/馆印”是李盛铎藏书印。李盛铎(1859年~1937年),江西德化(今九江市)人,晚号麟嘉居士。出生于藏书世家,因精于目录版本之学,能广求善本,并从日本购得许多汉籍。李盛铎从日本购求古籍主要通过二个途径:一是通过在上海开设乐善堂药店的日本人岸田吟香购得,二是利用出使日本的便利购求古籍。李盛铎曾2次访日,期间通过日本藏书家岛田瀚获得日本藏汉籍,其中包括国内失传的珍稀宋本医籍,如日本影宋抄本《太平圣惠方》、宋刻本《医说》、元刻《永类钤方》等,同时还搜购了许多日本、朝鲜的木刻、活字及抄本等,江户医学馆所刻聚珍本《圣济总录》可能是此时购得。
在以往的传统初中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中,学习内容相对容易并且单调,很难让学生对体育产生兴趣,学生容易感到厌恶或者无聊。而有效的体育游戏则可以让学生能够在愉悦的环境下吸收体育知识,锻炼运动技能,增强体质,从而有健康的身心发展。所以,不妨适当而合理地把体育游戏融入到体育与健康教学中,提高教学内容的有趣度以及学生对学习体育的兴趣,进而有效提高对课堂活动的主动参与意识。
李氏藏书颇丰,北京大学图书馆得木犀轩藏书达9 087种58 385多册,其中宋元善本约300种。李盛铎去世后,其子李滂于 1939年将木犀轩大部分藏书以四十万元售于日伪政府,这批藏书最后归属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藏书基本得以保全。
李氏重要的藏书楼木犀轩,从其曾祖一直延续4代。李盛铎藏书楼还有麟嘉馆、凡将阁、建初堂等,藏书印有“李盛铎印”、“木斋”、“木犀轩藏书”、“麟嘉馆藏”等。北京大学藏聚珍本《圣济总录》钤“麟嘉馆藏”印者,正是李氏藏书佐证,麟嘉馆是李氏于京师的藏书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虽未著录此本,但确是李氏藏书无疑。
2.2 国家图书馆藏本:方功惠藏书印
国家图书馆藏本在卷三首页“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卷第三”卷题后钤有“方功/惠藏”白文方印。
方功惠,清代湖南巴陵(今岳阳)县古萝塅人,嗜好古籍,闻人家善本,必多方钩致之,其藏书印“好书到手不论钱”、“书癖”、“书奴”。家有藏书楼碧琳琅馆,父时藏书颇丰,至方功惠庋藏更盛。日本明治维新时,方功惠先于杨守敬在日本购书,光绪初年即遣人去日本,曾购得日本曼殊院、尾张菊地氏、知止堂特别是著名的佐伯文库藏书。方功惠辞世后,其孙方湘宾将藏书运到北京待卖,并请同科举人乡试旧交李希圣为其厘定书目。李氏由此得以亲见方功惠藏书,“遇旧椠精抄,随意记录,间加考证,以备遗忘”,“于方氏藏书,不过九牛之一毛而已”[15]。今查国家图书馆藏李希圣《碧琳琅馆珍藏书目》,载有:“影宋本(朱文小字)。《圣济总录》二百卷,一百本,一箱。”证明方功惠确实藏有《圣济总录》,后经李希圣过眼,但李氏将其称为影宋本是不确切的,实为聚珍本。后方氏部分藏书卖给北京琉璃厂,另有部分藏书经李希序推介捐赠给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方功惠藏”印鉴者,当为方功惠收藏之本,但究由何途径藏于国图尚难查明。
2.3 湖州中医院藏本:傅云藏书印
湖州中医院图书馆藏聚珍本《圣济总录》200卷。在“聚珍版圣济总录序”序题后有“□□傅岩/珍藏书籍之章”朱文长方印,见图7;在“闻波居士”手书的序后有“傅”、“稚云”朱文方印。

图7傅云藏日本聚珍本
傅云(1875年~1945年),字稚云、耜颖,名岩,号闻波居士,浙江湖州人,曾购得聚珍本《圣济总录》,书前有傅云题跋云“余于戊午冬购此倭本二百卷,完全无缺,虽非原刊,亦殊难得,为志其略如此。闻波居士傅岩”。傅云藏书后皆捐为公有,1947年湖州医学图书馆“景行轩图书馆”成立之际,傅云藏书10余箱约2 500册由其子傅维德捐赠给中医师公会。1957年湖州市联合中医院成立后,景行轩图书馆藏书全部移藏湖州市中医院,中有傅云藏书,现湖州中医院所藏聚珍本《圣济总录》即是傅云藏本。
2.4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印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聚珍版《圣济总录》200卷,在“大日本文化癸酉”牌记处、每册封页内面钤“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朱文方印,每卷末钤“国立国会图书馆”朱文长方印。另在序文页及每卷目录页右侧栏框外钤“赠寄/……/殿”朱文长方印,中有“长谷川ェツ”蓝字,见图8。国立国会图书馆实行图书“呈缴”制度,由出版藏书机构呈缴图书,其馆藏包括明治维新后日本所有出版物,此部聚珍本《圣济总录》应属于呈缴本,有“赠寄/……/殿”印鉴。

图8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日本聚珍本
3 日本抄本
3.1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卷藏本:邓邦述藏书印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日本抄本200卷,书前有邓邦述手书题跋,题跋右侧有“群碧楼”朱文长方印、“钞本”朱文长方印,左侧有“正闇/经眼”白文方印,见图9;次在“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序”序题下有“群碧/楼”白文方印、“清真/堂主”朱文圆印;在目录页“大德重校圣济总录目录”文字下有“史语所收藏/珍本图书记”朱文长方印;在每卷开首有“群碧/楼”白文方印、“清真/堂主”朱文圆印、“史语所收藏/珍本图书记”朱文长方印,每卷末有“清真/堂主”朱文圆印。

图9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日本抄本
邓邦述题跋说明了得此书始末,云:“此足本也。吾国所刊行者,曾不及半。往岁吾友冯敏卿,乞余在都门觅一本,即吾国本。敏卿审其不足,嗣余遍访之书肆,乃知日本尚有足抄本。盖皆病其卷帙太繁,不能覆刊。此则日本所抄,兼用朱笔校过,致为罕觏,惜余不知医,又无力为之刊布,仅为吾国留一足本。世有精岐黄之术者,待其探索可也。壬子津门正闇写记。”邓邦述《群碧楼书目初编》载“《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日抄足本”,说明群碧楼曾藏有200卷日本抄本。又其《群碧楼善本书录》与邓邦述题跋内容大同,云:“《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一百二十八册。宋徽宗御撰,日本抄本……有清真堂主一印……壬子七月津门正闇。”《书录》所言“清真堂主”印与笔者所见相吻合。从其题记“壬子七月津门正闇”,推测邓邦述可能是于民国壬子年(1912年)辞官后在天津得此抄本,后携至苏州的群碧楼,最后转卖于中央研究院,现藏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综上可见,此部日本抄本的传藏过程为:邓邦述群碧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3.2 天津市图书馆200卷藏本:天津图书馆、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印
天津市图书馆藏日本抄本200卷,见图10。“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序”序题上方钤有“善本/鉴定”朱文长方印,下方钤有“天津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朱文长方印;在天头正中有“直隶□/检查图□”朱文长方印(盖倒),因章未盖全,故难以辨全。经向天津市图书馆研究人员咨询,得知印章全称为“直隶教育厅/检查图书之印”,部分文字另钤他处作存档用。

图10天津市图书馆藏日本抄本
这三处印鉴与天津图书馆变迁有关。天津图书馆的前身是天津直隶图书馆。1907年成立直隶图书馆,1912年直隶图书馆改为“天津直隶图书馆”,1918年改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1928年直隶省更名河北省,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隶属河北省教育厅。1937年天津沦陷,1938年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将省馆改名为“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河北省立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志》)。解放后馆名及馆址又有数次变迁合并,如有天津第一图书馆、天津第二图书馆、天津人民图书馆,1982年定名为“天津图书馆”。
“直隶教育厅/检查图书之印”,为直隶教育厅所钤印鉴。直隶教育厅成立时间为1917年10月,由此推断此印章钤盖时间为1917年以后;“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为日伪占领天津时(1938年~1945年)天津图书馆的印章;“天津图/书馆藏”印鉴是现今天津图书馆的印章(1982年以后)。
综上可见,此部日本抄本的传藏过程为:天津直隶图书馆→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
4 康熙抄本
4.1 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78卷藏本: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印
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康熙抄本178卷,馆藏著录:“藏印:‘甲’朱文圆印、‘马佳/宝文/私印’白文方印、‘怡府/世宝’朱文方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朱文长方印、‘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怡玉贤/书画印’朱文长方印、‘绳须馆珍/藏书画印记’朱文长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今见卷一右侧天头处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之印。
由印鉴推知,康熙本曾由怡亲王府世藏,“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怡府/世宝”皆怡府印鉴,说明此本经允祥、弘晓父子递藏。“绳须馆珍/藏书画印记”说明江藩曾过眼,江藩为乾隆至道光年间名儒,深究考据学,博通经史。《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民国四十六年,1957)卷三“甲编”著录此书:“《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存),一百七十八卷,一百六十册。宋徽宗敕编。清康熙间影抄元刊本。缺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三十、卷四十三至卷五十三、卷九十一、卷九十五至卷九十七、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八十三至卷一百八十五,凡二十二卷。”[12]32可见民国年间康熙抄本曾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后转藏于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其“影抄元本”说法不正确,因为元大德本的行格是每半页8行,每行17字,此抄本行格是每半页11行,每行21字。
由以上印鉴大体推断康熙本的传藏过程为:怡府允祥、弘晓→江藩→国立中央图书馆(民国)→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5 题为“朝鲜本”
国家图书馆藏有题为“朝鲜活字本”的《圣济总录》2册4卷,即卷185、186、197、198,但勘查实为日本聚珍本。卷185目录页右下有“好盦书库”朱文圆印;在正文页右下有“北京图/书馆藏”朱文长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文方印,见图11。

图11国家图书馆藏“朝鲜活字本”
5.1 郑振铎藏书印
“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为著名藏书家郑振铎藏书印。郑振铎(1898年~1958年),字警民,号西谛,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21年至商务印书馆工作。郑氏注重收藏图书,广罗古籍。抗战期间,为免国内珍稀藏书落于日、美之手,发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海内藏书特别是江南藏书家流散的书籍。“八一三”事变上海开战以后,郑振铎坚持留守上海,而在1941年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郑振铎不顾生命安危继续滞留上海,流离颠沛之际不断搜求书籍,常常居无定所,但救书之志未移丝毫,“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生命”,从其所著《求书日录》《西谛书话》可见拳拳救护之心。解放后任文化副部长等职,1958年外出访问时因飞机失事殉职。家属遵其遗愿,将其全部藏书17 224部94 441册捐献给政府,由北京图书馆接收。1963年赵万里主编《西谛书目》,著录医书六十种,其中包括朝鲜活字本《圣济总录》,现在国家图书馆4卷题“朝鲜活字本”《圣济总录》原为赵振铎收藏。
5.2 北京图书馆藏书印
郑振铎藏书捐献后由北京图书馆接收,此4卷藏本亦在其中,故有“北京图/书馆藏”的藏书印。
《圣济总录》成书于北宋之际并由政府组织编撰,其书不论是学术价值还是版本价值都非常高,故一直被医学界及海内外藏书家所重视,复经多次官私传抄刊行,版本情况至为复杂。因为经由多位名家递藏,钤盖官私印章颇多,从而为我们查考复杂版本提供了多重证据及有力线索。故借助印鉴及目录题跋,结合版本的实地调研,对于考察《圣济总录》不同版本流传系统,梳理海内外各种重要传本的流传始末及传藏脉络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