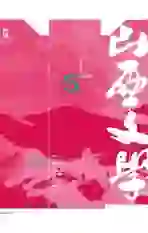追念式反思:历史的野蛮生长与底层的精神状态
2020-06-22马明高


1
在这之前,路内写的最好的小说无疑是《慈悲》。《慈悲》的好,在于他写出了工人阶级令人刻骨铭心的苦难。他不仅写出了底层的工人阶级是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苦与难,而且写出了他们是如何以慈悲之心宽待那些苦和难。“慈悲”,这个书名真的很好。更好的是,路内是以“慈悲”之心来写《慈悲》的。
当然,路内也是以“慈悲”之心来写这部最新的长篇小说《雾行者》的。无疑,《雾行者》没有《慈悲》深刻,因为《慈悲》是当下的,是一部忠实记录此时此刻的小说。但是,《雾行者》要比《慈悲》复杂、宽阔得多,而且也比《慈悲》丰饶、迷人得多。因为它写的是中国1998年至2008年三四线城市的野蛮生长,写的是这些三四线城市的底层青年的荒芜而复杂的精神状态,正如小说的内容简介所言:“迷惘与自戮,告别与重逢,一群想要消灭过去之我的人,以及何之为我。”我们倘若回望中国历史上的1998年至2008年,可能有98大洪灾、2008年的世界奥运会,可能还有汶川地震、南方雪灾、全民抗击非典、“9·11”恐怖袭击等等,但是,做为那一代青年人,对于这十年间的自我成长和时代认知,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你想想那十年间每年的“春运”,再想想那十年间官方对于人口流动的统计数字,“不包含打工者的家属,已经达到2.4亿人,这只是中国农民工的规模。”这只是触及到《雾行者》中像林杰、杨雄、梅贞、凌明心等等这些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还没有真正触及到《雾行者》中像周劭、端木云、辛未来等等从大学出来的打工者,像沉铃、玄雨、李东白、单小川等等从城乡出来而四处涌动的文学青年和像陆静瑜等从台湾等海外而来的打工者。我们再想一想,这么多的年轻人,为了生存,为了博得一个前程,主动抑或随波逐流地在中国大地上大规模地流动,这是多么令人震撼啊!但是,这同时又是多么复杂而宽阔啊!还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像这样正儿八经地去写那么多的文学青年,写他们的野蛮生长和他们对文学与小说的认知。我们会看到好多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作家、诗人和电影导演,诸如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莫泊桑、海明威、顾城、托马斯·伍尔芙、鲍里斯·维昂、侯孝贤、蔡明亮和杨徳昌等等,不时地在小说中的这十年间游荡。而且,我们很可能会通过这部厚厚的小说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小说家路内,从中看到他的文学观、电影观以及他对自己人生或过往创作的自嘲。所以,对我而言,这部小说又是那么丰饶而迷人!
《雾行者》的叙写方式是追念式的,是回忆式的。小说是在对过往十年生活的回忆中追寻历史的意志与人的生命意志,那么多事情,那么多人,那么多孤独、痛苦、欲望、爱情和伤害,四十七八万字,就那么洋洋洒洒地铺写在记忆这条绵延的长河之上,“似乎没有什么必要,然而回忆纷纷跳了出来,是回忆告诉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已经站在了自己的生活之外,这些遥远的‘事件和我们不再有什么关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就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回忆不是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它们还能有什么用呢?”(法国作家西奥朗语,转引自袁筱一的《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經典文学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第153页)纳博科夫说得好,好的小说家都是魔术师。好的小说都有它寓言性的一面,隐喻性已经成为现代小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的,好的小说家都在用更高级的方法,或者说他们在寻找一种更高级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们不再囿于对现实世界的描摹和对方芸芸众生的敏感神经的触动,他们在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中,架空了现实世界里的时间与空间的经纬,他们是在预言了某种存在的可能,而不是在描绘某种静态的业已存在。
人的一生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它是如何的绚烂或者卑微,我们毕竟只有一生,只有一种可能。而且,人生的悲剧就在于所有的经验一经获得,永远无法重来。何况,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在找些什么,又想弄明白一些什么。但是,我们身处的历史与环境,正处的时代与现实,会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具体的人。这样,我们与他人、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具体而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具体而复杂的关系,正是小说家和小说所关注的东西。正如批评家袁筱一所说:“我们成为在绝对意义上他人不可能重复的个体存在。是在我们和他人、和客观的物质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产生了爱、恨、冷漠、快乐、痛苦、欲望等情感:这一切都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第005页)
《雾行者》恰恰正是如此,它面对中国的1998年至2008年这么一个特定的时代,写出了这么一群特定的人,这么一个个特定的人的爱、恨、冷漠、快乐、痛苦、欲望等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存在在历史中的位置,看到了人的生命意志在历史意志中的自然淹没,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孤独、卑微和野蛮生长,看到了人的命运的不由自主和变化无常,看到了一系列关于人的重大问题,其实都潜藏在人物的命运之中,让我们看到了无论时代多么伟大,人都会活得比他的时代更长久。
路内的确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把他对历史与时代、世界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全部都落实在人物的现实生活与具体环境中,落实在每一个人物的身上,从而写出了人内心的深度,写出了人的疼痛与希望、爱和恐惧,从而让我们尽可能的去思考他们在那个历史与时代中生而为人的意义,去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与社会中生而为人的尊严所在。
2
是的,路内仍然是以慈悲之心去写这些在工业中国如雾一般的一大片城镇中这么一大群人的。那么,什么是慈悲之心呢?对于小说家而言,我觉得可能就是,怀着内心的热爱去同情。正如托尔斯泰所说:“要学会使你自己和人们血肉相连、情同手足。我还要加上一句:使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还很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要怀着对他们的热爱来同情。”(转引自伍尔夫:《俄国人的观点》,收录于《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至240页)
时值2007年,在一个梦境般的南方城市,“尤其夏天,植物在建筑之间疯长,台风和暴雨经常光顾,时而溃烂,时而金光闪闪,不会期待夏天过去,不会为冬天做准备,抒情和虚构都落在眼前,因为南方城市庞大而密集的细节足够描摹,即使梦,也达不到这种饱和度;这里的男人女人,粗鄙或精致,都有很强的距离感,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活着就像夏天午睡的人”(《雾行者》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版,第369页)。端木云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回忆自己所走过的那么多城市,回忆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在麦当劳里写小说”,写一本名为《人山人海》的小说,也就是《雾行者》的第五章:《人山人海》(1999—2007)。但是,“他说那不是小说,因为写的是他自己,但也不是自传,因为有别人的故事。故事看上去断断续续,枝节并生,人物称谓也不统一,一会儿直接引语一会儿间接引语”(同上)端木云就是路内长篇小说《雾行者》中的主人公之一。从第二章《逆戟鲸》(1998)中,我们知道,端木云与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周劭相识于一所三流大学的文学社。文学社的副社长是辛未来。端木云与辛未来投缘,周劭认识她比较晚。但是,周劭性格开朗,端木云有点内向。端木云“有一天看见她抱着一束花在街上走,那神情像梦游,端木云问说是谁送的花,辛未来说,当然是周劭那个傻瓜。端木云说,周劭会写点小说,还不错。辛未来说,你只关心小说,我问你,周劭这个人怎么样,他想和我谈恋爱。端木云说,不错啊,可以交往。辛未来说,我很犹豫,刚才拿着花走路,我想,随便挑一个人问问,如果这个人说OK,那我就OK了,如果这个人说不OK,那我就拒绝他。”(同上,第124页)两人恋爱了半年多,毕业前的两个月,他们来到上海,周劭边找工作边租了一间屋子,两人住在了一起,“周劭没有家底,辛未来更穷”“两个人把身上的钱凑在一起,确定了吃饭、抽烟、买避孕套、市内交通这四项开支,后来仍然不够,打电话给同学,只有端木云寄了两百元给他们,是他的稿费”。(同上,第34页)没过多久,辛未来就在上海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周劭回到学校找她,“端木云困惑地告诉他:辛未来带话,忘记她吧,她已经拿了毕业证走掉了。”他找到她住过的宿舍,床铺已经全部撤空,“只留下一张海报贴过的痕迹,海报上是前苏联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素描头像,这是辛未来最爱的诗人。”那正是毕业情侣们分手的季节,“他看着校园里热吻着的、痛哭着的情侣们,不知道错在了哪里,然而也只能这样了。”(同上,第36页)
周劭和端木云只好又到上海四处边找辛未来边找工作。因为穷,两人只能换穿周劭的西服去面试,甚至在同一家公司面试,当场换西装,天冷了,周劭拿出自己的两件被虫蛀的毛衣,一人一件套上,犹如一对温情十足的贫贱夫妻。两人做过一阵保健品推销员后,周劭发现一个女孩跟与他不辞而别的辛未来长得很像,而这个叫梅贞的女孩是铁井镇台资企业美仙瓷砖公司储运部的录入员。为了接近她,他两人又一起应聘美仙公司,结果两人都成了公司储运部的外仓管理员。这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工作,平均每半年更换一座城市。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些仓管员们就开始不停地在一个个按字母编号的城市间迁徙。而这些散落在各个城市的库区,都是在一些被废弃的曾经的工业区,浓雾笼罩的衰落之地。于是,一百来个人物,就在河北、山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州、重庆、綦江、拉萨等二十多个省市地区的那些衰落之地流动。由此带出一个个都市传说,和传说背后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还有许多反水、追案、杀人的故事,以及“十兄弟”的传奇。梅贞以前和仓管员林杰好。现在和周劭好上了。梅贞告诉周劭,“她说我做过妓女,用词准确,像是自虐,然后又不免为自己开脱:时间很短,只有几天。周劭不知该怎么回答,愣了很久才问,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梅贞说,当然是为了钱。周劭就说,你不该把这件事说出来,当然,我也绝不会说出去。梅贞说,我现在后悔,我到这个地方来,本意只想找一份活,挣一点薪水,如果能逃脱流水线女工的命运,我已经满足了。周劭说,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尽管我非常想安慰你。”(同上,第312页)正如林杰与杨雄对话所言:“他问杨雄,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杨雄说时间、生命、爱情、自由、尊严。林杰说,这些都能买到,唯独钱是不能花钱买的。钱得是你把一切自认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作为赌注押上去才能换那么一点回来。”(同上,第463页)可是,底层青年缺的就是钱。由于缺钱,常常使他们变得走投无路。正如梅贞所感觉到的:“这些世界上走投无路的男人都有一副无所谓的表情,都蠢,都在黑夜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同上,第322页)如林杰,如周劭和她哥哥,如那些已经跑路消失的仓管员。所以,“梅贞感到凄凉”。
我们也心同身受,“感到凄凉”。然而,在那轰轰烈烈的十年间,无数的底层打工者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们自然地从这样一位“怀着内心热爱的同情”写作者,有情义,对历史与时代有所思考的书写中,感受到了那一代人的失去与痛楚,理解了那一代人的奉献与被剥夺,理解了那一代人的付出与得到。
3
小说有一种极强的伤感气质。尽管作家路内采取的是一种耐心、克制、冷静甚至冷酷的态度去叙写的,但是,小说时时刻刻会给人一种令人心碎的巨大力量。这是因为作家采取的不是一种线性结构,不是一种霸权式的现实主义,不是一贯到底的“第一人称”或全知视角的叙写,而是一种时空在不同章节的有序穿梭,不停地回环反复,不停地回到起点,又不停地在中间拆解。小说的第一章《暴雪》(2004)、第二章《逆戟鲸》(1998)、第三章 《迦楼罗》(1999)、第四章《变容》(2008),运用的是全知视角,在各个不同的时空中自由而有序地叙写着过往的岁月和人事,我们仿佛跟着一位历经沧桑的侦探一路躲藏、观察、逃离,我们迷茫、紧张、困惑、恐惧,心虚。这些担心与后怕的复杂情感时时挤压着我们的心脏,只留下一点点可以喘息的空间。因为我们感到小说里每一个人都在每一章节中不停地穿梭,不停地野蛮生长。这个人可能在第一章里仅仅是一个配角,或者过客,但是到了第二章他又变成了主角。那个人在前一章里面是一个被叙述的人,被别人叙述者,可是到了下一章他又变成了叙述者,他在叙述着别人。过往的十年岁月,过往的人和事,过往的事故和案件,过往的爱情、传说和欲望,都是那么的郑重而不可蔑视,都是那么存在而不可磨灭,都在不同的叙述和被叙述中逐渐呈现,逐渐?充和完善,形成呼应,构成复调。第五章《人山人海》 (1999—2007),运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以文学青年端木云的视角又对过往的十年进行了一次回望、重读、追念和反思。作家用一种面目全非的模糊化,对小说前半部分的主调进行了省思式的处理。冷峻的罪孽、寒冷的天气,都营造出一种奇异的氛围。在这种冷峻的反思中,作家开始从一个仓管员的生活转向对这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特殊时代,以及那种特殊的生存环境进行窥探与省思,进而使前面的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身上爆发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核。正如评论家杨庆祥所说:“这部小说不是那种单一的霸权叙述的现实主义。这个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他自己的声音,这所有的声音又汇集成历史的喧哗。”(《雾行者:所有声音汇集成历史的喧哗》《北京青年报》2020年1月17日)
小说会有如此强烈的伤感气质和让人心碎的巨大力量,当然,小说这种独特而精致的结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小说散漫与紧密相结合的叙事风格,极为意象化的书写笔触和口语诗化的语言调性,以及“梦境、寓言、当代现实、小说素材、文学批评”杂语相陈的复杂强悍叙事体等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这是要强调,还是作家“怀着内心热爱的同情”的慈悲之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作家借小说中的人物端木云所说:“我说,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青年评论家讲小说,他说如果你(指的是另一位作家)的小說写到的那些人,用了他们的隐私,触动了他们的内心,却不能给他们以安慰,你最好赶紧去死。尽管在当时,我不以为然(认为小说应该是绝对的、超乎道德的),但现在我可以部分地同意这个观点,比如说,除了安慰以外是否还有惩罚,惩罚是否也可视为对另一部分人的安慰,还是它仅仅局限于惩罚。最重要的是,究竟何为安慰,很显然,道德(或超乎道德)并不能给人以安慰,它不在这个范畴之内。落幕之外,你的姿态也并不重要,无论你是装成伟大作家还是邪典大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我所听到的步伐声。”(同上,第556,557页)只要有“你被我所听到的脚步声”,作家就肯定是深扎到了我们所未知的历史与时代的海洋内部,已经迅速而有力地捕捉住了那些被公众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想,应该是如此。小说《雾行者》的重要性或者魅力之处,可能还就正在于此。
【作者简介】马明高,山西孝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著作20余部,曾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文艺理论评论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