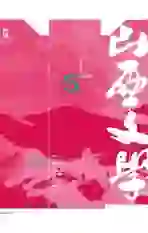吹地鹟(外四篇)
2020-06-22刘成群
我小时候那么小,总觉得地远天遥,看不到任何边际。村东的旷野里,麦子如同一派漾漾的碧海,广漠无限。那时候的风,直接从高天坠落,嗖嗖地,在麦海上砸出片片绿痕。高天蓝得很梦幻,太阳精光闪烁,孤独地悬置一方。天空中或者还有各种鸟儿飞过,然而我看不见,我只能看到云堆飘移,一团又一团,悠悠地,沉寂无声。
那时候,在沉寂的绿和沉寂的蓝之中,突然会传来几声粗笨的叫声,嗡——嗡——,闷闷的,却非常具有穿透力。我找不到声音的来源,旷野里的绿和高天上的蓝截然分明,宛如刀割一样。绿和蓝里,空荡荡的,连一个黑点都没有,有点像海上,又有点像是在梦里。
那时候我没有见过大海,不知道海的辽远,但我的梦里却有很多梦,有很多美好,绰约,朦胧,月亮常常带着几点星光,透过窗户,照进梦来。做梦的时候,鸟儿的叫声又会响起来,嗡——嗡——,村里似乎没有人,又似乎全在屏息听着鸟叫。月色如水,空气里回荡着鸟叫,像是在梦里,又不像是在梦里。
我似乎问过我瘫痪在炕的爷爷,然而我对爷爷的记忆也如梦一样的模糊,或许就是爷爷告诉我“吹地鹟”那样一个名字,说是有长的嘴,绿的背,在绿色的旷野里会隐去存在的痕迹,只有嗡——嗡——,一声,两声,敲打人的耳膜,刺入人的灵魂,然后归于沉寂。或许别人听不到,不过我能听到,躺在炕上的爷爷也能听到。
爷爷去世后,我忙于成长,从那么小长到不算那么小。旷野依然那么绿,天空依然那么蓝,爷爷融入醉人的绿蓝之中,不知道他是否还可以听到吹地鹟。嗡——嗡——,那个声音不管谁去世了,也不管谁在长大,只是在沉寂的空气里,猛然会响起几声,然后一切凝重如死,宛然没有了任何色彩。
村里每年都会有人死去,也都会有人逐渐长大。死去的人不会理会绿蓝的分割,长大的人不再感到地远天遥。对于死去的人和长大的人来说,孤独的滋味都是一致的,那半夜孤悬的明月下,陡然嗡——嗡——声起,仿佛钝刀直插心肺。在半夜孤悬的明月下,死者有寂寞的死,生者也寂寞的生,他们只是从来不觉得。
村里有很多好热闹的鸟儿,如麻雀、喜鹊、山雀、黄雀和野鸽子,那些鸟儿在村西暖阳里的榆树上排比了又排比,罗列了又罗列,成点连线,织就一张唧啾唧啾的网。榆树上的鸟儿,村里人都能叫出名字,然而,对于嗡——嗡——的吹地鹟,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
我曾经固执地去寻找那沉闷而辽远的声音,有时它在如注的暴雨里响起,那时候天地迷蒙一片。有时它在漫天的大雪中流荡,那时候视野里空无一人。偶尔有流动的影子可以跟踪,我跑啊跑,但只一两声后,便再无痕迹。
多年后,野不再绿,天不再蓝,那时候也就没有了陡起的嗡——嗡——声。村西的榆树上肯定还有鸟儿聒噪,然而从来与梦无关。孤悬的明月下还会有人死去,也有人悄悄成长。也许大家已经不再寂寞,那个嗡——嗡——的声音仿佛不存在了。
在我残存的记忆里,捉到过一只长嘴绿背的鸟儿,那一刻我想起过去世的爷爷。是不是吹地鹟吗?我不能确定。似乎我不小心一松手,让它飞到了明奶奶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从那以后,我偶尔能听见南边院里嗡——嗡——的鸟声,甚至有一次还恍惚看到那只鸟隐匿于沙果花丛中,褐色的影子一闪一闪,仿佛有绿色的光芒。
毛桃
毛桃为平原上的土著桃种,只要种上桃核就能成长为毛桃,不需特别的整饬。至于蜜桃是不是本地所产,我不晓得,但蜜桃需要嫁接却是尽人皆知的。我们小时候种上蜜桃核,长成后结的都是毛桃,颇不甘心的振辉试验过无数次,然而结出的都是毛桃,无一例外。
虽然毛桃没有蜜桃个儿大,但花儿却是无异的。清明前后,平原上雨水渐多,桃树枝头的花蕾也都膨胀起来。有时在一夜之间,就能开得满树绚烂。古人用“灼灼其华”来形容桃花是十分到位的,桃花开时,即有一种动人的粉色,在初春昏暗的背景里,确乎自带光芒。振辉家有一棵大桃树,每到春光骀荡的日子,粉色光芒四射,都能照亮天空一般。振辉家那棵桃树没有经过嫁接,结出的果子是毛桃,我好像也吃过,但却记不得许多了。
我与振辉都喜欢找些桃树栽在家里,然而并不专业,栽了许多年也活不了几棵。相对而言,占山哥算得是奇才,他栽什么果树都能盎然一片,他的院子里有毛桃也有蜜桃,大抵有几十棵,春天的时候,真如一片锦绣,占山哥穿行在桃花小径里,花雨缤纷,恍如诗境。占山哥是不是个诗意的栖居者,我不知道,然而占山哥确乎不愿与人交往,他的毛桃蜜桃都不曾与人,我好像扒过一些,但也记不清具体的味道了。
占山哥的性格颇有些寡合,但他却破天荒给了我一棵桃树。那棵桃树将要结果的时候被另一位寡合的人——囤哥悄悄地接成了蜜桃,不过,最终的命运是长了几个蜜桃之后就死掉了。我自小喜欢栽树,但少有成活的,即便成活,也都弱不禁風,苟延残喘。这大概与我属于火命有关。像栽树极好的占山哥、囤哥应该是木命吧,或者水命、土命也是相宜的。
火命、水命、土命之说,想来也是无稽之谈,占山哥与囤哥都是有意栽树之人,树长得好固不稀奇。然而,有的人并不有意栽树,即无心插柳之举,也能长成葱茏一片,便使人啧啧称奇了。如领哥,他只是在旧院里随手扔了一些桃核,结果竟长成一派蓊蓊郁郁的桃林。我记得在读初中时常去领哥的旧院,那时候的确没有桃树,10年后他家的旧房颓圮,然而房前桃影却是婆娑摇曳了。
领哥旧院里的桃树不知几许棵,没有任何的修剪,没有任何的整饬,它们乱糟糟地挤在一起,有些泼辣,有些野蛮,有股蓬蓬勃勃的冲劲儿。想来春天桃花绽放时也会涌荡奋腾,如火如霞地放出光芒来。遗憾的是,我没有在春天来过,或许领哥也不曾来。但每当桃子熟了的时候,我俩总能聚在一起,也都会去领哥旧院吃桃子。这样的情境持续了好多年,直到那个旧院卖掉后才戛然而止。
那些时候,领哥正处于人生低谷,我也有待升华,虽然阅世未深,却都是尝到了些苦楚的滋味,幸好有桃子可吃,能带来一些甜甜的慰藉。领哥旧院里的桃子无人嫁接,结出的桃子必然是毛桃无疑。然而那些毛桃很甜,虽然没有蜜桃多汁,但却自有一种软糯的口感。毛桃熟透后,可以将果皮轻轻揭去,露出莹白的果肉,只一口便可以吞在嘴里,甜糯的味道在舌尖齿底流动时,所有的不快也就抛之脑后了。
领哥家的旧院是个十分幽静的所在,毛桃成熟的时候却有些热闹,那些麻雀、白头翁、喜鹊以及众多不知名的鸟儿纷至沓来。好在桃树每年结果多,也不必吝惜那些鸟儿的喯啄。领哥家的毛桃从没人管理,也没人疏果,是以串串累累,堆积在枝头,闪耀出红彤彤的光芒。那时候领哥也没有什么朋友,只是年年将我引进院内,然后一顿饕餮。当是时,鸟儿们纷纷回避,树影晃动,叽喳之声不绝于耳。
我和领哥蹲在树间饕餮的时候,谁也不做声。只有风吹过来的声音,细如微吟,大如镗鞳。白花花的日光像水一样直泼下来,使人影黑白相间,使桃林斑驳一片。我与领哥什么也不想,只是剥皮开吃,一口一个,吃了一个又一个,核扔了一堆又一堆,直有点快意恩仇的感觉,尽管是时运不得意,与恩仇并无半點干系。
一口一个,吃掉一个毛桃只需几秒,十分容易,但吃的人多不为此琢磨桃子生成之艰难。从严冬到酷夏,那一口便吃掉的桃子也需熬过许多难熬的岁月。种地也是一样,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在风雪霜雹中,哪一种作物不道怎一个“熬”了得?我与领哥都是种地出身,自然都明白就中的艰难,因此也就不消多说了。每年在桃林里饱餐一顿,可以借此检点年来走过的路径,挥却许多的失落的意绪。
多年后,我与领哥在寂寞中熬了过来,只可惜那片桃林早已不在了。以前的时光很慢,现在的时光很快,在飞逝的时光里,太多的细节都遗忘了。就像我忘记了振辉家毛桃的滋味,忘记了占山哥家毛桃的滋味,有时候也怕领哥家的毛桃同样逃出我的记忆,因此每年见到领哥我都会提醒:“你还记得那些毛桃吗?”
如今每年都可以和领哥聚谈,也吃着肉食海鲜,喝各种各样的酒,唯独没有秉烛相对,再尝尝毛桃的滋味了。领哥不爱好文学,振辉也不爱好文学,他们肯定不知道狄更斯,但与他们聚谈时,我总会想到狄更斯小说那如出一辙的结尾,熬过来的朋友们必定相聚在某个夜晚,有炉火、有圆桌、有热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氤氲里,那些旧日的时光永在。
谷
小米在碾稃之前称为粟,俗名谷子,吾乡只叫“谷”,发音阴平。吾乡粮食很多,但大米来自江南,麦子源自西亚,而玉米是美洲的舶来品,真正属于本土的只有“谷”。华北一域,人口迁移频繁,但某些物种终始不变,古籍里说神农之时天雨粟,当代磁山文化遗址发现近8000年的碳化粟遗存,都间接或直接证明这一物种的古老与坚韧。
谷系旱地作物,整个生长过程无需特别浇水,在机井并不完全普及的时代,种谷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改革开放之初,冀中平原上还有大量的旱地。我们村东的沙窝,村西的大地就都是旱地,村民们在其间种谷也最多。谷的生长期不长,大多于夏至以后抢墒,不需特别浇灌。嫩芽儿出土时如密集的绒毛,待到盛夏,则一派齐刷刷的苍绿,微风拂来,如荡荡的碧波。
秋收时节,谷与其他作物一并走向成熟,那些沉甸甸的谷穗闪出白、黄、橙甚至是暗红来,俗话说粟有五彩,几乎每块地的颜色都不太一样。然而,乡民们却不着意于审美层次的追求,在他们看来,颜色不同,也都是口粮而已。品性相同,收割方法也没有什么差异,大抵都用镰刀割开来,捆成谷个子拉回家。秋收的时候,天空往往高而蓝,阳光烁烁而不炙,鸟雀叽喳,秋虫唧啾,牲口呃啊,人语盈盈。收获的幸福飘荡在空中,如烟如缕。
谷拉回家,就交由老太太们,她们用爪镰一对一地将谷穗掐掉,然后收集在一起。男人们则赶来牲口拉着碌碡来回地轧,如此,谷粒便可脱落。老太太们掐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无异于一幅温馨的风情画,她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很随性地聊着天,匣子里随性地播着评书,烟圈随性地飘来飘去,那些时光绵绵软软,明显有种甜香的味道,一如奶奶烧柴火熬制的小米粥。
老太太们掐谷用的爪镰呈梯形,单刃,此器具大抵由来已久,或可追溯到上古时期。陕西的双庵,河南的二里头,都发现有类似形状的石刀,固是粟作文明的标志。不过,爪镰在吾乡还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就是配合咒语治疗带状疱疹,大约是古代巫风的遗存。我小时候村里就只有大淑妗子会这一神术,后来她去世了,村里也不再种谷,爪镰遂都被当成生锈的铁片扔掉了。
乡民不再种谷,大约与牲口的退场有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吾乡的劳作还是极大依赖着畜力。家有骡马,户有驴牛,置办大量的草料是必不可少的。谷的秸秆十分挺实,是优良的饲草。睡虎地秦简记载有上缴国家的“刍稿”,那个“稿”大抵就是谷的秸秆。谷的秸秆在吾乡称为“干草”,干草常在秋后铡碎,待到冬季拌以麸子于夜间喂养牲口,如此才能使牲口在草木枯黄时保住体力。迨至九十年代,机械开始普及,牲口迅速淘汰,干草遂成为无用之物,这极大影响了谷的种植。
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田律》记载受田之民要为国家缴纳草与庄稼秸秆,“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豤不豤,顷入刍三石、稿二石。”
不过,即便没有了牲口,干草也不能说完全无用,在吾乡,干草另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即作为“燎祭”的燃料使用。吾乡除夕有墓祭的习俗,当是在节日表达慎终追远之义。因在黄昏时分举行,故名“燎星”,以前“燎星”必用干草,不知是否为古风的遗存,甲骨文多记载燎祭,使用干草者当不为少。近年来,吾乡不再种谷,遂无干草可用,“燎星”的燃料为玉米秸秆所替代。玉米秸秆不易点燃,效果差强人意。而怀旧的人总觉得不伦不类,但在干草消失的年代,有玉米秸秆可用也聊胜于无了。
玉米秸秆可以代替干草,但制作炉糕时,玉米面就不能代替小米面了。吾乡在过年时有制作炉糕的风俗,所用食材就是磨成面的小米。小米磨成面后,用水拌成稀粥状,然后再通过发酵,便可一一倒入特制的鏊子里,只呲啦一声,软软糯糯的炉糕便可食用了。我的姥姥很喜欢摊炉糕,以前大量种谷的时候,她每到过年都会摊上很多,然后上顿吃下顿吃,一直可以吃到正月十五。那时候,我的寒假作文里常常提及摊炉糕,那一声声的呲啦,仿佛比炮仗更像年的声响。
平原上的谷消失以后,爪镰也消失了,干草与炉糕也消失了。此外,碌碡与镰刀也都弃置不用,甚至连以前常吃的小米饭也都不见了,乡民充其量只喝点小米粥罢了。多年以后,我和亚青还清楚地记得,最爱在当街吃饭的石头爷,常常端着一大碗黏稠的小米饭,蹲在十字街旁大口大口地吞吃着。那时候夕阳西下,落照打在黄澄澄的小米饭上,更加灿灿如金。
马蔺
我家房后有个菜园子,村里二队的人们都在那里种菜。菜园子的最南端有一眼机井,机井里的水通过一条向北的明渠输送到各家各户的菜畦里。明渠在吾乡有一专门的称谓,叫做“垄口”,垄口由土筑成,中间走水。乡民浇地时,垄口是重点监控区,因为一旦垄口漏水,则多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平原上春天干旱,几乎天天有人浇菜。那一淙涓涓的水变成了孩子们的乐园,然而大人们却不喜欢孩子们停留在垄口上,除了口渴饮水外,其他的嬉闹都是不允许的。不过玩水似乎是孩子们的天性,尽管有驱赶,有呵责,孩子们依然不愿离开,乃至躲躲闪闪,与大人们打起游击。大人们无奈之下,只能是对垄口培土再培土,以防止溃坝。
离机井最近的垄口的两边是普蓉家的菜园子,大概是为了保护她家的菜园起见,她在那垄口的两边栽种了不少马蔺。其时,我并没有亲眼看见她栽種,只是听说是她。一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了春夏之交时,垄口两旁竟然闪出无数墨绿色的铁条来,它们根根上举,如暴怒的刺猬。当时我并不认识马蔺,一直以为是兰花的。同属于二队的同乐舅姥爷有一本《十竹斋画谱》,曾借与我看过,我觉得里面的兰花与普蓉种的东西很像,还曾跑着去告诉爱花的山叔:“普蓉在二队菜园子里种兰花啦!”
普蓉是刘连城村最勤劳的人,但她没有文化,未必理解兰花的雅趣。不过她的丈夫义芳却当过县教委的科长,颇有些见识。义芳退休后在家也养些花草,他还曾送给我一棵天竺葵,我于是想在菜园子里种兰花当是义芳的主张。当然了,一口气种上那么多固是普蓉的风格。那些“兰花”掩映在垄口两边,任由一汪清澈的水流泠泠穿过,也颇有些画谱里的意境。
对于那些兰花,我颇有些倾心,十分想挖上一棵回家种养,于是把这想法告诉了五丫哥,五丫哥听完笑着说:“什么兰花啊,那不过是些马莲,随便你挖吧!”马莲是吾乡对马蔺的俗称。看五丫哥的态度,马莲当不是什么好货,于是我有些泄气了。到垄口边来拔,又因其根系发达难以撼动,于是我一怒之下回家拿来铁锨,不想恰好邂逅老肥爷。老肥爷曾因我啃过他的瓢葫芦而一直耿耿于怀,他腆着大肚子凶巴巴地问我:“你要干什么?”于是我只得夺路逃走。
多日之后,我再去垄口边看那些马蔺,却惊奇地发现它们开出了一朵朵紫色的小花。那些小紫花并不绚烂磅礴,然而迎风笑傲,没有一点自小的神色。当然,在众菜众草中,紫色花也颇有些鲜艳的芳姿,但它们又低眉垂袖,表现不出自矜的样子。总之,是静静开放,仿佛一切都可以欣然接受,仿佛到处都可以随遇而安。我看到了那些花,相信那些花也看到了我,不知道它们会怎么想?我计较过它们是不是兰花,也计较过要不要种在家里,现在看来,都是落于下风。
那时候我年齿虽小,但也有些小情绪,于是那条开着马蔺的垄口就成为我排遣不快的处所。无论是在细雨中,还是在夕照里,我都会去那里转转。无论什么时候,那些小紫花都是恬淡安静,如淡淡的春风,一瞥之际,拂去心头点点的灰尘。那时候,我总觉得,那些马蔺是懂我的,尽管它们只是静静开放,从不言语。
马蔺与我对话不知持续了多少年,一年又一年仿佛年年如此。马蔺后来什么时候没有的,我也记不清了。它们的消失也宛如淡淡的春风,将一切吹得了无痕迹。大概二三十年后,普蓉、义芳及老肥爷都去世了,都没有人记得二队菜园子马蔺的事情了。只是偶尔回忆吾乡童谣时才会想起马蔺,童谣云:“马蔺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以前孩子们做游戏时常常唱起,但迄今我也不知道是在表达什么意思。
臭椿
臭椿之所以叫臭椿,大概是相对香椿而言,其实臭椿与香椿的关系并不是一臭一香那么简单,它们叶子不一样,一奇一偶;它们树皮不一样,一滑一皱,它们果实也不一样,一翅一蒴,它们漫说不是同一种属,其实连同一科都算不上,臭椿系苦木科,香椿系楝科,从基因角度来说,差得还不是一点半点。
在以前的村里,香椿并不多见,只有毛猪爷、占山哥等少数家庭栽种了几棵;现如今为了春天吃菜计,几乎各家各户院里都种植了香椿,它们千篇一律地伫立在窗前门后,形态体量如一个模子铸就,端的是呆板。与之不同的是,近些年来,臭椿却有点遭遇灭顶之灾的趋势:原来那些巨大的臭椿被砍伐殆尽,而一些冒冒失失破土的臭椿苗也被乡民随意铲去,大概是因为臭椿叶不能吃,干不堪樑,总归是无用的缘故吧。
对于一棵树来说,不能吃,不堪樑就是无用了。虽然椿木可以用来制作樗蒱,但樗蒱又有什么用,不过是玩物丧志罢了。“樗”为臭椿雅称,《诗经》里说“采荼薪樗”,也就是说,臭椿最大的功用就是作为干柴烧火。臭椿生长速度极快,因而并不致密,属于易燃的木材,农村过年时大锅炖肉常烧臭椿,那火苗的确突突的。如果一种木材仅仅用于烧火,那被贱视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以前臭椿也是无用的材质,但乡民们却允许它们在村里自由地疯长,院里院外,街头巷尾,似乎无处不可挺出。乡民们当然不以臭椿为至重,没有人会去有意栽种臭椿,但臭椿种籽会凭靠自身双翅,纷纷扬扬,飞得到处都是。只消一场春雨,臭椿芽就会飞速抽出,一排排,一片片,恣肆窜升。尤其是在一些闲院或空地里,无人理会它们,它们遂杂遝并起,如苒苒的绿云。
吾村最大的一片臭椿是大队部的门口,明远舅姥爷的房之东。那片臭椿大约有七八棵的样子,皆粗壮高大,有直举参天的状貌。然而,臭椿是一种短命的树,即使有参天的伟岸,树龄也过不了五十年。《庄子》里提到的可以活到八千岁的大椿其实是木槿,跟臭椿实不相干。明远舅姥爷房东边的臭椿应该也没有多长的树龄,但它们亭亭如盖,确乎可以遮风挡雨。那时候明远舅姥爷常常戴着高度眼镜,袒胸露怀,坐在树下的马扎儿上,慢悠悠地与他人抬着杠。微风拂来,椿花簌簌如雨,像是为抬杠伴奏一般。
抬杠是无用的,即便令对方词穷,却也未必能实现全面压服。明远舅姥爷晓得这个道理,他抬杠的时候十分有风度,从来都是自由随意,且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甚至都讲究些纵控张弛。我后来觉得,那些无用的抬杠对他来说,或许也有些偶寄闲情的意味。明远舅姥爷最能抬杠时,村里杠倒律师后起之秀还没成长起来,也不知道他是否有罕逢敌手的寂寞。后来明远舅姥爷去世,大臭椿树下就没有了无用的抬杠,不久后,那些巨大的椿树也全部伐除,自由而无用遂成为一种传说。
1995年,吾乡一带爆发了樗蚕狂潮。乡民没有见过樗蚕,只是觉得恶心可怕。那些蠕动的青白虫子很快就爬满了臭椿树,几个昼夜便将叶子吃了个精光。然后蔓延到其他树上,即便路上也是密密麻麻,骑车常常压得黄水飞溅。光秃秃的臭椿刚又长出一点新芽,马上就被樗蚕瓜分,反反复复几次之后,很多臭椿就死掉了,我一直怀疑后来村里臭椿大量减少是与那次樗蚕浩劫有关。
臭椿开花如黄色米粒,带着一种异味,这也是臭椿得名的由来。不过,臭椿的异味还是可以忍受的,习惯了似乎还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亲切感。花落后不久,臭椿便可结出大量黄红相间的翅果,那些翅果点缀在绿叶间,煞是好看。我小的时候,椿花飘落、翅果纷飞是司空见惯的情境,但后来却难得一见了,即便是我后来到了一所以“自由而无用”著称的学校,也未在校园里见到一棵臭椿。
【作者简介】刘成群,1978年生,河北高阳人,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著有散文集《时光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