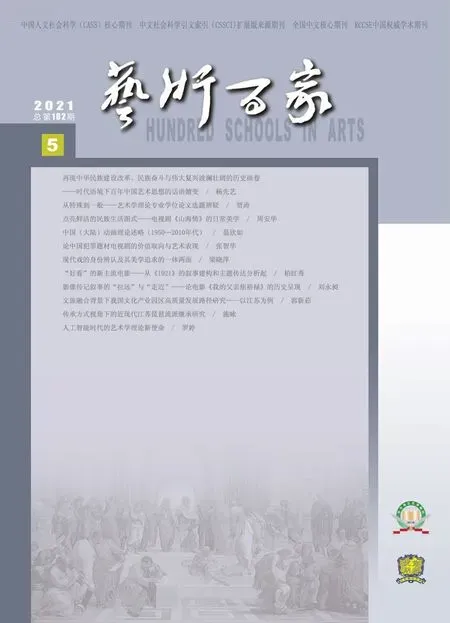论草书先于正书*
2020-06-21骆冬青
骆冬青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草书先于正书,这一命题,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它将艺术的自由创造置于一切既定秩序之前,将造字原则置于“正字”“正体”原则之前,既为汉字造字探本,又为书法艺术立法,更指向了美学的超越之境。这一命题,郭绍虞先生曾在1961年从书体、字体以及书法史角度提出:“我们既认为草先于楷,那么也应当承认行先于楷。”[1]1972年,晚年郭沫若从另一更为根本的角度,即造字角度,将此命题的意蕴提到新的层面。应当指出,郭沫若似未曾注意到郭绍虞的论述。①这位曾经狂飙突进的创造社诗人,始终“心有天游”,即使晚年,犹在其意中生出漫天疯长的野草、春草——草书,正是那种自由的象征、创造的表现!
郭绍虞和郭沫若两位先生的命题,其意蕴如今需继续深化。我以为,两位先生所采取的文字学、书法学视角,仍然是最重要的。不过,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新发现、新成果,为重新论证这一命题提供了契机。更重要的是,哲学、美学上的新进展,为我们思索这一命题贡献了更多的向量。
郭沫若说:“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认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南宋的张栻(号南轩,与朱熹同时)曾经说过:‘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虽出以意必,是卓有见地的。”[2]又曰:“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从书法观点来说,也就是草书先于正书。”[2]将刻划符号的创造归功于劳动人民,姑且存疑;说刻划符号的形式草率急就,我以为真乃意必之言。但是,其推论则允为超拔。从“指事先于象形”,竟迁想妙得,得出“草书先于正书”的结论,郭沫若毕竟是灵感激荡的诗人!盖从创造的根柢上看,造字与写字(书法——创造性地写字)来自一种冲动,即将内心所具有的一切表达为符号;创造的形式,则均为某种“造型”;而共同归宿,则是超越感性的灵智的飞翔。
本文以“变形记”“解形记”“超形记”论之。
一、变形记
草书,郭沫若仍承传统想法,以为“形式是草率急就的”。草率,与严谨相对;急就,与即兴相同。这一似乎最能代表汉语中那种龙飞凤舞、大象无形、天马行空精神的书体字体,却没有一个看起来具有学术严谨性的定义,使我们的论述失去了起码的基点。尤其别扭的是,让“草书先于正书”这一命题首先依赖于“正书”,方可定义“草书”,郭沫若引张栻所谓“写得不谨”,其实反而挑明了自身论断中的悖谬,因为“谨”应为原态、常态。所以,正书、草书的定义,均需首先审视。我以为,正书、草书概念,需要打破断代概念,将其推至汉字书写以及字体中的普遍性层面。行书介于正书、草书之间,可由此两种定义规定。也就是说,将正书、草书规定为汉字书体、字体的普遍概念。郭绍虞认为:“就汉字而论字体,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指文字的形体;二指书写的字体;三指书法家的字体。就文字的形体讲,只须分为正草二体。就书写的字体讲,一般又分为正草隶篆四体,或真行草隶篆五体。就书法家的字体讲,那是指各家书法的风格,可以分得很多,最流行的如颜体、柳体、欧体、赵体之类便是。”[3]这里所说的正书、草书,既是指字的形体,又是书写的字体,因此,从文字学角度看,可以作为汉字字体的普遍概念。至于书法家的“字体”,乃是书写的个人特征,应纳入风格范畴,当从文字字体概念中区分出去。
在郭沫若论述的语境中,正书、草书,当是指自有文字以来,任何时代通行的字体、书体与其变体。正书与楷书、真书、正楷等概念,乃后起,是始于汉末的汉字字体规范化、规正化的产物。研究字体常引用宋代《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之说,这里的楷书实际上是指王次仲所创的八分书,而不是现代所谓的楷书。郭绍虞先生曾作明确区分:“我们要从本质来分别正体和草体,不要泥于旧时古籀篆隶分楷行草种种名称。”“凡是对于字体有整理规定的作用的,如《史籀篇》《仓颉篇》以及后世所谓《三仓》或《石经》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文字的正体。凡是为了书写便利,或减省笔画以趋约易,或随笔转折不求整齐,这些又都可看作是文字的草体。”[3]我以为,“正体”“正书”乃任何时代某一区域中规范化、规正化、模件化的字体,并不只是指后世的方正平直的可作楷模的楷书。而草书即“草创”之字体书体,《论语》有“裨谌草创之”语,张怀瓘《书断》谓“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窃以为“草创”之意尤可深味:此“创”字有两重含义,一是最初的草创,是首先的创立;二是指后来的草书,乃是要从正书回归到草创状态。草书之“草”,常解作草率、草稿、潦草,均含一定贬义,但却说出了它的某些特征;至于匆忙、急就、即兴等表示快速之意的言辞,则描述了动作,可是,这些却也会遮盖更为重要的性质。草书,具有强烈的动作性、变化性、易简性,即所谓“纵任奔逸”[4]64“示简易之旨”[5]2,因此,草书与心灵的激越状态密切相关。艺术的草书,乃是当文字书写本身成为一种抒情,文字、图象、动作、笔墨等的遇合,构成了一种奇迹般的姿态——书写艺术、书写痕迹与书写动作本身合一,成为一个美学事件。所以,草书的美学,是灵感的形状,是激情的成功革命,是图象的飞翔意态。草书创造了新的存在符号,以意向、意念、意想,创造出特殊的意象,抽象而姿态灵动,夭矫而不屈。最初的造字,正是来自“天雨粟,鬼夜哭”般的灵感,后世的草书创作,则需回归汉字初创时那种“笔落惊风雨,诗(书)成泣鬼神”的情境。以创造性书写,留下的即时的动作痕迹,将成为会意读解和心灵沟通的符号。
最早的汉字难以寻觅。甲骨文告诉我们,什么是无羁创造,什么是立象尽意,什么是象外之象,什么是大象无形!人、日、月、山、水、牛、羊等,真的是所谓“象形”字吗?没有在先的“指事”,“象形”难以成立。“象形”即“变形”。郭沫若认为,最初的文字,有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造字则指事先于象形。我以为,只是有了指事的抽象,才使得“象形”成为造字原则有了可能。
以往许多人认为,象形先于指事;文字是从图画变异而来。直到现在,仍有以为汉字乃象形字的意见。郭沫若重申许叔重的排列,并证之以原始刻画的符号。我想,若象形在先,则许多民族均早已有图画,却难以造出文字。其原因在于,图画只能非常有限地“画”出一些具体事物,且“画”的方式难以成为“写”的方式。只有以抽象符号为代表的指事,方可创造以“写”的方式来“画”出事物,并且涵盖万有。所以,以抽象的指事符号来“象形”,才产生了象形“字”。单纯的绘画产生不了文字。西方拼音文字超越象形,只用字母表音,即证明“指事”的“象声”性质。超越象形,乃造字之必要环节。指事先于象形,即符号创造先于图象系统,乃文字产生的必然。明乎斯理,方可谈文字。
由于指事先于象形,故“象形”已是“变形”,是“抽象”而“变形”。沈兼士谓汉字为“意符字”,以诸简单符号组合而成。他以象征主义(Symbolismus)概括指事字;以模型主义(Typismus)概括象形字,谓其“由记号的进化而为象形的”;以因袭主义(Konventionalismus)指称“借象字”——因袭实物的形状,以代表作者的意思;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us),指称“复象字”,或象形兼会意字,“渐渐脱离实物标本的束缚,作者能自由拼合各象形体,以发挥其意思”;主观主义(Subjectivismus)指称会意字,所谓“能超乎迹象,主观地把各个文字间的关系看做有机的,而化合之,以表现作者的意思”[6]4-5。沈兼士以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希特(Lamprecht)划分的人类思想五时期,来框架汉字,颇有启迪,却也颇为机械。我以为,他以超越性的意符为文字的最高阶段,固含卓识,但其实却应颠倒——只有这种具有最高表意功能的符码自由拼合,才是文字产生的因由。所以,指事之中,即含会意。自然,指事之中,即推至象形——“由记号的进化而为象形的”。六书中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乃是抽象出事物的某种特征,并且以抽象符号表现之。如“日”“月”“牛”“羊”诸字。并非“随体诘诎”,也不可能做到“随体诘诎”;所谓“画成其物”之“画”,只有成为文字笔画,即抽象的符号,才会成为构字元素,而非任何别的绘画形式。故六书“象形”实是以“指事”为前提。草书尚简的属性,正与指事通。毋宁认为,所谓“图画字”自非字,不过,只有出现“图画字”草书,才有了字,如“牛”字、“象”字。只有在刻画和刻画符号以及图形意识中方才可能有“文字”。有图画无文字的民族多矣;有文字而非“图象”文字者犹多。其实,只是因为有了文字,才有所谓“图画字”,才有把图画“认”作“字”的观念。清代翁方纲有言:“空山独立始大悟,世间无物非草书。”那是先有草书,才会悟到“无物非草书”。
在面对“天”和“神”的时候,漫天神灵飘舞,“无物非草书”才成为现实。甲骨文中,许多字,均有不同写法,一个“人”字,就有48种字形[7]1-2,勾勒着侧面“人”的形态——为什么我们可以认出是同一“人”字?那是以草书的眼光,看殷商人的浪漫表达!那种来自生命、来自美学的不安分,让甲骨文里的字常常变形、变幻、变换出不同的形式,其中,既有从生命本原出发,勾勒人体、自然以及想象世界的不同形态,又有从美学本原而生的“字”本身的不同形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那个“画”,在甲骨文特定书写工具与书写载体中,已经演化为线条的“诘诎”蜿蜒,抽象造型意识随着某种抽象线条而展现,但是其中勃勃蛹动的美学精神,却变化出万千形态。草书的意的极度扩张,令一切抽象、变形。甲骨文中的自由表现,无论“你”变出多少种形状,我们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你!“任凭你在千种形式里隐身,可是,最亲爱的,我立即认识你”,歌德著名情歌似乎最好地表现了甲骨文中那个自由的精灵:“我外在和内在的感性所认识的,你感化一切的,我认识都由于你”!那个喜爱变形的精灵,却总是以某种方式出人意料地打动我们“外在和内在的感性”,它就是汉字最初的美学。草书极度意化的拓扑变形,却以情感力量,让我们“认”出“她”来!这就是精神的超越性。
即使是镌刻固定的图象,却在有限中表达自由。在那个巫术时代,人内心的神灵与天上的神灵在文字中相遇,迸发出的创造力只有少量留存,却以伟大的符号固定为永恒。所以,我要说,甲骨文最具草书精神,不仅因其乃汉字草创未久的形态,更因其夭矫多变的书写。不过,这种存留下来的特殊书写,恐怕仍然未能表现出彼时应当具有的别样书写。考古证明,甲骨文镌刻前或已有毛笔书写痕迹。如果畅想甲骨文时代的非甲骨文书写,那肯定是一个何其烂漫自由的存在!在未定形与已定型之间,在未入框架与已入框架之间,正是一个草书的时代。
从西周金文到战国文字,汉字经历的纷纭变幻,迄今犹未从“字理”上得到很好的阐释。直到秦的规范统一,让一切变得单调贫乏:即使创造,也只剩下一个同一的意志。篆,那个以弧形的圆满形成的字,以弯曲消解了一切自由,却固定了秩序。
二、解形记
解形,是对形成的固定乃至僵死秩序的解构,是对“同一”的反抗。指事先于象形,首先是对“象形”之“形”的解构与解放。所谓图画文字,乃是既有文字之后,仍然有以图像代文字者,如甲骨文已有“象”字,金文中仍有“象”字图像,表明那种以图像、图形代文字,以表尊荣,显示其艺术性,还是一种奇特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当今电子媒介中,以“表情包”、火星文、图片、视频等形式与文字混排,作为某种语言形式存在。似乎具有文字功能,却较之文字倒退回具体的感性表征,其中意味,尤当深思。窃以为,汉字,乃是对这种本能的原始象形的反抗,却又在很深层面依赖于这种本能。这种反抗,乃是草书。一方面,草书的易简思维,在《周易》中简化为阴阳两爻,是最抽象的线。阴、阳两爻抽象叙事在某种特殊层面代表了草书精神。草书对字形的简化,乃是重要特征。另一方面,草书书写时的飞快速度必致痕迹的如线一般的特征。甲骨文在很大程度上面对的就是就两个问题:图像本能和书写中“如线”本能。甲骨文特殊工具令后者成为常态,而前者则是尤为本质的改变——“字”解散了“形”。
字体改变的一个重要时刻,是所谓“隶变”。隶者,奴隶也。但是低贱往往带来肆无忌惮,带来弱者的特殊反抗。这种反抗,即书写时的“草”,表现出一种率意和怠惰,但却又包含着可能的创造。启功先生曾从“写字”角度指出:“古代有些字体风格,从甲一大类型变到乙一大类型时,也常是从一些细微的风格变起的。例如篆和隶现在看来是两种大类型,但在秦代,从篆初变隶时的形状,只是艺术风格比较潦草一些、方硬一些而已。这足见字体的演变常是由细微而至显著的。”[8]1郭绍虞则更具学术史眼光:“籀文偏于繁体,是晚周文字的正体,而许书之古文,则是当时的书写体,可说是具有草体性质的字体。因此,从籀到篆,是繁体的演变;而从古到隶,则是简体的演变。所以在当时,篆是正体,而隶则有草体的性质。”[1]在论述草书的正体化时,郭绍虞曰:“章草之正体化,发展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变为汉隶,即是有波势之隶,已如上述。另一个方向变为楷书,使点画俯仰之势成为悬针垂露之形,于是又在字体上产生了一大变化。”[9]郭绍虞还总结说:“正体的性质属于静,静故不易变,也不要求变。草体的性质属于动,动故容易变,而且也有变的要求。所以字体演变,不在正体而在草体,草体才是字体演变的关键。”[9]其中,最有意思的现象是,隶书竟在一些方面向甲骨文回归:“我们作戎字不从小篆作而同甲文作戎,尘字不从小篆作而与甲文作同意,也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了。”[1]稍作推论,则可说,甲骨文尽管受到书写工具限制,但仍然最为充分表现出草书的草创精神,那种蜿蜒曲折复杂多变的图象,那种贯穿一气的奔逸放达,尤其是以指事的虚灵象征洋溢着的意向体验,可以说,先验地、先在地规范了汉字的格局,却又让我们从三千年的暌违中认出了那里隐藏着的精神世界。
刘熙载说“草书意多于法”,我认为,这揭示出某种真相,草书之“意”正在于那种不羁的精神;可是,更深层次看,“法”自“意”立,那么,草书之法,来自于怎样的“意”?若不是泛泛而论,需深入到草书创造的汉字图象营构规律之中。通常,从易简、快捷这两个角度勾勒草书特质,大体有道理;可是,相反命题也可成立,简化与繁化共生,“匆匆不暇草书”,“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乃书学中重要现象。草书,尤其是具有美学性质的草书,恐当从草书图象的角度,从创造心态与创造过程等方面进行探讨。其中,关键在于草书建立的图象,尤其是草书对汉字图象的创造——“草创”。
汉字来自“象”,形成“象”,又创造“象”。许慎定义汉字之“文”为“象形”,“依类象形谓之文”;谓“象形”为“画成其物,随体诘诎”。那么,如何“依类”?如何“随体诘诎”地“画”成其“物”?也就是说,一旦“依类”,即需“指事”,将“物”抽象。而在“画”的过程中,所依据的乃是内心的图象。草创之际,这一内心图象依据的乃是“意”——“音”与“心”构成的“意”字,代表着的超越意味,自然超越了具体“物”象,而指向了物的“类”之“象”。西方画家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的非具象艺术、抽象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与汉字的创造相通,都指向“依类”而“象形”,这就解构了原来的“物”形,而指向了“无形”。“形”即图象。盖“形”与“型”通,“型”为铸冶以土范物,故意通于“图”,彡者,毛饰画文也,本指具体图像,但汉字中强大的含意在抽象的“图”的规引下,“像”递进为“象”,故“字形”乃字的图象。[10]
草书草创图象的创造性在于,它是没有母本的摹仿。章黄学派有从初文求本义的传统,“初文”作为汉字图象,可以追问其“初文”之“初文”吗?窃以为,造字中,从“逻辑在先”来说,指事先于象形,即可推知,“相”先于“象”,“象”先于“像”。也就是作为范畴、概念的“相”(佛教谓为“名相”),是“象”的“先验”条件和先验感性结构之本原。那么,何以有“相”或“名相”?太初无名,只有浑沌中的“草创”。此根本性的草书,乃创造世界符号之精神。从“无名”到“有名”,从“无字”到“有字”,世界这本大书上的“原字”,必自指事始,必自草书作。也就是以一种含有“几何学”的激情和冲动,以拓扑变形的图象创造形成精神世界。它结构了世界,解构了原初世界。
所以,草书与指事的关系,是“心”凌驾于“形”。“心中有数”——“形数”成为心灵抽象而超越、灵动而欲飞的媒介。时、空、数,三者实统一于“数”。草书,恰在时、空上,构造了飞动着的审美世界,凝定、规整、规范为“正书”“楷书”。草书那种自由的表现,是精神自由的绽放,是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中,努力地从限制中显示身手“形而放”的表现,故能“龙飞凤舞”,世间本无虚幻的龙凤,却在笔下变换莫测,夭矫不群。
最初的草书,即甲骨文。那些甲骨文字中,许多表现“姿态”的字,或立或卧,或侧或反,或长发飘然,或大眼灼然……可是,它所属的那个“本体”呢?不见!哪怕是眼、手、足等本身,也失去“本体”,唯余“姿态”乃至“神态”。这与汉字拓扑变形有关,无论是拉伸旋转还是收缩移位,其形变之规律,似难捉摸,却自在心中;非无规律,实蕴至理。盖“形”之变,存乎心,存乎心中的拓扑“几何”也。物象转化为心象(相、像、象),心象解构着物象。草书中,因三维(时间之维)而解散二维图象,因四维(空间三维加时间)而解散三维图象。故后世草书欲回归那种自由书写,必先赋予图型(式)以图象(形象),而赋予“正书”“楷书”以三维乃至四维图象。
在“正书”“楷书”中,“心象”“物象”更消失殆尽:固定的笔画构件,乃至书写顺序,让汉字图象拓扑变形的某种单一形式成为典范。所谓笔画,割裂了图象;所谓笔顺,很大程度上悖逆了书写自由。甲骨文以刀笔为之,但仍然努力地创造出许多“一笔”画出的图象,更有曲折蜿蜒的弯线。这固然是后世草书未及见过的世界,但却又是草书一直“梦见”,并且表现出来的,加以毛笔“唯笔软则奇怪生焉”的特质,故后世之“一笔书”乃是那种一意贯之、连绵婉延而又如音乐般既深入内在感性,而又外在奇怪叠生,灵动活跃的精神延续。草书的动态,乃是拓扑变换的图象呈现。
三、超形记
汉译西方概念中,“形式”一词非常重要。康德美学即推崇纯粹形式。“形”在汉语中,亦作动词用;草书也有动词义,草书之“形”乃是双倍的“动”。超“形”,乃指草书超越“变形”“解形”而指向某种更高的美学抽象之境。变形,是“指事”对那种“象形”本能的反叛,抽象的冲动征服了低水平的感性复制,如原始符号刻划对原始图画。解形,则是解散原型,解构形状,走向自由的姿态,呈现自由的意态。正是在纯粹形式中,草书体验到的积极自由,令其反观形式自身,在形式本身寻求变化。并不自由的限定形式,却在草书中“逼”出自由的创造,于是,超越某些字体的超形,在汉字历史上,也从来不乏其例。草书的超形,最后往往被正书接纳,成为形态意识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陆宗达所谓从笔意到笔势。草书创造的“笔意”,最后必成正书、楷书的“笔势”。陆宗达说:“什么是笔意呢?许慎认为最古的汉字,它的字形结构,保存了造字的笔画意义,叫‘笔意’。《说文解字·叙》说:‘(古文)厥意可得而说。’意即笔意。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提出,许慎分析文字是用笔意解释字形的。他说,‘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什么是‘笔势’呢?汉字的形体是不断变化的,笔画日趣约易,加以书法取姿,致使原有的笔意漫漶不明,已不能分析它的点画结构有何意义了,这种字形叫‘笔势’。”[11]70其实,所谓笔势,乃是超越原来字形但似乎仍可“意会神契”的某种“个人知识”。不过,笔势来自书写的超越,来自草书,陆宗达却未明言。
超越曾经有过的形,创造自己的个人独有的形,却成为群体的“默会知识”,其中自有美学精神的重要作用。康德美学实通贯知识学与伦理学,以及后世之阐释学。草书“超形记”,乃鲲化为鹏的“怒而飞”。无穷之“意”如何向着高远处提升?“形”如何化为神韵(音乐化)?在“超形”阶段,必将回归草书的精神实质。
其实,草书拓扑变形的极致,冥冥中,一点一画中的意义既未消失,反倒升华。拓扑转换中蕴含着的自由的秩序,让汉字图象的意义更加自由地生成。草书中的简化、繁化,草书的速与迟,凝结为图象后,却在正书、楷书中获得了安静的位置。从笔势反求笔意,是一种训诂的方法,窃以为,更当是中国精神家园的回望、守望,也应是从正书、楷书中,体会到沉默心音和勃勃心动的必须。
日本假名中,以取于汉字草书的平假名居先,片假名居后。根据近年的考古文献,平假名和片假名其实都是唐代的音符,日本人以乐谱上的音符充作文字,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古琴谱“减字谱”亦出于汉字,但似乎代表着不同思路。我以为,草书确似字母也。在飞扬中凝定的抽象,乃音乐精神的象征。音乐乃时间艺术,乃内心的抽象感性。音乐中那种抽象的抒情,那种自由精神,似乎只有草书才可以表达——抽象的音与形相遇,似乎无意义的意义,在草书图象中结合为一。
音乐(无形)的记谱符号,声音的抽象符号,在平假名、片假名中表现出汉字的“形”“声”合一特质,但此“形”非所谓“形声”字之“形”,而是更为抽象、更为形式化的“形”本身。以此,才可使得符号直接表示声音。草书似乎可以直接成为拼音文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不可知。但以指事符号驾驭象形符号,符号的抽象之美令其为虚数(复数)符号。指事具有虚数意义,故可刻划无形之“事”。汉字草书之“意”化,与指事先于象形,二者确有根本联系。
数学中,数与形的纠缠,令其不断升上新的灵境。虚数(想象的数)令数学进阶,令象进入数,由此而飞翔。“万物皆数”,数与乐一体。宇宙音乐奏响在草书中,令其超越于形。草书与音乐节律神秘地统一,草书作为凝固的音乐,必固定为正书,为中国精神的一种建筑!
《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书”具有的,是“在天成象”的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天文”需要我们用心将其连接。“正书”则如“在地成形”,“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大地,仍然要用心灵来构画轨迹。天地之“象”之“形”,是否可作汉字世界隐喻?不妨以心解悟。
① 按:郭绍虞先生提供的汉字演变的许多论据,较之郭沫若给出的全面且有力,显示出醇厚大气的学者风度。我们说郭沫若可能未见郭绍虞之论,盖郭绍虞所给出的一些有力论据以及论证,郭沫若若见到,必当采纳。后来,郭沫若之论为大家所知,郭绍虞论述反淹没不彰,哀哉!但,郭沫若将此命题尤为鲜明地提到一个高度,可能是重要原因。汉字必须研究字形的几何学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拓扑变形。此为朱崇才教授首发之辞。拓扑是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的一门学科,它只考虑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形状和大小。见骆冬青、朱崇才、董春晓《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前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