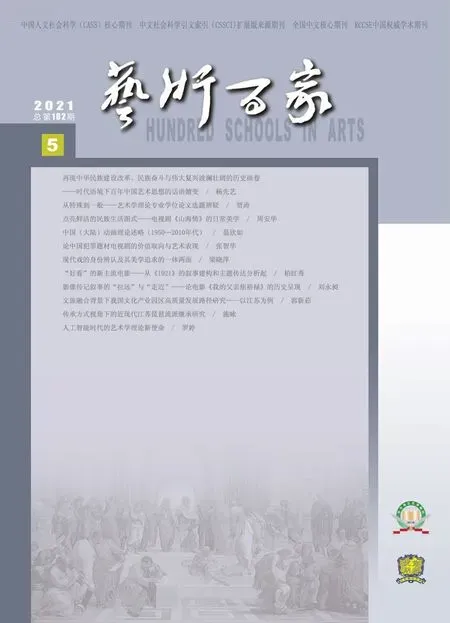中国文化背景下书法的历史承载和审美价值*
——从葛承雍《书法与文化十讲》论书法与人文、人性的关联性
2020-06-21郭大兴
郭大兴
(贵州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近期,在艺术界“好书推荐”信息的引导下,本人读到葛承雍先生《书法与文化十讲》(以下简称《十讲》)一书。严格说来,作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现代学者,其研究内容涉及古代建筑、古代风俗及社会学等方面,而对书法艺术的涉猎还是首次。虽为“十讲”,看起来没有夺人眼目的“大名”,然自翻开目录始,其标题形式就显示出其内容的独特性。“十讲”之名,首先体现了作者治学的严谨与谦怀。从研究角度、方法、深度及广泛程度来看,该书的确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好书。该书从书法的起源谈到文化的推动、美学建构、人性的自由创造以及技艺发展脉络等,研究视野都根植于中国古典文化史的大背景,突出了书法艺术的哲学、美学审美思想和中国文人的创造本能。同时,该书也揭示了中国历代书法艺术审美创造的本质和发展脉络,极大地彰显了历代书法艺术家的审美品德、艺术精神和自然情怀。
目前,对于书法从文字演变到艺术的审美创造这一历史性的转化,还没有一部著作能够细说详尽,大都是从书法史和理论史的角度进行一系列的概括和总结,千篇一律、司空见惯。一些关于书法美学史的研究,大多是为赶时髦,突出“美学”字眼而进行的一般性叙述,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识、哲学根源、创作精神与美学趣味,并没有被深刻地阐发出来。因此,研究书画美学只有从先秦哲学的源头出发,进而对两汉审美的孕育、魏晋南北朝的审美形成等关键环节进行认真梳理、提炼,书法艺术的相关哲学内涵和美学价值才能被阐述出来。那种隔靴搔痒式的“美学”挂靠,严重影响着书法爱好者和艺术家的阅读兴致及学术认识。葛承雍《十讲》则突破了以上所谓书作的浮皮潦草。他另辟蹊径,从文化史的视野对文字的起源、书法艺术的形成、审美创作主体“人”的主导作用、各历史时期书法艺术审美创造的路径等方面一一进行了哲、史、美的综合性概括与阐述,让读者耳目一新。
这种把书法史融入中国文化史、人性史及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合理的。《十讲》认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文化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各个时期创造主体“人”的修养和审美上。所谓“人性”,主要包括书法艺术家的人生、人品、人情、人格、人伦、人心、人道等十个方面。《十讲》通篇围绕文化史、书法史、人性三个方面进行对应阐述,从而形成了“十讲”的主要内容。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以文为基、以史为述、以人为本、以哲为理,扼要地阐明了各个历史时期创作主体“人”对书法审美和技艺创造的作用。这一研究方法无疑打破了一贯的书法史论的叙述常态,回到了文、史、哲、美、论、技的综合研究方法上来,这无疑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对于书法艺术在各个历史文化时期的演化与审美特征,葛承雍都结合时代文化背景特征,把握人性审美发展的脉搏,广采博引,强调了书法与文化、人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正如他所说,透过书法线条的形式美,呈现出来的往往是“人性”的文化[1]1。作为人性化艺术表现形式,其审美创造是技艺方法演变的根本。也就是说,书法的审美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性修养的重要表现方面。
二、文化对人性品德的推动
自古以来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文明的进步首先体现在人文素质和修养上。当然,人性有善恶之分、美丑之别,但作为文化史的内涵,书法艺术表现的主要是人性自然无为的美德和修养。《吕氏春秋》曰:“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2]45
可见,这里的“修节”“止欲”就是人的情性、品德,是圣人与俗人相区别的关键。人性论在文化上的表现,首先体现在人的情感、情怀、意志、抱负及审美趣味等方面。我国古代文学诗歌一开始就注重抒情的美学特征,强调诗歌要抒发作者的感情志向和审美趣味。《尚书·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的“志”“言”“永”“声”,均为人性情志的主要表现。古人把“诗”作为与社会秩序密切联系的重要文化,其作用自然是天下“鬼人以和”。这就明确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格情性的一种“陶铸”和教化作用。
文人的“诗言志”,是他们情性、品德的一种表达方式,“情”和“志”本身就是文人情怀、品德、修养的完美统一。这一点我们在先秦著作中都能体察的到,如《论语》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曰“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庄子·大宗师》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就连《易传》之设卦也是为了“尽情伪”“类万物之情”。自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既是文人情性、品德、修养的自然流露,又是社会文化、文明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慎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古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也。”[3]3可见,自文字产生的那一刻起,文化、文明就随之被记载、流传下来。中国文明在“鸟迹代绳”“刻契凭信”的文字初始阶段,所体现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化、文明发展的渊源和开端。刘勰曾说:“文之为德也,大矣。”[4]3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内涵分“自然”和“人为”两种。而“自然”的表现则是天地万物的无为美德,“人为”的创造彰显的则是人类文明的道德人性,如器物的创造、文字的生成、书画的表达、圣贤的文篇及思想等。但这些为文化范畴之属,它首先表达的是人类的情性、品德和修养。一个时代的人文发展所彰显的审美品德,即是这一时代的文化内涵,它是反映天地万物及人类文明、品德的重要载体。由此来看,文化包括人文审美思想和艺术创作形态表现。“文之德”恰恰反映了这一点。刘勰认为,文化不但包括古代文字,同样包括“沿圣垂文”“明道”的文学创作,体现社会文化与人性的密切联系。“鸟迹代绳”,反映了“文字始炳”;《河图》《洛书》体现了“人文之元”;伏羲八卦、仲尼《十翼》及其纪、文、骚、诗、赋、歌、颂、经、史、传、赞、碑等,都是“天地之心”[4]3。刘勰确切地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4]14也就是说,能依据自然之“道”而进行文化创作的就是“圣人”,能够理解圣人的思想并加以阐述的则称之为“知明”。因此,文化既体现“圣人”的功德意愿,又“陶铸”人类的文明“性情”和“品德”。可见,中国自远古文化始,就体现了圣哲、明贤的崇高品德,这种高尚的品德具体到人类现实生活中,就是一种人性的审美表达。因此,文字的形成与书法艺术的审美演化,同样是人类文明、人性审美品德的重要体现。所以,刘勰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4]10也就是说,自然之道要靠圣人著写的文章才能得以彰显,而圣人的文章所阐明的道理同样符合自然道义。文,充分体现“圣人”的情性本心和高尚品德。也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圣人“垂文而明道”,才最终形成中国的本土文化特质,铸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人文情怀及书法艺术的魅力。
很明显,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至两汉,统治者开始探求先秦文化对朝政治理的弊端,窦太后的“好老庄”“文景之治”、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东汉文人士大夫对具有“弘道兴世”作用书法的审美探讨,都与古典哲学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典文化卓越的贡献,不但体现在对人类文明品格的审美确立上,还体现在对文人士大夫书法艺术的审美创造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是文人文化修养的一个集大成者。文人们在发挥自己技艺、性情、审美的基础上,依附自然,进行“类物象形,睿哲变通”“存载道德”的书法创造,极大地凝聚了中国圣哲明贤的博大智慧和技艺才能。
东汉文人、书法家蔡邕强调:书法在“任情恣性”书写的同时,应“肇于自然”,察其“阴阳”,窥其“形势”,“入其形”,最终达到“纵横有象者,方谓之书”[5]5、6。这里的“自然”,既有老子“道法自然”之意,又有自然万物所指。“阴阳”,同样存在《易》的玄妙和丰富的审美意识。可见,蔡邕已率先把“人文性情”列入东汉书写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方式中来,并密切同老庄道家审美思想相联系,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趣味创造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也为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美学化发展,注入了哲学审美内涵和艺术创作活力。西晋文学家成公绥《隶书体》说:“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灿矣成章,阅之后嗣,存在道德,纪纲万事。”他把隶书技艺的表达看作是“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耀焕”(《隶书体》)。西晋书法家索靖《隶书势》同样认为,书法是由“睿哲变通”而来,卫铄《笔阵图》也强调书法“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也”。王羲之则认为,“夫书者,玄妙之伎也”(《书论》),“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记白云先生书诀》)。
可见,先秦圣哲的文化思想,不但对历代文人的人性品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历代文人书法的艺术审美创造,同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葛承雍《十讲》就抓住了这一点。古典文化的作用首先是对各时代人文品德教育的推动,其次就是文化艺术的演变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推动,各时代书法艺术的审美风格和表现形态,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书法艺术家人性、品德的眷顾。总之,古典传统文化思想对人性品德的陶铸和教化,以及对书法艺术的审美润泽,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文化对书法艺术的促进
中国文化伴随着人类文明而生,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大大加快了自身审美性的演化与发展进程。据考古界证实,中国文明可追溯至六千多年前,而这些依据首先来源于早期符号文字的发现。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六千年多年前的文字图画符号、书写符号,揭示了中国书法早期的文化起源,至公元前16世纪的殷商甲骨文字的形成,则体现了中国文字“类物象形”的“自然”发展轨迹。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是文字符号,也正是魏晋南北朝书画艺术家常说的“书画同源”之始。远古先民通过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成文字,大大助推了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自具有“书”艺信息的《周礼》《易传》始,文字就已经充分显示出其所具有的哲学本质和审美内涵。许慎《说文解字序》曰:“古者庖牺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认为,古人依据自然物象的道理,不仅创造了“八卦”,也创造了“书契”。自然物象构成文字及书法艺术的母体形态,依次形成以自然物象为基础的审美演化顺序:图画符号—书契—图像文字—甲骨文—金文—大篆等古今文字体系。它们每一阶段的演变,都是以“自然”“象形”为基础的审美创造。近代学者章太炎说:“契者,刻画作凭信也。古人造字,本以记姓名,立劵契……其后人事愈繁,文字之用乃广,行文立言,皆后起之事也。仓颉初造字之文,为独体象形与独体指事。”[6]3他简明地阐述了“书契”的作用及最初文字的发展途径,同时也充分突显了文字的自然形态和功能性作用。葛承雍对“自然”的作用同样有着鲜明的认识,他说:“自然,是美的化身,自由的元素,永恒的象征。”[1]2
随着秦帝国大一统格局的建立,文字的统一体——小篆,明显成为秦文化的统治工具,并发挥了政治统治作用。汉人对“自然”“自由”的审美追求,成为汉字艺术审美演变的重要因素。文字是文化的基础元素符号,而文化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葛承雍遵从这一汉字书法审美生成原则,认为汉字书法一方面要“崇尚自然”,另一方面则是“笔补造化”的结果。这种认识,充分反映了汉代书法的“人本位思想”和“美学创作境界”,即“功能性”和“艺术审美性”的统一。从文字到书法艺术的这种发展演变轨迹看,书法各书体的形成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影响下的人文意识之变和自然审美观念的“道”悟。
因此,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书法艺术的形成同样也包含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的重要元素。而中国书法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标准,恰恰反映出这一传统文化结构现状。所以说,书法艺术深刻包含着先秦哲学、美学思想,并成为书法审美创造至关重要的形成条件和品鉴标准。
所以,从文化史的角度探寻中国书法艺术审美的成因,成为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方法和渠道。中国书法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本质,首先取决于老、庄、《易》“玄学”对书法艺术审美创造的影响。汉初窦太后“好老庄”及“文景之治”对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依赖,促进了老庄哲学、美学思想在两汉文化及后期书画艺术方面的渗透和转化。艺术家先后把一些传统哲学命题、概念和思想范畴,逐步转化到中国文化中来,形成了中国书画艺术审美的概念、命题和范畴,从而加快了中国书法艺术在东汉及后期审美创造形态的发展趋势。
魏晋南北朝书法形态风格的形成,显然是这一时期文化思想及审美高度自觉的标志,葛承雍对六朝众《书品》考察后认为,理论家考察书迹也是根据士族名门所体现的风度来品定,有点类似于美学与伦理学的混合物。他认为,品藻之风既是人的高蹈的精神气质的追求,也是理性思辨色彩的折射和人的价值的升华。艺术文化和政治制度结合得如此紧密,如此直接,不仅影响到这一时期文化的历史进程,也关系着书法本身的位置和命运。[1]95老庄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显学,这一时期的文贤以“自然”为基,以“道法”为理,以审美创造为趣,成就了中国书画技艺审美创造的一个重要时代,为后期中国书画艺术的美学化发展开辟了一条鲜明的路径。
在对待唐人的技艺创造时,作者葛承雍打破“唐人尚法”的定律。他“不同意用简单抽象的‘尚法’两个字来概括整个唐代书法的进展和成就”[1]99,认为初唐楷书及中唐狂草的出现,是唐代书法家对前人技法的一种重要突破,也是书法从重“法”向重“意”、从“志气平和”向“逸气纵横”转化和突破。他还认为“狂草”同唐楷一样,是最能代表大唐盛世书风的一种书体,它们相继冲破“形”和“法”的束缚,体现了艺术家情感、兴致、意象等因素对书法创作的重要性。因此说,“尚法”不是唐人的独特个性,而重情感,重兴致、意象才是唐代书法艺术的重大贡献。[1]99中国自老子“大象无形”审美思想树立始,意象、意境审美就一直成为中国历代艺术家的审美品味和技艺追求。无论是书法的“狂草”,还是绘画的大、小写意风格,都是历代艺术家精心追慕、研究、创作的方向。“狂草”作为唐代书法艺术家表达情感的一种大意象草书,在遵循“法”的同时,突出的是艺术家本人之“意”和情性。“狂草”与中国大写意绘画的美学价值是相同的,就目前看,“狂草”出现的年代比大写意绘画还要久远。从东汉书论与魏晋南北朝书论比较看,在对待老子哲学、美学“意象”“意境”的审美上,书法可谓占据了创造先机。
在阐述宋文化和“尚意”书风时,作者葛承雍首先将其归功于传统的“儒家精神和处忧旷达的禅、道思想”[1]182。他从文人代表苏轼书法创造的美学思想中窥探出“尚意”的几条内涵:一是具有哲理的表现或体现,讲究“意”“道”;二是表现出渊博的文化知识,讲究“书卷气”;三是强调人品性情,讲究“书品如人品”;四是注重表现个人意趣,讲究“妙在笔画外”。他还认为,“尚意”要“适性”“虚静”“不拘”“豪放”“随意”“旷达”[1]182-186,而这些概念和命题均为老庄玄学审美心胸下艺术创作状态的表现。
总之,《十讲》一书对文化与书法艺术的审美创造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传统文化对历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促进作用。
四、书法与人文、人性的联系
(一)书法与人文的联系
书法的产生首先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好奇,自觉、自由的人性本质促使人们对技巧、方法进行创造和积累,使形象化符号表现出客观事物(自然)的意象形态,充分体现人的个性、意志、品德、思想、情感、修养等。虽然这些方面体现了文化的内涵和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人本位”的表现。书法的产生和发展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书法艺术蕴启着丰富情感和审美情怀。《十讲》认为“自然是书法审美的化身”,书法是“人类童年与自然的最早对话”的结晶。[1]2中国早期图腾文字,体现了原氏族文化的“意象”初始形态;大汶口陶器符号的刻划,代表着“结绳而治”时代的结束和“书契”文明新时代的开始。“书契”时代是中华民族早期人与人和谐共处、相互沟通的一种特殊文明表现形式,而这种时代文明恰恰反映在文字的生成和演变过程中。图腾文字代表的是中国书画“同源”“同法”的最早源头,“肇于自然”的图像形态在社会化发展和演绎中,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先民们逐步丰富起来的文化生活需求,所以“会意”结构的文字便随之产生,契刻文字就更加具有文化的内涵。因此,早期文字在单一的客观“象形”上又增加了人性的主观感情色彩,从这两个方面看文字明显具有了人文的审美意识。
随着殷商甲骨文字和商周金文的发展,图画符号逐步被契刻文字所代替,充满人文内涵的造字原理,渐渐具有了“六书”的内容,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文字形成早期的这一现象,代表着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图腾崇拜”,而“契刻”文明所表现的现象,则成为早期人类之间和谐共处的文明缩影。应该说,殷商甲骨文的产生真正体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成熟,“贞人”利用占卜来掌握天、地、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契刻“卜辞”,代表着中国早期文化融入艺术的方式。在表达书法艺术和功能作用的同时,前人逐步把文字转化成语句、篇章,这无不反映出中国书法与古代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葛承雍也看到了这一点,并运用书法与文化的这种密切关联,对历代书法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概述和剖析。
对于商周铭文的认识,《十讲》说:“随着文字的增多,文字由原来的图画模式逐渐变为抽象的线条结构,这种净化了的文字线条,不是一般青铜器上图案花纹的静止形式和规范装饰,而是活生生、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强烈人性意识的一种文化。”[1]12这种概括突出了书法的自然形态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审美内涵,而成为秦国秦小篆“功利主义”文化驱使的标志性产物,秦人把古大篆迅速发展为代表统治者审美意识及政治意图的小篆模式。同时,秦王朝政治、文化专制,“焚书坑儒”,扼杀文人、泯灭人性。而以李斯为代表的士人文化,又为秦小篆书体的统一注入了活力。这突显出秦小篆书法是在封建专制文化的炮制下生成的。新兴士人文化的“柔性”审美被表现出来,但是,相应地也阻碍了书法向艺术审美化发展的进程,这也正是篆书在汉代及之后发展缓慢的真正原因。但这种阻碍对书法艺术的自然化、自由化发展而言,其影响是相对的。从“程邈造隶书”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种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隶人佐书,以其“从速”“从快”的功能价值,一跃成为两汉不可缺少,乃至成为主流标准书体,充分显示出时代文化对人性教化在书法演变中所起的重要助推作用。葛承雍同样认为这是书法从书写到“人文”、再到“哲学审美”的一个重要转折。
(二)书法与人性的关系
文化彰显人类文明,而人类文明又充分体现时代人性。人性包含人品、人情、人格、人伦、人心、人道等,这就是《十讲》所论及的书法与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而文字从简、从易、从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滞,“以趣约易”的隶书在夹缝中骤然形成,并以其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成为母体文字,并在两汉期间演变出楷、行、草书,这无疑体现出人类从美向善、求自由、尊“自然”的本能“人性”。
因此,隶书的形成有赖于“助篆所不逮”“以趣约易”。它是篆书的一种辅助字体,是规范化的篆书形体经过“草率方折”的“人性化”简化、规范所形成的文字和书法。追求“趣味”“简易”是人性的本能,这也成为隶书迅速形成的主要因素,它一度改变了篆书的圆、连、曲、繁,形成了隶书、方、折、直、简的技法特征。总之,隶书去繁就简的“人性化”功利目的,改变了篆书“屈曲回环”的笔道形态,冲破了古人造字的本义。潇洒、简率、流畅、自如的审美感逐渐渗入隶书的书写过程,大大拓展了隶书审美创造的表达空间。书法人性化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汉代各书体的演化及成熟,尤其是东汉草书的形成,为书法的人性化书写增添了更加自由、自在的审美创造乐趣。这种迹象表明,书法艺术的审美创造和发展,已经不单单受政治、文化的束缚。人性自由的追求和审美意识的增强,已经成为传统哲学、美学思想向书法艺术渗透拓展的重要因素和条件。而这种哲学、美学思想主要依赖于老庄道家一脉。“进技于道”使书法家回归自由人性,书法技艺体现自然无为品德,达到畅顺、恬淡、致柔的审美境界。而这种审美境界,正是草书的审美形态表现。草书又分西汉章草、东汉今草和唐代大草三个部分。章草与今草的主要区别在于“连”与“不连”,它们的艺术特点都在于书写的“自由性”和“审美性”,而这种自由和审美首先归属于“人性”的审美自觉。再就是草书的“应时谕指”,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即崔瑗《草书势》所总结的“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简之变,岂必古式”。可见,草书的出现迎合了人们功利性的需求,成为“人性化”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明显突破了政治和文化的约束,体现人性对书法发展的重大作用。从东汉崔瑗《草书势》对草书的比喻看,草书的书写首先给人以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感受,再者就是草书的笔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它是一种从意象到意境的思维和情绪的发展升华。《十讲》将老庄之“道”与书法技艺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庄子“进技于道”的创造自由、创造快感及思想上的超越,已被草书家深刻理解和把握。
中国古代书法技艺演变和发展的主动权,历来掌握在历代文人士大夫手中,而书法首先表现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审美思想影响下的人文品格与哲学、美学相互作用的深刻内涵。从没有明确记载的远古文字,发展到有明确记载的先秦文字、到秦朝丞相李斯、中车俯令赵高、御吏程邈等对书法各体的创造;再到汉代杜度、崔瑗、蔡邕、张芝、钟繇,以及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文人对书法艺术的审美创造,大都是文化积淀深厚的门阀士大夫所为,一些文献也明确记载了文人士大夫较早参与到从文字到书法艺术演化的整个过程,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中国书法的演变和审美更具有“人性”趣味,因此说,文人的“人性”创造对中国书法诸体的形成和演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结语
葛承雍《十讲》所提出的“文化论”“人性论”与书法技艺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表明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发展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时刻受历代文化发展因素的制约和推动,同时还受到各个时期人们的人性、人品、人情、人格、人伦、人心、人道的约束和推动。书法艺术正是由于遵循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性”自律、艺术自觉和“人文”创造规律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人性”促进“人文”,“人文”蒙养“人性”,“人性”创造发展了书法。“人生”“人品”“人情”“人格”“人伦”“人心”“人道”与书法的关联,《十讲》都分别进行了深入探讨,充分体现了书法艺术家的“人性”品格,以及“书法”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总之,中国书法技艺的演变和发展,始终是沿着中国历代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的。文化决定人文思想和审美品味的趋势走向,同时也决定文字的生成和书法艺术审美创造的发展轨迹。中国书法的演变与发展始终没有离开文化大格局的影响和滋养,始终没有离开人性本身对艺术审美创造的追求。而作为创造本体之人的学养、修养、技艺训练和人性情怀,在书法审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样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