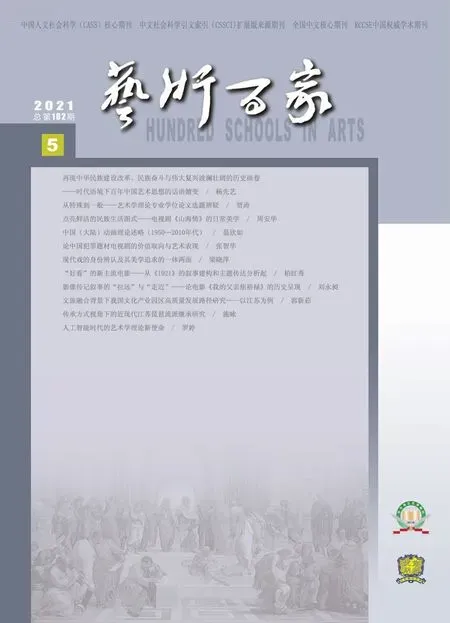从《长物志》看传统文化在物化审美上的秩序性建构*
2020-06-21王冠孔庆茂
王冠,孔庆茂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明代中晚期,手工业水平的大幅提高,经济的空前繁荣,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物的地位在晚明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也因为此,世俗化的物欲生活渐成主流,类似“逍遥余岁,以终天年……受用清福”[2]的生活目标成为晚明时人生活写照,当是时,奢靡之风遍及南北,“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3]1,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重道轻器”,认为道德追求、精神修养高于物质利益的心与器的主次秩序,也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壁垒井然的生活秩序,晚明时期,富商巨贾以财富为阶梯,进入官场,而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读书人亦广泛进入商贾行列,传统社会阶层的礼法、道德、伦理秩序均在物的影响和冲击下有了不同程度的瓦解。“俗尚日奢”[3]2,这种一味追逐物奢华精巧的审美方式让传统审美的标准变得混乱。这种传统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审美风尚、社会秩序的动摇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士人阶层的警觉,其中身为士绅阶层代表的文震亨在其著作《长物志》中,从室庐、花木、水石、书画、器具、衣饰等十二个生活场景中以评定器物雅俗的方式试图重建晚明士人在物的审美上的文化秩序,在其书原序中,文震亨表示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堤防之”[4]1,全书随处可见文震亨以其士人身份在当时物化审美语境中,凭借传统文化资源区分雅俗、厘定正统的秩序性建构。
一、传统物化审美秩序的崩塌
传统中国文化生活“安贫乐道”“重道轻器”,重视对道德、精神和个体的修养,追求一种超脱物欲的淡泊境界,如《论语·里仁》中就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5],类似这样的表达在儒家典籍中俯拾皆是,器物在中国士人阶层的生活中始终处于不被重视的境地,“重道轻器”的传统道德观念与生活策略让士人阶层追求一种以道德、精神力量压抑、规避或消解现实生活中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然而晚明时期物质的空前繁荣,让以心御物的生活方式不再被重视,“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6]的用物原则也逐渐被抛弃,晚明人的生活不仅以奢靡为风尚,更借助对物的审美取向,以玩物、赏物等追求生命的自我完善。
晚明时期,对物的欲望也让当时的世风僭滥之极,人们竞相追求时尚、奢用,违礼逾制。明代前期对物的审美取向同样崇尚简朴醇厚,明太祖认为元朝“风俗相承,流于僭侈……贵贱无等,僭礼败度”[7]导致政权崩塌,从《明史》“礼志”“乐志”“舆服志”等文献中可看到,明代建国,士农工商各阶层在服饰、饮食、器用、房舍、乘舆、节庆礼俗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定制,不可僭越,吕坤就曾说过:“凡名器服饰,自天子而下庶人而上,各有一定等差,不可僭逼。”[8]1在服饰上,明初尚尊礼制,据万历年间《兖州府志》卷《风俗》中记载,山东兖州府定陶县在明初时“服不锦绮”;据嘉靖年间《洪雅县志》中《疆域志·风俗》卷记载,四川嘉定州雅洪县“其服饰则旧多朴素”;而据万历《新昌县志》中《风俗志·服饰》卷记载,浙江绍兴府新昌县“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极俭素”。可见成化之前,明代服饰秩序明确。成化年间,服饰渐变,山东兖州府定陶县从明初的“服不锦绮”到成化以后逐渐奢侈。浙江绍兴府新昌县成化以后“士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潜服之”;四川嘉定州洪雅县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则“妇女好为艳妆,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男子则士冠方巾,余为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为之,谓之凉帽,与有丧者同,甚觉不佳。”万历年间,服饰变化更加脱出常轨,南直隶《通州志》称当时服饰倏忽变异,所谓服妖;明代末年,据崇祯《乌程县志》中《风俗》卷记载,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崇祯时“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以续纹被,衣罗绮,富贵家纵容仆隶,亦僧巾履,新巧屡更”。服饰审美从早期的淳本务实变为奇装异服,不分阶层,无视身份,竞以绮靡奢侈为上。
在居用上,明朝对各阶层的屋舍都有详细的规定,比如洪武年间,规定品官房舍门窗不许用丹漆,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然而成化之后,民房奢华富丽已属常见,嘉靖末年“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9]不仅居所,在家中器物摆放上“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癭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10]可见晚明时期,物的极大丰富带来的消费习俗的变化已让传统礼制秩序荡然无存。对器物的审美态度也从传统的合制、俭朴、素雅,变为奢靡、俗艳,追逐工巧。
晚明政治混乱、吏治败坏,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商业的繁荣恰好为人们对物的追捧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而晚明人日常生活对物的审美态度也与前代截然不同,在传统生活中,人们对物的要求除了满足基本生存外,也是带着超越物质体验的审美方式与精神情感的。晚明时期,人们通过对物质体验的感官满足,物欲追求充分体验和享受物质欲望、感官刺激所带来的快乐,追求奢用、精巧、多彩,这也引起了士人阶层的不安与警觉,吕坤发现当下社会“百亩之家不亲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业……身衣绮縠,口厌刍豢,志溺骄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为”[8]2,可见物的崛起带来的是传统人际关系、伦理秩序的混乱,而大批博物君子,如屠隆、董斯张、方以智、宋应星、文震亨、张岱、计成、张谦德、袁宏道、袁枚、李渔等人则以对物的品鉴来重新塑造人与物的关系,试图用士人对物的审美品鉴这种话语构建的方式重塑器物与文人传统、士人阶层之间关系的秩序。《长物志》则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作,文震亨从审美角度出发,将器物归入文化与美学范畴,为雅俗定秩序,重新规范人与物的关系,主动承担起尝试为当时社会提供一套器物与人之间正确审美范式的规则与方案的文化使命,其物化审美的评定依据则依旧是来自中国传统儒道文化。
二、《长物志》对物化审美秩序的重新建构
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晚明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变革,物在中国社会所有的秩序标准正在被打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物的追求、营构、依赖甚至于标榜让物的地位一再凸显,同时也造成晚明时期人们标新立异,去朴从艳的畸形审美,深刻改变了晚明时期的社会秩序、审美取向和人格建设。
晚明时期士人对商业文化所代表的审美品位多有疏离、排斥,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从春秋战国时期诞生起,士人阶层就有着相当的文化优越感,为了将文人传统与商业文化区别开,士人多著书立说以分雅俗,文震亨的《长物志》就力图以对生活之物百科全书式的品鉴展现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用品“长物”的才情修养构建文化等级秩序,以物的品鉴来重新规范因物的泛滥所造成的阶层模糊。这种秩序的厘定标准,雅、古、朴等美学标准实际上都来自于文震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与汲取。
(一)宁古无时的传统秩序
复古是明代文艺思潮的主流,比如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等,均是以复古为己任,反映在生活上,则是对古朴风格的追求,在器物的品鉴上体现出的则是宁古无时的复古倾向。
《长物志》中随处可见“古雅”“古意”“古风”“古淡”“天古”“古朴”“古拙”等品鉴标准,这种雅俗区分,将市井气、粗俗气排斥在外,对不古不雅的器物,文震亨往往斥之为“恶俗”“不入品”“俗不可耐”等。比如卷六写几榻时有“古人制几榻……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调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4]2。卷七谈到琴时,文震亨所追崇的是“以古琴历年既久,漆光褪尽,纹如梅花,黯如乌木”,“琴轸,犀角、象牙者雅”“琴囊须以旧锦为之,轸上不可用红绿流苏”[4]3方佳。卷九舟车中谈到巾车时说:“今之肩舆,即古之巾车也,第古用牛马,今用人车,实非雅士所宜”[4]4。类似这样的品鉴文字,书中俯拾皆是,其品定雅俗的秩序标准是以古制为上,比如阶“愈高愈古”[4]5,庭除“自然古色”[4]6,花木”必以虬枝古干”[4]7,其隐含的雅俗区分标准即今不如古,今是俗,古是雅,比如书画中的单条,古无此制,文震亨就认为不雅,哪怕是古人真迹用了单条的形式在审美标准上,也落了俗套,宁古无时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审美规则与秩序。
这种厚古薄今的审美思想实际上来源于我们传统文化中极其深刻的尚古传统。从《论语》中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5]1到《礼记》中“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11],从《老子》“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12]1到秦汉时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13]都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尚古薄今的传统,这种思想传统的根底里既有着中华文明由祖先崇拜延伸出儒家孝道传统的思想演变,也有着礼乐制度以周为蓝本在历代沿革中的复古传统,由于中国的士人阶层一直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这种复古思想对士人审美的影响则是“尚古”艺术精神的突出,无论是北宋初期苏轼、米芾等人提出的“高古”“古意”的美学理念,还是明代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书画家所提出的推崇摹古的艺术主张,都让中国的士人阶层在日常生活中有了天然的对古朴风格的向往与追求。《长物志》所恪守的正是这样“宁古无时”的传统秩序,将古意与时尚对立,区别出文人物化审美与大众物欲追求之间的区别,以古今为秩序,厘定出雅俗基本分界线。
(二)宁朴无巧的自然秩序
如果说古今之别是器物雅俗秩序的第一道界限,那么“古朴”则是器物雅俗之辨的重要品格。《长物志》中对器物的一大品鉴标准即是“古朴”,如卷一室庐中“石用方厚浑朴,庶不涉俗”[4]8,卷六几榻谈到方桌时“旧漆者最多,须取极方大古朴”[4]9,卷七器具写香筒“略以古简为贵,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成俗品”[4]10,这些大巧若拙、返璞归真的审美取向无不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朴素、自然的审美追求。《论语·八佾》中有“绘事后素”[5]2的观念,认为“素”是“绚”的前提,高级的美感是毫无雕琢的和谐自然之美。道家审美思想的核心则是道,而“道法自然”[12]2,自然是道的本质。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14]1“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14]2,浮华炫丽只会迷惑心智,高层次的美应该是人与自然的混融。
在《长物志》中,文震亨所推崇的雅的最高标准同样是自然、古朴。比如器物的纹饰上,文震亨屡屡提到无文,镜“光背质厚无文者为上”[4]11,几榻“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4]12。他认为,“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4]13才是器物得以气韵生动,可称之为雅的条件。这种审美取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儒家以“比德”的方式追崇自然的审美观,在《论语》中有“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3在儒家美学观念中,自然给予人的是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的关照,天地四时的美在于其大而不言,生生不息的秩序,《荀子·宥坐》中提到:“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其故,子曰:‘夫水,大遍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而卑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水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不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就解法,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15]孔子在这里所提到的对自然之水的认识实际上都是儒家对自然所映照的理想人格的赞美,而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成为士人阶层在生活上的自我比照,合乎自然秩序的是为美,不合乎自然秩序则是俗,内在的美学逻辑依旧是传统的以物比德观。《长物志》以品鉴长物达到品人的目的,在物态环境与人格比照中,美与德融为一体,物境成为人格的化身,同样是儒家传统比德观的延伸。
如果说儒家比照自然的思想对《长物志》美学上的影响,在于品定雅俗时器物与人的精神、与自然规律的混融,那么道家自然无为,剥离了道德化、群体化的审美态度则让《长物志》的品鉴标准超越了世俗功利,对美的体验更加纯粹。无论是书中的“云林清,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4]14,还是“系舟于柳荫曲岸,执杆垂钓,弄风吟月”[4]15都把客体的物与主体的我相融合,同于造化,复归自然,以宁朴无巧的审美标准重新规范器物的审美秩序。
(三)宁俭无俗的身份秩序
晚明时期,原先属于士人阶层的风雅活动,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人人皆可的物化追求,柯律格在其《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中指出在文化消费上,富人阶层将古物或风雅之物当做商品购入,以跻身风雅之群,而“底层人物对特定文化消费类型的亦步亦趋,进入到了以往因文化和经济屏障而受限制的领域,这种情形令当时的士绅评论家颇感忧烦。”[16]士人所忧烦的实际上就是身份秩序的混乱,士人独有的生活方式被商贾、平民所模仿,斯风日炽就连下层贫民日常生活也少不了焚香、啜茗、置古玩等,审美风尚异化为对物的追求,这种物化审美消解了阶层,模糊了身份,对此《长物志》以严格的雅俗对举,品鉴某物怎样是雅、怎样是俗的方式重新规范士人身份,建立基于物的品鉴基础上的社会身份秩序。《长物志》有意将物质文化的时尚、奢靡、精工与俗划等号,用“不韵”“不佳”“不妙”“板俗”“可厌”“不入品”等为这类流行的炫耀性消费画上标签。
晚明时期,奢靡成风,人们往往以精繁的工艺、昂贵的材质彰显品位、炫耀家财,明代张瀚就曾记载“以元勋、国戚、世胄、貂珪极靡穷奢,非此无以遂其欲也。自古帝王都会,易于奢靡。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沿袭既深,渐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3]3斯时,家具器皿无不以金银、玉石、象牙、犀角、花梨木、嵌螺钿、雕漆等为上。
而《长物志》中则特别指出器物的工艺、材料绝非奢靡为上,雕琢过分、人为痕迹较重的,书中一律斥之为“俗”,认为“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4]16,有“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4]17,在文震亨看来,材质不足贵,工艺不足贵,最重要的是形制,比如说橱“杂木亦俱可用,但式贵去俗耳”[4]18。他以宁俭无俗的士人品格廓清俗不可耐的物化追求,以士人的品鉴标准臧否物化审美下雅俗不分的时代之疴,试图以传统文化为资源,在器物的品鉴区分上重建士人身份秩序。
三、物化审美秩序重建的意义
秩序是生命价值体现的外在形式,生命的任何价值体现都必然需要经历杂乱到秩序,秩序到价值的过程,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秩序是艺术价值的基础,而日常生活则经由审美活动而显现出生命的秩序化道路。《长物志》对生活之物审美秩序的重塑构建了一个中国士人阶层理想中的美的世界,物化审美秩序的确立则将人们的日常生活规范进中国传统的理想的审美境界,为生命带来美的价值。
在《长物志》中,文震亨以中国儒道文化的尚古传统、自然原则以及对器物之美的本质追求对抗商业文化的粗俗、鄙下,描绘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精微、优雅,充满审美与艺术气息的世俗生活,这种世俗生活不同于晚明时期文人普遍的颓废、纵欲心态,既没有对传统道德的刻意回避,也没有纵情生活的享乐,而是充分保持了士人阶层的理性以及极其真诚的时代责任感。
《长物志》对物化审美的秩序追求往往从对物的功能性介绍开始,但物的功能性在《长物志》文本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的文本内容都以区分、建立、标示不同为主要目的,比如在花盆的选择上,“盆以青绿古铜、白定、官哥等窑为第一,新制者五色内窑及供春粗料可用,余不入品。……石以灵璧、英石、西山佐之,余亦不入品。”[4]19在书画内容的等级上以“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4]20这些等级秩序的判定则是以倡古/斥今、崇雅/贬俗为最终价值准则,可以说《长物志》的物化审美秩序的建构实质上就是一种排斥性的文本机制,以古斥时,以朴斥巧,以俭斥俗,通过对古雅审美情趣的肯定,对抗晚明市井文化中的拜金、奢侈,抵制崇商重利、好色好货,崇尚新奇、追求享乐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
在《长物志》中,文震亨以古雅为美,清雅为美,朴素为美,适宜为美,以雅化俗,批评时人“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4]21。至于当时流行的“极尽人工之巧”的果核雕刻等,他们认为“终是恶道”[4]22。让对物的审美成为一种审美理想的再现,以之批判流于俗、欲的审美表象。
《长物志》的这种物化审美秩序准则对于在今天的消费语境下对抗消费社会中的物欲泛滥来说有着深刻的批判意义。当今消费语境下,各种令人炫目的美学新词汇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商品披上生活美学的外衣,鼓励消费又造成物欲的普遍甚至泛滥,人们产生一种通过消费可以将物品以及物品所附着的文化、审美经验带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从而消弭现实社会中的等级秩序的想法。比如拥有奢侈品包似乎就拥有上流社会的入场券,买回拍卖会上的古董仿佛就拥有文化品位、历史厚度,购买艺术作品好像等同于拥有艺术欣赏、艺术审美的能力一样,这种虚幻的获得感实际上是被消费文化绑架的明证。《长物志》的意义正在于以看似严苛的审美标准让人们重新看到物与审美、物与文化的关系,并重新认识到物给我们带来的生活情境与精神体验。
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长物志》品定雅俗的审美标准看似都来自传统文化,但这种审美标准与儒家主流思想中重道轻器的器物观已经完全不同,书中不再有压抑物欲以追求心性、磨砺道德的倾向。虽然对器物的很多评价标准依然是自然,认同“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但与道家去欲的价值理念亦完全不同,不仅正面肯定了物与身心之间互相濡养的超越关系,还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濡养关系的由来、表现、第等、秩序,充满了时代性。比如《长物志》卷九衣饰中开篇即写“衣冠制度,必与时宜”[4]23,在文震亨所生活的晚明时期,衣冠制度早已混乱无序,奢靡斗丽,甚至历代之制混杂。而服饰制度、衣冠典章的恢复绝非士人可为,文震亨则从审美层面对服饰设立标准,如“吾侪既不能披鹑带索,又不当缀玉垂珠,要须夏葛、冬裘、被服、娴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之象”[4]24,用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的标准对士人阶层的着装提出合时宜、应娴雅,在城市有儒者之风,在山林有隐逸之气的审美层面与精神层面的要求。可以说文震亨用《长物志》尝试为当时社会提供了一套器物与人之间正确审美范式的规则与方案,希望借此塑造一种与当时时代相适应,却又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新的生活秩序,而这些秩序的标准既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又不同于旧有的传统观念,而是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塑造新的主体状态与审美取向,创生成新的物化审美秩序与士人生活形态,重新激活固有的文化价值,并将新的时代意识安顿于已有的文化价值基础之上,创建出新的物化审美秩序。
在当下现代化进程中,巨大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文明危机,高消耗、高消费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的威胁让与人类文明紧密相关的自然资源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物欲主义带来的对物的极致追求,奢靡之风背后的价值缺失让生命价值失去秩序,审美标准的异化也让现代化带来的精神价值危机越发凸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震亨《长物志》里物化审美秩序的重建对晚明时期物欲追求、奢靡之风的矫正则显得意义深远,对我们如何在当下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的冲击下,指引现代人走出物欲主义的迷局有着相当的启发性。
四、结语
明代中晚期,世俗之乐的追求遍及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物成为欲望表达与身份表征的最佳手段,物的蔓延突破了晚明社会的等级秩序,也让物的文化意义、审美意义、精神意义变得模糊不清,深感危机的士人阶层代表文震亨以《长物志》一书从文化角度对物进行阐释,通过制定宁古无时的传统秩序将古雅与时尚对立,区别出文人物化审美与大众物欲追求之间的区别,厘定出雅俗基本分界线。通过宁朴无巧的自然秩序让人们重新感受到复归自然的天地大美,通过宁俭无俗的身份秩序廓清俗不可耐的物化追求,以士人的品鉴标准臧否物化审美下雅俗不分的时代之疴,以传统文化为资源,在器物的品鉴区分上重建身份秩序,缓解身份界限模糊、审美原则缺失的焦虑。对于当今消费社会而言,《长物志》对在物的包围中无所适从,在商业化社会中迷失的现代人如何以传统的审美标准重塑有精神秩序、文化意义的生活有着特别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