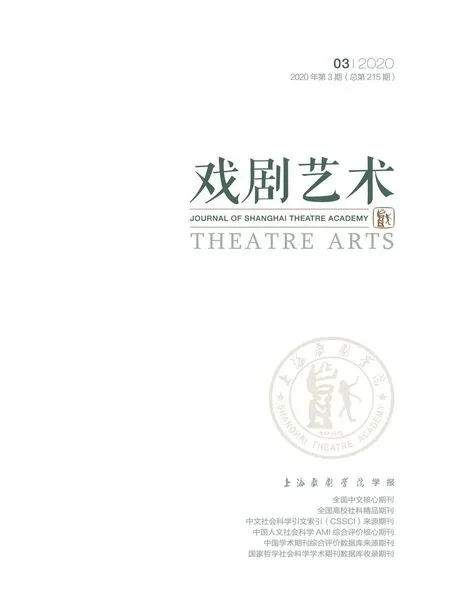“戏剧场”的演进与戏剧本体论的发展
2020-06-18徐海龙
徐海龙
自从有了戏剧,就有了对戏剧艺术本质的追问。长期以来,理论界都把“戏剧性”作为阐述戏剧本体属性的基础。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说,“这个故事(或遭遇)很有戏剧性”,“这场比赛一波三折,极富有戏剧性”,似乎“戏剧性”就是指“戏剧”,“戏剧性”就是戏剧之本质符号。事实上,只要沉浸在戏剧创作或观赏之中一段时间,就会体会到单单“戏剧性”是远远不能承载戏剧本体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戏剧观争鸣中,谭霈生先生的戏剧本体论成为较有代表性与系统性的理论。他在之前国内外学者所研究的基础上,以“人”的因素作为研究基点,提出,“所谓‘戏剧的本体’也就是情境中的人的生命的动态过程”。(1)谭霈生 :《戏剧本体论纲》,《剧作家》,1989年第1期。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仍然闪耀着生命之光,但随着戏剧从舞台开始向电视扩展(如电视戏曲),出现了各种新形态戏剧,在跨屏欣赏过程中应该对“什么是戏剧安身立命的东西”进行新的本体性思索。
一、传统戏剧本体论与“电视戏曲”之问
本体是本质与存在之整合。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谈到,“实体(即本体)至少有四种最主要的意思”,“因为,是其所是、普遍、种被认为是个别事物的实体,还有第四种即载体”。(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苗力田译,苗力田主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 卷中否认载体是实体后,在下一卷中(1042 a 26—30) 又断言载体是实体,即质料、形式及二者的结合。还可参见余纪元 :《亚里士多德论ON》,《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颜一 :《实体(ousia)是什么?——从术语解析看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本质与本体并不是同义词,因为本质只是指本体最根本的特征,除此之外本体还包含其他非本质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事物下定义的时候,并不需要将其所有的特点都罗列出来,只要表示出其本质特征就够了。那么,这些非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是事物的偶性和特性,举例来说,“白”可能是某个人的特性,但却并不构成他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体显然不等于本质,而是由本质与其他特性组成的统一体。”(3)苏宏斌 :《何谓“本体”?——文学本体论研究中的概念辨析之一》,《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
因此,本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性概念。以戏剧为例,戏剧本体不是一个戏剧作品绝对的专属,例如文学、舞蹈都具备戏剧的一部分特征(情感、生命、戏剧性、动作、表演等),但都不是典型的、圆满的,无法像戏剧那样完整地、完美地融为一体从而充分显示自身的艺术魅力。这种圆满即“本质——特性(个性)——作品形态——作品载体”的统一。因此,本体是一种艺术形式安身立命的东西,若该种艺术形式失去了或破损了其本体,该作品可以继续存在,但失去了其完整性。戏剧本体即那个使某一艺术作品成为“完整戏剧作品”的东西。谭霈生说过:“所谓‘本体论’,指的是对存在本身的探讨,亦即探讨对象的本质的学说。戏剧本体论,正是把戏剧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的实体,探讨它自身的本质和基本特征。”谭氏戏剧本体论阐述详尽,学界也多有总结和概括。简而言之,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动作与戏剧性是戏剧本质特征。“所谓‘戏剧的本体’也就是情境中的人的生命的动态过程。”(4)谭霈生 :《戏剧本体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这段话可被视为谭先生《戏剧本体论》的核心思想。有学者据此认为,谭霈生戏剧本体论是与戏剧存在本身的动态性、复杂性、综合性相一致,“乃是由生命本体、情境本体和表演本体动态合成的”。(5)汪余礼 :《生命·情境·表演——试析谭霈生戏剧本体论的基本构成与内在张力》,《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所谓生命本体,谭先生明确地指出:“戏剧艺术的对象是具有感性丰富性的人,是人的生命的动态过程,是人的心灵的最深沉的和最多样化的运动。”(6)谭霈生 :《戏剧本体论》,第313页。所谓情境本体,谭先生在《戏剧观念与走向》一文中说:“戏剧的形式是什么?……戏剧就是把人的完整的生命运动定型化。靠什么定型?而这一点恰恰是戏剧形式的本质,也是戏剧的本体。这个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情境。”(7)谭霈生 :《谭霈生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118-119页。所谓表演本体,谭先生指出:“演员的表演艺术是戏剧艺术的本体,它在综合整体中居于主导地位和中心地位。”(8)谭霈生 :《戏剧本体论》,第138页。这个观点最大的价值就是明确了戏剧本体论绝非只是对于戏剧文学之本体特性的论述。当学界提出这三个本体观点的对立统一问题之后,谭先生又发表文章论述道:“个性与情境的契合,使内在生命运动具体化为动机和行动,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演员的表演艺术以直观的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使内在生命运动显现出直观的丰富多彩性。”(9)谭霈生 :《对“戏剧本质”的再认识》,《戏剧评论》,1988年第1期。谭先生的戏剧本体论在电视技术尚未迅猛发展和覆盖的时期,是比较完备的,直到电视戏曲的出现,引发了一些新问题。
“电视戏曲”是采用电视艺术手段,将戏曲舞台演出加以重新编排和呈现。新中国电视戏曲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文化工程”,该工程从1985年提出和论证,到1994年7月开始成批录制,再到2002年8月完成任务,历经了17个年头,选择了梅兰芳等115位京剧艺术大师的录音作品进行配像,“复活”了460部作品,涉及京剧各个行当、各个流派,基本囊括了近代京剧黄金时代大部分名家的代表作。(10)京剧音配像的工作程序是,首先选择京剧老艺术家最佳的录音版本,聘请高级录音专家,组织老艺术家的亲传弟子或后代优秀中青年演员进行配像,从表演风格、演唱技巧、形体特征、动作节奏乃至心理创作状态,进行认真学习和反复排练,按照录音对口型配像,力求最大限度地展示和接近各位老艺术家的流派特色,以体现他们的唱腔美、形体美、语言美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最后,经过电视导演的前期、后期精心制作,使之成为音配像成品,完成播出和出版发行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各地电视台的戏曲栏目百花齐放。2001年7月,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开播,播出了很多音配像作品。随着影碟出版、电视栏目和专业化频道的运营,越来越多的电视戏曲节目在荧屏上呈现,成为戏曲观众新的欣赏平台。不可否认,音配像工程、戏曲频道、戏曲栏目和大型晚会极大地拓宽了戏曲传播范围,推动了传统戏曲的教学、研究和普及,使民族传统艺术得以保存和流传——这些工作是功德无量的。
但是,也应该承认,剧场体验与电视体验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观众看电视戏曲会觉得不如在剧场“过瘾”、痛快。类似地,现代戏剧的传播还是最适合于剧场。如果说剧本、演员、表演、舞美基本不变,那么是什么导致戏剧(戏曲)的一部分魅力消失了?戏剧艺术作为“独立自足存在的实体”,其本体内涵的界定是否应考虑剧场中的舞台与电视中的舞台有不同的传播过程?
二、作为戏剧本体的“戏剧场”
谭先生的戏剧本体论显示了文学本体论的色彩,即形式本体论(戏剧性、情境);人学本体论(生命本体);语言本体论(戏剧的语言:动作、表演)。电视戏曲证明:谭先生提出、后人总结的几个内涵,不足以让戏剧“独立自足”地“存在”——生命、戏剧性、表演、动作、故事、情境,这些都是戏剧本体要素之一,但还不是全部。一些其他要素在变成电视戏曲后消失了,从而也影响和削弱了“生命”“戏剧性”“表演”等要素,使自身不成为“戏剧”。
若以传播学视角看,很容易发现这些“消失”的要素。影视与戏剧的传播的重要区别在于媒介,而媒介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电子媒介(包括数字技术、网络)隔断了戏剧表演与观众的直接交流,割裂了舞台与观众席的天然脐带,拆解了戏剧的“在场”。除了传统本体归纳之外,戏剧本体要素还应包括:现场观众、观演关系(传播过程)和剧场(传播载体)。这些不是外围因素,而属于本体范畴,因为它们让戏剧“整体性地存在”。除了戏剧性的故事和角色之外,戏剧艺术是身临其境、直接凝望的对话;是生命间的活生生的交流;是一次次的期许、向往乃至仪式的聚会和论坛。戏剧不是单向传播的影视文本,而是火星四溅、情绪碰撞的剧场狂欢。
谭霈生曾提出“戏剧情境”来解释戏剧本体: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情况、特定的关系——三者相互联系构成特定的情境。而电视戏曲/戏剧无法把谭霈生所谓的戏剧情境完整地挪移到电视媒体上。笔者在“戏剧情境”的基础上,结合格式塔心理学,尝试提出一个拓展谭氏理论的“戏剧场”观点。
“戏剧场”的核心是观演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审美关系。其传播载体应该是剧场。其一,戏剧是最直接的和观众交流的表演形式,每一次演出都是“活人与活人”的交流。剧场中,演员的动作、表情、语言需要和观众的感受、评价齐头并进,都具有实体的质感。演出是一个不断进行心理和情绪反馈的流程。这是“场”的作用力的产生基础。其二,戏剧是同时空的群体性艺术活动,剧场中,演员和一个观众群体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身处此种情境的人容易产生心理的趋同性。这表明了“场”的磁力的作用范围和方向性。上述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戏剧“场”的产生。剧场里面以演员的舞台表演为中心,对舞台外围的四面八方产生吸引力,众多矢量力指向一个共同方向,在物理上指向舞台,在心理上指向集体体验的“彼岸”,这种氛围就是一个剧场内的“场”。
广义上讲,剧场以其本身的特质,衍发出一系列动态的戏剧审美活动(创作、彩排、宣传、评论、观众期待和看戏前后的一系列相关活动),把审美的主客体包融于一体,建构了一个戏剧审美的时空“场”。剧场事实上已远远超出自身物理范畴,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符号、精神的象征和寄托。也就是说,在演出当中,剧场内部以舞台为中心形成引力场,而在整个社会环境和时间进程中,剧场外围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场”,剧场是这个更大范围的“场”的中心,成为了人们心中艺术的圣殿、社会生活中的一块乐土、人类情感的寄托之所。如《浮士德》中剧场经理描述的一样:“众人如潮水一样涌向我们的戏棚,一再汹涌地挤过那狭窄的恩宠之门,四点以前天一亮就跌跌撞撞,狂奔到票房前面来,如荒年在面包铺门口抢面包一样,不惜为一张入场券打破脑袋……”(11)(德)歌德 :《浮士德》,杨武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
当某一个戏剧活动开始、观演关系建立起来时,就如同在一堆铁屑中放入一块磁石,多向交流、心理反应、情绪变化以及深层体验,所有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开始相互作用,产生一种力的效应,弥漫和流转在整个戏剧活动过程里,并在现场演出的某个时刻达到高潮。微观上,“戏剧场”是一种以“物理场”(剧场)为基础的“心理场”“情绪场”;宏观上,它是人们社会活动和情感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往复交流的情感凝聚和爆发,是当下呈现的历史记忆。
如果把剧场(现场)与观众加入本体范围,那么戏剧就真正意味着带给每个戏剧参与者“亲身经历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像戏剧情节一样波澜起伏。无论是“观”还是“演”,当一次演出终结时,是很难复原当时的情状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契诃夫的《海鸥》一剧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当时由于该剧在彼得堡上演失败,恶评如潮,斯氏的剧团和契诃夫都深受打击,契诃夫还因此患上严重的肺结核。当《海鸥》再次在莫斯科上演时,成功与否对于经济窘迫的剧团和契诃夫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次戏剧活动中,由于演出以外发生的一些事件而使这次演出在开始前就产生了一种悬念,一种场的矢量力。接着在演出过程中,演员在开始前的紧张和企盼、演员对观众的刺激(“就像冰碴一样刺了观众的心”)、观众有节奏的反应(开始是“坟墓一般的寂静”,“突然发出了一片吼叫声和狂热的掌声”)、演员之间的交流(互相拥抱、向扮演玛夏的李琳娜欢呼)等等,这些观演双方的戏剧体验完全是靠现场交流获得的,并一直延续到事后久久的回味中。(12)参见(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我的艺术生活》,史敏徒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266页。这种不可分割的历史性的行动过程以及由此达到的高峰体验,哪怕是在紧跟的下一次演出中都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复存在了。试想,一个闲散的、家庭化的电视收视环境与圣殿般的剧场相比,戏剧体验的饱满和澄净程度会相差多大?在屏幕前“看”完一场戏剧与亲身参与整个戏剧活动,其价值又有何不同?这才是谭霈生真正所指的戏剧“情境”。
三、“戏剧场”的限定与生命
论述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提出两个异议。
第一个异议是,“戏剧场”是否范围过于宽泛,除剧场内之外,是否也包括创作者们的思考、探讨、排练、预演、修改,以及观众看戏之前的准备工作和心理期待等?这超出了本体意义。

第二个异议是,去剧场看音乐会、演唱会、舞蹈、相声,去体育场看一场足球比赛,甚至参加社会公共活动,这些与“戏剧场”的观演关系是一样的,那么专属于戏剧的“戏剧场”是什么?
对此的解释是,其他艺术表演或公共活动的确也都是类似戏剧的现场交流,但“戏剧场”的观演关系的建立不仅仅靠剧场,还必须有“故事”和“戏剧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戏剧场”不是颠覆而是完善传统戏剧本体论的缘由。 戏剧与音乐会或社会集会等不同的是,它在现场要以活人演一个人生故事,该故事具有戏剧性。戏剧是充分人性化的艺术,它所表现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遭遇和命运,并且要以丰富细腻的、具有感性表现力的动作把人在矛盾、危机、压抑、死亡中的内在生命运动和心理活动呈现出来,以引起观众的共鸣。每一次戏剧活动都是具体鲜活、独一无二的生命体的活动。
总之,“戏剧场”可以描述为:以(正在演出的)剧场为场域,以舞台为中心,依靠观演关系的建立而产生矢量力,这种矢量力在观众间、演员间交叉产生作用,总体指向舞台和艺术体验。这不仅是一个实体场域形态,更是一个心理场域形态,其间流转着情绪与生命的能量。传统本体论所谓的动作、情境、戏剧性、生命、对话等本体要素都需要这个自在、完满的场域把它们融为一体,实现戏剧情境;缺了此场域,就是电子传媒化的戏剧。“戏剧场”是建筑场,更是心理场和传播场。
回到本文开头,谭霈生提出戏剧本体是“情境中的人的生命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以戏剧场的角度提出,戏剧是“以剧场为传播载体,观演双方生命主体通过命运故事进行在场对话和交流的过程”。
四、“戏剧场”的现实意义
“本体”非“本质”,而是一个丰富、和谐的体系。 对于戏剧,传统观点强调“戏”,即从案上文本到舞台;笔者强调“剧”——“剧场”,即戏剧不仅是观赏,更是参与。谭霈生曾提到戏剧演出自始至终充盈着演员与观众之间生动的直接交流,包含着观众的参与和创造。但是,对于观众和剧场,谭霈生没有真正提高到本体高度来论述,所谓戏剧性、动作和情境还是限定在戏剧艺术自身,没有从传播视角以及产业化角度来看戏剧。
学者陶庆梅在《作为社会论坛的戏剧》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北京演出之时热烈的互动氛围。作者说:“有了空间,戏剧就有了表达的场所,观众有了可以聚集的地方,观众在观看时的态度与反应,就会积聚在这个空间里,逐渐形成一种氛围,再反馈给观众。这种很具体、又很无形的东西,碰撞在一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14)陶庆梅 :《作为社会论坛的戏剧》,《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这种“空间”,在数字传媒、尤其是网络虚拟现实高度发达的当今,成为戏剧这种古老文化艺术形态的生命要素。笔者用“戏剧场”来重提戏剧本体论,是因为戏剧在当下新传媒环境中面临一个生存危机与抉择,而“戏剧场”能为戏剧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生存发展之路。
首先,戏剧在创作和表演上始终要秉承观演现场互动交流的艺术形态。这是老生常谈,但目前的戏剧演出作品似乎逐渐丢掉了这一传统,越发倚重于精美豪华的场景、单向传播的“景观话剧”和“镜框话剧”。在强调现场方面,内地原创小剧场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做出了一个范本,它通过一对年轻演员的双人秀,真实而夸张地展现了现代城市中青年打工族的遭遇和心路历程,讽刺了种种荒诞的社会现象。它在台词、舞蹈、唱歌、击鼓、哑剧表演等各个环节都恰当地实现了作品、演员与观众的交流互动。该作品2007年在北京首演,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演出三百余场,至今还能够巡回演出。
第二,从宏观意义上讲,“作为社会论坛的戏剧”才能实现“戏剧场”。戏剧可以并擅于演绎一个包含社会讨论和批评的故事,并能形成现场的共同讨论(这种讨论大多产生于内心之间,但却依存于现场演出)。德国戏剧活动家曼弗雷德·拜尔哈茨说:“在社会变化的当口,戏剧是最重要的。戏剧给我们一个公开的论坛,表达我们的思想、感觉与政治境遇,它是一个想象的实验室。”(15)转引自王晓鹰、袁鸿、水晶 :《小剧场艺术呼唤精神向度》,《人民日报》,2009年3月31日,第16版。《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令每个观众捧腹和深思,展现了把话剧作为“论坛”来使用的方法与过程。北京有大量人口,有颇具影响的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艺,各行业的文工团就有几十家,大小剧场也有不少。目前北京话剧市场日渐兴盛,演出旺季时剧场都有些供不应求,但是,国家话剧院或北京人艺每年的原创剧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搬演国外经典剧目或自己的家传老戏,有时也做名著改编。由于对票房的担忧,剧院方面也一般不敢上演原创剧,现有的原创剧集中在婚恋、人际关系、古今穿越、娱乐搞笑等领域,几乎不触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
第三,在戏剧宣传和营销上,也要营建“场”的环境和力度。首当其冲的就是票价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观众的参与程度。在欧美,话剧属于普通文化消费,好戏的票价也大概只相当于最低月薪的六十分之一,因此公众看戏是家常便饭。但我国内地戏剧观众群不成规模,因此票价难以下降,尤其是民营话剧对票房依赖很大。这就需要我国像欧洲一样对话剧进行政府补贴。话剧既然是表达思想、情感和政治境遇的“社会论坛”,就应该让大多数民众能进得起剧院,能“在场”真实互动,从而逐渐产生一种戏剧心理场和参与习惯。否则,话剧门票的高门槛把爱好戏剧的老百姓拒之门外,也使有条件的戏剧人转而热衷于制作“戏剧大片”。而仅靠百万投资、豪华舞美、大腕明星和完美视听效果来吸引观众,其实是背离了戏剧本体。除了票价,在戏剧外部宣传策略上,要利用“场”效应进行一种事件化、仪式化乃至神圣化的宣传模式。要把单一的“看话剧”,营造成一个有明确目的与成就感的“事件”,甚至一种艺术朝圣仪式。这种“戏剧场”让观众从走出家门直至剧院、再到参与演出的整个过程成为一个“行为艺术”,它具备社会活动般的强烈的归属感、参与感和宣泄感。
最后,回到电视戏曲的问题上,中国戏曲和现代戏剧可以借助影视技术,但不能盲目地走“影像”化道路。影视是流动于现场之外的,戏剧是现场聚集的,要注意和发挥二者的特色。为了实现“场”效应,一部“影视戏剧”首先应围绕一次戏剧演出,收录其前前后后的一系列相关内容,如幕后作品创制团队的工作过程和访谈、演员的彩排过程、观众的观前期待和观后体会、作品的历史和后续故事等,以此营造“场效应”和烘托核心演出。在舞台演出拍摄的环节(尤其是戏曲演出的拍摄环节),摄影机位的位置要从台下固定位置拓展到舞台之上,结合剧情发展、情绪的起伏节点、演员的表演姿态和走位、舞台调度等,来精心设置多个固定镜头机位和景别,设计移动镜头的路线和风格,并适时地让镜头游走在观众席中。同时,戏剧原有的演出元素和程式也会配合镜头拍摄而重新编排和设定。从目前来看,如此灵活而全方位地展现一场戏剧和戏曲表演的影视作品非常少见。视听语言与“戏剧场”的融合,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语言系统和美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