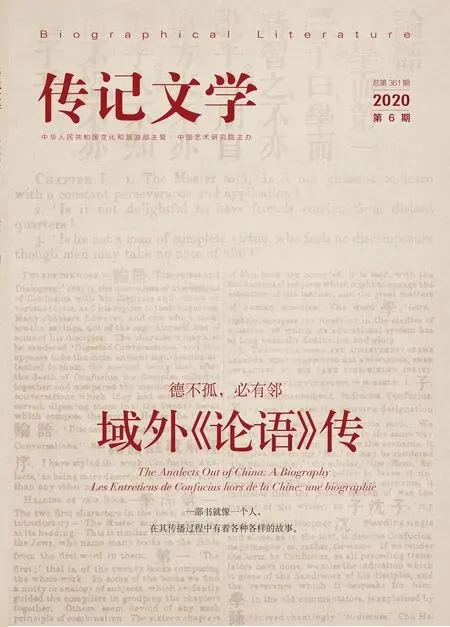杨晦的北大岁月(之三)
2020-06-18胡经之
胡经之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
六
在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转折关口,晦师再次给予我指点和帮助,1960年年底把我留在了北京大学。
研究生毕业时,我本来想回家乡,罗根泽早就劝说我去南京大学研究中国古典文论。那个时候我虽已到北京8年,但一直不大适应北方的气候。我父母先在苏州,后又到南京任教,希望我能回到南方工作,阖家团聚。我也很想念父母,读唐诗“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竟常发生联想,勾起相思之情。我的未婚妻张景贤,曾跟随王瑶先生进修过两年,后回到辽宁大学,一直动员我去辽大。我的师兄赖应棠是毕达可夫的研究生,在辽宁大学当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也一再劝说我去,一片深情,我亦感到为难。
就在交完毕业论文不久,晦师找我作了一次长谈,我也因此作出了决断。当初,录取文艺学的副博士研究生一共有4 名。一位是从华中师范学院来的陈安湖,乃陈贻焮的同学。当时华中师范学院正在培养他当中文系副主任,竭力挽留。安湖兄来北京见过晦师,长谈后不久就回到华中师范学院,继续教现代文学。另一位是家炎兄,他专心致志读了一年多,却被系里说服,转为讲师,立即开课讲授现代文学去了。只有我和世德兄二人坚持到了最后。但在1959年反修正主义热潮中,副博士学位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产物,读完4年,临到毕业,却没有授予任何学位。世德兄被高教部分配去支援四川大学。晦师对这种朝令夕改、说变就变的做法虽然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他劝我不要去辽宁大学,也不要去南京大学,还是留在北京大学,安心做些学问。当时,专攻中国文艺思想史的年轻教师已有邵岳、张少康二人,但文艺学应发展新的学科,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开拓。当时吴泰昌、毛庆耆等一批新招的研究生刚刚入学,郁沅也还没有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晦师真诚地希望我留下,师生情谊,溢于言表。晦师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我永生难忘。他说:“做学问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机缘可遇不可求。我前半生大多在为生活而奔波,不能专心做学问。你现在的条件好多了,应该珍视,你不是想研究美学吗?朱光潜、宗白华几位先生都在这里,可以常请教,还是留下来吧!你爱人的调动我一定要学校优先解决。”晦师的爱护之心,使我感动万分。最终,我说服家人,下决心留在了北京。
我被安排住在教师单身宿舍,和裘锡圭同一室,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1961年春,刚开学不久,晦师叫我到他家里,微笑着说:“你现在安定下来了,又是单身,你不是喜欢做研究工作吗?给你找了一个深造的机会。周扬在抓文科教材,由蔡仪主持编写《文学概论》作为全国统编教材,要我为他推荐人才。我把你推荐给他,要住到中央党校去,可能要好几年,正可以进行研究。北大还有吕德申去,但他还要照顾教研室的工作。你则可以专心致志,不需再管学校的教学。”我听了当然高兴。他想得很周到,问我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为我出主意,要我和爱人商量争取在“五一”就结婚。因为过了“五一”就要去中央党校,一去就是好几年;如果不结婚,北大就会把家属调动的事情搁置下来。晦师对学生的关爱,就像冯至所说,比受关爱者自己还要想得周到,真的是无微不至。
就这样,我在“五一”结了婚。晦师不仅给我们送了礼品,还亲自参加婚礼并当主婚人。王瑶先生夫妇和师兄严家炎夫妇也到场祝贺。过了“五一”,妻子回到东北,我就从北大迁入中央党校居住。这一去就是两年多,直到1963年秋才回到北大。在晦师的帮助下,我妻子也顺利从沈阳调来,从此得以安居乐业。我们搬进了清华园公寓居住,离燕东园不远,就有机会不时去晦师家看望。回到北大后不久,我就逐渐发觉,晦师的精神不如以前好,话也少了起来。1964年春节,我去看他,感到他情绪低落,不愿说话。我以为,随着年岁的增长,精力减退,大概是自然现象。但是,在多次交谈中,我慢慢懂得,在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他正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进行沉思,心有郁结,化解不开。高等学校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晦师也是一直提倡的。但是,想要培养出对国家真正有用的人才,还是要把远大理想、爱国热忱贯彻到踏实学习中去,使教学走上常规,真正按教育规律办学。学校不能动不动就因运动而停课,说要去修路筑水库,收麦抢耕,一下子又把师生拉到乡下,教学怎么能进行得下去?晦师为北大的未来忧心忡忡。
那时,我的心情也甚为不好。我的父亲一辈子当教师,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才50 多岁,竟得了癌症。我从南京把他接到北京来寻医求治,竟无一所医院肯接受治疗。父母和我们只能挤在清华园的一间房里,一家5 口人共睡两张床。白天出门到处求医,晚上回来精疲力尽。父亲看我求助无门、束手无策,不愿再连累我弄得鸡犬不宁,坚决要回南京,不到半年就过世了。我赴南京奔丧,回到北京后,一股深深的悲哀长久笼罩在心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自困惑,读书到底有什么用?读书人连自己的父亲都救不了,想在后半生侍奉他的机会都没有,还谈什么读书报国!晦师一生献身教育,懂得教育规律,可又有何用,还不照受批判!我有些懊悔来北京了。
这个时候,反倒是晦师来给我开导和劝慰,使我度过了一场精神危机。他娓娓劝道:“人生总会有挫折,但不要在挫折中倒下。能在挫折中站起来,就会学得更坚强。读书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能一言兴邦,也不可能一言丧国,但还是要去追求真理,不要丧失人生方向,要有韧性。书还是要读,课还是要上,文还是要写,学问是不一定马上有用,但若是真理,就会在将来有用。”我听晦师谈了几次,心里也就渐渐平静下来,继续安心在北大教书。
“大跃进”之后,国家在1960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深得民心。晦师从此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精心培养研究生,加紧步伐培育专业接班人。晦师把我列入重点培养对象,鼓励我加入文艺学学科建设者行列。当时,北大中文系老一辈教授学者大多已在60 岁以上,渐现青黄不接之势。经晦师等师辈商定,还是要适当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重点培养一批年轻的学者,如陈贻焮、刘学锴、袁行霈、赵齐平、严家炎等,都由指定的导师林庚、吴组缃、王瑶先生等加以重点指导,我的导师仍是晦师。晦师想竭力恢复马寅初、江隆基时代的北大学风,重建“三严”(严密的教学计划、严格的基础训练、严谨的科学作风)和“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秩序。
我在中央高级党校编了两年多书,1963年9月初回到北大。我去燕东园见晦师,听他为我安排教学任务。他一见我就说:“你回来得及时!”马上就要我为祁念曾那个班开讲“文学概论”一课。他告诉我,魏建功副校长在抓文科教学,要提升基础课的教学水平,他和社会科学处处长王学珍已商定,要把“文学概论”这门课作为重点教学试点,他和王学珍可能会去听课。晦师一再叮嘱,要我先把这门“文学概论”基础课开好,过一两年再开一门新课,为中文系开讲结合文艺实际的“美学”课程。
讲“文学概论”这门课,我不需花太多精力,因为编了两年多的书心中有数。虽然教材还没有公开出版,但已经有内部打印稿,讲课时压缩一下,重点再发挥一下。1964年,我接着为西、东、俄三系的文学专业学生又讲了一遍。那时我的心思主要放在准备开设的“美学”课程上,考虑这门“美学”课如何能更好地和文学艺术的实际相结合。那时,哲学系杨辛、甘霖等已在全校开了“美学”课,供全校文科学生选修,中文系的学生反映,对文学艺术的剖析不大深入,泛泛而论不解渴,希望能开出适应中文系需要的“美学”课,这就颇费我的脑筋。所以,从1964年开始我就大量阅读美学书籍。正好曾镇南、董学文、赵园那一届入学,我讲“文学概论”时,就加进了不少讲“美的规律”的内容,讲文艺创作的规律,如何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转化为美的规律。曾镇南是“文学概论”课的课代表,他告诉我,因为我常讲规律,那班学生就在背后给我起了个绰号:“胡经之,字规律”。我一听,警觉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讽刺,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还在大讲“美的规律”,脱离实际,书生气十足。
我把直觉告诉晦师。晦师一听,就立即为我出了个好主意:立即在“文学概论”之外,再开一门选修课“文艺理论专题”。这两门课分开,“文学概论”还是要讲基本理论,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花了两年多编出来的教科书,还是要让学生知道这些文艺理论的基本知识,不能放弃。而“文艺理论专题”就专门讲当前正在争论的文艺理论问题,关注当下现实。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1964年正是文艺界接连发生大事的岁月,热闹得很。《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广受欢迎的影片都挨了批,人道主义人性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也都受到了批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受晦师启发,我在1964年就新开了“文艺理论专题”课,原计划开的“美学”课也就暂时搁置。两年后,“文革”袭来,这一搁就是十多年。
早在“文革”风浪起的前两年,晦师这位安于寂寞,难合时宜的“五四”老人已经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受到了批判。1964年夏,北京大学党委在十三陵新建的昌平分校召开党内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清算北大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在北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试点。参加会议的有80 余人,作为党内专家,晦师和冯至都去参加了。因为是党内会议,出于对党的爱护,晦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思考多年的真实想法。他语出惊人:当前的问题,哪里是什么右倾?反右斗争以后,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一会儿去抢麦收,一会儿去修水库,哪还有教学秩序?他还拿出了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依据周总理在广州会议、新侨饭店会议所作指示精神而制订的《高教六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逐条加以对照,一一指出了不符合条例的种种举动。最后,他呼吁校方,当务之急乃是落实《高教六十条》,而不是什么反右倾。晦师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一出,全场哗然。冯至说:“一时议论纷纭,与会者感到惊奇。”有人说,杨晦平日沉默寡言,如今忍不住气了,语出惊人。有人说,这都是右派言论,早几年说出来,准是右派无疑,是个漏网右派。还有人说,眼前正要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今杨晦自己跳出来了,正好!
面对责难和批判,晦师沉着应对,不慌不忙,摆事实,讲道理。他说,北大是高等学府,是人才生产部门,既不是物质生产部门,也不是阶级斗争部门,不能和工厂、农场、部队一样,不能动不动就要开展阶级斗争。把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都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符合实际。像中文系吴小如先生,新中国成立时还是青年,如今已算中年,十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教书做学问,前几年应急开了一门新课“工具书使用法”,立了大功,很具开创性,受到学生欢迎,听课的有两三百人。可是,系里就有人批评晦师重用了资产阶级文人(吴小如在解放前当过报纸副刊主编)。晦师说,像吴小如先生,如今还把他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公平,他应该算是周总理、陈毅所说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那时,我正在为东、西、俄三系开设“文学概论”,为中文系讲“文艺理论专题”,希望北大内部安定团结,为教师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但1966年初,以北大党委已选定北大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点对象,历史系是副校长翦伯赞,哲学系是校党委副书记冯定,中文系就是前副教务长、现中文系系主任杨晦,都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我记得,那是在1966年春节的前一个月,花了将近三周的时间,中文系的教师党员集中在燕南园63 号原马寅初的住地,由北大党委直接领导,进行了党内整风,批判矛头直指晦师。北大党委派了副书记和团委书记亲自压阵督战,还分别找我谈过话,要我勇于参加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帮助我的老师转变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这两位领导对我比较熟悉。1963年秋,我从中央党校回北大,首先按新编的《文学概论》(蔡仪主编)来给学生上课,当时主管全校教学的副校长魏建功把此课定为全校重点课程,副教务长王学珍以及副书记、团委书记都曾来听过课,在学生中作调查研究。他俩都知道我和严家炎都是晦师的研究生,所以要动员我站出来批判晦师,想帮助我站稳立场,参加战斗。但说来惭愧,我当时和严家炎站在一起,不仅没有批判晦师,反而为晦师作了诸多辩护,从而引起了他俩对我的失望和不满。幸而,经历了那场“文化大革命”后,大家都懂得那是个历史的误会,都相互谅解了。
严冬凌厉,寒气逼人。北大中文系里最年长的学者、年已67 岁的晦师每天都要从燕东园横穿燕园,走到燕南园63 号,接受批判。我和严家炎对此颇感不平,时常站出来为晦师作些解释,说明晦师在特定境遇下所说的原意,并非如有些人所说,乃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说话。教育自有规律。晦师一生都贡献于教育,懂得教育规律,他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乃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等等。当时,上海纺织女工出身的中文系总支副书记华秀珠,也站出来为晦师作辩护。负责教师党支部的邵岳,跟随过晦师研修中国文艺思想史,视晦师为忠厚长者,也不时站出来介绍晦师的为人。中年学者冯钟芸(任继愈夫人)、彭兰(张世英夫人、闻一多门生)和晦师接触较多,也都纷纷出来说话,肯定晦师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一生贡献于教育事业,希望通过此次党内整风,提高政治觉悟。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运动,对晦师来说乃是他一生中所遇最大悲剧,使晦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心力交瘁,寝食难安。那一阵,晦师甚至闪过轻生的念头。家炎去看他,他对家炎说,他常站在阳台上徘徊,不敢朝下看一看,怕自己会纵身一跳。我也只能安慰他,风物长宜放眼量。后来晦师转移注意力,开始集中精力读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为了能读原著,他在这67 岁之年,还向好友冯至求教,专心学起德文。“不合时宜”的他,从此甘于寂寞,虽然还挂着系主任的名号,却再也不参与行政事务了。
七
1966年的那个春节,我们都没有好好过。我去看望晦师,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我也只能劝他心胸放宽、静观待变。其实,我也是心神不宁,不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
在“文化大革命”中,晦师靠边站了,却也未受更大的冲击,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燕东园整风中已经受难,反而受到大家的体谅和同情。晦师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上。那时,马恩全集翻译过来的还不多,晦师为了读原著,从那时开始自学德文。他用放大镜一边查德汉辞典,一边读马列原著。他读马列原著,是想弄清楚,马恩他们所倡建的社会主义究竟应是什么样的,以解当下心中的困惑。这使我想起,朱光潜在十年前受批判时,竟也是学起德文来,学会德文好读马恩原著,以便弄清楚马恩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是不是都如那些批判者所说的那样。老一辈学者喜欢追根问底、实事求是,这种执着较真的学术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幸运的是,晦师受到了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保护。中文系的师生在当时也成立了这个组织,选出女工出身的华秀珠和贫农出身的邵岳等来主持这个委员会。经过燕南园的党内整风,华秀珠和邵岳都对晦师有了全面了解,知道他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不能打倒,对受冲击较大的王瑶先生也采取了尽力保护的方针。

从1966年夏到1968年夏,我们在晦师的小客厅住了两年,因此,也就有了和晦师朝夕相处、促膝谈心的机缘。这是十年动乱中,我们过得最为安宁的两年。课早已不上了,刚搬去时,我受命在周培源副校长和留学生办公室主任麻子英麾下接待外宾。那时,涌入北大校园来“取经”看大字报的人士,一个月就有上百万,还有不少的外国使馆人员来观摩,我忙得不可开交。但从9月初起,我又被周培源的得力助手郭罗基纳入他组建的一个特别教学小组,去友谊宾馆授课,当了西哈努克王子的“太子太傅”,这成了我的世外桃源。此时,晦师已与世隔绝、不再外出,所以很盼望我去他书房里随便聊天,从我这里多知道一些外界的情况。那时,夜晚常停电,书也没法看,晦师就邀我到楼上书房,点上蜡烛,秉烛夜谈,自由聊天,聊了些什么?时过境迁,大多已经淡忘,记不起来了,但有些我感兴趣的话题,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觉记忆犹新。
那时,北京扫“四旧”,我在看《日知录》,顾炎武在此书中竭力称颂“风俗之美”。我问晦师:“风俗有美丑吗?”晦师当即说道:“当然有。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在江南推行美育,颂扬真善美,很有号召力,上海有一杂志,就叫《真善美》,在赞扬自然美、艺术美之外,还不时称颂江南的风俗美。耕读传家、尊师重道,这都是风俗之美,应该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晦师那个时代,会有什么样的人际交往?以前,我只知道他和冯至等创办的沉钟社,晦师实际上起了精神领袖的作用,相互关系甚为融洽。而在这多次聊天中,我发现晦师除了和冯至、蔡仪交往密切外,还和臧克家、何其芳、章廷谦(川岛)交往甚多,堪称深交。晦师在北大读书时,交往最多的就是章廷谦。晦师在1917年进了北大哲学门,章廷谦要比晦师晚两年,是先后同学。章廷谦虽学哲学,但像晦师一样,爱好的是文学,而且一入学就已表现出了他的文才,“依马长才,下笔千言”,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还在读书时,就已请他参加新创办的《北京大学日刊》的编撰。当时校长办公室发送的不少重要文稿,就出自于章廷谦之手。晦师对《北京大学日刊》密切关注,每期必读,并由此而和章廷谦相识。当时北大学生住处分散,信息不灵,北大发生的重大事件,晦师都是从章廷谦那里获悉的。再以后,晦师知道章廷谦是周树人的同乡好友,就更敬佩这位师弟了。晦师在1920年毕业后,辗转南北,但只要一回北京,有几位熟人是一定要见面的,张凤举、冯至、蔡仪之外,章廷谦亦在其列。章廷谦在1922年毕业后,就留在哲学系当助教,又兼任校长室秘书,继续编撰《北京大学日刊》。李大钊在辞去图书馆馆长之后,就当上了校长室主任,章廷谦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李大钊遇难后,章廷谦到处奔走,在香山南侧的万安公墓找到一块墓地,准备安葬。共产党人为李大钊刻了一块墓碑,但当时不能公开,也是章廷谦当机立断,把此墓碑连同灵柩一起埋在地下,得以保存下来,直到即将解放,才从墓地挖出,矗立于墓前。我和章廷谦虽然熟识,但这段历史,我从未听说,周海婴也从未说起过。晦师的深情回忆,使我对章廷谦肃然起敬,备加敬重。
著名诗人臧克家时常称晦师为老师,那确有来由。臧克家在1923年考进山东省第一师范读书,就认识了还在文学专修科任教的晦师,参加了晦师领导的文学社团。正是在晦师的引导下,臧克家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他的同班同学李广田走上了文学评论之路。1943年,晦师和臧克家都到了山城重庆,久别重逢备感亲切,相互照顾亲如一家。那时,晦师在国立西北大学受国民党迫害,到重庆来投奔左翼文化界自谋出路。臧克家尽力相助,请好友吴组缃竭力推荐,把晦师请进了中央大学执教。正是在重庆的两年多里,晦师得以集中精力写出了十多篇重要的文艺评论,有的还在《新华日报》发表,产生了广泛影响。长达三万多字的《曹禺论》就是1944年在重庆写成并发表的,引起了文艺评论界的关注,美学家吕荧还曾撰文参与争论。臧克家在《新华日报》发表讽刺国民党的诗篇《侧起耳朵,瞪着眼睛》,晦师拍手称好,立即致信:“努力吧,克家兄!”鼓舞臧克家勇往直前。国民党当局早已对晦师有所警惕,抗战一胜利,中央大学立即解聘晦师。幸而,中央大学的进步学生陈秀霞、陈秀云说服了父亲陈鹤琴,把晦师请到了上海幼师专科任教。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年间,晦师和臧克家在上海相互支持,共同战斗,在臧克家主编的《文讯》上,陆续发表了《中国新文艺发展的道路》《追悼朱自清学长》等重要文章,一起度过了白色恐怖的苦难岁月。1949年初,晦师、臧克家两家人又由地下党护送到了香港,在九龙度过了一段时光,然后才到北京共同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晦师、臧克家虽属师生,但亲如兄弟。“文化大革命”中,北大红卫兵曾有人去找臧克家,想搜集晦师的资料,臧克家二话不说,斩钉截铁地只说了一句:“杨晦?红色教授!”回忆过往,晦师深情赞叹:“我和克家,是铁哥们!”
晦师和何其芳在解放后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早在第一次文代会后,何其芳就秉承周扬意志,动员晦师去作家协会专事文艺评论。丁玲那时也在张罗筹建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请晦师参与筹建当委员,寻求合作。但晦师听从冯至劝告,还是留在北大,边教书边研究,没有卷进文艺界激烈斗争的漩涡之中。何其芳早在1951年就和晦师合作,策划筹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趁院系大调整的时机,把适合作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列入研究所行列,不再从事教学。那时,何其芳的夫人牟决鸣就在参与筹建。1953年北大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何其芳不让夫人在同一单位,就把她调到了文联。俞平伯、余冠英、钱锺书夫妇正是在那时进了北大文学研究所。年轻一代学者——曹道衡、樊骏、刘世德、沈玉成、王信、卢兴基、徐子余等人,都是晦师经过挑选,然后和何其芳一起商定,陆续调了过去。何其芳对晦师十分尊敬,他住燕东园35号,和晦师的住所只有百步之遥,穿过草坪就能相访交谈。《文学研究》(后改为《文学评论》)在1957年创刊,何其芳立即请晦师当编委,文学研究所订学术规划,必请晦师参与相商。因我和牟决鸣相识,所以常出入她家,也识得了何其芳。那时,何其芳刚到四十,热情洋溢、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何其芳和蔡仪都从燕东园搬出,迁入东单的西裱褙胡同去了,但我每当去文联参加活动,还是会跟着牟决鸣去她家看望一下何其芳和蔡仪。
在和晦师自由聊天中,我进而知悉了晦师和何其芳的密切关系乃有历史渊源,而且和臧克家有关。1944年,臧克家在重庆时已享有盛名,是著名的左翼诗人。那年,毛泽东、周恩来派了何其芳和刘白羽去重庆向国统区文艺界传介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解放区的文艺政策,臧克家和何其芳一见如故,然后,臧克家又将好友晦师介绍给何其芳相识。晦师说,他当时在重庆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受益于何其芳。何其芳在那里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来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令晦师深为感动。何其芳也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比晦师小13岁,1931年才进北大,但他也像晦师一样爱好文学,热爱写诗文。在北大读书期间(1931-1935),何其芳已出了名,和李广田、卞之琳一道,被称为“汉园三诗人”。毕业不到一年,1936年何其芳就出版了散文诗集《画梦录》,享誉文坛,被朱光潜、沈从文、林徽因等请进“京派”沙龙。然而,何其芳在1938年就去了延安,成为周扬办鲁迅艺术学院的得力助手,从此献身于解放区的文艺事业。晦师没有去过延安,但受到何其芳现身说法的感染,很快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激发起革命热情,就在那两年,在国统区积极开展文艺评论。1945年,何其芳受周恩来所托,担任了《新华日报》副社长,晦师好几篇文章就是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晦师和何其芳的友谊早已在那时开启。
和晦师的自由聊中也不知不觉地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疑窦。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曾和我说起过,他在延安时,亲耳听过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五四”时的北大新闻研究会,列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杨兴栋(即晦师)。方汉奇去查阅历史资料,发觉真有其事,就问我:“杨晦当时和毛泽东有交往吗?”在自由聊中,晦师告诉我,他和毛泽东一起听过《京报》主编邵飘萍的新闻学课,相互知道姓名,但并无交往。1918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有50 多位会员。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常来听邵飘萍的课。晦师当年还叫杨兴栋,只是个19 岁的青年,接触的人不多,所以并未和毛泽东相识。晦师估摸,毛主席在延安时提及自己,可能还是因为何其芳的缘故。1945年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何其芳从重庆召回,让他说一说当时重庆文化界的情况。何其芳把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如实说了。依他之见,像臧克家、沙汀、晦师这样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真心信服毛泽东文艺思想,正是在重庆期间,臧克家、晦师成了何其芳的莫逆之交。
这是我一生中能和晦师促膝谈心、无所不聊的最难得的机缘,以后再也没有了。
难得还有一事不能忘怀,值得一说,那就是在1968年的“五四”,晦师要我约了周海婴和章廷谦在中关村的科学院福利楼共进午膳,同忆往昔。
我在1967年抓紧时机,为西哈努克王子安排了两次访问。一次是在当年9月,趁浩然陪同巴基斯坦作家参观回来之际,我陪西哈努克王子拜访了浩然,得赠《艳阳天》。一次是在当年5月,去景山东前街七号拜访了许广平和周海婴,西哈努克王子接受了许广平送的一套厚礼:紫檀木匣装的《鲁迅全集》(1938年版),高兴得不得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许广平,1968年3月3日,她就在医院病逝,之前周总理曾亲自到北京医院探视过。周海婴在母亲逝世后,搬出了景山东前街入住三里河三区。那年4月,我到阜成门广播大楼去看他,海婴情绪低落、旧病复发,我颇为他担心。回到燕东园住所,我当晚在和晦师聊谈中说起了此事,晦师一听,感到心情沉重,沉默深思,然后对我说:他和刚从德国回来的冯至、姚可昆夫妇在1935年9月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内山书店附近的咖啡店里,没有见到许广平和海婴。一年后,鲁迅去世,他和冯至参加了送殡行列,直到万国公墓。他们向许广平和海婴致哀,但未能交谈。如今,许广平也过世了,他希望我能找个机会见一见海婴,当面安慰。他知道我和海婴熟识多年,所以要我安排,由他做东请客,了却他的一个心愿。
为了实现晦师的这个心愿,我特地去中关园找章廷谦商量。章廷谦出了个好主意,趁“五四”北大校庆,由他约好海婴,中午到中关村福利楼午餐,由我陪晦师来,一起聚会。章廷谦是中关村福利楼的常客,听从他的安排,一切顺利。“五四”那天,我陪晦师从燕东园走到中关村福利楼,晦师特地带了一罐他喜欢的茶叶碧螺春和一盒长白山人参,作为礼物送给海婴。海婴也带来了一瓶绍兴黄酒,就在当餐喝了。晦师一见海婴,就对他说:“时间真快,在万国公墓见到时,你还是小孩,想不到如今是这么高的大高个儿!”那天,海婴没怎么说话,就听章廷谦回忆往事了。章廷谦讲到,1926年当初是他劝鲁迅离开北京这是非之地,他跟着鲁迅一同去了厦门大学。又说起,许广平、海婴从香港到北京后,他帮许广平物色了大石作胡同买了下来,那是靠近景山的好地方等等。饭后,我陪晦师回燕东园,他在路上几次说,人生难测,世事难料,颇为伤感。但他又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许广平去世,还是到了古稀之年。那年,晦师69 岁。我告诉晦师,海婴育有三男一女,鲁迅后裔,人丁兴旺,听后晦师稍感欣慰。
正是在这两年,我对晦师的内心世界有了较深入的了解。那几年,每逢“五四”北大校庆,总有各种传媒,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来采访,要晦师回忆当年他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晦师患白内障,视力已差,就由他口述,我整理加工,再写成文章。为此,我又把他过去写过的不少文章找来看,对他的过去又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晦师出身贫寒,历经沧桑。这就和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朱光潜很不一样。晦师从小就经历过许多苦难,在那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年代,他经受住种种挫折,因而性格中具有坚强的韧性。他经历了太多社会悲剧,因而转向古典悲剧的研究,并且也动手创作悲剧。在平时,他沉默寡言,但遇到不平,则悲愤填膺。他青年时代的悲剧精神,在老年时代仍有表露,我认识他31年,也仍能时常感受到。晦师的形象和鲁迅很相似,他那坚毅不拔的精神更像鲁迅。他在北京和上海,都和鲁迅有诸多交往,在已出版的《鲁迅日记》中就有七处谈及晦师,鲁迅对晦师、冯至等积极坚持的沉钟社评价甚高。

八
1977年5月底,邓小平接见了即将调任北大党委书记的周林和北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要他俩立即在北大恢复高考制度。此后,周培源被任命为“文革”后的第一任校长,撤消了革命委员会。从中央警卫团调来当革委会主任的王连龙等撤回中南海,军宣队退出了北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北大又回归了教育本位,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晦师欢欣鼓舞,虽已年近八旬,但还是积极投身教育。1978年,教育部开始实行学位制,分别设立了学士—硕士—博士不同层次的学位。接任晦师当中文系系主任的季镇淮教授坚请晦师担任研究生导师,晦师积极响应,从1978年开始招收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1978年冬,我当时正在为新生开讲“文学概论”课,并开始准备选修课“文艺美学”。晦师把我叫到他家里,苦笑着对我说道:“你读了四年副博士研究生,可一‘反修’,把学位也取消了。出尔反尔,说变就变,导师都不满意,可又无可奈何。如今要走上正轨了,我要招硕士生了,可我已年迈体衰,精力不济,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还是要招这第一届,开个头,你帮我作些具体安排。我就招这一届,以后,让你招了。”“文革”十年,积压了大量优秀人才未能继续培养,这批文艺学首届硕士生,就来了不少我本科教过的学生,如董学文、曾镇南、郭建模等,晦师亲自培养了这一批硕士生,我则协助他,还曾求助于冯至,请来陈焜等开讲当代西方文论。于是,这些大学时代我的学生,成了我的师弟。晦师露出了笑容,幽默地说:“这终究不是历史悲剧,最后还是个喜剧。”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喜悦。
最后几年,晦师都把心思放在扶持后进上。当时负责中文系全面工作的吕梁,曾要我专门去找晦师,询问是不是要为他配一个学术助手。晦师也曾想把他多年的思考写成《文学论》,但是出于对后学的爱护,他还是没有要。他托我向吕梁道谢:“感谢组织关怀,但我不能再要助手。中青年一辈,历经磨难,时光耽误,要让他们抢回失去的时光,抓紧做自己的学问。”

杨晦先生与学生在一起
在晦师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在1981年开始独立招收文艺学硕士生。那时,我在开设“文学概论”课之外,已在1980年新开了一门“文艺美学”课,受到了高年级学生的欢迎。受此鼓舞,我就大胆向晦师建议,想在“文艺学”下另设一个专业方向,就叫“文艺美学”,以区别于“文艺理论”。晦师在1963年就准备要我开选修课“美学”,但时势不对,一直未能开出,如今不如就叫“文艺美学”。我把我的设想告诉了晦师,我想沿着鲁迅1912年在教育部所作的《美术略论》的内容来展开研究。蔡元培在当教育总长时倡导美育,鲁迅积极响应,1912年在教育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会”上连续演讲了四次《美术略论》,1913年以《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署名周树人)一文载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向全国推广。鲁迅的基本观点可表述为:“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他所说的美术,包括了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直接功用,乃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但文学艺术还有间接功能:“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我觉得,鲁迅的《美术略论》,正是我心目中的艺术概论的雏形,文艺美学正可以接续鲁迅的见解作更深入的研究。晦师看过鲁迅的论述,觉得入情入理,听了我的解释,他就积极支持我另辟文艺美学专业方向,报请北大研究生部核准。也就在此同时,我受命北大出版社,发起组编一套《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聘请朱光潜、宗白华、晦师三位为学术顾问。没有想到,晦师没有见到这套丛书的出版,竟先朱、宗二位作古了,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我年轻时到北京求学,在京30 余载,有幸受到许多老一辈学者的教导。王朝闻、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在美学上给我引导;何其芳、林庚、吴组缃、章廷谦、王瑶等在文学方面给我启示;冯至、季羡林、杨周翰、闻家驷、李赋宁等在外国文学方面给予我教诲;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等也在“红学”方面予以点拨。这些前辈学者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在诸多前辈学者中,对我人生道路和学术发展,影响最大、帮助最多、指导最久,使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我的导师——“五四”老人杨晦。
晦师在1983年5月逝世。在八宝山向他遗体告别时,我含泪徘徊,默哀良久,不忍离去。回到北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写了一篇悼文在北大校刊发表,寄托哀思。师兄赵齐平也发表了一首悼诗,叹晦师一生:“早逐狂飙骋绣鞍,耄心犹自赤如丹。沉钟声远回荒野,九鼎论新肃讲坛。”我甚有同感。
1984年,我应深圳大学校长张维院士之邀,和汤一介、乐黛云一起来参与创办中文系,开始三年还往来于北大、深大之间,到1987年落户深圳,离开了北大。我在北大整整35年,感恩北大。所以当我的《胡经之文集》出版,我首先要送北大的师友,可惜,晦师已经不在,难再登门讨教了,不禁叹息!
1998年,我回北大参加百年校庆,特地去林庚先生家看望这位87 岁的老人。他一下就认出了我,向在座的一群学生说:“他是杨晦的学生。”一下子就把我带进了对晦师的回忆之中,回来后我写下了一篇《诲人不倦启后人》,后送交了杨铸。

本文作者胡经之先生
受教30 余载,我敬佩晦师的为人,特别是他那诲人不倦、一丝不苟的人格精神。晦师一生,遵循李大钊所说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又深得鲁迅的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晦师虽逝,精神永在。
(完)
承蒙北京大学杨铸教授、深圳大学黄玉蓉教授的帮助,才得以完成此文,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