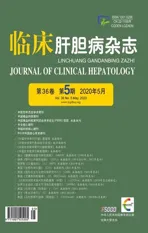肝内固有抗原递呈细胞调控抗HBV免疫应答的作用及机制
2020-06-17谢晓红杨东亮
谢晓红, 杨东亮, 刘 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感染科, 武汉 430022
据2006年的统计资料,我国现有慢性HBV感染者9300万人,其中慢性乙型肝炎(CHB)约2000万例,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CHB所导致的终末期肝病,如肝硬化和肝癌[1]。阐明HBV持续性感染的机制,探索清除HBV持续性感染的新靶点和新策略是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作为被HBV侵犯的主要器官,肝脏具有极其特殊的解剖结构和免疫微环境。肝血窦是肝脏所独有的特殊结构,是肝脏微循环血流灌注和免疫应答的主要发生部位。血液中的各种成分(如淋巴细胞和病原体等)在肝血窦内可较长时间停留,并充分与肝血窦内的各种细胞发生相互作用,这一过程对于肝内天然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发生非常重要[2]。肝窦内皮细胞(liver sinusoidal endothelial cells,LSEC)和枯否细胞(Kupffer cells,KC)是肝血窦内最主要的固有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可从血液循环中有效摄取、加工抗原并交叉递呈给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既往研究[3-5]认为,与成熟的专职APC递呈诱导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活化不同,LSEC和KC交叉递呈抗原往往诱导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形成耐受,表现为T淋巴细胞丧失细胞毒效应及产生效应性细胞因子(IFNγ和IL-2等)的能力。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除诱导T淋巴细胞耐受外,LSEC和KC等肝内APC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促进肝内抗HBV免疫应答的发生,从而介导HBV的清除(表1)。本文就肝内固有APC调控肝内抗HBV免疫应答的作用及机制加以综述。
1 肝窦内皮细胞(LSEC)
LSEC构成了肝血窦的血管壁,是肝内非实质细胞的主要群体,约占肝非实质细胞的50%。由于LSEC在肝血窦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其暴露于血液中各种成分的刺激之下,并与血液中的淋巴细胞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LSEC是一种高效的APC,表达参与抗原递呈过程的多种分子,如CD54、CD80、CD86、MHCⅠ/Ⅱ和CD40等,可向CD4+和CD8+T淋巴细胞递呈抗原[6-7],从而调控肝内的T淋巴细胞应答。
1.1 LSEC介导T淋巴细胞耐受 与DC类似,来自于病毒等病原体的外源性抗原可以被LSEC摄取和加工处理,并以交叉递呈的方式递呈给抗原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7]。且其交叉递呈可溶性抗原的能力相较于DC更为高效[8]。与在淋巴结内活化的T淋巴细胞不同,LSEC交叉递呈致敏的抗原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会在肝内滞留[9]。LSEC递呈抗原给CD8+T淋巴细胞后,在最初的24 h内T淋巴细胞表面CD25、CD44和PD-1等分子的表达升高,CD62L的表达下降,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发生增殖[6,10],这一过程与成熟DC致敏CD8+T淋巴细胞的过程相似。但与DC致敏诱导T淋巴细胞持续增殖不同,LSEC致敏的T淋巴细胞只发生短暂地增殖[11]。LSEC表面高表达PD-L1(B7-H1)分子,抗原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被致敏后PD-1分子表达上调,二者相互作用,导致T淋巴细胞无法进一步持续活化[10,12]。LSEC表面表达的MHC-Ⅰ和CD54等分子决定了LSEC对CD8+T淋巴细胞的黏附能力[13],这两种细胞相互作用之后,LSEC表面CD54分子进一步上调,从而稳定LSEC对T淋巴细胞的抑制作用[9]。但T淋巴细胞也不会经历凋亡,其机制可能与LSEC致敏的CD8+T淋巴细胞表达大量的抗凋亡分子bcl-2有关[10]。未经刺激的LSEC几乎不表达IL-12,这一关键共刺激信号的缺失,导致T淋巴细胞被LSEC致敏后的活化无法持续,IFNγ的产生水平低下[14]。最终被LSEC致敏的T淋巴细胞被诱导形成耐受,接受TCR再刺激后缺乏IL-2和IFNγ等效应细胞因子的产生[9],IL-2缺乏进一步抑制CD8+T淋巴细胞活化[6]。此外,LSEC可通过影响其他细胞功能调控肝内T淋巴细胞免疫应答。LSEC与肝内DC相互接触后,可降低DC表面CD80/CD86等共刺激分子的表达,抑制DC对初始T淋巴细胞的活化功能[15]。LSEC还可以以TGFβ依赖的方式诱导Treg的生成,抑制T淋巴细胞免疫应答[5]。通过LSEC递呈抗原,被致敏的CD4+T淋巴细胞会发生增殖,但是不能分化为促炎性的Th1[14]。相反,LSEC可以促进CD4+T淋巴细胞向Th2方向分化并分泌IL-4[4]。其机制可能为生理条件下门静脉血中内毒素诱导LSEC产生IL-10和前列腺素E2,降低LSEC表面MHCⅡ和CD86等分子的表达,从而抑制了LSEC致敏CD4+T淋巴细胞产生IFNγ的水平,更易向Th2方向分化[16]。上述因素共同参与了LSEC介导的肝内T淋巴细胞免疫耐受形成。
1.2 LSEC介导T淋巴细胞应答 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在病毒感染或特定天然免疫通路活化等条件下,LSEC可逆转其耐受属性并促进T淋巴细胞应答。加入CD28可以解除B7-H1依赖的LSEC介导的CD8+T淋巴细胞的耐受性,表明共刺激/共抑制平衡决定了免疫耐受或免疫活化状态[17]。静息状态下LSEC缺乏IL-12表达,而外源性IL-12则增加了LSEC对记忆和幼稚CD4+T淋巴细胞的辅助功能。在组织损伤时单核细胞会渗透到肝脏,由肝脏的APC诱导的局部免疫反应可以通过血液来源的单核细胞产生的IL-12增强[14]。有趣的是,将脾脏细胞加入到LSEC和CD4+T淋巴细胞的共培养体系中,导致了Th1表型的诱导,这表明LSEC介导的幼稚CD4+T淋巴细胞的失活可以被其他APC细胞群所克服[14]。笔者前期的研究[12]也显示,TLR1/2配体刺激LSEC可诱导其活化,分泌IL-12且维持PD-L1表达水平不上调,进而诱导抗原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增殖并且产生IFNγ。改变抗原浓度也会对LSEC的免疫活性产生影响。LSEC递呈低浓度卵清白蛋白抗原时,诱导抗原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产生耐受,而当提高抗原浓度10倍,LSEC不仅不能诱导CD8+T淋巴细胞产生耐受,相反,CD8+T淋巴细胞分化为功能性效应T淋巴细胞[18]。Kern等[19]在小鼠巨细胞病毒感染模型中首次表明,病毒感染LSEC后可诱导其功能成熟,进而促进CD8+T淋巴细胞免疫。Bottcher等[20]首次提出LSEC交叉递呈抗原致敏的抗原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还存在第三种命运,即分化为具有增殖潜能的记忆性T淋巴细胞。这些记忆性T淋巴细胞与中枢记忆性T淋巴细胞相似,可重新定位到次级淋巴组织,再次接受TCR/CD28/IL-12共同刺激时,可以快速分化为效应T淋巴细胞。这种记忆性CD8+T淋巴细胞分化伴随着迅速而短暂的颗粒酶B(GzmB)的表达和效应功能的诱导,早期短暂的GzmB表达依赖于LSEC分泌的IL-6介导的跨信号转导途径[21]。在此过程中,如果存在激活的Th1,其分泌的IL-2可显著增强LSEC致敏的CD8+T淋巴细胞GzmB的表达水平,且启动更加迅速[22]。
LSEC的活化状态对调控肝内抗HBV特异性T淋巴细胞应答至关重要。笔者的研究[23-24]显示,刺激NOD1信号通路在体内体外均可诱导LSEC活化和成熟,促进肝内抗HBV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应答,进而在HBV慢性复制小鼠模型中加速HBV的清除。在HBV自然感染过程中,T淋巴细胞表面膜CD100会被剪切释放形成可溶性CD100,这一分子可诱导LSEC活化,进而促进抗HBV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应答并介导病毒的肝内清除[25]。笔者新近研究发现,HBV感染过程中产生的HBeAg也具有诱导LSCE的免疫功能成熟进而促进CD8+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此外,LSEC表面可结合活化的血小板,进而使得活化的HBV特异性效应T淋巴细胞可以锚着于其表面,通过LSEC间的窗隙与HBV感染的肝细胞接触,发挥杀伤作用[26]。上述机制显示LSEC在急性HBV感染的肝内免疫清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枯否细胞(KC)
KC是肝脏的常驻巨噬细胞,除了由肝源性前体维持[27],还可以以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依赖的方式从单核细胞衍生。它们与LSEC一起形成应对病原体入侵肝脏的第一道屏障。KC的主要功能是清除门静脉循环中的内毒素、释放可溶性介质和提供抗原,有效地将抗原呈递给免疫活性细胞[28-30]。在抗原摄取或刺激下,KC可被激活并分泌一系列的细胞因子(IFNα/β、TNFα),进行T淋巴细胞的招募[31-32]。
2.1 KC介导的T淋巴细胞耐受 KC是肝内免疫应答调节的重要参与者,通常与维持肝脏免疫耐受环境相关[33]。在体外诱导分化之后,KC显示出更快速且持续地上调抗炎细胞因子编码基因的表达[34]。相较于脾脏DC致敏的T淋巴细胞,KC致敏的T淋巴细胞表达相当水平的CD69,但CD25表达水平及IL-2分泌水平低下,从而导致T淋巴细胞失能[35]。在脂多糖刺激下,KC同样释放出大量的IL-10[36],而生理条件下门静脉血中内毒素即可诱导KC分泌IL-10[16],肝窦局部IL-10浓度较高,诱导T淋巴细胞耐受。与此一致,IL-10受体阻断可以部分恢复CD8 T淋巴细胞功能[37]。此外,与LSEC相同,KC可以抑制DC诱导的T淋巴细胞活化[35]。在病毒性肝炎中,大多数KC被激活并表达高水平的CD80、CD40和MHC-Ⅱ分子,从而获得专职APC的表型[38]。
HBV感染的慢性化与年龄显著相关,KC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39]显示,HBV阳性孕鼠的HBeAg可刺激子代小鼠的KC,诱导其分化为M2型巨噬细胞并上调PD-L1的表达,从而抑制抗HBV特异性的T淋巴细胞应答。这些HBeAg暴露过的子代小鼠出生后再次接受HBV攻击后会发展为慢性化感染。此外,接受HBV攻击后,幼年小鼠的慢性化比例要显著高于成年小鼠。进一步研究[40]显示成年小鼠肝内KC较幼年小鼠显著减少,且其细胞上的TLR4表达也较幼年小鼠低,也提示了KC在介导HBV慢性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敲除幼年小鼠的KC可增强Ly6C+单核细胞的肝内募集,促进HBV特异性CD8 T淋巴细胞的扩增及效应功能,加速HBV的清除[40-41]。乙型肝炎核心抗原可通过激活TLR2信号通路诱导KC产生IL-10,从而诱导HBV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耐受并致感染慢性化[42]。TLR2基因敲除或敲除小鼠的KC可增强小鼠体内的HBV特异性CD8+T淋巴细胞应答并促进HBV的清除[42]。笔者近期研究[37]也发现,HBsAg也可通过TLR2信号通路诱导KC扩增以及增加IL-10的分泌,进而抑制效应T淋巴细胞的功能。另外,HBeAg通过抑制NF-κB磷酸化以及抑制活性氧生成,抑制KC的NLRP3炎症小体活化与IL-1β产生,这可能也是HBV免疫耐受形成的机制之一[43]。
2.2 KC介导的T淋巴细胞活化 KC可以在肝脏原位激活抗原特异性CD4+T淋巴细胞[44]。KC识别HBV或HBsAg后,迅速诱导IL-6、IL-1β、TNFα产生,促进自然杀伤细胞活化[45],并且可以在感染早期控制HBV复制[46]。Poly I:C可以显著上调KC表达MHC-Ⅱ、B7-1、B7-2和ICAM-1,增强活化T淋巴细胞的功能;另一方面,吲哚美辛可以抑制KC分泌前列腺素,抑制KC介导的T淋巴细胞耐受[35]。Poly I:C还能上调KC表达CXCL13,促进肝内免疫,加速HBV清除[47]。KC在炎症刺激下产生的细胞因子也可影响肝窦内其他细胞的活性[36]。
3 肝内其他APC
肝窦内的低速血流有利于淋巴细胞和肝细胞之间的相互接触。肝脏微绒毛可以通过LSEC窗隙延伸到肝窦腔[48]。T淋巴细胞胞质也会形成伪足穿过LSEC窗孔延伸到Disse腔,与肝细胞微绒毛紧密接触[26,49]。肝细胞表面大量表达MHC-Ⅰ和ICAM-1分子,可递呈抗原给T淋巴细胞[50]。值得注意的是,肝脏ICAM-1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集中分布在肝窦表面。LFA-1在淋巴细胞微绒毛上表达,可能通过其配体ICAM-1与肝细胞相互作用[49]。新近研究[51]显示,HBV感染过程中,肝细胞可递呈抗原给CD8+T淋巴细胞并诱导其活化和增殖,但不能使其分化为效应T淋巴细胞,而是表现为功能耗竭T淋巴细胞的特征。如果给与IL-2信号刺激,可挽救这些T淋巴细胞的功能。
肝星状细胞也能够处理外源性抗原肽,递呈给CD4+T淋巴细胞,并以交叉递呈的方式致敏CD8+T淋巴细胞,诱导T淋巴细胞活化并发挥功能[52]。
4 总结与展望
肝内固有APC在调控肝脏免疫应答、维持肝脏免疫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生理条件下,肝内固有APC可以通过多种机制诱导T淋巴细胞耐受,避免肝内病理免疫损伤的发生。然而,上述机制也会被HBV利用从而帮助其建立持续性感染。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已发现在HBV感染过程中,多种机制参与了调控肝内固有APC的活化状态,进而决定肝内抗HBV特异性T淋巴细胞应答的强度并影响病毒的清除。但目前对于肝内APC功能的研究多停留在单个细胞亚群的水平,仍缺乏对肝内不同细胞群体间以及肝内和肝外免疫细胞间的互作网络的整体认识。进一步深入阐明相关机制将为探索更有效的阻断HBV持续性感染的免疫干预策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

表1 肝内固有APC调控肝内抗HBV免疫应答的作用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