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文章百世人”
2020-06-09樊树志
樊树志

吴应箕画像
崇祯年间的复社,与万历年间的东林书院,后先辉映,在历史上留下了耀眼的身影。复社成员都是年轻的知识精英,以文章道德气节相标榜,引领时代精神,澄清社会风气,时人誉之为“小东林”。继张溥、张采之后,吴应箕是复社的第三位领袖人物。
吴应箕,字次尾,号楼山,池州府贵池县人。面对岌岌可危的时局,他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挚友周镳说他,“每扺掌时政,奋髯垂涕,悲愤交作”。最令人称颂的是,他顶住压力起草《留都防乱公揭》,为惨遭阉党迫害的东林诸君子伸张正义,声讨妄图翻案的阉党分子阮大铖,在明末的南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全国为之震动。复社之所以被称为“小东林”,在吴应箕身上印证得淋漓尽致,他把复社的声望推向新的高潮。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给了他高度评价:“复社领袖也,言谕风旨士争趋之,公卿以下视其臧否以为荣辱。阮大铖在南都,应箕率诸名士噪而逐之。”
一、“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晚明文人结社的风气很盛,人杰地灵的江南尤其如此,先后有常熟的应社、松江的几社、太仓的复社,宗旨都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围绕科举考试,切磋学问;以后发展到关注社会,议论时政,影响超越一时一地。初创于崇祯元年(1628)的复社,原先是众多文社之一,由于“娄东二张”—张溥、张采无比强大的号召力,第二年扩大为众多文社的联合体,正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说:“阅岁,群彦胥来,大会于吴郡,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尽合于复社。”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崇祯二年在吴江县召开的尹山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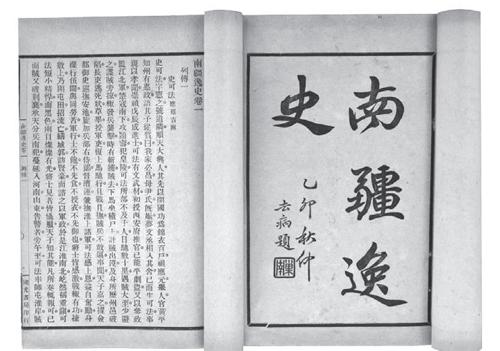
《南疆逸史》 〔清〕温睿临撰上海国光书局排印本 1915 年版
之后,崇祯六年的苏州虎丘大会,使复社的声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友,“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盛况空前,人们赞誉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朱希祖《钞本复社姓氏传略跋》认为当时复社成员有三千余人,井上进《复社姓氏校录》统计出复社总人数为三千零四十三人,如此庞大的规模,是以前文社绝无仅有的。
这其中有吴应箕的一份功劳。撰写《明通鉴》的历史学家夏燮,在《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中写道:“崇祯元年戊辰,先生三十五歲。是年,娄东张天如吉士(张溥)与同里受先大令(张采)始创复社之会,苏松名士杨解元(杨廷枢)、夏考功(夏允彝)、陈黄门(陈子龙)皆附之;大江以上则先生(吴应箕)及刘伯宗(刘城)预焉。一时有小东林之称。”
夏燮的主要依据有两条。其一是刘城《贵池吴应箕传》所说:“当崇祯初元,三吴中创为复社,才十余人耳,不佞(刘城)与次尾(吴应箕)实共之。十余人者尚名谊,摈逆节同,而次尾好讥呵特甚。”其二是冒襄(辟疆)追记吴应箕的文字:“(复社)大江以上为吴楼山(吴应箕)、刘伯宗(刘城),大江以下为杨维斗(杨廷枢)、张天如(张溥)。然则此十余人皆执牛耳,主坛坫,为东林之中兴。先生(吴应箕)其一也。先生是时未至吴中,而声气之通若合符节。迨庚午(崇祯三年)金陵大会,复社之名遂闻于朝野。”
吴应箕是复社“执牛耳”者之一,他有诗称颂“主坛坫”的社友:
同时太仓张太史,下笔顷刻布连卷。
华亭陈子工作赋,宣城沈生书翩翩。
吾邑公干有逸气,吴门杨雄独草玄。
吾曹兄弟尚六七,眼前穷达相后先。
(自注:太仓张公溥,华亭陈公子龙,宣城沈公寿民,吴门杨公廷枢,吾邑公干刘徴君城也。)
崇祯三年金陵乡试时,吴应箕与同乡刘城率领复社成员成立“国门广业之社”,参加金陵乡试的生员(秀才)逢此大比之年,在南京国子监的广业堂中,论文考艺。吴应箕《国门广业序》写道:
南京故都会也,每年秋试,则十四郡科举士及诸藩省隶国学者咸在焉。衣冠阗骈,震耀衢街……自崇祯庚午秋,吾党士始会十百人焉为雅集。
崇祯三年金陵大会之后复社名闻朝野,与“国门广业之社”的助推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才有崇祯六年虎丘大会数千人的盛况。
正当复社声誉蒸蒸日上之时,内阁首辅温体仁企图把复社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指使其弟温育仁在虎丘大会时申请加入复社,遭到张溥严词拒绝。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事关系,深层的原因是政见分歧。
在此之前,崇祯四年会试,内阁首辅周延儒担任主考官,复社的张溥、吴伟业被录取为进士,成为周延儒的“门生”。崇祯六年温体仁把周延儒赶下台,升任内阁首辅,为了把周延儒的“门生”拉到自己麾下,指使他的弟弟温育仁加入复社,遭到拒绝。恼羞成怒的温育仁依仗兄长的权势,雇人编写《绿牡丹传奇》,讽刺挖苦复社,继而炮制谣言,污蔑复社。甚而至于捏造一篇声讨复社十大罪状的檄文,罪名十分吓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等,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诬陷不实之词。
温体仁执政以后,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打击东林君子不遗余力,钱谦益、钱龙锡、文震孟、郑鄤都是被他整肃的。在他心目中,复社是东林的延续,必欲除之而后快。崇祯十年,温体仁与蔡弈琛密谋策划,指示陆文声、周之夔攻击复社“把持武断”,干预政府事务,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件。
案件细节颇堪回味。太仓望族王时敏是前内阁首辅王锡爵的后人,与温体仁有两世通家之谊,由于张溥倡立复社之后,门墙炽盛,许多望族子弟多贽居门下,王时敏因此蓄怨于复社,对陆文声说:“相君(温体仁)仇复社,参之正当其机。但相君严重,不轻见人,而主局为德清(蔡弈琛)为政,宜就商之。”陆文声起草了一份奏疏,编造张采“结交上官,把持武断”等事,交给了蔡弈琛。温体仁看了蔡弈琛送来的疏稿,回应道:“谁为张采?不过三家村兔园学究耳,乌足渎圣听。今朝廷所急者张溥耳,能并弹治溥,当授官如(陈)启新也。”陆文声获悉此意后,修改疏稿,集中火力攻击张溥“结党恣行”。
皇帝看了奏疏后,命令苏松提学御史倪元珙查究。倪元珙请求苏松道冯元飏调查此案。冯元飏秉公办理,结论是:“复社多高材生,相就考德问业,不应以此定罪。”倪元珙据此报告皇帝:“结社会友,乃士子相与考德问业耳,此读书本分事,不应以此为罪。”
这是一个转折点,社友冒襄非常感谢冯元飏的正直气概:“即复社一案,先生(冯元飏)独不阿权贵,不奉严行,毅然抗疏为士子表正谊明道之功,于世道挽拔山举鼎之力,保全善類,曲庇清流。”吴应箕对此是有同感的。对于秉公办案的倪元珙,后人给予高度评价:“时张太史溥,张仪部采,倡立复社,四方名士络绎奔会。而苏州推官某,以漕兑事与张讦口,遂迎执政(温体仁)意,举以入告,几搆党祸。事下提学御史勘议,公(倪元珙)力护持,辨言:‘诸生引徒众讲习,实非党,无可罪者。且文章为上精心,即国元气,厉治士不便。”
但案件并未了结。温体仁下台后,继任内阁首辅张至发、薛国观传承温体仁衣钵,紧追不舍,复社岌岌可危。在家养病的张采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崇祯元年进士及第,次年出任江西临川县知县的张采,告病归家十余年。在复社危急之际,写了《具陈复社本末疏》,强调复社是为了科举应试而倡立的文社,遵循“楷模文体,习翼经传”的原则,没有一丝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他义正词严地指出,陆文声、周之夔之流“罗织虚无”,“事必诬搆”,愿意和他们在公堂对质,辩明是非曲直。
御史金毓峒、给事中姜埰等官员据理力争,还复社清白。皇帝终于明白真相,下达圣旨:“书生结社,不过倡率文教,无他罪,置勿问。”继而又明确指示:“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这位皇帝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但关于复社的表态令人敬佩,敢于直言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了不起!
二、触及时事的史论与策论
吴应箕二十五岁参加金陵乡试,到四十六岁第八次参加金陵乡试,都没有中举,始终是一名生员(秀才)。这令这位意气横厉的才子颇为郁闷,《题贡院壁》诗流露了此种心情:
自我低眉入,蹉跎二十年。
临文嗟战蚁,仰屋想飞鸢。
意气何堪此,功名况未然。
徒怜军抱足,起视月初圆。

《牧马图》 〔明〕吴应箕绘
是他没有学问吗?是他不通世务吗?非也。由《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可知,天启年间的三次落第,明显是政治因素。阉党头面人物把持科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论策触珰忌”—考卷所写策论触犯阉党的忌讳;另一种是“阉党钻营,试差关节,贿赂公行”,最明显的例子是阉党头面人物崔呈秀之子在顺天乡试中举,周应秋之子在金陵乡试中举,当时称为“秽榜”。吴应箕“以不第为幸”。至于崇祯三年、六年、九年三次不第,原因在于科场舞弊,考生买通关节—开后门通路子,没有买通关节的考卷,考官根本不批阅,遑论录取!吴应箕《留都录》写道:“南都贿赂公行,司房多取夹袋之关节充数,余皆弃不阅。即予一人甲子、癸酉、丙子三科之卷,皆未动一笔。”至于崇祯十二年的落第,他认为原因在于“主考张维机、杨觐光张眊不省事,所出论策题浅俚不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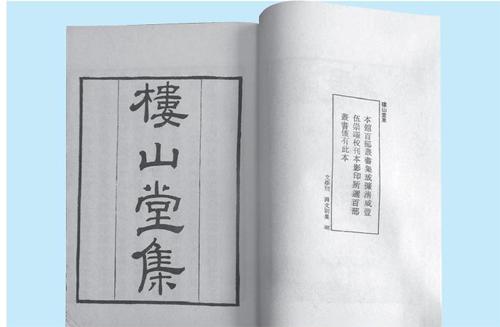
《楼山堂集》 〔明〕吴应箕撰 清粤雅堂丛书本
久困场屋之后,吴应箕有闭门著书之志,之后眼见时事日艰,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有关时务的策论。挚友陈子龙说他“博极群书,通世务,善古文,独慷慨负大略”。门人刘廷銮说他“于制艺外,发愤为古文,上陈王霸大略,下该近今之务”。
他的《楼山堂集》卷一至卷六,是历年所写的史论,点评先秦到唐宋的著名历史人物近五十名,夹叙夹议,透过历史评论,阐述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先哲有言,史论即政论,对吴应箕的史论亦应作如是观。
更加直接论述现实政治的看法,莫过于他的当代史著作。写于崇祯二年的《两朝剥复录》,是对这年三月公布的“钦定逆案”的呼应。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以后,顺应舆论的呼声,开展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运动,崇祯二年三月十九日公布阉党逆案名单,阉党骨干分子按照罪行分为首逆、首逆同谋、交结近侍、交结近侍次等、逆孽军犯、交结近侍又次等、谄附拥戴,分别惩处两百多人。皇帝要求无一漏网,除恶务尽。但是要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谈何容易!魏忠贤遍置死党,盘根错节,参与清查逆案的官僚,本身就与阉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阻力重重。李逊之《崇祯朝记事》说,主持此事的内阁首辅韩爌“持正有余,刚断不足”,具体操作者吏部尚书王永光曾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由他清查逆案,显然有“私庇同党”的嫌疑。吴应箕的《两朝剥复录》揭示天启年间的阉党专政到崇祯初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历史。夏燮《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崇祯二年条写道:“三月,钦定逆案示天下。先生(吴应箕)著《两朝剥复录》叙至南北二京察止。盖二察即逆案之张本也。按:二察皆以除逆案为主。”
写成于崇祯十二年的当代史著作《东林本末》,显然是针对温体仁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以及张至发、薛国观推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有感而发的。他态度鲜明地指出:“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又说:“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小人用“朋党”的帽子打压君子,万历时已经形成风气,到了天启时登峰造极,炮制黑名单《天鉴录》《东林点将录》和《东林党人榜》,请求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反对阉党的正人君子。因此之故,吴应箕说:“近时所角者皆朝臣,角之不胜,至借宦竖(太监)以扑之”;“然则不有东林,其可谓世有士人哉?”所以他要为东林书院正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人品理学遂上千百年未有之盛”。
到了魏忠贤专擅朝政的时候,“东林”二字成了阉党迫害正人君子的一项罪名,“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就是典型的冤案。为了给他们平反昭雪,吴应箕在崇祯十三年写了《熹朝忠节死臣列传》。他在引言中说:“初魏忠贤乱政,首撄祸杖死者万燝也后因汪文言狱,逮死者六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后又因李实诬奏,逮死者七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兵先逮周宗建、缪昌期也。以吏部尚书遣戍遇赦,为逆珰所抑,卒死于戍所者赵南星;以争梃击首功,为逆珰论劾逮死狱中者王之寀,各有传,共十六人”;“诸臣死十有余年矣,余恐后此听闻之言或失其实,则死者有知,谓当世何?”
为东林正名,也就是为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正名,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吴应箕针对当前朝政的弊端而写的一系列策论,旨在为朝廷出谋划策,较之史论更加直接而尖锐地触及时事。刘城《贵池吴应箕传》说:“又见国事日棘,中外大小臣碌碌取充位,无一能办者,既摩切历诋之,遂好奇计画策。”
《楼山堂集》收录了“拟进策”十篇,序言中说明:“崇祯丙子(九年),臣从邸报见天下更民言事者甚众,上皆报闻,至有骤荷进用者。臣窃览其章于天下大计俱有未当也,私以为言者皆负上,又以为天下事非一疏能尽,于是退而拟策十首。”他的策论不同凡响,正如门人刘廷銮所说,“他人揣摩十数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处得之;他人嗫嚅踌躇首鼠而不敢尽者,或乃冲口出之,虽触忌讳、犯势家,而不辞也”。
他的拟进策十条,第一条是最要紧的“持大体”,以张居正的过于操切来反衬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宽大,看起来似乎是“倦勤”,其实是“得体”,知道持大体,所以几十年海内晏如。然后话锋一转,一面表扬当朝皇帝远超励精图治的汉宣帝,一面批评他治国颇为失体。九年来大权独揽,过于操切,反而导致欺罔奸佞丛生,何以故?请看他的分析:
然臣固有虑焉,事无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无是非俱得达陛,使天下皆裹足不至者,奸佞之丛;大臣无所执持,小臣相为朋比者,衰乱之徴也。是故欲惩贪而贪以风之,欲革弊而愈以启之,何也?失体也。
他批评皇帝不善于“别邪正”,结果使得君子日趋孤立:“而其病由于人主不分邪正,复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杂进,于是君子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为小人。”如果能使“力攻朋党”的阴险小人无以售其奸,国家之治理可以计日而待。
此外,诸如谨信任、审言术、励廉耻、重变更、储边才、罢无用、养民财、塞贪源,都有的放矢,针砭时弊,指明改进的方策。
比吴应箕年轻二十四岁的侯方域,为《楼山堂集》写序,特别推崇他对于时势的忧危之言:“当神宗时天下无事,而《楼山集》多忧危之言,何其早见也。迨其后,天狼墉鼠,祸机将发,大臣将相又皆畏罪持禄,不为补救,甚且不惜以身为饵。余则尝见吴子张目奋袂而言之,祸福利害一不少动,盖其素志之定也。”确实,吴应箕本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很自负的,曾说:“文章自韩欧苏没后,几失其传,吾之文足以起而续之。”侯方域是认同的,联系到他以身殉国的结局,感慨系之:“韩欧苏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随于时,亦尝遭贬谪弹射,固未至断颈绝胫以殉之也,而当世见其片言只字,皆爱重之不衰。设以若韩若欧若苏,而且以大义断颈绝胫而死,则当世之爱而重之,后世之凭而吊之者,又何如也?”侯公子写这段话时,吴公早已碧落黄泉,无须阿谀,当是发自肺腑之论。
三、《留都防乱公揭》始末
崇祯元年清查阉党逆案,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向皇帝请求,为惨遭迫害致死的杨涟、魏大中、周顺昌等正人君子平反昭雪。死难诸臣的遗孤纷纷为亡父湔雪冤情,原任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的次子魏学濂的申冤奏疏特别强调,阮大铖、傅应星、傅继教、傅魁之流,务必严惩。他写道:“先臣(魏大中)之嫉奸者既甚,奸人之嫉先臣者亦从此眈眈。而倾危之阮大铖遂兄事忠贤之甥傅应星、傅继教,以固援于内,并率傅魁兄事应星、继教,以植党于外。既夜叩忠贤于涿州,进百官图,旁签王振、刘瑾故事,导之杀人,以肆毒于外。”揭发阮大铖乘魏忠贤前往涿州进香的机会,卖身投靠,进献类似于《东林点将录》的《百官图》,要魏忠贤仿照王振、刘瑾的榜样,杀戮异己分子。倘若说阮大铖之流是谋害杨涟、魏大中诸君子的帮凶,并不为过。然而崇祯二年颁布的钦定逆案名單,阮大铖仅仅以“交结近侍又次等”,定罪为“颂美赞导”,从轻发落,判处削籍而已。到了温体仁当权之时,为阉党翻案的妖风甚嚣尘上,阮大铖蠢蠢欲动,妄图东山再起,成为众矢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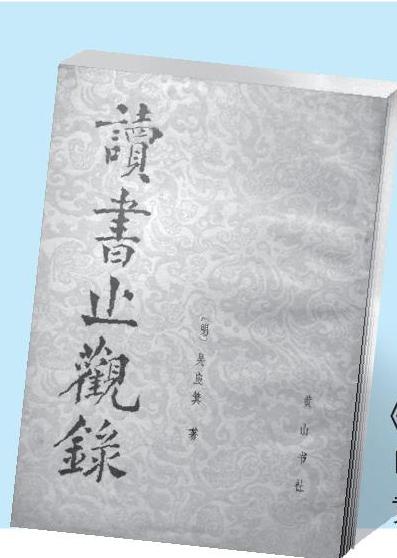
《读书止观录》〔明〕吴应箕著黄山书社 1985 年版
乘崇祯九年金陵乡试之机,吴应箕在南京举行“国门广业之社”的第三次大会,与会的有冒襄(辟疆)、陈贞慧(定生)、顾杲(子方)等人。会后,冒襄在秦淮河桃叶渡寓所,招待天启死难烈士魏大中、左光斗、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黄尊素、李应昇遗孤十三人。魏学濂向社友出示血书与疏稿,血书中提及,魏大中之死与阮大铖有关,与会众人义愤填膺,齐声痛骂阮大铖。冒襄回忆道:“丙子(崇祯九年)子一(学濂)以荫入南雍(南京国子监),怀宁(阮大铖)欲甘心焉。予大开桃叶渡寓馆,挟子一(学濂),大会死事同难诸孤儿……共十三人。陈(定生)则梁长歌,末句有‘独恨杨家少一人,以应山(杨涟)公子不至为恨。观者如堵,子一(学濂)出血书、疏稿及孝经,共展书画淋漓。齐声痛骂怀宁(阮大铖),意阻,楼山(吴应箕)大快。”
夏燮在吴应箕年谱中提及此事:“值大铖方居金陵,欲以新声高会,招徕天下,为夤缘起用地。复社诸君子适睹此疏,公愤填膺,于是始起留都防乱之议。”说得很正确。吴应箕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是在崇祯十一年,留都防乱之议早在崇祯九年的桃叶渡大会已经酝酿了。
崇祯十一年六月,吴应箕东游无锡,住在顾杲家中两月。其间,在顾杲陪同下瞻仰被阉党捣毁的东林书院废墟,感慨系之,吟诗道:
同展道南祠,而伤东林址。
东林何负国,草色已及纪。
不见崔魏时,金碧连云起。
巍巍九千岁,蓬蔂安所倚。
万古此东林,子无忘所始。
七月,陈贞慧(定生)也从宜兴来到顾杲家中,吴、顾、陈三人一起商议防乱公揭之事,吴应箕当即提笔起草《留都防乱公揭》。
崇祯十二年,又逢金陵乡试,吴应箕召集复社成员,正式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在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头的是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遭阉党迫害致死的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阉党逆案的老底—“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钦定逆案公以后,图谋翻案,“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复社诸君子誓与阮大铖不共戴天,公开声明:
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同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锧,轻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臣之必不容于圣世哉!
真是大快人心事。夏燮如此描述当时的盛况:“夏五月,(吴应箕)至金陵,始与归德侯公子方域定交。时四举国门广业之社,凡揭中一百四十余人大半入会中,周仲驭以至焉。于是留都防乱之揭传播南中。大铖与求解于侯公子不得,遂与社中人为水火之仇。”又说:“揭中之执牛耳者,布衣则推先生(吴应箕),荐绅则推仲驭(周镳),贵胄则推定生(陈贞慧),而东林之后推子方(顾杲),忠臣之后推南雷(黄宗羲),日置酒高会,辄集矢怀宁(阮大铖),嬉笑怒骂以为常。”
《留都防乱公揭》刊刻成“大字报”形式的传单,公之于世,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此举并非一帆风顺,有人反对,有人不以为然,签名的人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吴应箕在给朋友的信中议论道:“当刻揭时,即有难之者二,谓揭行则祸至。此无识之言,不足辩矣。又谓如彼者何足揭,我辈小题大做,此似乎有见,而亦非也。”他深刻分析批判阮大铖之流的必要性:“夫法加于人,有时而尽,邪根中于人心,逆气流为风俗,天下之患可胜道哉?使我辈不言,则将来变为从逆世界,必有以钦定者为非,而恨魏忠贤之不复出也。足下以为此可已乎,不可已乎?”在大是大非面前,复社诸君子义无反顾。人们津津乐道的明末四公子明辨是非,投身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他们是:吏部左侍郎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定生),湖广宝庆副使冒起宗之子冒襄(辟疆),湖广巡抚方孔炤之子方以智(密之),户部尚书侯恂之子侯方域(朝宗)。
阮大铖慑于清议的威力,不得已躲进南门外牛首山,暂避锋芒,派遣心腹四处收购《留都防乱公揭》文本,孰料越收越多,传布越广。彷徨无计之时,想到了刚刚来到南京的侯方域。阮大铖与侯恂有年谊,算是侯公子的父执辈,试图利用这一层人脉来缓和与复社的关系,派亲信王将军代他出面示好,用重金撮合侯公子与秦淮美女李香君的好事。李香君大义凛然,敦促侯公子抵制阮大铖的图谋。侯方域为李香君的气节所感动,拒绝了阮大铖的收买,写了一篇《李姬传》,收在《壮悔堂集》中,追记此事:
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美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

《壮悔堂集》(全三册)〔明〕侯方域撰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姬曰:“王将军贫,非能结客者,公子曷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言。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陈贞慧),其人有高谊;闻吴君(应箕)尤铮铮,今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因怏怏辞去,不复通。
夏燮《忠节次尾先生年谱》说,王将军代阮大铖做说客一事,成为孔尚任《桃花扇》“却奁”一折的蓝本,所不同的是做了文学性虚构—王将军变成了杨文骢。他认为可以理解:“传奇之体,装点排场,巧配脚色,义亦无嫌”。
由“却奁”中的一段对白和唱词,可以看到侯方域的犹豫和李香君的坚贞。请看《桃花扇》的原文:
杨文骢:“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阮大铖)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辩。每日向天大哭,说道:‘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所以今日谆谆纳交。”
侯方域:“原来如此,俺看圆海(阮大铖)情词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
杨文骢:“果然如此,吾党之幸也。”
李香君怒道:“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随即唱道:“不思想,把话儿轻易讲。要与他消释灾殃,要与他消释灾殃,也提防旁人短长。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侯方域唱道:“平康巷,她能将名节讲;偏是咱学校朝堂,偏是咱学校朝堂,混贤奸不问青黄。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只为这点义气,我若依附奸邪,那时群起来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
说“却奁”以史事为蓝本,并不错,错的是时间弄颠倒了。这一点,夏燮已经指出:“惟以侯生纳李姬,大铖办装,系之癸未(崇祯十六年)三月,则不然也。”各种史料表明,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二年,绝不可能发生在崇祯十六年。
《桃花扇》中“偵戏”一折,也有蓝本,巧的是,时间也弄错了—系之癸未三月,应该是崇祯十五年七月。汪有典《吴副榜传》根据冒襄的回忆,写道:“壬午(崇祯十五年),予(冒襄)又同楼山(吴应箕)、子一(顾杲)、李子建(嘉兴),看怀宁(阮大铖)《燕子笺》于鱼仲(刘履丁)河房。(楼山)大骂怀宁竟夜,多侧目楼山者。惟予知楼山五岳在胸,触目骇心,事与境忤,潦倒拂逆,奋袖激昂,或戟髯大噱,卧邻女旁,挝鼓骂坐,皆三年后死事张本也。”夏燮所写年谱,提及此事,考证道:“按:此见冒序,即《桃花扇》‘侦戏一剧之所本,其误与‘却奁同。”但是夏燮没有注意到,“侦戏”一折中,看戏的只提到宜兴陈定生、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遗漏了大骂阮大铖的主角吴应箕。不过,剧本中骂阮大铖的话倒有点像吴应箕的口气:
“为何投崔魏,自摧残。”
“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也不过仗人势,狗一般。”
四、“半世文章百世人”
崇祯十五年八月,吴应箕第九次参加金陵乡试,这次没有落空,中了副榜。所谓副榜,是科举考试的附加榜示,又称为备榜,并不授予举人身份,不能与举人同赴京城参加会试;如果下次乡试中举,方可参加会试。据说,此次副榜有一百余人,似乎是考官大发慈悲,给屡次落第的士子们一点安慰。这对于才高八斗,自诩韩愈、欧阳修、苏轼再世的吴应箕而言,简直是另一种形式的羞辱,即使退一步想,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人们对他的称呼,从吴秀才一变而为吴副榜,仅此而已。
然而报国之心并没有丝毫减退。
崇祯十七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建立,福王朱由崧登上帝位,实权掌握在马士英手中,阮大铖报仇的机会来了。
却说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出,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得力于复社名士张溥、吴昌时的助推,又得到冯铨、侯恂和阮大铖的资金赞助,多方打点。事成之后,阮大铖向周延儒讨官,周延儒回应道,你的名声不佳,碍难照办,不妨推荐你的代理人如何。阮大铖举荐自己的门生马士英,马随即出任兵部右侍郎、凤阳总督。计六奇对马士英的评语是“手长智短,耳软眼瞎”,这八个字可谓入木三分,此人大权在握,丝毫没有忧患意识,成天考虑党同伐异,结党营私,为了报答房师阮大铖的举荐之恩,起用他出任兵部右侍郎。
一旦权在手,阮大铖便谋划打击报复复社诸君子,编造《蝗蝻录》,将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一百四十多人,全部编入黑名单,仿照当年的《东林点将录》《天鉴录》,如法炮制。周镳、陈贞慧、黄宗羲被捕入狱,吴应箕得到消息,逃亡避难。他在《党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蝗蝻录》政治报复的实质:
天启间有所谓《东林点将录》及《天鉴录》,皆逆党藉朝臣之公忠清执者,号为党人,以肆其一网之术者也……于是前遗党未尽者则益恐,又作《蝗蝻录》一书……予闻其所籍姓名大要,谓“蝗”者多前二录之遗老,及今缙绅素有称之人;而“蝻”则皆未通籍之名流,以其为物害多而种繁,是即向者一网之故智,而但欲下锢草野,则意尤恶矣。
陈贞慧《山阳录》描绘阮大铖杀气腾腾的架势:“将尽杀天下,酬所不快,下周镳、雷演祚于狱发起端。时语所亲曰:‘吾五六年来,三尺童子见我姓名,辄詈而唾者非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切齿者十人列于上,曰:此拥戴潞藩以图不逞者。又造为十八罗汉、七十二金刚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绍徽《点将录》故事,一网杀之。”第一个被处死的是周镳,正当阮大铖准备大开杀戒时,迫于内外交困的马士英立即叫停,释放了被捕入狱者。
由于吴应箕起草《留都防乱公揭》,阮大铖恨之入骨,故意放出风声,如果向他道歉致谢,可以不再追究。吴应箕岂肯向阮胡子屈膝,对侯方域说:“今有欲吾谢大铖,可转祸为福者,岂不为范滂所笑哉!”真是掷地有聲,铮铮铁汉!范滂是东汉清流名士,不畏强暴,伸张正义,遭受“党锢之祸”;出狱还乡,南阳士大夫自发出城迎接,车辆达几千辆之多,显然把他看作衣锦荣归的英雄。吴应箕以范滂为榜样,绝不玷污清流名士的英名。
朝廷要迫害他,当朝廷处境危险时,他却不计前嫌,挺身而出。
崇祯皇帝朱由检死后,他的太子下落,成为明朝遗老遗少关注的焦点,关系到明朝国祚的延续。朱由崧和马士英出于自身权益考虑,讳莫如深。弘光元年(1645)三月,太子抵达南京,朱由崧和马士英极力扬言太子是假冒的。此举引起南明封疆大吏的强烈反弹,左良玉以此为借口,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从武昌发兵东下,声称“本藩奉太子密诏率师救援”,声讨马士英八大罪状。马士英一意孤行,把左良玉当作头号敌人,集中全部兵力去对付左良玉,竟然在朝堂之上大喊:“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
在此紧要关头,吴应箕写信给长江沿线四省总督袁继咸,希望他以朝廷大局为重,在九江阻挡左良玉:“今因左兵东下,南中一日数惊,而又实无一备,公卿虽多,事权不一,且大度者实少。”希望他从社稷起见,本着春秋出疆之义,力挽狂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江北的清军如入无人之境,逼近南京。五月初七日,朱由崧在清议堂召开御前会议,南京政府的掌权者马士英、王铎、蔡弈琛、钱谦益等十六人,竟然主张投降,美其名曰“纳款于清”“降志辱身”。南明小朝廷的都城竟然如此这般不设防不抵抗,等待清军来接收。朱由崧、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率先逃跑,五月十五日,清朝豫王多铎率领清军进入南京,弘光小朝廷分崩离析。
国破山河在,各地义勇奋起抗击清军。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金声在徽州绩溪起兵抗清,吴应箕在池州发兵响应。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担任官职—南明唐王政权授予的池州府推官监纪军事,在家乡招集义勇攻打池州府城,后又攻打建德县、东流县。
金声兵败被杀,形势岌岌可危。十月间,吴应箕写信给家族父老:“夫尽忠而妻死节,夫何憾乎?但恐乡里不安耳。死者为我收敛,生者烦为我安顿,我此身已置之度外矣。”这年深冬,他在泥湾山中兵败被俘,死于贵池县之石灰冲,时年五十二岁。
他的绝命词已经散佚,只留下一句:“半世文章百世人”。
这一年,他的长子孟坚十一岁,次子穉圭十岁。多年以后,孟坚带领儿子整理编校《楼山堂集》和《楼山堂遗文》,使得吴应箕的声音流传于世。
改朝换代之后,吴应箕的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侯方域的祭文写道:“呜呼,次尾死矣,余早决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时时见吾次尾之面冷而苍,髯怒以张,言如风发,气夺电光,坐于我上,立于我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