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在当代剧场的探索
2020-06-04文景彻
文景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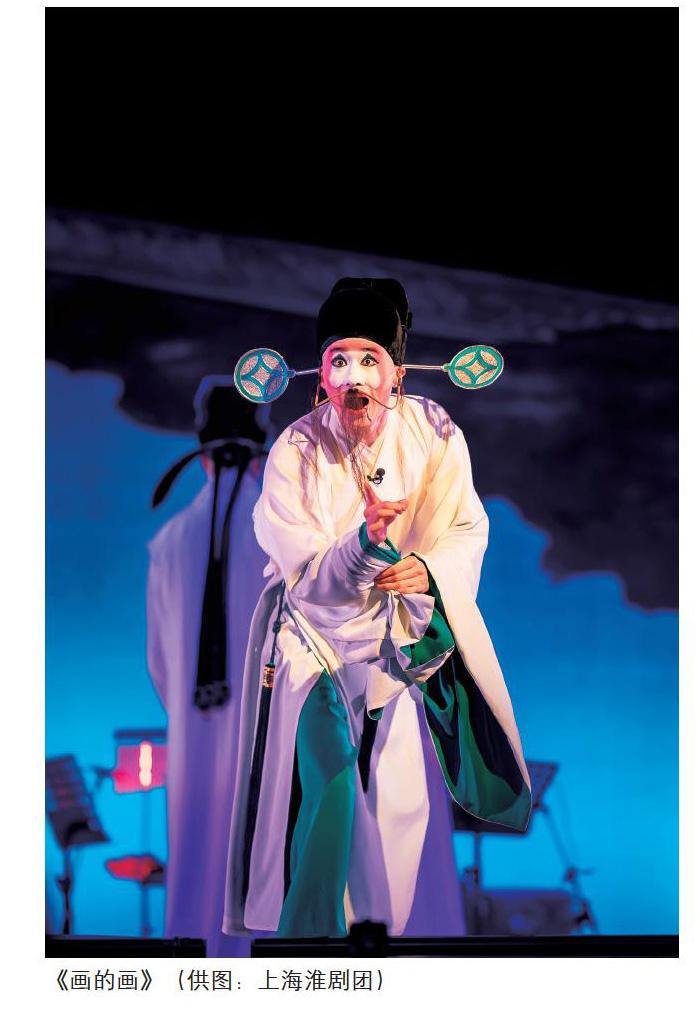
7天9个剧种9台戏,从原创题材创作、西方戏剧改编到传统剧目新编,相比前几届,第五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暨首届中国(上海)小剧场戏曲展演在剧种数量和剧目选题的多样性上都有扩展,然而纵观本次展演,同一展示平台的亮相,也暴露各剧目在艺术追求、审美风格等方面呈现出的缺陷和短板,试探这一现象的根由,或与创作者们对小剧场戏曲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有关。
小而新,小剧场戏曲的生存之道
小剧场之小,字面是指相较于常规大剧院,在演出空间范畴上的“小”、时间上的“短”,深层则是创作理念和方式的“新”。镜框式舞台在中国的兴起,扩大了剧场容纳观众的数量,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戏曲三面舞台的演剧模式,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型现代化剧场的投建,伴随着诸如国家艺术基金等资金扶持项目的推动,使得动辄几百万投入的大型史诗戏曲屡见不鲜,为了与高科技的“声光电”和磅礴大气的作曲配乐等舞台元素相匹配,舞台上的群演场面依次铺排开来,并且愈演愈烈,似乎没有几场大场面,就没办法彰显一家院团之雄厚实力。这样的状况势必导致了创作上的局限:与其略做创新就遭到质疑、否定,倒不如稳扎稳打,不越雷池来的实际,毕竟大制作的修改甚至推翻重来需要更多的财力和精力。长此以往戏曲也就如同大象的屁股一般,推也推不动了。
相比大剧场大制作,小剧场体制上的“小”和理念上的“新”,有着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使它比传统剧场在探索和创新上更加有效。自诞生以来,它高擎实验和探索的大旗,在叙述结构、主题立意、观演形式、审美表达等方面积极寻求着传统戏曲在当下生存发展新出路的使命。然而,即便如此,那么是否所有的小剧场作品都自觉以创新的信念在创作呢?分析此次小剧场戏剧节的9部参演作品,我们却发现:诶,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其中高甲戏《阿搭嫂》、绍剧《灿烂八戒》是由大剧场剧目经删减、选编而成,即这两部作品并非为小剧场专属定制。因此为了适应小剧场空间的容量,同时又要在100分钟之内完成演出,两部戏在不同程度上对文本和舞美设计进行裁切,重组,从演出效果来看,抛开削足适履所造成的文本不连贯、舞美不达意等不足之外,小剧场版本与大剧场版本并无特别突出之处,甚至不如大剧场版看的、听的过瘾,那么费心制作小剧场版意义何在?《故人心》和《四美离歌》都以“多剧种”应工,《故人心》根据川剧折子戏《阴阳河》、昆曲《牡丹亭·冥判》、《牡丹亭·魂游》、越剧《情探·行路》改编而来;《四美离歌》以中国四大美女故事背景为素材,用京剧、昆韵、滇剧、花灯四个剧种演绎了四段相对独立的故事。不管是“一赶三”还是“赶四”, 明眼人一瞧,咳,这不是折子戏专场嘛!论戏,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论功,不管扁担功、长水袖,也还是传统的技巧套路;论戏与戏之间的勾连,串场人不约而同充当了晚会主持人风格的报幕,除了突出主要演员驾驭多剧种的能力和自身技巧的娴熟外,这样的小剧场作品并无新意。
剩下的几部,越劇《宴祭》改编自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在将故事越剧化的过程中,青年主创团队力图在表演和舞美意象的运用上有所突破;实验京剧《回身》,在不到60分钟的时间内以一个京剧演员独角戏的形式,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戏中戏《雅观楼》中的李存孝、恩师小王桂卿交叉演绎,打造了一部“自传体”小剧场作品;京剧《赤与敖》以《三王墓》和《铸剑》为底本,在对义、勇、信三个主题进行升华的过程中,以蒙太奇的手法对文本进行解构和重新结构;昆剧《桃花人面》根据明代孟称舜杂剧《桃花人面》改编,因地制宜,根据长江剧场红匣子非常规观演区的划分和三面多媒体屏幕的条件,探索了戏曲以270度T台演区交互观演体验作为核心演出的样式;黄梅戏《薛郎归》脱胎于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的故事,是当代戏曲人对王宝钏这一女性角色的再度解读,展现了当下女性意识的哲理思辨。可以说,这几部戏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了“新”元素,是“小剧场戏曲”作品,但就舞台呈现来看却不让人十分满意,下文就《宴祭》《赤与敖》《桃花人面》《薛郎归》四部重点来谈。
越剧《宴祭》:“满”招损,“简”受益
小剧场越剧《宴祭》从《莎乐美》中汲取创作灵感后,对故事进行了大刀破斧的中国化改编:重建故事背景、剔除宗教成分、再塑莎乐美——“朱砂痣”变成了“白月光”,一个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其实这样的文本改编模式在越剧中并不少见,在此前提下,该剧主创将目光锁定对舞美意象和表演的创新。作为与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和审美心理一脉相承的演剧艺术,戏曲在含蓄、典雅中追求着诗化的神韵和意境,反映在舞台美术方面,从一桌二椅的多义表达,到越剧开创的写实布景,再到如今极简写意风的回归,尽管外在不断变形,但内核始终秉承着中华美学的基本原则,在虚实结合中寻求“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以景诉情、以情塑人”的绝妙境界。因此,在创作小剧场戏曲时,因为空间的局限创作者会更偏重空、简,那是因为空灵、简约的舞台环境对突出强烈、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演员表演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有着很好的辅助作用。
然而,在《宴祭》的演出过程中,观众看到的却是天幕满绘的唐风壁画、自由组合的高低平台、垂直而下的朱漆木柱、团扇、月亮、水花,所有的视觉元素松散堆叠在小小的舞台之上,让人不由感叹:嚯哟,这部戏真是满姑娘的荷包,花样也太多了吧!花样多,本身并不是贬义,但花样是否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派上用处才是关键所在。彼得·布鲁克曾提出,一台演出在考虑要不要增加布景元素时,首要确定的是这些增加的成分是不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能充分发挥功效。对标《宴祭》,场面宏大、色彩瑰丽的天幕,原本应为烘托戏剧氛围、制造舞台幻觉所用,但在实际演出中,它不仅没能依照剧情发展,和灯光进行有效配合以营造出摇曳生姿的幻灭感,且因画面过“满”加剧了小剧场的促狭。平台或四角分立做宫殿内景、或框起三面呈狱前空地、或做一字排开拼成浮桥、道路的组合,在不同场次中它担任着空间划分的重任,创意是好的,但是高高低低的阶梯对演员造成了显著的障碍:为防止踩空、绊倒,她们总是不经意的看脚下,遗憾的是低头间人物已然出了戏。此外,平台和从舞台上方垂直而下的木柱以上下夹击的形式压缩了小剧场的演区范围,想要在这样繁复、逼仄的空间中有所发挥,只能代演员说一句“我太难了”!团扇、月亮和女主舞蹈时所溅起的水等意象,如昙花一现,在观众还没咂摸出滋味前早已消失。其实对于这部戏的文本来说,已经超出了小剧场所能承受的容量,在导演二度的过程中,是否能考虑通过相对简约的形式进行平衡,我想,做减法或可一试。
在表演方面,小剧场戏曲因为观演距离的缩小要求演员更精致、更细腻、更有分寸感;同时距离的缩小也造就了观众们放大镜一样的直接观感,这使得创作者如果想突破戏曲程式在表演上有突破,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尽管相较京昆等剧种,越剧在程式表演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自由不代表没有界限,自由应是在保持剧种本体特有表演风格的基础上进行尝试。反观《宴祭》,导演为刻意树立风格,为剧中人物精心设计了仪式感十足的台步动作,即以慢动作的方式夸大正常戏曲台步的每个环节,在分解步骤般的抬腿、停顿、落地之中,不经意打乱了演员表演的心理节奏,破坏了观众的剧情代入感。
京剧《赤与敖》:叙事结构的创新与问题
打破常规的叙述结构,以倒叙、插叙等形式演绎故事是小剧场戏曲探索的形式之一,小剧场京剧作品《赤与敖》即是此次展演中鲜明的一例。
《赤与敖》在进行符合戏曲舞台的改编中,编剧采取了原故事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进行叙述,从第一场设置悬念到后几场冲突迭起引人入胜,文本相较其他几部参演剧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并且在继承原作精神的基础上,编剧还赋予了剧本新的人文内涵。
但可惜的是在二度创作上导演选择了对结构的重新铺排。早在上世纪20年代,戏剧大师梅耶荷德在执导《森林》一剧时,为改变该剧结构不甚理想的弊病,以电影蒙太奇的创作方法将情节切割成若干单元,并将这些单元重新调整次序后再组合排列,结果相较之前,剧作产生明显的提高:喜剧性与正剧性的场面交替出现,单调乏味被取代,对比鲜明的场次安排使演出极富跃动感,在调剂冷热场之外又将核心人物和场次重点突出。随着相关译作的普及,梅式戏剧电影化的叙事方式逐渐被更多中国戏曲人所熟知并采用,小剧场开山之作《马前泼水》即运用切割、倒叙、闪回的手段在朱买臣、崔氏夫妇二人的回忆中上演了婚姻生活的冲突与反思。
回到我们所看到的《赤与敖》,在对文本进行切割、重组时,导演犯了几个忌讳。第一,对情节的切割过于碎片化,原本简明顺畅的剧情,因单元划分过多出现了故事讲不清楚的问题。第二,在对这些剧情单元进行拼装时过于随意。第三,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片段,如王杀干将,本是通过莫邪之口讲出来的,但在《赤与敖》中导演却将这一事件搬上舞台敷演,甚至相同的事件出现了两次!第四,重点情节的忽略,“铸剑”的故事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两段,一段是敖以赤项上人头和雌剑为信,答应代赤复仇,赤敢相信敖并把头交给他,随后敖扛着赤的头且行且歌,这段戏如果正面演绎震撼力十足,但导演将它处理变成了倒叙,敖出现在王面前时已拎着赤的头,当结局已成定局舞台感染力大大削弱;第二段是三颗头顱在沸鼎中的撕咬和挣扎,诚然在戏曲舞台呈现这样的情景很难,但小剧场实验、先锋的特性不就是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难题吗?不管是用象征的办法,还是采取更加写意的手法,找到一种合适的体现方式,这段戏绝对可以出彩,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只是让三人的躯壳和魂魄脱分离出来了,以站立演唱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样的处理不免让人怀疑导演的避重就轻。
尽管小剧场戏曲是最先锋的,但也必定是最传统的,小剧场作为载体,形式的创新一定要立足戏曲的本体,应做加分项,应从实际出发,不能单纯追求形式上的变化而乱用形式,弄巧成拙。
黄梅戏《薛郎归》、昆剧《桃花人面》:找准剧目定位,彰显剧种风格
第四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上,由《烂柯山》改编而成的黄梅戏小剧场作品《玉天仙》一炮而红,这种对传统剧目经典人物进行再度解读、传达当代理念的创作模式在小剧场中也经常见到。此次,《玉天仙》的创作团队乘胜追击,又带了了第二部作品《薛郎归》,但遗憾的是这部戏并未成功。
《薛郎归》归脱胎于传统京剧剧目《红鬃烈马》,以王宝钏苦守寒窑的故事为主线,用一句“十八年前荣华富贵你不就有了吗?”对剧中人和当代观众发出了灵魂的拷问。作为《玉天仙》的姊妹剧,本以为这部作品也将在完整的剧情中促使观众生发思考,没想到该剧却是对王宝钏、薛平贵爱情故事的情景再现,并且还是没讲清楚具体情节的缩略版再现——从彩楼配到三击掌、再到别窑从军、大登殿,剧中情节点到为止,大段的重复唱词在剧中反复出现,拉杂单调。说书人的频繁出现造成了人为的间离效果,过多的打断了剧情。用可移动的白纸墙面上营造剪影效果本是好创意,但王父喷血等桥段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纯天然无污染”“骨感美”“因为爱情”“请唱黄梅戏”“没钱买道具”等不甚高级的笑料扎堆出现,即便黄梅戏较为通俗直白,但闹剧般的风格对此剧的品格还是有着不小的影响。
相比之下,同样改编自古典戏剧作品的昆剧《桃花人面》则如同一首细腻抒情的散文诗,较好地发挥了昆曲的诗意特性。一棵桃花树的装置从空中吊下,四面环绕可升降的投影纱幕、T型舞台,在小剧场的空间里给了演员足够的“留白”,使得昆曲的身段程式配合唱词刚好能有发挥的空间;昆曲歌舞的抒情性又恰好能抒发人物内心思想和情感,将精神层面的情绪以歌舞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美中不足,浸入式的演出因观演空间过于接近,观众和演员都曝露在灯光之下,创作者没能设计出适合的场景和互动,身临其境的浸入感变成了略显尴尬的侵入感,折损了原剧的诗意。
回溯戏曲艺术的发展历程,这一综合艺术向来不是凝固在舞台上一成不变的,从宋元南戏《张协状元》中以人做门板到开门、关门等程式的出现,从跨竹马以表现骑马的状态到马鞭的自由运用,戏曲在流变过程中不断的革新与进步,正是其永葆活力的根源所在。因此,小剧场戏曲被赋予了重望,但是想“玩儿”好小剧场,想探索、想实验、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对于年轻的戏曲人来说并不那么容易。小剧场是试验场,但不是漫无目的的求索,不是挑战观众对创新的支持和宽容,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小剧场戏曲节的主办方,我想都应自觉地传承和保护传统之美,同时再以开拓精神去探索当代戏曲艺术的多种可能性。
作者 独立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