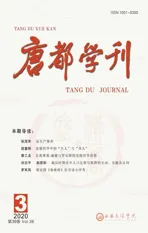张载哲学中的“大人”与“圣人”
2020-06-03段重阳
段重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如何成就圣人”是理学家的核心议题,而横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奠定了这一议题的论说框架。《横渠先生行状》说道:“学者有问,(横渠)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1]383在这里,通过“知礼成性”而“变化气质”似乎构成了通往“圣人”的道路,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在横渠那里,“大人”与“圣人”有着明显的区别,“成就圣人”的道路并不意味着一种工夫的同质进行。横渠对这一区别的论述主要是依据对《易》的注解而展开的。《宋史·张载传》言其“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1]386,对《易》的注解构成了横渠展开自身理论系统的重要部分。《横渠易说》便是这样的作品,而且其中的关键话语也被收入《正蒙》中。因而,通过对《横渠易说》中对“大人”与“圣人”的区别论述的分析,以及这种区分在后来的理学思想中的表现,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领会张载的哲学以及理学的复杂面向。
一
横渠对“大人”与“圣人”的区别论述主要来自于对乾卦的注解。乾卦爻辞、《象》和《文言》中频繁出现的“大人”为横渠的注解提供了可发挥的文本,而《文言》中出现的“圣人”则提供了可资对比的论述。横渠对“大人”与“圣人”的区别有一个总括性的论述:
大人成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圣犹天也,故不可阶而升。圣人之教,未尝以性化责人,若大人则学可至也。[1] 76
“学可至”与“不可阶而升”构成了“大人”与“圣人”的工夫区别,前者可以通过“知礼”而“成性”以达之,而后者则要求“化”。横渠通过对乾卦爻辞的发挥具体阐发了这种区别。
乾卦初九爻辞曰:“潜龙在渊”,横渠解曰:“孔子喜弟子之不仕,盖为德未成则不可以仕,是行而未成者也。故潜勿用,龙德而未显者也”[1]72,“颜子未成性,是为潜龙,亦未肯止于见龙,盖以其德其时则须当潜”[1]75,此时“学”之刚始,尚未成就“大人”。乾卦九二爻辞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横渠解曰:“庸言庸行,盖天下经德达道,大人之德施于是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著矣。然非穷变化之神以时措之宜,则或陷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此颜子所以求龙德而正中,乾乾进德,思处其极,未敢以方体之常安吾止也。”[1]73横渠认为九二之时,大人之德虽然普施,但是此时大人所行之“礼”可能会陷入一种执定化的“方体”之中,即不能够有“时措之宜”而“陷于非礼”。横渠论礼曰:“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者皆是也。”[1]264处于九二的学者尚未通达礼之根本,而只是掌握了仅供施行于一时一地之礼,故而有所“方体”。在横渠看来,对“时措之宜”的通达要求较高,“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观其会通以行典礼,此则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1]264,九二之学者仍处于“知礼”之路程中而未能“精义入神”而有所会通。乾卦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爻辞曰:“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横渠解曰:“乾三四,位过中重刚,时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济之,虽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趋变化,内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艰于见德者,时不得舍也。”[1]74处于九三、四的学者可能会处于危难之中,因此需要不断忠信立德、修辞立诚之工夫。九五爻辞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象》曰: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横渠解曰:“乾之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跻圣者尔。若夫受命首出,则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1]71九五便是圣人之位而有天德流行,“九五言上治者,通言乎天之德,圣人之性,舍曰‘君’而谓之‘天’。见大人德与位之皆造也”[1]71。不言君而言天,以此圣人之位是学者自造而得,非世袭之君位,此位只有通乎天之德者可得之。“受命首出”“所性不存”者,取自《孟子·尽心上》:“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言圣人受命而化成天下,气质之性不彰而天地之性存焉,“知礼成性”之事毕矣。
这里似乎有着一个从初九到九五的渐修过程,但是横渠明确否认了这点。横渠说:“若二与三皆大人之事,非谓四胜于三,三胜于二,五又胜于四,如此则是圣可阶也。三四与二,皆言所遇之时。”[1]76也就是说,九二、三、四只是大人所遇之时的区别,并不是大人的修行过程。如果说这里面有着修行过程的话,那就是初九和九二、三、四的区别,“乾初以其在初处下,况圣修而未成者可也”,“况”取描述之意,即乾卦初九可以用来描述修行未成之情况,而九二所言“利见大人”便已经是大人之事,从初九到九二就是横渠说的“大人之事,修而可至”[1]77。倘若在这之后的九三、四相对于九二是一个上升的过程的话,那就意味着九五相对于九四也是同质的上升过程,这样就会是“圣可阶”,这在横渠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横渠认为九五是不论“时”的,“九五则是圣人极致处,不论时也。飞龙在天,况圣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阶而升也”[1]76。另外,倘若九五是相对于九四同质的上升,那么就意味着上九的“亢龙有悔”也是用来描述圣人的,这就会导致不能够接受的结论。横渠针对上九曰:“言君位则《易》有极之理,圣人之分则安有过亢……上以居极位画为亢,圣人则何亢之有”[1]76,故上九不言圣人,则上九并不是九五之转进,故初九以至上九便不是渐修之过程,九五之“大人”亦不同于九二、三、四之“大人”,九五之“大人造也”其实是指“圣人造也”。
那么,大人与圣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前文提到,是否“修而可至”是这一区别的特征。这一区别的依据在于“化”:“以理计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则无修,故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待己实到穷神知化,是德之极盛处也。”[1]76-77“穷神知化”构成了圣人的特质,即“化至圣人”:
大与圣难于分别,大以上之事,如禹、稷、皋陶辈犹未必能知,然须当皆谓之圣人,盖为所以接人者与圣同,但己自知不足,不肯自以为圣。如禹之德,斯可谓之大矣,其心以天下为己任,规模如此;又克己若禹,则与圣人直无间别,孔子亦谓“禹于吾无间然矣”,久则须至尧舜。有人于此,敦厚君子,无少异圣人之言行,然其心与真仲尼须自觉有殊,在他人则安能分别!当时至有以子贡为贤于仲尼者,惟子贡则自知之。人能以大为心,常以圣人之规模为己任,久于其道,则须化而至圣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即是天也。[1] 77
这一段是理解“大人”和“圣人”区别的关键。横渠指出“大人”与“圣人”很难区别,然后给出了几个例子来说明“大人”与“圣人”的区别。从这些例子看来,“大人”与“圣人”的区别在于“心化”,并且,此“心化”似乎只能“自知之”。横渠首先提到的是禹、稷、皋陶与尧、舜的区别。在通常的圣人系谱中,禹毫无疑问是被列入的,这也就是横渠说的“所以接人者与圣同”,“接人者”即后文之“言行”,即禹与圣人之言行“无少异”。在《正蒙·作者》中,横渠提到,“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1]37,也就是说,倘若从功业来看,禹与尧、舜似乎并没有区别(此外,孔子之圣也不在于“作”),因此,大人之禹和尧、舜之圣人的区别须落脚于“心”之“德”。故而横渠称赞禹之心以天下为己任,久则至于尧、舜。换言之,从大人到圣人的变化,不是外在的功业的增加,也不是阶梯式的上升,而是其心经过长久的工夫后的自然而化,此即“人能以大为心,常以圣人之规模为己任,久于其道,则须化而至圣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够有对此心的助长工夫,即不能够把捉此心,“故尝谓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盖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则不可加功,加功则是助长也,要在乎仁熟而已”[1]77,大人到圣人的转变也就是“有为之修”转变为“无为而化”,如此才是易道,才能够有圣人作《易》之事。并且,这种转变不是于“大人之事”之外别有工夫,而是“熟而化之”,此即 “如此则是全与天地一体,然不过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1]77,正如王夫之所言:“盖圣人之德,非于大人之外别有神变不测之道,但诚无不至,用以神而不用以迹,居德熟而危疑不易其心,及其至也,物自顺之而圣德成矣。”[2]254因而,对“神”“化”的理解就意味着对“圣人”之为“圣人”的深层领会。
二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神无方,易无体,大且一而已矣。”[1]15这是横渠在《正蒙·神化》开篇就对“神化”做出的总括性说明,然而,如何理解这句话却是横渠诠释史上的争议焦点。这种争议主要体现为两种诠释方向:其一是将“神”与“太虚”理解为存在学(Ontology)意义上的本体宇宙论概念,这一诠释方向主要有牟宗三、丁为祥等;其二是从气化的角度来理解“神”“太虚”等概念,这一诠释方向主要有王夫之、杨立华等。具体分析其中的曲折并不是本文的任务,尽管本文主要采取第二种诠释方向(1)第一种诠释方向似乎陷入三种前提或者成见之中,其一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或者存在学(Ontology)的成见;其二是佛教有所谓本体论的成见;其三是伊川朱子之学的成见。从张载自身的文本出发,我们很难做出第一种诠释的种种理解,除非已经陷入某种理论前设之中。。而对这句话的理解核心就在于对“体”和“用”的理解。王夫之对这句话的解释为:

尽管我们不能把“体”和“用”理解为存在学意义上的“本体”和“现象”,但是“体”仍然是对某种根源性的寻求,“体者所以用,用者即用其体”就表明了这一点。“体”是使得“用”得以可能的,而“用”就是“体”自身的作用,这一点在佛教体—相—用的表述中也有体现(2)参见陈坚《不是“体用”,而是“体相用”——中国佛教中的“体用”论再思》,载于《佛学研究》2006年。。与佛教以般若佛性为“体”不同,横渠在这里以气(太虚)为“体”,此“体”首先意指“实在”的“形体”,即“气,其所有之实也”。“气”保证了存在者整体的实在性,从而拒斥了佛教缘起性空之论,而横渠哲学的“意义在于天道观上实现哲学视野的转化:以如何存在的问题取代了是否存在的问题”[3],“神”和“化”就是对“如何存在”的说明,即“神,气之神;化,气之化也”。“神”意指着气自身所具健顺之性而能够聚散万物,“化”即此气化流行之万物聚散,故“神”为气之体,言其能使之“化”,此即所谓“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1]16,“化”为气之用,言气之阴阳摩荡而万物生,此即所谓“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1]16。概而言之,“化是对宇宙间氤氲不息的生灭过程的实然把握,而神则是其内在根据”,“神是天下所有变化的内在根源”[4]。冯从吾评价横渠之学曰:“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5]“神化”者,言天也,此即“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1]17。“穷神化”者,人也,此即“故大而位天德,然后能穷神知化”[1]16,故“大人”之为“圣人”,就在于“一天人”。
而“一天人”的关键在于“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的转变:“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1]21,“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23。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横渠的“性”。横渠有一个著名的判定:“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1]9对 “虚”“气”的理解历来争议纷纷,在部分著作中学者倾向把“虚”理解为一种存在学意义上的“本体”(3)比如牟宗三《心性与性体》中的“太虚神体”,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中的“太虚本体”,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解释如果不是受到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那么也是将朱子学中作为“所以然者”的“性”代入到了横渠思想中。在《正蒙·太和》中,横渠针对“性”说道:“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1]7,在这里对“性”的描述指向的就是“天地之性”,意指着太虚之气可以因阴阳相感而聚散万物的能力,“虚”表明了这一气化过程之聚散无形,此即“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1]62。而“合虚与气”之“气”则指向了“有形之气”,即所谓“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1]7。也就是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之“虚”意指着“天地之性”,“气”意指着“气质之性”,“性”意指着“人之性”。而“一天人”之过程,就在于返“虚”,此即“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1]274,“虚心”亦即“心化”。换而言之,当人之成形之后,“变化气质”意味着“心”的转换,即由“见闻之知”转变为“德性所知”,其关键就在于“体天下之物”而不囿于有方体之知,此即“由象识心,徇象丧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谓之心可乎”[1]24,而所需之工夫,就在于“四毋”:“毋四者则心虚,虚者,止善之本也”[1]307。
我们可以从上节的九二来说明这一过程。九二主要涉及的是“大人知礼”之事。在《经学理窟·礼乐》中,横渠有一段话点出了“持性”与“成性”的区别:
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礼即天地之德也,如颜子者,方勉勉于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礼非止着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原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1] 264
在横渠看来,“礼”乃是出于“天地之德”亦即“天地之性”,因而“持礼”即“持性”,由此可以反“本”,即“太虚”。出于“天地之性”的“礼”并不是自然而有的,而是由圣人所制作,故“礼之原在(圣人之)心”。圣人制礼的关键就是“时措之宜”,故而“亦有无体之礼”,即不固于方体,这便是“大人”与“圣人”的区别。在横渠看来,从“大人”到“圣人”的转变就是“勉勉以成性”的过程。对“圣人”的追求必须从“持礼”开始,此即“知及之而不以礼性之,非己有也”[1]191。而 “知礼成性”就意味着向“天地之性”的复归:“知极其高,故效天;礼着实处,故法地。人必礼以立,失礼则孰为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1]192在这里,“知礼”的“大人”“法地”工夫构成了通往“圣人”必由之路,此即所谓“大以成性”:“所以成性则谓之圣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节而成性,若圣人则于大以成性”[1]78,“然清和犹是性之一端,不得全正,不若知礼以成性,成性即道义从此出”[1]192。换而言之,横渠认为成就圣人必须从“知礼”的“思勉”“勉勉”工夫做起,久之熟后可以“成性”而圣,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摆脱“礼”的“方体”,领会作为“无体之礼”的“天地之德”,从而由“持礼”之“大人”成就“制礼”之“圣人”,亦即“心化”。然而,这里有着一种工夫上的质的跳跃。横渠有言:“穷神知化乃养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1]216-217,“自然”和“思勉”构成了“圣人”与“大人”工夫的区别(或许圣人之“自然”无所谓工夫),而这种区别也贯穿了整个理学史。
三
横渠和二程关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争论就是“自然”与“思勉”之别的一个例证:
二程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只穷理便是至于命。”子厚谓:“亦是失于太快,此义尽有次序。须是穷理,便能尽得己之性,则推类又尽人之性;既尽得人之性,须是并万物之性一齐尽得,如此然后至于天道也。其间煞有事,岂有当下理会了?学者须是穷理为先,如此则方有学。今言知命与至于命,尽有近远,岂可以知便谓之至也?”[6]115
尽管这里的“只穷理便是至于命”是二程的共法,但是结合明道给横渠《定性书》之事,可以从明道与横渠的区别入手而更好地领会这种区别。明道在《定性书》中展现的就是一种纯任自然的工夫,似乎有一种直接契入圣人化境的要求,“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6]460,即要求君子通过对“天地”的领悟而直接成就“圣人”,这与横渠要求“思勉”的“大人”工夫有着明显的区别。郭晓东指出,“对于横渠来说,在理论上先预设了天人之间的对立,然后一方面通过‘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作为入手工夫以上达天德,是为‘性天’而‘知天’;另一方面通过大心穷理以尽性,是为‘知天’而‘性天’。然不论是哪一种工夫取向,其前提都在于认为对治人生气禀所带来的一切可能的局限性是上达天德的第一要务。而在明道看来,天与人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对立的关系,因而也就无合可言,人由当下之此心,即可以见此心即天,所以明道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是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不可更外求’。”[7]这种“对治”就要求着“思勉”的工夫,即要求一种工夫次序。
横渠的这种对次第工夫的要求与朱子的“格物补传”有着相似之处。朱子有言:“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8]在这里,对每一物的“致知”就意味着一种“思勉”的工夫,而对“用力之久”后才能“豁然贯通”的强调也与横渠相似,这也似乎旁证了朱子将《定性书》不列入《近思录》的原因。
这种区别在阳明学那里也有着类似之处(4)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14页。,王阳明甚至用到了“太虚”这一概念:“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9]117-118这里对“太虚”的引用是为了说明“无善无恶之良知”。而阳明在给来自关中(渭南)的南大吉回信时也说道:“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彻,廓然与太虚而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9]302,“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9]303,这表明阳明对横渠之学是有深刻的领会的,这种领会与“无善无恶”的境界相关。与横渠类似,在阳明那里,这种境界也是需要从“为善去恶”的“诚意”工夫转进而来,此即“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9]88。“着实用意”就是“思勉”之工夫,但仍需往“天之太虚”“良知本体”处转进,这与横渠有相似处,即都要求向“天”的复归首先以“诚意”之工夫为前提,尽管他们对“诚意”的解释不同。横渠有言,“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所谓勉勉者,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继不已,乃善而能至于成性也”[1]266,由“勉勉”而“自然”,此即阳明由“诚意”而“正心”(5)关于王阳明对“诚意”和“正义”的区别,可参考拙文《“诚意”与“正心”:致良知工夫的两种路径》,载于《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6期。。然而阳明后学对“先天正心”工夫的强调和对“后天诚意”工夫的疏离就是要求跳过“勉勉”之工夫而直达“自然”之境,横渠在理学初创时期提出的“大人”与“圣人”之别所牵涉之问题在理学临近终结之时又成为争议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