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学时代”
2020-06-01石梦洁
石梦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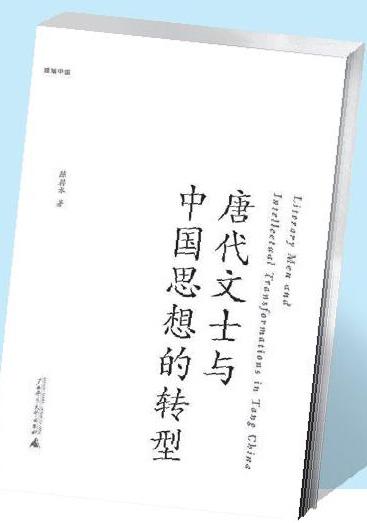
《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陈弱水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唐代文士,常常被赋予浪漫的色彩—江海山川、田园边塞、抒情咏史、怀古悼今,字里行间尽是诗酒风流。
抱歉,我们今天不谈唐诗,谈的是写诗的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陈弱水教授,是余英时先生高足,三十多年来致力于唐代思想的研究。《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是其研究成果的集结,二○○九年出版,二○一六年增订。鉴于唐代“全民作诗”的特殊背景,我们过去常常将此时的“文士”定义为“诗人”或“文人”,从而让研究多局限在文学领域。而本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跳出文学的框架,从历史的角度对文士群体做出了新的定位与考量。
序言第一句便点明:“本书探讨唐宋之际思想巨变的起点:安史乱后的儒家复兴,尤其着重文人与儒家复兴的关系。”这句话其实明确了整个研究的框架:时间上是安史之乱,即七五五年以后;而书名所谓的“思想转型”则主要是向儒家转型;同时,陈氏默认,这一时间节点和转型模式,是“唐宋思想之际的起点”。
无论是思想史还是文士阶层,前人的研究时段大多集中在中晚唐。也许是习惯将长期作为官学的儒学思想置于正统地位,因此认为安史之乱前后模糊的思想世界只是向后来“儒教复兴”的过渡,因而无关紧要。而在陈弱水详尽周全的论述中,这些模糊的问题逐渐变得清晰。
“文学”何以推动思想?
全书之总说,《中古传统的变异与裂解—论中唐思想变化的两条线索》一文,基本显示了知陈氏问题意识之所在,及其對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整体构想。所谓两条线索,其一是通过观察中古文人的文学论说,来展示中唐儒家复兴的来由和形成轨迹;其二是儒家复兴与中古思想传统的关系。
上篇“文人与文化”详论第一条线索,主要从三方面切入:“文人思想中的文人与文化”“八世纪后半的文坛变异”,以及“‘道与文学的脱中心化”。陈氏注意到,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知识界的领导者多为文人,所以文人的思想能够具有这样大的推动力。而“文学”,恰是集中反映文人意念的处所。这是陈弱水以文学论说为主要研究材料的原因。
厘清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在为之后的论证做铺垫—如果说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那么“文学”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足以推动思想的转型?
从汉末魏晋时期曹丕、陆机、刘勰、萧纲等人“独立文学观”的发达,到“初唐四杰”逐渐强调“文学”与“国政风教”(尤其是儒家政教理想)之间的关系,陈弱水深入讨论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独立性”所受到的拥护与反对,从而阐述文学如何从一种类似“艺术”的形式变成具有经世价值的“文化”。
这种“文学”到“文化”的转向在八世纪下半叶越发深刻。在安史之乱的催化下,独孤及、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一面将“文章中兴”追溯至初唐的陈子昂,一面高呼“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号召回向三代。在这场古文思潮中,北方士族出身者尤多。一方面这些人原本深受北方“重政教,轻文章”的感染;另一方面,在唐代文风兴盛、科举重要的背景下,北方士族钻研诗文者也大幅增加。二者相结合,终于形成了所谓的“儒教文学观”。
这些主张“文章中兴”的文学家,否定了独立的文学传统,而期望文学服务于儒教经典,或作为经典的延伸。文学改革者对于文学的新要求包括“德行”和“教化”,其中“教化”既包含传统的儒教文化,更包括由安史之乱引起的文化省思。无论哪一点,都在强调文章的经世功能,呼吁士人们担负起振兴政教的重任。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都必须植根于经典,与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核心紧密相连。
而在独孤及和梁肃身上,这种“以经典为本”的文章观又逐渐转变成“以道(德)为本”。陈弱水在文中对这里的“道”也加以注解,他指出,这一时期的“道”尚未被儒家垄断,而是兼容佛老的广泛意义上的“道”。至此,尽管“文章中兴”思潮已起,但尚未形成足以牵动力强大的“思想运动”,直到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古文运动的蓬勃。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陈弱水认为,古文运动,既是文学运动,也是思想运动,并为之归纳了四个特点。第一,“文”和“道”联系在了一起,且“道”仅指儒道,而对这一点贡献最大的是韩愈和柳宗元。第二,尽管对文章经世的要求并没改变,但对文学的独立性依然肯定,这一点受到了当时古文运动领袖,如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人的普遍支持,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涌现出具有文人身份的思想家。这也就形成了古文运动的第三个特点:对儒道的探索逐渐开始独立于文章写作,而此前文人思想中,“文”与“道”的界限甚是模糊。第四个特点则在于古文运动的“古”字,这是在文学和思想上同时发生变化。
这里对后面两个特点多做一些阐述。陈氏认为,尽管韩、柳二人的“文”与“道”都是逐渐独立的概念,但韩愈的“文本于道”,强调的是“道”既存于六经义理,行文布章皆要以此为理论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著述皆约六经旨而成文”(《上宰相书》)。而柳宗元则主张“文道异质”—一方面“文以明道”,“文”具有主动探索“道”的义务;另一方面“道”应存在于实际民生之中,而“文”则是一种表达工具,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同时,柳宗元在文章写作方面崇尚西汉,但在儒道阐释方面则批判西汉,这也是柳氏“文道异质”思想的表现之一。古文运动的第四个特点,文章与思想的复古问题上,陈弱水还是以韩愈为例。韩愈既追寻古道,也钻研古代文辞,但“古道”更具有优先性,通“古文”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古道”。韩愈的“古”,具有整体性,一切古代以“孔子之道”为核心的精神,在韩愈心中都是为“古”;此外,韩愈的“古”还具有精神性,他将此作为以人伦价值为唯一准绳的秩序,且为此付出了舍我其谁的一腔孤勇。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陈弱水发现,文学以外的关怀在中晚唐已降的士人群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道”的追求,标志着文学脱中心化的开始。古文运动使得原先就暗流涌动的儒家复兴思潮,从暗处走向了明处。而这一肇端于文学家群体中的思想运动,也使得陈氏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文士”群体的动机得以成立。
从和谐共生的“二元世界观”
到一枝独秀的“儒学正统”
下篇探讨“儒家复兴”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陈弱水谓之“中古思想的一个基调及其挑战”。显然,这里的“挑战”便是指儒家复兴。那么原本的“中古思想”内涵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陈氏始创“二元世界观”的概念,据他在注释中所言,学界对此尚且没有具体详尽的考察。在收入本书的数篇文章,譬如《墓志中所见的唐代前期思想》《排佛论说与六、七世纪中国的思想状态》《思想史中的杜甫》《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等,陈氏都反复引入这一概念。
所谓“二元世界观”,简言之,就是以内/外作为二元区分的主轴。在内心世界,或类似的“本”“方外”的界限中,中古士人通常倾向于依从佛、道(包括道教和道家思想)思想,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而在外部世界,或称之为“末”“方内”,他们则习惯于遵循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和集体秩序。
尽管中古士人常有内外二元,但并不意味着两者相互对立或互不相属,人们往往同时肯定儒家经典教诲的神圣性和佛道所赋予的超俗理想。这种划分方式虽属新声,但其缺點也确如陈氏自己所言,“二元世界观”只是一个形式性的概念,看不到对内容的提示。不过,总体而言,以这种“外儒内道”或“外儒内佛”作为魏晋以来文士思想的普遍形态,确实对我们探讨中古士人乃至是当代人的心灵世界都极具启发意义。
陈弱水对中古士人的这种二元心态进行了追溯。他认为,这种观念是在玄学思潮中形成的。其中一支来自王弼的“崇本以举其末”,王氏主要立论于老庄,认为天地万一皆以无为本,其他一切看得到、接触得到的,包括儒家伦理规范,皆是“有”,是“末”。而另一个玄学流派则是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相比之下,竹林中这二位的态度比王弼要来得激进—王弼的本末之论尚有轻重,而嵇、阮二人索性抗拒名教,超越世俗,直奔方外而去。无论是哪一个玄学流派,不难看出中古士人心灵的“二元”区分,在魏晋时期已然初显。
“二元”观念的进一步强化,是在佛教兴盛之后。中国士人常以老庄思想和玄学的眼光来理解佛教义理,而佛家又自称“内学”“内教”,于是安顿内心的功能在士人那里更加突出。道教则长期汲取佛、儒、玄学之精华,亦步亦趋以“内”自居便是自然而成。于是内/外二元在中古士人的心中更加根深蒂固。值得一提的是,陈氏指出,由于“二元世界观”的形成,中古佛教、道教得以具有正当性,登上历史的舞台,获得发展的空间,这也让中古思想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
而儒家复兴就发生在这种思想环境下。陈氏早在开篇就纠正了人们的一个误解,即认为唐代中叶儒家已失去了正统地位,故有“复兴”之说。陈氏说明,安史之乱之后的儒家复兴,是一个和缓的“旧教复兴”,并非死灰复燃或重新崛起,而是“一个多少已经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传统出现了新活力、新探索,而且有了一些改变—有的还是深刻的改变”。儒家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前面所提到的“文章中兴”。这一潮流的领导者们一方面标榜儒家式的文学观,一方面鼓吹儒家的文学价值。但在文章中兴之始,领导者们与方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剑拔弩张,对于释道二教,他们的包容甚至是亲密,远远多于打压和排斥。
这种和谐共生的思想格局直到八、九世纪之交,韩愈、柳宗元等人崛起之后,才被打破。尤其是韩愈,他无比强烈地渴望创造一个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一统世界,作为激进的卫道士,他和他的“战友”们挑起的与佛、道的战争,终于让中古思想发生了变动。这种“一元世界观”对原本“二元世界观”带来的巨大冲击,让唐代儒学发生了突破,也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自此以后,儒学在正统意识形态中一枝独秀,至宋代以后,更可谓浩浩荡荡,成为统治中国民众长达千年的主流思想。
他们是活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你我
就这本书而言,《中古传统的变异与裂解—论中唐思想变化的两条线索》一文是为“总说”,是针对中唐思想变化起源与性质的大规模、长时期、结构性论述。而后面的“分论”则是对于相关具体问题的探讨。
譬如《思想史中的杜甫》一篇,陈弱水从以杜诗为研究材料,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子美心灵的特质及其历史意义。陈氏并未如很多方家一样,老生常谈地指出杜甫的思想中三教兼容,而是直接讨论杜甫的儒家情怀。这应当是对书名中“转型”二字的一种回应—既然“转型”是转向儒家,那么莫若就来讨论他的儒家思想有多大的推动力,或者说,是否符合让中国思想发生转型的要求。有意思的是,那句常常被用来佐证子美儒家思想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这里被陈弱水指出子美的儒家观念并不纯粹。通过考察杜甫其他关于民风淳朴的诗句,陈氏发现,“风俗淳”与其说是指儒家的移风易俗、礼乐教化,其实更符合道家民风淳朴、安居乐业的价值与向往。
《排佛论说与六、七世纪中国的思想状态》可看作是对“二元世界观”的补充讨论,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六、七世纪的排佛论著如何反映二元世界观;二是观察这些论著如何动摇二元世界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陈氏很喜欢创发一些新的概念,这在当今哲社学界实属难得,其勇气与洞察力都委实令人钦佩。这篇文章中,陈氏在讨论动摇排佛论的议题时也是如此,先后创造了“国家全体主义”“儒家中心主义”,以及“自然主义”或“理性主义”几种概念。第一类以荀济、卫元嵩、北周武帝和唐太宗为主要代表,主张以统治者为中心的一元主义;第二类以王通、姚崇等人为代表,强调以儒家作为主导思想,但在六、七世纪时,这种思想尚显模糊,人们对宗教方外的世界虽无鼓励,但也未明言反对;而“自然主义”或“理性主义”的立场则最为薄弱,这一类士人并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因而对佛道有所抗拒,在我看来,倒有些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因呼唤人文和理性,从而反对宗教的意味。
书中另一篇笔者很喜欢的文章是《墓志中所见的唐代前期思想》。关于唐代前期的思想史,在很多中国思想史的论著中是一段留白。葛兆光先生在二○○○年撰写的《中国思想史》中,更是直接将这段时期的思想定义为“盛世的平庸”,剖析和批判了当时信仰的模糊与秩序的混乱,在思想史的写法上可谓新的突破。但葛氏在书写这一篇时,其实多从统治阶层去论述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忽略了在庙堂和江湖都颇具影响力的文士群体。而陈弱水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这段空白的填补。通过对“墓志铭”这种盖棺定论的文体的考察,陈氏读到了这一时期士人们凭儒学求知治世、借佛道体会宇宙人生本体的二元世界观,读到了将政治生活和精神追求合二为一的可能,读到了佛教和道教思想中对人间集体秩序的关怀,也读到了以君王为中心的单一秩序观(国家全体主义)。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盛世怎么会是平庸的呢?而这一点也恰恰提醒了我们,在我们公认的“盛世”中,思想从来都是多元共存、充满生机的,而不是整齐划一、墨守成规的。而这些墓志铭的主人也很有特点—他们是士人,但大多在历史上默默无名。他们不是姚崇宋璟,也不是李杜王孟,他们只是士人中最普通的群体—他们是活在一千四百年前寂寂无名的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