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边界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
2020-05-29赵书峰
赵书峰
族性(ethnicity)“是指血统与文化的社会构建(social construction)、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 system)的逻辑内涵与含义。”(1)〔英〕斯蒂夫·芬顿著:《族性》,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同时也是指“拥有某种族群的认同并认为是其中一员,并因为这种隶属关系而同特定其他群体具有排他性。”(2)〔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著:《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第12版),黄剑波、方静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2页。当下,有关传统文化的族性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人类学领域,尤其以挪威当代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人类学经典之作——《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3)〔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认为族性建构不能只强调建立在生物遗传学“原生论”(或者称“根基论”)思维基础之上,而应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去思考基于社会资源竞争与利益诉求背景下的族性重建问题,此即“工具论”或“建构论”思维。换言之,有关族群边界的思维不但要注重其文化边界的思考,而且更要关注其社会边界的形成。因为,族群边界并不止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文化“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也不一定是指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指“社会边界”。(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受到后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思维的影响,已经开始关注到少数民族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问题。尤其结合历史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等理论,重点审视与观照基于民族、国家、区域自治政策等综合语境去思考少数民族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问题,是当下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本文将基于上述学术语境,结合笔者多年的田野考察积累,针对湘、桂边界区域内的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变迁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笔者认为,湘、桂边界“平地瑶”(5)“平地瑶”属于瑶族的一个支系,属于汉化程度较高的一个族群,目前主要分布在湘、桂交界处的湖南江永、江华、广西富川、钟山等县。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与明王朝以来对于“瑶乱”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军事等治理政策有关,是一种通过早期的军事“招抚”与“编户齐民”(6)“编户齐民”是历代中原王朝政府实行的户籍制度,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等项目载入户籍。因为,早期高山瑶在没有被“招抚”之前属于“生瑶”,是一个明代之前没有被王朝纳入户籍管辖范围的族群。策略,以及当代民族区域自治等策略完成的文化重建过程。国内学界关于平地瑶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音乐学界已有的平地瑶音乐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何芸、伍国栋、乔建中《桂、湘、粤边界瑶族民歌考察》(7)何芸、伍国栋、乔建中:《桂、湘、粤边界瑶族民歌考察》,《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第49—60页。、常龙飞《湘、桂地区梧州瑶民歌研究》(8)常龙飞:《湘、桂地区梧州瑶民歌研究》,中国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黄福新《湘、桂、粤毗邻地区瑶族民歌的节奏演变》(9)黄福新:《湘、桂、粤毗邻地区瑶族民歌的节奏演变》,《民族艺术》,1989年,第3期,第132—138页。等。尤其是何芸等三位学者的文章是目前学界较早涉及到湘南平地瑶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当下,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尚无学者关注到湘、桂边界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并对之进行深入思考。为此,本文将运用历史文献学、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念,结合湘、桂边界平地瑶音乐文化形成的历史语境、音乐的“濡化”与“涵化”、音乐的历史与当代建构等理论视角,重点审视与观照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问题。
一、平地瑶音乐形成的历史语境
首先,“潇贺古道”(10)“潇贺古道”是指秦汉时期开辟的,由湖南潇水连接广西贺江流域的“潇贺古道”及其岔道的辐射区域,包括汉代的临贺郡和部分苍梧郡地。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大致包括湖南的道县、江永、江华,广西的恭城、平乐、苍梧及贺州市,广东的怀集、封开等市县的全部或部分,相当于湘、桂、粤三省(区)交接地。(参见韦浩明《潇贺古道区域瑶族认同汉文化的历史建构》,《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6页。)(又称“湘桂古道”见图1)客观促进了瑶、汉跨族群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为明代高山瑶汉化成为平地瑶提供了便利条件。“潇贺古道往北,借湘江联接了中原,往南则有贺江,直达广州,向西则沿西江直通西南及东南亚一带,中原先进的文化借古道南下,并与南方文化融合,不断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11)钟世华:《贺州潇贺古道文化调研报告》,《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2页。先秦以来形成的“潇贺古道”,客观上为北方汉族传统文化的输入以及南岭民族走廊区域内平地瑶音乐族性的历史建构铺垫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尤其是以军户、商户、逃犯等为代表的北方汉族携带的中原文化对于该区域内高山瑶语言、宗教习俗、建筑、教育、经济生活等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客观上促进了瑶、汉传统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交流。随着历史、社会的变迁,加速了高山瑶被汉族传统文化“涵化”的进程,也为平地瑶音乐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基础。
图1.平地瑶分布与“潇贺古道”示意图(12)彭迪于2020年2月制图。

其次,明代频繁的“瑶乱”事件有力地推动了平地瑶族性的建构过程。明代湘、粤、桂区域内的“瑶乱”事件时常发生,成为明王朝的一个“心病”。比如,据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人语·瑶人》记载:“万历初,两广寇之据者曰罗旁瑶,瑶每出劫人,挟单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则编合为筏,所向轻疾,号为五花贼。其畲有九星岩,一石窍深二尺许,瑶辄吹之以号众。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渊渊作鼓声,瑶亦以为号。其谣曰:‘撞石鼓,万家为我虏。吹石角,我兵齐宰剥。’”(13)〔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人语·瑶人》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页。又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永明县(即江永县)瑶民起义,与官府武装对峙,攻克两县边境部分乡村,后失败。(14)零陵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零陵地区志·民族志》(内部资料),2001年,第12页。因此,明代为了治理“瑶乱”分别在瑶族聚集区的湘、粤、桂交界处设立梧州千户所、贺县千户所、富川千户所,以及郴州千户所、桂阳千户所、常宁千户所、宁远千户所、江华千户所、宜章千户所。(1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六十六·兵二》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15页。据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富川县志》记载,为防范和镇压当地民族起义,在征蛮将军韩观的疏请下,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矮石设立“千户所”,拨给旗军1249名,实行屯田兵役,将县内绝户抛荒民田分给军士领种,列入军户。到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仍有军户45户,弓兵户91户。(16)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52页。据笔者2018年10月调查发现,江永桃川镇所城村是明代桃川守御千户所驻地,如今该村共有36个姓氏,至今还保留重修关帝庙、城隍庙、军庙、佛堂等碑刻,并呈现出饮食文化的多元性、语言的丰富性、姓氏的复杂化等特征,是卫所制度影响下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交融所致。所以,正是由于大量的汉族军户的迁入,其携带的传统习俗进入到瑶族地区,为瑶、汉跨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提供了可能。比如通过语言、教育、宗教等文化的传入,改变了高山瑶文化体系的表述系统,瑶族开始大量学习汉族文字、生活礼俗,包括唱本和经文在内均用汉文抄写;在音乐方面借鉴和吸收汉族传统乐器(如唢呐、锣、鼓、镲等等)与传统曲牌。有学者认为,南岭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历史上不断有中原汉人和瑶人迁入,成为汉族与瑶族杂居地区。后来迁入的一些汉人,为了避“徭役”投入瑶籍与瑶族相互通婚,逐渐融入瑶族当中,成为平地瑶的一部分。(17)袁丽红:《平地瑶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南岭走廊民族关系研究之一》,《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第156页。总之,明代洪武年间为了防止“瑶乱”,在湘、粤、桂区域内纷纷设置大量的守御千户所,这些军户的移民主体多是北方汉族,其携带的汉族传统文化对于高山瑶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加速了平地瑶的族性建构过程。
再次,明代“招抚”政策加速了平地瑶的形成。明王朝通过“招抚”手段进行“瑶人治瑶”,借以实现南岭民族走廊区域的少数民族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的有效治理。同时对于高山瑶的军事“招抚”,形成了军户包围下的汉族文化圈,汉文化的持续性渗透加速了被“招抚”后的高山瑶传统音乐体系的解构过程,从而为平地瑶的族性建构营造了重要的前提。如江永县内以“四大民瑶”(18)“四大民瑶”属于湘南平地瑶,主要分布在湖南江永县,包括:“勾蓝瑶”“扶灵瑶”“清溪瑶”“古调瑶”。为主的平地瑶就是明代军事“招抚”下的一种族群建构。据江永古调瑶村保存的清代嘉庆十八年(1813年)碑刻记载:“扶灵瑶、清溪瑶、古调瑶、勾蓝瑶,该四瑶自明洪武招安,各瑶把守粤隘。”(19)笔者于2019年1月在湖南江永县源口瑶族乡古调村村委会调查时拍摄到此信息。据道光年间重修的《永明县志·风土志·瑶俗》记载:“清溪源、古调源、扶灵源、勾蓝源,以上四源,自明洪武二十九年归化,皆为熟瑶,服物采章,与编氓无异,有司岁犒牛酒,以示羁縻,其所居为邑门户,藉以防御粤寇,最得其力,……岁科两考,额取新生三名,又于清溪、古调,设立新学,……瑶有生熟之别,服王化,供租赋,如清溪、古调、扶灵、勾蓝,谓之熟瑶。”(20)〔清〕道光丙午重修:《永明县志·风土志·瑶俗》卷之三,1933年翻印,第11页。所以,明王朝为了加强对于粤隘的军事治理和管控,分别针对江永县境内的清溪、古调、扶灵、勾蓝四个村寨瑶族进行“招抚”,分别施以良田、准许瑶族参加科举考试、减免赋税等相关优惠政策,使这个区域内的高山瑶纷纷下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从而实现“以瑶治瑶”的目的。在传统仪式乐舞方面,除了保留盘王信仰、长鼓等等之外,包括语言、习俗、服饰、建筑等方面与说勉语的高山瑶传统文化相差很大,成为了汉化后的“熟瑶”。据《江永县志》记载:“明代‘四大民瑶’归服王化后,始设私塾。清代,在清溪、古调设置义学两所。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每年县学科试录取瑶童附生3名。乾隆年间减为1名。”(21)湖南江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江永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714页。总之,笔者认为,经过军事“招抚”后的高山瑶为了自身生活利益的需要等原因,提高了他们学习汉族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并有力地推动了其汉化过程,为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文化保障。
最后,平地瑶是明代“编户齐民”制度下的一种族群建构。明代北方汉族居民为逃避赋税,冒充瑶族改变族群边界,并在“编户齐民”背景下成为一种合法化的瑶族身份,这种改变族群边界的策略也是平地瑶族性构成的又一个主要来源。据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瑶人》记载:“盘瓠为大宗,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瑶。……曲江瑶,惟盘姓八十余户为真瑶,其别姓赵、冯、邓、唐九十余户皆伪瑶。……其无板者曰民瑶,耕山者花麻而不赋,耕亩者编户与庶民同。”(22)〔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人语·瑶人》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6—237页。又据《零陵地区志·民族志》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东安县吉狱率兵血洗溪峒瑶民住地,方圆四十里皆空。后来纳县人文昶建议,将河南西华县来的流民唐、廖二姓安置在里溪峒耕种,冒领瑶民。”(23)零陵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零陵地区志·民族志》(内部资料),2001年,第11页。所以,移民到此区域内的汉族由于长期居住瑶区,生活风俗逐渐靠近瑶族,后来在政府“编户齐民”背景下成为了平地瑶,虽然其族群身份发生变迁,但是其拥有的汉族传统文化习俗仍然继续保持,由此形成了平地瑶以汉文化为主体性的族性特征。
二、平地瑶音乐的族性是瑶、汉文化“濡化”与“涵化”互文建构的结果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认为,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传播过程,而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则是发生在异文化之间横向的传播过程。(24)〔美〕卢克·拉斯特著:《人类学的邀请》,王媛、徐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4—75页。换言之,文化“濡化”是“文化习得和通过代际传递的社会过程”,而“涵化”则是指“文化特征的交换。当群体发生持续不断地直接接触;一方或双方群体的文化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25)〔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著:《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第12版,黄剑波、方静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页。笔者认为,平地瑶音乐的历史建构过程是对高山瑶音乐文化的一种纵向历史传承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互动交融的产物,即音乐的“濡化”“涵化”互文建构的结果。首先,平地瑶音乐是对高山瑶传统文化的“濡化”。由高山瑶汉化形成的平地瑶,其文化中还保留有盘王祭祀与打长鼓的习俗。据清代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衡人赛盘瓠,……误祈许盘古。赛之日,巫者以木为鼓,圆径手一握,中小而两头大,如今之杖鼓,四尺者,谓之长鼓,二尺者谓之短鼓。圆径一斗余,中空两斗大。四尺者,谓之长鼓,二尺者,谓之短鼓。巫有练帛长二三尺,画自盘古而下三皇五帝,……是日,以帛画悬之长杆,鸣锣击鼓吹角,巫一人以长鼓绕身而舞;二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26)〔清〕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下》第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可以看出,高山瑶传统乐舞文化中的核心主体主要是盘王祭祀仪式和跳长鼓舞,经过高山瑶汉化的部分平地瑶如今还保留盘王祭祀与打长鼓的习俗,这是平地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于高山瑶传统乐舞文化的一种“濡化”现象。因为其文化的“传承链”至今没有断裂,这体现出平地瑶对其原生性族群文化认同的一种典型表征。如今在江永“四大民瑶”、江华县上伍堡、大路铺镇宝昌洞平地瑶的民间信仰祭祀活动中仍保留有跳长鼓舞的习俗,但是从音乐形态特征观察已经与高山瑶音乐相去甚远。另据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发现的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瑶族“梅山图”中的乐器“长鼓”图像资料,可以在当下的湖南江华县上伍堡平地瑶盘王祭祀仪式中找到类似这种形制的长鼓乐器实物的原型(图2、图3),这充分说明平地瑶音乐是对其传统乐舞文化的一种“濡化”过程。又如江永“四大民瑶”之一的勾蓝瑶“水龙祠”壁画中的梅山教张五郎神、江华大路铺镇八洞村的盘承云师公保存的梅山教经书、盘王祭祀经书、度戒经书,等等都是平地瑶文化对于高山瑶传统的“濡化”现象。(27)笔者于2018年10月在江华大路铺镇八洞村采访盘承云(33岁)师公时得知,他是高山瑶的后裔,后来与汉族通婚后成为了平地瑶,如今家里保存有很多神像图和仪式经书,尤其是梅山教经书很多,他说梅山教仪式主要是在师公去世的时候做的,平时不用。
图2(28)曾迪于2004年12月拍摄。.广西恭城瑶族“梅山图”中瑶族打“长鼓”场景

图3.江华上伍堡平地瑶盘王祭祀用的长鼓

其次,平地瑶音乐的形成也是瑶、汉文化“涵化”的结果。经过军事“招抚”后的高山瑶在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不断地持续性建构自己的音乐文化认同,并在传统音乐、民俗节庆仪式、语言宗教、民族教育等方面向汉族学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在盘王祭祀、婚俗仪式等平地瑶传统文化中,从仪式音乐到经文书写等方面吸收了诸多汉族文化元素。在平地瑶传统民俗仪式中还大量借鉴与吸收汉族传统道教仪式音乐,特别是当地比较典型的道教仪式——“罗天大醮”“接龙”等,从乐器构成到传统曲牌大多是汉族天师道音乐元素。而具有祭、戏互文特性的汉族地方戏曲(彩调、祁剧)的展演以及具有瑶族自身特色的对歌仪式则构成了平地瑶传统仪式的世俗音声景观。例如,江华县大石桥乡大莲塘平地瑶归宗庙会中举办的“罗天大醮”(通常举办七天七夜),仪式活动主要有:道教仪式、对歌、唱大戏(湖南祁剧),其中不但有当地民间道士主持的神圣性仪式,而且还有当地民间艺人组成的乐队为神奏乐,道教仪式与音声构成则与汉族道教文化别无两样。又如,江华县上伍堡平地瑶婚嫁仪式中的“坐歌堂”环节中的唢呐音乐:《花子烤火》《晓宫》《四合子》《瞎子过街》《老鼠过街》《水罗音》《一枝花》《叠断桥》《小开门》《尺子调》《八月桂花遍地开》《妈妈的吻》《梁祝》《说句心里话》《珍珠堂》(广西桂剧音乐),以及伴奏乐器:二胡、京胡、唢呐、小锣、三弦、小鼓等等唢呐曲牌与乐器构成明显受到汉族传统与当代音乐的影响。再如,江永县勾蓝瑶村寨的“水龙祠”壁画中的“三星锣”(图4),与汉族、侗族的打击乐器——“三音锣”(29)福建莆田地区流传称为“三音锣”,又称“三响”,用于“十音乐队”。(参见刘东升编《中国乐器图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3页)。侗族称“三星锣”,为侗族打击乐器。侗语称“沙拉能”,又称“叮当夺”。流行于贵州省黎平、从江、榕江和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等地(参见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6年,第316页)。(图5),在乐器形制、击奏方式等方面极其相似。可以看出,平地瑶传统音乐所呈现的跨族群文化的互文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跨文化之间的“涵化”作用导致的。
图4.江永勾蓝瑶“水龙祠”壁画中的乐器“三星锣”

图5.侗族打击乐器“三星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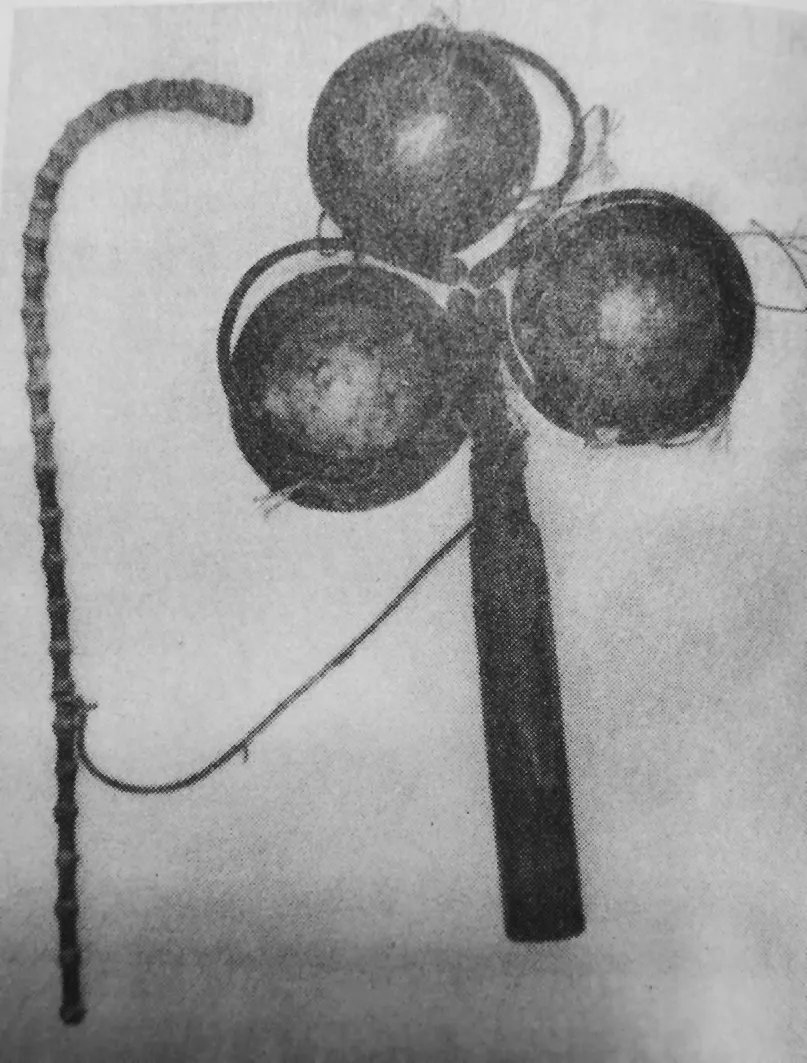
同时,平地瑶对于汉族文化的吸收也表现在礼俗信仰中。如江华、江永、富川等地庙宇中大多配有唱神戏的古戏楼,如江永勾蓝瑶村寨盘王庙与“旗山庙”中的古戏楼(图6、图7),这种庙宇加戏楼的配置充分反映出平地瑶文化受到北方汉族礼俗传统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山西、河南等地的道观中,有庙就有古戏楼,戏楼的功能主要用来唱神戏,借以达到“祭戏互文”的文化功能,这足以说明汉族礼俗文化对于平地瑶传统信仰的“涵化”现象。
图6.江永勾蓝瑶盘王庙中重新修缮的古戏楼

图7.建于乾隆22年(1757年)勾蓝瑶旗山庙古戏楼

还如,笔者在考察湖南江华大路铺镇宝昌洞社区平地瑶都衙庙祭祀仪式乐舞时,看到其中保留有高山瑶传统的跳长鼓舞仪式,而舞蹈伴奏乐器则已经由早期的芦笙或唢呐伴奏,改为了现代以笙鼓为主的一种乐队组合形式(图8)。
图8.江华大路铺镇宝昌洞社区都衙庙祭祀仪式中的长鼓舞(2018年10月拍摄)

图9.江永县清溪瑶乐器(2019年1月拍摄)

第二,在乐器、民歌等方面平地瑶传统音乐明显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在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交融过程中,平地瑶音乐吸收和借鉴了当地部分汉族传统曲调(“涵化”)。因为,平地瑶的很多乐器多来自汉族,甚至是民歌旋律曲调受到当地汉族传统音乐的广泛影响。例如,平地瑶目前使用的乐器构成主要包括:二胡、笛子、锣、鼓、长鼓、京胡等,这些乐器融合了汉族与瑶族传统乐器的特征(图9)。又如江永勾蓝瑶“水龙祠”(30)有关江永县勾蓝瑶“水龙祠”的兴建年代,“据村民的口述,水龙祠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后来分别于明代万历年间、清代嘉庆年间和1949年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参见刘灿姣、林伟:《湖南江永水龙祠壁画的发现报告》,《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第18页)。壁画中的乐器——长号(又名“招军”“喇叭”),据笔者查阅资料得知,它属于汉族传统乐器,主要用于明清以来的军乐中,现代多用于浙东锣鼓、十番锣鼓等乐种中。河南北部地区的古老剧种大平调、大乐戏也用它作为伴奏乐器。当地称为“尖子号”。(3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38页。江永“水龙祠”壁画中的“长号”从乐器形制、吹奏方式来看,与广西贺州黄洞瑶族乡、贺街镇等地的高山瑶、富川县葛坡镇的平地瑶传统乐器——长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图10、图11)。结合湘、粤、桂区域内繁多的明代“卫所”文化可以看出,“水龙祠”壁画中的“长号”应为“招军”称谓,属于明清军乐器在湘、粤、桂交界之地跨族群文化传播的产物,由此说明明代中央王朝对于南岭民族区域的政治、军事、社会治理的缩影以及平地瑶对于卫所文化中传统军乐的一种借鉴与吸收,即跨文化之间的“涵化”结局。
图10.江永勾蓝瑶“水龙祠”壁画中乐器长号(2018年11月拍摄)

图11.贺州黄洞瑶族乡婚礼仪式乐器长号(2013年7月拍摄)

第三,从相关音乐形态分析,也可以看出平地瑶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某些“涵化”现象。如江永“四大民瑶”之一的源口瑶族乡清溪瑶民歌《采茶歌》(谱例1),其中第3—8小节的旋律音构成与广西汉族地方戏曲——桂林彩调《十月花》(谱例2)音乐的前4小节的旋律结构与风格有诸多相似之处(32)笔者于2020年2月再次通过电话对江永县清溪村平地瑶民间艺人田万载先生进行访谈,进一步求证了笔者的观点。,这鲜明地呈现出平地瑶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之间所具有的互文关系,即音乐的“涵化”现象。同时也折射出同属于南岭民族走廊区域内的两个相邻地区(广西桂林与湖南江永县)的平地瑶与汉族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现象。
谱例1(33)谱例1由江永县清溪村平地瑶民间艺人田万载先生于2018年10月提供。.


谱例2(34)谱例来自于沈贵芳编写:《彩调音乐》,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162页。.

总之,湘、桂交界处的湖南江华县大路铺镇、河路口镇,以及江永县兰溪瑶族乡、源口瑶族乡等平地瑶聚居区的传统民俗仪式音声景观的构成融合了诸多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元素(特别是以广西彩调、湖南祁剧等为代表的地方汉族地方戏曲)。据笔者考察得知,目前湖南江华县上伍堡平地瑶每年一度的“还盘王愿”仪式声音景观构成,既有高山瑶传统的“盘王祭祀”仪式,又有周边汉族传统地方戏曲(如广西彩调、湖南祁剧等)的上演。我们知道,文化“涵化”多是建立在双向互动的基础上,在湘、桂交界处的瑶、汉聚居区不但有瑶族对于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同时也存在改变族群身份前的汉族民俗信仰体系中对于瑶族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如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松柏村傩神中还吸纳了翻坛倒立的瑶族梅山神张五郎。所以,平地瑶传统音乐的声音景观构成不但传承了高山瑶传统,而且在与周边族群传统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中还吸纳了汉族传统音乐元素,致使平地瑶传统音乐文化系统成为了对自我文化的“濡化”以及对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涵化”现象。
三、平地瑶音乐族性的当代建构与文化认同
(一)民族区域自治语境下的平地瑶音乐族性的当代建构
20世纪50至80年代,在国家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导下,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政府纷纷申请成立少数民族自治县,为了增加其少数民族人口基数,在政策允许下,一些与少数民族有血缘关系的汉族纷纷改变族籍,其中包括大部分汉族民间艺人,进而其使用的音乐在申报各类级别的“非遗”项目时被归类为少数民族音乐。(35)另如,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族性建构与历史变迁问题也属于上述类型。(参见赵书峰:《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41—46页)
首先,湘、桂交界处广西富川、钟山县,以及湖南江华县的“梧州人”(36)有关“梧州人”的族性界定,据《富川瑶族自治县志》记载:“县内汉族的称谓。解放前自称‘民家人’‘梧州人’‘客家人’。……有少数汉族后裔融有瑶族血缘关系,按政策规定改为瑶族外,境内民家人、梧州人、客家人统称为汉族。”(参见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本属于汉族族群。但是它于20世纪50年代江华成立瑶族自治县之际被改成了平地瑶(又称“梧州瑶”)身份,当然其拥有的二声部民歌——“蝴蝶歌”也被政府默认为平地瑶歌曲。然而,在临近广西富川、钟山县除了部分“梧州人”改为平地瑶之外,有很大部分却仍然保留了汉族身份。广西富川县将“梧州人”的“蝴蝶歌”以平地瑶歌曲于2008年申报成了国家级“非遗”项目。(37)有关“梧州人”的信息,笔者于2018年至2020年之间曾多次求教于广西贺州市原民委主任黄盛全先生和广西钟山县平地瑶民间艺人徐维生先生。然而,这种通过国家政府行为建构而成的平地瑶音乐,虽然族群身份发生变迁,但是其文化的核心元素还是汉族血统。同时,通过对江华“梧州瑶山歌”(如《石榴青》《我俩好》《讲了要来就要来》《夜了快快回》)音乐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与当地其他“平地瑶山歌”(如《唱得好来唱得乖》《等妹来》)的旋律形态与风格方面差别很大。江华“梧州瑶山歌”(如《上山砍柴柴打柴》,见谱例3)的旋律音阶基本是以la、do、re三音列为骨干音(偶尔出现mi音),结束音为la音。其他“平地瑶山歌”(如《等妹来》,见谱例4)的旋律音阶为:sol、la、do、re、mi、sol,结束音多为sol音。可以明显看出,作为湘、桂平地瑶族群亚系的“梧州瑶”音乐与其他平地瑶旋律形态与风格之间并不属于同一体系,但其仍然保持作为汉文化系统的“梧州声”风格特色。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湘、桂区域内明代卫所制度下的汉族“军户”文化的遗存为代表,借成立瑶族自治县、瑶族自治乡之际,改为平地瑶身份。据笔者2018年10月考察湖南
谱例3(38)《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编辑委员会编:《湖南民间歌曲集成·零陵地区分册》,1981年刊印,第233页。.

谱例4(39)同注,第232页。.

江永县松柏瑶族自治乡松柏村和棠景村得知(40)据笔者在2018年10月在江永松柏瑶族乡枇杷所考察得知,枇杷所城的现有居民1600多人,有王、罗、顾、欧阳、肖、周、于、蒋、林、毛等,每个姓氏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为明朝的将军后裔。,这里多是明代在此设立的枇杷千户所的北方汉族军户移民的后代。上述两村村民的姓氏构成主要有:王、欧阳、何、任、李、胡等。通过查阅王氏家谱发现,其来自山东青州府安邱县(图12),于元中期延佑元年(1319年)迁到松柏瑶族乡的大同村,约有700年的历史,后来与当地的瑶族通婚。通过对其语言学的调查发现,这里村民的方言中仍把父亲叫“爹”、爸叫“大”,这与鲁西南、豫东南的称呼大致相同。有学者研究认为,“有的平地瑶祖先是到此戍守的汉族官兵的后代。明代洪武年间在富川设有守御千户所(驻灵亭乡),清代雍正年间,又在麦岭、牛岩、小水峡、长圳、龙窝等地‘分建营舍,设兵汛防’,戍守在此的兵员虽有被招抚的本地瑶族,但其主体应是从外地迁来的汉族移民。”(41)袁丽红:《平地瑶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南岭走廊民族关系研究之一》,《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第158页。所以看出,操演傩戏的松柏村王氏家族(42)如笔者2018年10月在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枇杷所村考察王氏宗祠时,查看其碑刻信息记载内容得知:王氏家族是明初洪武年间从河南省归德府大同乡(今河南商丘市)迁来的,是枇杷所千户所的军户后代。和棠景村顾氏家族,随着20世纪80年代江永县成立松柏瑶族自治乡的进程,这些具有汉族血统的傩戏艺人的身份改为了平地瑶,随后其拥有的傩戏(图13)也理所当然地以平地瑶身份申报成了江永县级“非遗”项目,但其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汉族传统戏剧文化的遗存。
图12.湖南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松柏村王氏族谱(2018年10月拍摄)

图13.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松柏村平地瑶傩戏(2018年10月拍摄)

另外,通过笔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里的傩戏与汉族道教文化相互依存。比如,供奉傩神的“五岳堂”中的主神为真武大帝。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本地乡民会从“五岳堂”中将真武大帝抬出走街串户举行“游神”活动,寓意为全村人驱邪保平安。这种“游神”节日习俗在中国北方汉族地区比较多见。其傩戏伴奏乐器主要有:笛子、锣、大鼓、唢呐、钹、小鼓等等。唢呐演奏曲牌主要有:《大开门》《小开门》《一枝花》等等。演出节目主要有:《拜年》《嫁女》《看女》《大还愿》《小还愿》《开洞》《烧炭》《神公》《接公公》《读书》《判官》《关公》《总兵》《狮子头》等。其中五岳堂中供奉的傩面具主要有:小鬼子、狮子鬼、斧头鬼、小鬼四、獐子鬼、关公、师公、乞丐、判官、黑豆、白豆、大赖、总兵、牛头、马面、东西南北中各路神仙、哪咤、顺风耳、千里眼、武判、二赖、雷神、三姐、二姐、大姐、张五郎等等。上述的乐器构成、曲牌特点以及傩神构成等元素都彰显鲜明的汉文化特色。可以看出,湘、桂区域部分由汉族转化后的平地瑶,其音乐族性构成虽然通过“国家在场”语境下实施了改变族群边界的行为,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传统音乐文化的核心基因没有改变。
(二)汉族文化认同语境下的平地瑶音乐的两种话语表述
首先,平地瑶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既是明王朝对于南岭民族走廊区域的多民族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治理图景的一种缩影,又是中华民族区域自治语境下的与瑶族有血缘关系的汉族族群边界的移动与音乐文化认同的变迁产物。其不仅在早期达到了明王朝治理“瑶乱”以及高山瑶为了获取良田、参加科举考试等综合利益的目的,后来又为了满足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宏观政治方略背景下的一种现实性需要,而促现了平地瑶的客观认同,或称之为“表达性事实”。(43)“表达性事实”与“客观性事实”概念内涵对应了文化与社会认同的“虚构”与“真实”。(有关此概念的深入解读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事实与客观性事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6—95页)换言之,平地瑶音乐的族性虽然经历了系列性的社会建构,尤其是高山瑶原生性的部分音乐特质在逐渐消失,但是其盘王信仰、跳长鼓舞为核心特质的族群文化认同依然在传承,这一平地瑶音乐话语的“表达性事实”意味着高山瑶乐舞的“象征性的族性”(44)〔英〕斯蒂夫·芬顿(Steve Fenton)著:《族性》,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依然真实存在。同时笔者认为,此种表象表征了当下的平地瑶传统音乐的族性建构是历史与当下的高山瑶、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互文建构。比如高山瑶经过“招安”汉化之后的平地瑶,其传统仪式乐舞在保留长鼓舞与盘王信仰仪式等基础上,大部分传统音乐与乐器构成多呈现为鲜明的汉族文化特色。如民俗仪式与音乐经文的汉字书写、具有汉族元素的乐器与曲牌构成,以及汉族戏曲音乐等等构成了平地瑶传统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据笔者考察得知,除了传统的平地瑶对歌活动之外,以湖南祁剧、广西彩调等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戏曲是平地瑶传统民俗节庆仪式活动中的“重头戏”(图14、图15)。又如,笔者多次在江永县“四大民瑶”之一的“清溪瑶”村寨田万载先生家中考察看到,这里的民间艺人在日常的民歌(如《采茶歌》《敬酒歌》等)表演活动中,常用二胡作为伴奏乐器。而具有军户移民后代的汉族在受到当代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语境的影响,通过改变族群边界形成的平地瑶,其传统音乐的风格、器乐构成等等与汉族传统音乐差别不大,以致平地瑶在汉族传统音乐文化产生族性变迁之后,仍然对汉族传统乐舞文化保持着强烈的主观认同,或称之为“客观性事实”。
图14.江华神岗村平地瑶“接龙”仪式中的祁剧展演(2018年10月拍摄)

图15.江华平地瑶都衙庙祭祀仪式中彩调展演(2018年10月拍摄)

其次,平地瑶音乐是瑶、汉音乐文化互文现象背后所表征的,既是瑶族为了实现其生存利益诉求下进行的族性重构,又是高山瑶汉化后形成的一种“客观性事实”,以及成立瑶族自治县、瑶族自治乡背景下由汉族身份改成平地瑶族性的一种“表达性事实”。平地瑶音乐的构成及其族性认同正好是上述两种“事实”的一种综合表征。高山瑶“招抚”后形成的平地瑶的主体音乐结构其实就是汉族文化,同时隐喻了这个重建后的族群对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高度认同;而通过“编户齐民”以及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县背景下改成瑶籍的汉族,其深层的文化认同仍然是对汉族传统音乐的一种主观认同。如前述的湖南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枇杷所平地瑶保存的传统戏剧——傩戏,从剧目、祀神仪式、唢呐曲牌构成、器乐组合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特色。笔者2018年10月在江永、江华县由汉族改为平地瑶的社区(如江华县大路铺镇宝昌洞社区)采访时,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即,“我们虽然是瑶族,但是实际上我们过的还是汉族的生活”。所以看出,平地瑶音乐所具有的以汉族为主体性的族性特征,正是卫所制度下的军户文化、“潇贺古道”的跨族群互动交流,以及当代民族区域自治背景下的汉族族群身份的转换或者改变其音乐的族性等等多重因素导致的,进而造成平地瑶音乐文化的历史与当下的重建行为。这种基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主体性的平地瑶音乐的两种话语表述体系,是在当代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语境中为了分享社会资源而主动寻求的一种族性建构与文化变迁的产物。同时,平地瑶族群边界的移动与音乐认同的变迁行为表明:“现代社会中的族裔群总是在不断重新创造自己。族裔也被不断地重新发明,以适应本族和外界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45)〔美〕凯特琳·尼尔斯·康曾等著:《族裔的发明:族裔在美国》,载马元曦、康宏锦主编《社区性别·族裔·社区发展译选》,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第3页。
结 语
笔者认为,湘、桂边界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是从明王朝对高山瑶实施的军事“招抚”“编户齐民”开始,直至20世纪50至80年代国家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瑶、汉音乐文化身份的合流。作为瑶、汉两个族群传统文化合力建构而成的平地瑶音乐,是高山瑶与汉族传统音乐分别产生“濡化”与“涵化”后的结果,它们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核心文化认同。其中一部分高山瑶被汉化后形成的平地瑶音乐,汉族传统音乐的传入,构成了平地瑶音乐系统的主体性,进而形成了对汉族文化的一种主观认同,或称为“客观性事实”;而另一部分通过汉文化身份转换成的平地瑶音乐,虽然其音乐的族性发生变迁,但是音乐的主体性继续保持着汉文化特色,形成了某种客观认同,或称之为“表达性事实”。另外,平地瑶音乐的族性建构与文化认同变迁问题,从侧面隐喻了历史上的高山瑶与当下的汉族,为了分享社会资源与利益而选择的一种生存策略与文化诉求。换言之,传统音乐的族性建构不完全是基于生物遗传或血亲关系基础上的,而是受到现实社会利益需要或者资源竞争语境下的自我或被“他者”建构的传统文化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