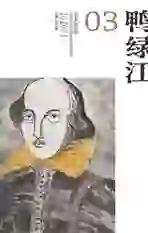浅析《浮生六记》的悲剧性
2020-05-25曾婷颖
摘要:清代乾嘉之际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具有一定的悲剧性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艺术屈服于现实的悲惨,艺术被生活同化而丧失高雅独立性,成为无奈现实的附庸品;二是陈芸人物所拥有的可爱性格同现实的不兼容性;三是在“艺术”和“爱情”两个要素相互联动的基础上,由于相继抽离而流露出的双重悲伤;四是作为回忆主体的沈复本人在书写该作品过程中所流露出的宿命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悲剧的震撼力量。
关键词:《浮生六记》;沈复;陈芸;悲剧;生活美学
中国古人,特别是中国文人,历来就将艺术视为高雅的象征。明媚愉悦处,艺术为美好生活做一补充增添;失意落寞时,艺术世界的构建,往往是以一种理想化和自娱性的方式逃离外部世界的污浊混乱或抚慰内部精神的失意落寞。对于沈复而言,艺术的意义就在于后者。
一、从沈复所生活的年代看《浮生六记》
从宏观背景上看,沈复所生活的年代,“康乾盛世”的繁荣已经逐步“泡沫化”,时局政治和社会风气日益沉闷,文人进入庙堂高阁的热情也逐渐趋弱。从微观个体上看,沈复的父亲以幕僚为生,自己也被安排了同样的职务。父亲权威下的影响和自我切身的经历将幕僚“热闹场中卑鄙之状”的阴暗面烙印在沈复心中。在此双重意义上,对污浊的厌恶衍生出对自然纯真的追求,而艺术便成为逃离世界的重要方式。从吟诗作对到书画创作,沈复都努力地用艺术气息构建另一个世界。他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善于在艺术上另辟蹊径,抒发自我独到见解。在对园林的点评上,他认为当时所受称赞的杭州西湖的湖心亭诸景“反不如小静室之幽僻,雅近天然”,这也突出了沈复重要的审美取向——崇尚自然,厌恶刻意雕琢。
然而,沈复将艺术作为妥善的逃世之方,并非完全割裂同外部世界的交流,艺术对沈复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还是沈复同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沈复没有因幕僚职业的失望而完全对人际关系失去信心,并发挥了自主选择交友的权利。沈复的朋友都带有艺术气息,如善工隶书的鲁半舫、善人物写真的杨补凡、善工山水的袁少迂等,他们通过共同的艺术情趣来建构“美”的社会关系,于萧爽楼雅集时的“四忌四取”约定——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四取:慷慨豪爽、风流慰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便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沈复的艺术带有强大的实践性,如叶朗所说“特别追求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营造美的氛围”,是自我构造整体性、充盈性、自足性的生活氛围和精神境界的体现。同体制环境的奢靡浮躁之风不同,也与市井百姓的小气拘束相悖,他善于发现生活之细节、细节之细微、细微之趣味,并以此为元素创造文人化的栖居环境。将扫墓拾捡的石头作为观赏石、装饰假山、以虫子标本装饰摆件等行为都真正做到了将生活陌生化和诗意化。
这样的艺术世界构建本为沈复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然而,在沈复第二次和妻子被赶出家门以后,二人由于家中经济来源的失去和生病花费的增加,日子愈渐艰难。妻子死后,沈复的生活状况更是每况愈下。他不仅开始售卖字画以换取微薄收入,甚至重新从事当初同艺术相比而显得低劣俗气、自己一度厌恶和放弃的幕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只能作为一种片刻慰藉手段,而丧失了成为一份完整独立的生存指南的可能性,艺术逐渐屈服于现实、服务于经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对“善”作出论述,据亚氏观点,善的事物可以有两种:“一些是自身即善的事物,另一些是作为它们的手段而是善的事物”,这样,在存在着需要时,我们只以满足我们当下需要的事物为善。对处于难以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窘境下的沈复而言,当前所追求的善便只有基本温饱,而非本身就充满价值和令人愉悦的审美需要。当美好生活烟消云散,只剩下在妻子墓前一句“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官,度此残年”的对生活基本生存欲望的渴求时,艺术的地位和价值逐渐发生了转化,从原来的主导性、坚固性到依附性、可变性。这一转化,是艺术从逃离现实的良方演变为服从现实的无可奈何,体现出同现实抗争失败后的悲剧。
而使得这一悲剧性得到突出体现的更在于上文所提到的:沈复艺术能力中的情趣实践能力。因为实践是同现实直接接触的纽带,其存在带有半封闭式逃离的意味,背后折射出的是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渴望同现实的和解和融合,无论是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还是同朋友之间的雅集,都是沈复以自我内心体悟对待生活的方式和渴望同世界和谐相处的召唤。若沈复对艺术的见解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缺少直接转化美的能力,缺少和现实世界的沟通,那么他再次被现实所迫的令人唏嘘程度便不会那么凸显,正是因为有所付出、有所努力,才更宣告了现实摧残建树的残忍和不留余地。
二、 从作品中人物性格看《浮生六记》
陈芸人物的悲剧不仅仅体现在她因血疾而英年早逝的结局,更体现在其所拥有的可爱性格同现实的不兼容性。林语堂先生曾说:“世界有这样的女人是可喜的事”,在他眼里,陈芸是最可爱的。“可爱”一词常被人们用来评价儿童,赞扬的是孩子身上不加掩饰和伪装的活泼心路。而用在陈芸身上,却也显得十分适合。从当时环境下“类”之间的比较来看,陈芸同大部分女子相比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沈复在回忆中也赞叹她“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陈芸非“女子无才便是德”式的人物,她有才情,偏爱李白的豪放,不刻意藏愁思于內心:
吾母诞辰演剧,芸初以为奇观。吾父素无忌讳,点演《惨别》等剧,老伶刻画见者情动,余窥帘见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内探之,俞与王亦继至。见芸一人支颐独坐镜窗之侧,余曰:“何不快乃尔?”劳曰:“观剧原以陶情,今日之戏徒令人断肠耳。”面对老伶人鲜活的悲剧表演,她受剧情感染便不忍再看从而起身而去,甚至“良久不出”,真可谓真性情之表露!同时,陈芸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她做出的几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胆行为:如为公公一心物色妾室、女扮男装只为去水仙庙游玩、同妓女憨园结为姐妹等。然而,这样的性格却使她遭受“不守闺训,结盟娼妓”的罪名,同沈复一起被逐出沈氏家庭。物色妾室本是公公的心愿,无奈却让陈芸被婆婆所怨恨,和沈复在信中对公公习惯性的称呼更成为了她“不敬”的体现;同妓女结为姐妹更为封建大家庭所不容。
这样的独特之处成为了陈芸违背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罪证,然而陈芸真的同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对抗吗?实际上并非如此。为社会眼光所不容的独特只是陈芸性格中的可爱魅力,丝毫不存在主观意味的同当时封建礼教和社会风气相对抗的倾向。陈芸自幼丧父,很小就承担起肩负家庭经济的重担,通过擅长的女红赡养母亲、供弟弟读书,自结婚以来,更是积极遵循夫家旧标准,“事上以敬、初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即使遭遇误解、冷漠和驱逐,她也未有过怨言,反说:“亲怒如此,皆我罪孽”,甚至临死时,还嘱托沈复续娶,以奉双亲。为公公谋取妾室是因为她对公公孝顺用心,只是处理的方式不佳而受人排挤;在她女扮男装而出门时,尚且存在害怕公婆发现而生气、难堪的顾虑,并非毅然决然式的;同妓女憨园结为姐妹更非有意挑战封建权威。事实上,陈芸在对待人际关系上向来善良,在仆人卷走家中财物而离去时,她抛去对当前生活艰难的顾忌,转而担心仆人的安全以及对对方父母的交代。其最交好的两个友人王二姑和俞六姑,一“痴憨善饮”,一“豪爽善谈”,可谓是两个差异较大的性格,但陈芸能成为游离于二人的中间状态,也充分表明了她的交友为人的智慧。
总而言之,陈芸虽有不同于当时封建标准的独特气质,但并非激进的、冲突的“锐点”,从整体上看,该人物更多地具有符合当时社会潮流和评判标准的性格成分。而当这两者共同融合在一个人物身上时,陈芸尚且拥有环境所能容纳的“女子应该是这样”的因素却依旧不能得到认可和接受,只因性格中的独特而受到强有力打压和根本性否定,丝毫不将占据陈芸更多行为的构成成分如乖巧懂事、孝顺公婆、善打理家事等纳入考虑范围和商量余地,因此,其性格中的可爱独特所受环境的摧残程度便可想而知。陈芸临终前“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的一句哭诉,更加充分揭示了该人物受环境迫害的、必然的悲剧性。
三、从“艺术”和“爱情”两个要素看《浮生六记》
对于沈复而言,艺术世界和爱情世界是其平淡安稳的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现实环境对艺术和陈芸的打压,实际上实现了对这两个世界的抽离,将沈复的生活推向曲折和破灭。同时,“艺术”和“爱情”两个要素又是相联相关的,这尤其体现在陈芸参与沈复艺术世界的建构上。如若没有陈芸的点缀和合作,沈复的艺术世界便会少却许多热闹的色彩。
在把日常的琐碎经营出文人的情趣中,“无论植菊、盆玩、焚香、插瓶,每一项都透着陈芸参与的巧慧”。她仿效画中草虫之法使插花“宛然如生”,为沈复营造出“幽韵而无烟”的焚香氛围,甚至发明“活花屏”此种“乡居之良法”,为生活增添了许多小欢喜。在寄居萧爽楼的岁月中,陈芸更是畅意舒心的悠闲生活的最大支持力量:“三白好洁,宅中便是地无纤尘。三白好客,喜与诗朋画友集会,陈芸便是热情的女主人、优秀的厨娘。三白喜小饮、不喜多菜,陈芸便置一精巧的梅花盒,装菜类多量少,可伴二三知己随意取食”。
可以说,陈芸不仅仅是沈复的妻子,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沈复的“知己”,了解他在艺术方面的热情,并帮助他一同参与艺术世界的经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陈芸的去世,不仅仅宣告了爱情世界的破灭,使得青梅竹马从此阴阳相隔,更使得沈复的艺术缺少了另一趣味因素,从而成为个人吟唱的孤单。而艺术世界本应由于更具有独立性而成为沈复的另一支撑,却也由于现实的打压而不复存在。并且,沈复开始贩卖字画,将艺术作为获取钱财的附庸品,实际上是从因陈芸之故同家庭关系决裂而失去经济来源、因陈芸之病而增强经济压力开始的。这样的悲剧境地一旦开始便很难得到缓和甚至愈发严重,天各一方,风流云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成为了沈复伤心的状态回忆,沈复的情感愈发深沉,因为“艺术”和“爱情”二者之间的相互联动和相互拆解,使得沈复不管回忆起哪一个世界、对哪一个部分进行书写时,都体会到了双重的悲剧体验。
四、从沈复本人的个人情感看《浮生六记》
沈复本人在书写该作品过程中所流露出的宿命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悲剧的震撼力量。比如“且恐其福泽不深”、“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陈芸偶有佳句是正常的现象,其英年早逝与李贺的早卒只是巧合;二人期盼月出而却遭受寒热困顿,和无法共白头的结局更没有必然的联系。
虽然沈复在《坎坷记愁》的开篇便说,自己人生中的坎坷是由于“多情重诺”,将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人生悲剧的原因归结到了自身。但从以上婉转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思想带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将原因指向到虚无缥缈和不可控制的“命”,是隐约而朦胧的。而又基于该文本是回忆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成为了人物经历重大坎坷后,面对生活所流露出的无意识感触。这种感触将自我主观意志同命运进行再度抗争的渴望和可能下降到了最低点,呈现出对现实困境产生的疲惫感和无力感。在此基础上的情绪积淀容易日积月累为爆发式的、怒吼式的控诉和悲愤,这就成为了沈复强烈性、感叹性的强音爆破,因此他写出“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和“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等直接的感情宣泄。然而这样的爆破在已经发生的现实面前是无力的,才会出现在文章尾声部分的“从此纷纷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一方面企图拥有一个虚妄美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又不相信生活顺遂会存在再度发生的可能。此时的情感基调便已经下降到最低点的层次,悲剧色彩最终也在这个结点上不断蔓延至最大化。
五、结语
在《浮生六记》中,艺术屈服现实的悲惨、可爱人物陈芸的悲剧、“艺术”和“爱情”破灭下双重要素的联动,以及语调叙说模式中的宿命感四个方面共同构建了该文章的悲剧性。从最集中的意义上看,《浮生六記》的回忆似乎是沈复努力寻找昔日美好和残酷现实二者之间的张力维度和宽广空间,而这一寻找最终以失败告终,便也是最大的悲剧了。而作为读者,虽然文学作品始终同现实世界隔了一层,但因《浮生六记》中人物要素并非是虚构形象,而是现实存在,因此对文学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和冲淡,我们也在接受该文学作品的同时受到其结局现实存在性的不断提醒和冲击,不断感受沈复的心情、心声和心境,加深了悲剧阅读体验。
参考文献:
[1]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梅素娟.浮生六记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07.
作者简介:
曾婷颖(2000.01-),女,汉族,福建省晋江市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