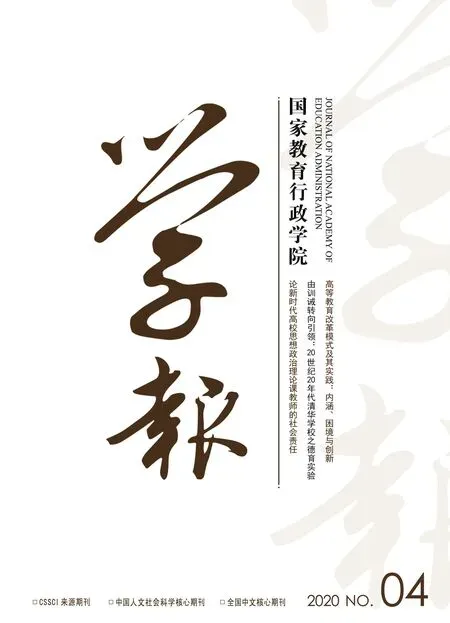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是否有“轨迹”可循?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2020-05-19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接收首批东欧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33名留学生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到中国探索和构筑自己的梦想。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 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长了0.62%。[1]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日益扩大,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有关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情况,以及是否有轨迹可循。本研究试图通过质性研究回应上述问题,进而探寻来华留学生学习情况的 “轨迹”。
国内学界对我国本土大学生学习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近年来,面对社会日益增强的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期待,国内高教界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如 “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团队并产出一系列研究成果。有研究者提出,对大学生学习情况的研究,不仅要剖析人类学习行为的生理与心理机制问题,还要研究学生学习得以产生的文化环境与土壤,认识影响其学习行为的民族文化认知和心智价值传统。[2]然而国内已有的面向中国大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对来华留学生群体关注不足。
国外学者对留学生群体的关注已有相当一段时间,积累了足够数量的研究成果,对留学生群体的研究视角广泛,从最初的临床心理学视角逐渐到社会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近些年又出现了从学生学习和发展视角开展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开展留学生教育,要意识到留学生学习经验的复杂性和非线性[3],以及异质性特征[4]。留学生的个体先前经验、家庭背景和院校特征[5],以及文化和社会资本对塑造留学生学习经验起到重要作用[6]。秉持从本土留学生实际出发开展研究,避免对西方概念和理论持“拿来主义”做派的原则,本项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和分析第一手资料,以展现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全景图式。通过全方位的窥视,建立在本土资料基础上的分析和理论建构,能够展示基本的符合大多数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的图景,揭开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情况。由于留学生跨越国界到异国接受高等教育,因而本研究对其文化环境与民族文化认知、心智模式,予以关注、进行剖析。
二、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的抽样方式是理论性抽样,抽样时只依赖每一案例所具有的理论性意涵,以对建立理论的贡献作为选择样本的考量。[7]本研究通过留学生的不断介绍和推荐的“滚雪球效应”,研究参与者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然而,为了使生成的扎根理论更为稠密,研究者随后放弃了继续 “滚雪球”的途径,先后来到5所城市,主动去留学生公寓和留学生活动区找寻那些能够促进更多类属和面向生成的留学生。当资料里的类属已发展得比较丰厚,在条件、脉络、行动、结果的各个部分联结紧密,类属间的关系都建立稳妥且验证属实,且再也没有新的或有关的资料出现,即实现了理论上的饱和时,本研究理论性抽样结束。研究者自2013年开展来华留学生学习情况研究以来,走访5所城市的11所高校,从2014年3月至2019年12月,先后对118位来华攻读学位的留学生进行时长1—1.5小时的深度访谈,并通过课堂观察、与其一起就餐等课外场所的互动,试图了解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情况。有时为了加强访谈的深度和把握动态性特征,研究者对留学生进行了多次访谈。118位留学生中,所在学校既包括 “双一流”高校 (4所),也包括非“双一流”高校 (7所),生源国籍广泛分布于亚洲 (61人)、欧洲 (29人)、北美洲和南美洲(12人)、大洋洲 (2人)以及非洲 (14人),学段覆盖本科 (44人)、硕士在读 (60人)、博士在读 (14人)。本研究以访谈资料为基础,依次进行了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与选择式编码。在对不同类属间的关系进行比照和分析后,得出 “与留学生发生作用的载体”“个体特征”“对载体的影响”“对个人的影响”四个类属,最终归纳出两个编码类属,即留学生学习经验的 “作用力”、留学生学习经验的 “反作用力”,以及一个核心范畴,即 “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本研究编码结果展示 (见表1和表2)。
三、研究发现
(一) 留学生学习经验的形成和影响因素
留学生学习经验嵌入在国家间关系、来源国国家发展、社会结构、制度环境、精神文化、家庭、个体特征之中,被其影响着和 “紧裹着”。每个个体都无法割裂来源国的家庭、组织、文化、国家的 “纽带”,也无法抹去它们带来的 “烙印”,他们在留学学习期间不断回顾和解读各种记忆和经验。留学生进入留学目的地国学习,与留学目的地国的载体发生了关系。因此,留学生也难以避免地受到留学目的地国载体对其的影响。从而,个体经验、家庭脉络、文化脉络、社会脉络、来源国和留学目的地国的组织、互动网络、来源国与留学目的地国的关系、国际形势等这些不同因素作为在后台“隐匿的脚本”维持着一种纵横交错的状态并作用于留学生,对留学生学习经验产生影响作用。
1.与留学生发生作用的载体塑造着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
(1)留学生来源国文化和价值观
留学生学习经验深受其长期浸没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紧裹。文化、价值观及信仰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也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共享的符号系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对课堂上开展活动的目标以及价值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来自亚洲国家的研究参与者讲述,他们偏好于中国教师以讲授为主的课堂方式,因为这与他们以前接受的教育 “更为接近”,他们在中国感受到一种 “文化相近性”,因而感到比较适应。来自欧美国家的研究参与者讲述,在欧美文化中人们被鼓励大胆而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欧美学生之前的学习经历中自我独立性特征较为突出,他们不希望老师在课堂上花大量时间和精力重复书本中已有的东西,当他们无法认同课堂学习活动的目标和价值时,往往 “我行我素”,选择自主上课抑或是不上课。留学生来源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形塑着留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留学生可能因为这些影响的印记而内化了参与的动机。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来自同一国家的留学生群体往往具有普遍的共性的特征。韩国留学生的参与就受到本国留学生群体规范的影响,他们往往一起来上课,一起下课回公寓,一起参与课外活动,似乎是 “被粘在了一起难以分隔”,韩国留学生金提到,在韩国文化中崇尚集体文化,“倘若不属于某个组织就觉得遭到了排斥,很不踏实的感觉”。

表1 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的 “作用力”部分编码结果

表2 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的 “反作用力”部分编码结果
(2)留学目的地国组织和制度安排
留学生所在的留学目的地国组织及其制度安排不仅为留学生提供了平台和发展机会,同时也对留学生学习经验起到了管理、约束和制约作用。留学生的时间不只是滴滴答答的钟表时间,留学生的空间也不再仅仅是满足其生活和学习的载体,而是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被固定下来。然而,“制度世界的客观性,不管它看上去对个体来说有多巨大,都是一个由人创造、构建的客体”[8]。留学生管理的制度性安排是由学校管理者所创造,因而被融入了管理者的逻辑,留学生的时间和空间也被掺入了组织的意义的构建。居住区和教学区是留学生在华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其进行学习活动和互动的基本空间。学校从方便管理出发对空间布局进行规划和安排。学校教育时间制度对维护学校教育的秩序、保障学校教育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功用。学校管理者确信这种结构性原则派生出来的程序和路径能够实现留学生个体生活和学习时间最大利用率,获得最大化学业收获。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承担起留学生在中国的 “家长监督角色”。
(3) 家庭载体
家庭载体对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的影响作用体现在,父母有意识地引导和塑造或者父母无意识的思维、情绪、行动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留学生在留学目的地国学习经验的积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传递的心智资本的影响,家庭传递的心智资本直接影响留学生的行为方式、情绪类型及思维定式,从而影响其在留学过程中的感知和经验。西方已有研究发现,对大学系统更了解的父母有助于帮助子女获得更多文化资源。[9]本研究中,有不少留学生提到自己的父母是大学生,或者曾经也是离开本国去留学目的地国学习的留学生。塔吉克斯坦留学生拉扎比提到父亲曾经是一名留学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父亲把曾经对留学学习的理解和实践经验传递给正在海外留学的子女。父母通过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子女习得如何在陌生的氛围中与他人互动并参与新环境下的活动,以较好的人际互动模式步入新环境。
2.留学生个体特征影响着其学习经验
(1)个体先前经验
留学生学习经验是对其先前经验的延续、改组或改造,经由惯习所引导,同时也受先前互动结果的影响。人们的行动绝大多数是凭惯习而为。布迪厄认为惯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来自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 (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10]早期实用主义者之一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认为,人的意识并不是从一个孤立的经验跃入下一个孤立的经验,而是将此前经验融入当前的阶段,创造出累积性经验。[11]个体心智模式具有一种思维惯性的力量,对留学生学习经验的影响作用非常显著。正是由于心智模式的作用,留学生在思维图谱中往往进入 “路径依赖”。泰国留学生米拉和巴基斯坦留学生莫辛很欣赏中国人做事的方法,相比较而言,他们认为自己做事“比较被动,比较慢”,将其归为长期受到本国人 “懒”和 “慢悠悠”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也希望能像中国人那样主动积极快速地做事,但认为自己 “做不到”。
在留学生的社会认知系统中,存在一种视为当然的 “背景知识”,一种类似于舒茨的 “手头库存知识”的非反思性知识。部分留学生往往借助 “手头库存知识”,获得亚洲学生 “害羞、敏感、自卑、不喜欢说话、比较听话、学习用功”,而中亚学生 “爱迟到、懒、打架、不团结同学、很难管、在乎钱”,欧美学生 “聪明、爱好广泛、不用功、自主性强、来中国只是体验”等刻板印象。访谈中,许多留学生将他者与自己划分为他群体和我群体,从而得出了他群体和我群体的分类。如果经过非反思性的 “手头库存知识”或刻板印象进行社会比较、社会评价,只会不断强化和再生产我群体和他群体的符号边界。
(2)个人能动能力
倘若留学生对留学体验感知不是那么积极,但如果能够积极主动地自我调适——而不是畏缩或回避,是可以获得较积极的学习体验的。留学学习体验积极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试图建构自身生活意义的个体们的主观决定。由此可以说,感到被孤立、自我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他们自身合作的结果。这种把自我处境完全推诿到外界的意识寄居于他们的身体内部,身体化了的意识随即又反过来又强化他们模式化的思想和行为。本研究中,那些有着明确的动机特别是内生动机、积极思维和态度、自我效能感、自我反思力以及复原力的留学生往往获得较为积极的留学学习经验,他们有着包容性的跨文化能力和适应能力,即个体调整过去的文化方式、去学习和适应新的文化方式,创造了与留学国的和谐关系。
(二)留学生学习经验的 “反作用力”
从 “反作用力”来看,留学生学习经验会丰富其个体经验,并对与其发生作用的载体,包括对其家庭、组织、互动网络、制度、文化、社会、国家、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
1.个体经验的丰富
通过与留学目的地国的互动,那些对留学目的地国感知较为积极或自我能动性能力强的留学生会吸收留学目的地国新的惯习,留学生的经验图示、意义架构、生活方式等获得了多样化、丰富化和复杂化的重塑。有不少留学生确定了人生的意义和未来志向,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里尔别克致力于 “在两国间搭一个桥梁”,“我知道每个留学生都会说 ‘我一定要在两国之间搭一个桥梁’,对我来说这不是大话,我就是要搭一个桥梁,让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通过我得到一定的促进”。随着离开本国土壤的那一刻起,无论其有意还是无意,留学生已不再是持有一种观念和惯习的封闭个体,而是或多或少融入了留学目的地国甚至是第三国家的惯习和行动方式,在多元观念和惯习的碰撞下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个体。接受访谈的留学生提及 “更爱中国”“更理解中国”“开拓视野”“对多元文化更加包容和理解”。泰国留学生米拉告诉我,来到中国对中国有所了解后,“更理解中国人,更爱戴中国”。
2.留学生的 “增殖效应”
留学生一方面受到载体和个人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参与到对与其发生作用的载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及自我的建构过程中,比如留学对世界形势、留学目的地国与来源国的国家关系、留学所在院校的制度安排和课程设置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在交通、通讯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亲属、朋友人际互动网络的推荐使得留学迁移态势像滚雪球般发展,并且他们对留学国家、城市和院校的选择受互动网络影响往往呈现趋同性和模仿性特征,即所谓的留学生的 “增殖效应”。留学生的增殖效应体现在每一个留学生都有可能推荐其互动网络中的成员步入到留学的轨道中来,甚至是步入到跟其相同的留学目的地国、留学城市以及留学院校。土耳其留学生阿斯兰推荐她在土耳其的同学和朋友来中国留学,认为来中国留学不仅可以学好汉语,对未来找工作也有帮助;但是她的朋友们更愿意去伊斯兰国家,因为在饮食和习惯方面较更为适应。阿斯兰希望她的朋友们能亲自来到中国亲身体会和感受中国的生活,可能便会改变想法从而来到中国留学。
3.中国形象的直接构建者和传播者
来华留学生既是中国形象的直接接触者,也是中国形象的直接构建者和传播者。作为“中国印象的传导体”以及 “中国形象掷地有声的发射体”,留学生可通过话语将其在华学习经验传递给其他载体。倘若留学生 “传导”的话语是负面消极的不切实的信息,那么将成为极具穿透力的反映着对留学目的地国形象的 “标记物”,通过留学生的分享和传播出口至留学生所在的国家乃至更多的其他国家,从而对留学目的地国甚至是留学目的地国与来源国的关系、国际形势都会产生影响。尽管 “感知”是个体的认知行为,不能推广到群体的共性和同质性,但是,留学生可通过话语载体把对中国的感知和印象传递给其他人。[12]
四、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留学生学习经验是个体跨国学习的实践与体验,看似毫无轨迹可言,让人捉摸不定,事实上,自他们留学动机产生、留学行为实现到对留学目的地国感知、人际互动、学习投入以及收获的整个过程,他们的行动选择都遵循着可以把握的 “轨迹”。本研究发现,留学生学习经验受到与留学生个体或直接或间接、或在意识层面或在非意识层面发生作用的载体 (包括社会结构、制度环境、精神文化)及留学生个体特征 (包含留学生先前经验)共同作用的形塑,同时留学生学习经验又对与其发生作用的载体、留学生个体特征产生影响。留学生学习经验正是在 “作用力”与 “反作用力”间如此循环往复。留学生学习行为的背后是高度匿名性的抽象事物的集合,社会、文化、组织、个体先前经验都是对其学习经验有投射作用的集合。他们的跨文化学习旅程也受到了跨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留学生学习经验,需充分认识到这样的不同因素的交织与互动关系,不能简单地给留学生归类或者标签化,不能将其从具体的社会、文化、组织、个体先前经验情境中抽离出来。
本研究展示出符合大多数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的图景,部分在欧美等国家学习的留学生所遇到的问题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比如,国外相关文献大多认为留学生有感到被排斥、受到歧视的消极感知。[13]在这样的逻辑之下,除了跨国学习者的身份之外,留学生似乎还隐隐被视为 “弱势群体”[14]、“受歧视群体”[15]来看待,部分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因此而对自我进行怀疑,丧失自信心。在本研究中,几乎所有留学生都对中国感觉良好,没有留学生明确地表达受到歧视或者受到责难的经历,更不认为其被视为是 “弱势群体”。再如,国外研究发现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对师生关系和师生互动不满意,他们希望教师能对他们给予 “清晰的指导、可以对学生有细致的关心,甚至是学生可以追随的道德典范”[16]。然而现实并不如其所愿,他们在那里找寻不到这样的 “理想老师”[17]。而本研究中留学生访谈者普遍感到与他们本国世界中的老师只负责学生的学习指导有所不同,中国老师亲切和蔼,不仅在学习上用心指导,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学生嘘寒问暖。他们对中国老师角色感知是 “亦师亦友亦父母”,不少留学生对他们的中国老师非常认可。
根据本研究所生成的 “留学生学习经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扎根理论可以看出,国家、组织、文化、家庭、其互动网络、自身经验都会作用于其在留学目的地国的学习经验并受到这些不同载体的影响再反作用于其载体及个体特征。因此,要提升来华留学生学习经验,需要国家、高校组织、教师、中国学生、来华留学生本人、留学生家人、媒介与当地社会这些与留学生发生作用的多方 “载体”的共同努力。多方载体需要创造滋养和提升留学生学习经验的条件,根据学生经验的不同特点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使留学生经验不断获得改造、提升和发展。
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要提高政府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整体统筹能力,用系统思维构建来华留学生教育治理体系,协同教育、就业、市场、移民、服务等多方部门,构建包括公共外交、教育、人力资源、经济、法律事务、医疗等在内的多维内涵的来华留学工作社会支持体系;高校和教师需要关注留学生个体的发展需求。高校所面临的教育对象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学习动机和基础,以及不同职业追求的具有多元化特点的学生。因此,教师需要关注每位留学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帮助留学生提高对中国的感知促进其学习投入。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改变 “刻板印象”,促进不同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留学生需要主动提高自我能动能力,包括激发个人对发展和学习的内生动机、培养乐观态度和积极思维、提升自我效能、注重对反思力和复原力的训练,积极投入到课堂学习中,主动参加学校的学术讲座等课外活动;留学生的家人需要意识到家长的心智模式对留学子女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积极引导,帮助留学子女积极乐观地思考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留学生对当地社会的感知与社会成员息息相关,社会成员需要提升公德意识,媒体和出版行业也可以在促进留学生对中国形成积极感知方面有积极作为。
总之,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一项涉及面广、需要较大投入的系统性工程。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需要政府、高校、教师、留学生本人、中国学生、其他有关联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周作宇教授对本研究给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