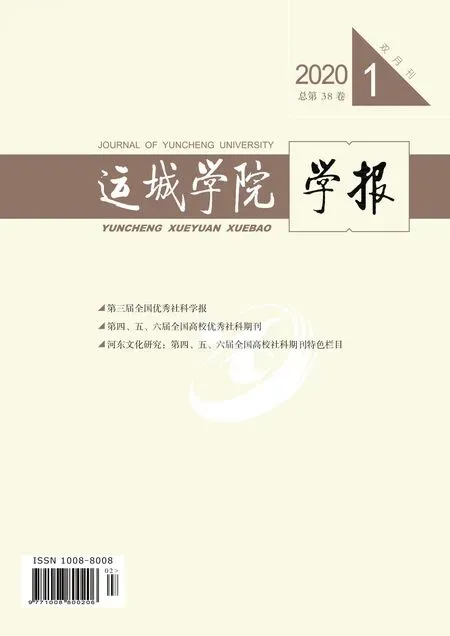论汉代的汾阴后土祭祀
2020-05-19姚媛媛
姚 媛 媛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西安 712038)
后土祭祀文化是中国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是农业根本,可滋长万物,有父天母地之称。古代社会为求五谷,统治者及民众会定期祭祀大地,由此形成后土祭祀文化。汉代在前朝基础上,完善了祭祀体系,“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一千五百四十”[1]97,而汾阴后土祭祀则是“三大祠”之一,并成为后土祭祀的源流。
有关汾阴后土的研究,学者从考古角度首先取得突破。1930年卫聚贤、董光忠等人在汾阴考察新石器时代遗址[2]71-81,在此发现了汉汾阴后土祠遗址。二人确定汉武帝到达的介山是万泉介山,而非介休介山,并认为汉汾阴后土祠就是后来的介子推祠,在旧万泉县东南的阎子疙瘩。李零等人的《汾阴后土祠的调查报告》[3]认为,卫聚贤等人在旧万泉县东南的阎子疙瘩发掘的是汉武帝祭祀汾阴时临时歇脚的行宫,即介山宫,通过实地考察,明确了汾阴后土祠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整个过程实地考察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分析了汾阴后土的渊源概况,价值颇高。除以上两次实地考察外,近年对于汾阴后土的研究也卓有成效。王世仁在《记后土祠庙貌碑》[4]273-277中,参考以往史料,对金代后土祠庙貌碑做了全方位论证,为研究汾阴后土奠定了重要基础。陆峰波《历代皇帝祀汾阴后土考》[5]85-87则主要考证了历代皇帝祀汾阴后土的时间及次数,但结果与李零等人的研究有些许出入。李玉洁在《汾阴后土祠神灵形象演变探析》[6]36中论述了后土内涵,提出后土的女性身份,并被世人所认可。向晋卫、穆葳在《秦汉时期的后土崇拜——兼论汾阴后土祠的建置背景》[7]16-20中对秦汉时期汾阴后土祠的创建做了分析,限于篇幅,并未对汉代的汾阴后土祭祀做全面论述。后世汾阴后土祭祀的几度繁荣都是在汉代祭祀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有必要对汉代的后土祭祀文化做全面论述,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此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汾阴后土祭祀的产生
汾阴后土文化渊源甚广。“后土载在祀典,肇自轩辕扫地而祭,其来古矣”[8]569,黄帝轩辕氏最早在此扫地为坛,开创祀后土先河。现今虽汾阴后土祠有黄帝扫地坛,但为后世附会所见,尚无考古资料辅证。此后后土形象历经了多次变化,终于形成了女性身份,也就奠定了父天母地思想的基础。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列国在依靠自身实力获取霸权的同时,也需要宣示自身的正统性。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周以来的祭祀传统被各国所看重,因此天地、祖先及山河湖海等祭祀文化在此时期得到进一步传播发展。秦以来,祭天“畤”文化兴起。西汉建立后,雍五畤、甘泉泰(太)畤祭天文化不断完善的同时,后土祭地文化也逐渐兴起,其产生与宝鼎文化密切相关。
汉初在汾阴设立后土庙主要为了“祠周鼎”。汉文帝时期,新垣平对文帝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9]1383。相传禹铸九鼎定天下,接下来的夏商周朝继承了九鼎,也就代表着正统,但周被灭后,鼎也不见踪迹。战国之际传言,代表正统的周鼎落入泗水中,秦始皇当年就命人捞鼎,结果不获。新垣平向汉文帝进言,泗水当中的周鼎逆流而上,可能出现在黄河中游的汾阴,此论明显是骗术[10]632,但文帝却深信不疑。“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9]1383。但后来新垣平因事被诛,此庙便成普通民祠。
汾阴后土正式成为祭地之所,始于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得鼎汾水上”[11]182,史家推测应为纪念此“祥瑞”,汉武帝遂改元为“元鼎”,宝鼎对于汉武帝的意义不言而喻。元鼎四年(前113年)冬,汉武帝在雍祭祀时,大臣议论道:“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9]461当时强调阴阳有序、天地对应,天被冠以父性,地也因滋生万物的属性,被冠以母性。汉武帝完成雍五畤祭天,但拥有母性人格的后土却尚未祭祀,因此大臣认为礼制不对应。当时的太史公、祠官宽舒等人依古制,提出了系列礼仪:“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9]461此论初步形成了后土祭祀规制。当时“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11]1222,汉武帝认为乃祥瑞,故“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9]461至此,汉武帝在汾阴脽上正式设立后土祠亲祀后土,礼制如同祭天,规格甚高。
宝鼎的再次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汾阴后土祭祀文化。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毋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9]464-465。汉武帝为保稳妥,遂咨询年老博学之人,并派人查验,此举正是渴望得到确定无疑的答复。使臣查验后,“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11]1251,得出了汾阴所出为宝鼎的结论。这次出鼎事件,奠定了汉代帝王崇尚后土祭祀的基调。
汉代汾阴后土祭祀能够产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地理位置看,汾阴当时属于河东郡(今山西万荣),属于司隶校尉管辖范围,且距长安较近,水陆交通便利,方便帝王祭祀巡游。从地形看,此地地处汾河和黄河的交汇处。因泥沙冲击,遂形成河中凸地,称为“脽上”。而“夏日至礼地祇于泽中之方丘”[12]1255,泽中方丘的地形,是祭祀地祇的绝佳场所。而汾阴“地形诡异,神道依凭,中断洪流,揭成高阜。俯联修壤,崛起而崔嵬;下望平皋,斗绝而盤郁”[8]549,此地地势较高,曲折陡峭,神秘壮观,正符合祭祀所需要的环境氛围。宝鼎的出现为此地带来了诸多“祥瑞”,其特殊意义,前人已有研究[10]632,不再赘述。河东郡汾阴县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汉武帝开创了帝王汾阴后土祭祀的传统,汾阴后土祭祀迎来了发展的上升期。
二、汉代帝王祀汾阴后土概述
据考证,历史上曾有8位帝王19次亲至汾阴祭祀后土[5]85-87,而汉代则有5位帝王15次亲至河东祀后土。汉代帝王祀汾阴后土情况参见表1[13]13-14。

表1 汉代帝王祀汾阴后土表
自汉武帝祀汾阴后土始,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光武帝又多次到河东祭祀汾阴后土。据表1,汉朝帝王祭祀汾阴后土活动特点如下:地理位置上,汉朝的政治中心长安、洛阳,都与汾阴相近,方便帝王祭祀。祭祀目的上,“朕以眇身讬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11]185,农乃立国之本,主要为百姓祈求五谷丰盛,此举正符合了当时社会现实,也从侧面反映了后土为土地之神的属性。祭祀时间上,汉武帝作为首位亲祀汾阴后土的皇帝,开辟了三年一祀的惯例,时间基本固定。祭祀路线上,基本都是东向北上,但具体路线见缺。虽如此也可从只言片语中窥探一二,“簸丘跳峦,涌渭跃泾”[11]3536,说明去汾阴可能从长安出发跨越渭河、泾河,一路颠簸,可见祭祀之路的坎坷。另外,“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11]1254,汉代曾在黄河边设汾阴渡,说明当年帝王很可能在跨越泾渭后向东北方向行进,过黄河而到汾阴。祭祀礼仪上,史载以“黄琮礼地”。汉代帝王祀汾阴后土是在泽中方丘,祭品比较单一,如黄犊、太牢,服制尚黄等,资料见缺。汉代的汾阴后土祭祀逐渐走向正规化、系统化、常态化,表明祭祀后土已成为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祠祭众多,但困于现实,废除淫祀的呼声日渐高涨。帝王离京前往各地祭祀,虽显诚心,但路途遥远,安全指数低,且西汉中后期祭祀花费已成重大负担,国力不支。汉元帝时,朝臣就对此有过讨论,准备废止不必要的祭祀活动。礼制的实际调整始于汉成帝。汉成帝接受匡衡的建议,把雍五畤和汾阴后土等祭祀活动迁到长安一同祭祀,以此减免开支。但后来匡衡坐事被免,“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11]1258,众人认为匡衡之所以如此,就是因其谏言废弃地方祭祀,加上成帝无子,太后终下令,恢复雍五畤、汾阴后土等。之后汉成帝多次到汾阴后土祈福,但都未达到理想效果,因此地方祭祀渐遭冷遇。王莽时期,礼制得以最终定型。诸多地方祭典被迁到京师附近,从此确定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并被后世沿袭。
总之,汉代帝王祀后土已形成基本规制,且因时发展,最终演化为北郊祭地,深刻影响了后世礼制及政局发展。
三、对汉代帝王祀汾阴后土的认识
自汉文帝在汾阴设庙祠鼎,至汉武帝真正设祠祭祀,到最后北郊祭地的确立,这一过程是皇权与神权相互利用、共同博弈的结果。汉代皇权较后世稍弱,为巩固专制皇权、加强精神领域的绝对控制,统治者多管齐下,祭祀为主要内容,特别是汾阴后土祭祀的出现。汉代统治者费尽心力地打造祭祀文化,其目的与现实统治密切相关。
从后土宝鼎文化看,后土文化与宝鼎相联系,是汾阴后土存在的特殊之处。后土大地之神的属性,寄寓着百姓祈望丰年的殷切希望,人人皆可祭祀。而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将人神交流的渠道所垄断,规定了只有皇帝才能代表民众对话后土,将后土祭祀权紧握囊中,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此举是将后土人格化,更将自己神格化。汉文帝在汾阴临河设庙的意图是祠周鼎,汉武帝时期宝鼎出现,众人一致认为,“陛下得周鼎。”[11]2797此说即是附会汉王朝继承周朝遗产、本为正统的理念。“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9]465,宝鼎的确切年代不易断定,来源更无法确认,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时人将此鼎附会为受命而王的象征。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11]2798吾丘寿王认为,本朝顺应天命,这是上天给予大汉的馈赠,因此应为汉宝,此论赢得了汉武帝的大加赞赏。吾丘寿王言明鼎为“上天报应”,其实就是从天人感应角度作出的有利于汉王朝的言论。这两种理解虽异,但无一例外都有着为统治阶层服务的目的,群臣乃至汉武帝都知晓其政治意义,也就心照不宣地将鼎秘密供奉在甘泉宫,此举是借“祥瑞”事件强化正统性的举动。唐朝也有宝鼎出现,也掀起过新一轮的祭祀高潮。官方借自身优势垄断了解释权,强化自身与上古先贤的联系,可以说如出一辙。
从礼制系统看,汉代继承秦代的雍畤祭天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北畤祭祀黑帝,由此形成雍五畤祭祀,后演化为甘泉太畤,又在因缘巧合下进行了后土祭祀。除此之外,在长安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宗庙祭祀文化。这样西方的甘泉祭天、中央的长安祭祖、东方的汾阴祭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祭祀线路,横跨了汉王朝的中间疆域,标志着汉王朝祭祀系统的正式形成。自此以后,汉代帝王都予以谨守,特别是汉光武帝即位后恢复西汉祭祀礼制的举动,就是表明自身奉行刘姓祖制,乃为正统。这一方面是汉代尊崇祖制孝文化的微观反映,另一方面则是贯彻汉王朝统治理念的重要方式,汉成帝在罢黜多项祭祀活动后遇到了“异事”,刘向回答说“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11]1258,可见西汉王朝的礼制是不可轻易撼动的。
从实际影响看,后土祭祀与其他祭祀形式都为帝王的统治工具。“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11]3522,汉成帝已废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等地方祭祀,将其迁到京师附近统一祭祀,但之后其却出现常年无嗣的“凶兆”,由此引发众人恐慌。受当时社会风俗的影响,为避免更多“不详事件”的发生,汉成帝随即便恢复了地方祭祀系统,此举明显是有求于后土神灵。但时人对此也有异议,扬雄在《河东赋》中用绚丽的辞藻描述了汉成帝祀后土的盛况,其实是劝谏汉成帝“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11]3535,表面看是当时国力难以支撑浩大费用,实则帝王沉迷于各种“祈求神灵”事务中,忽略了现实统治。汉武帝时期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在此阶段已不复存在,安于享乐、铺张浪费严重。扬雄等有识之士意识到,如果统治者再不身体力行、力挽狂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可能会受到挑战。巡幸地方早已变为统治者荒靡政治的重要内容,相关人员很快以变革礼制为契机,借此挽救王朝危机。
汾阴后土祭祀乃汉代盛事,时人对此有所深思。汉武帝在汾阴祀后土时曾作《秋风辞》,其中“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14]1180,描述了当时汉武帝及群臣在祭祀完后土泛舟汾河水面的盛景,鼓声隆隆、箫声阵阵,进而引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感慨。历来学者对《秋风辞》的解释存异,但从汾阴祭祀事件本身出发,尽管后土祭祀场景隆重,汉武帝发出年少欢乐却躲不过衰老哀情的感慨,与以往雄心壮志、意气风发的评价不同,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有血有肉、敏感多思的汉武帝形象。作为帝王本欲通过祭祀方式一方面获得天地神灵保佑,另一方面则希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也知道生老病死、欢乐哀愁的自然规律,折射出其无可奈何的心境。如果说汉武帝的《秋风辞》是对人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宏观忧思,扬雄的《河东赋》则是对后土祭祀的微观思考,“齐法服,整灵舆,……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羲和司日,颜伦奉舆,风发飙拂,神腾鬼趡。千乘霆乱,万骑屈桥”[11]3536,扬雄用夸张的词语描绘出了汉成帝祭祀汾阴后土的盛大场景。车舆服制齐备、人员准备充分,一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这样豪华的场景必定是建立在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之上。汉元帝初元四年祀汾阴曾下诏,“赦汾阴徒”[11]285,虽未言明具体是由,但推测这些汾阴刑徒应为汾阴祭祀而修建工事之类的相关人员。汉代在进行帝陵等国家项目时,刑徒是主要劳动力,为了顺利完工,刑徒的待遇很是凄惨,汉景帝阳陵陵园中就有刑徒墓地,当时出土有带刑具的刑徒尸骨。后土祭祀虽不及帝陵的营建,但作为国家项目,必定会驱使大量刑徒从事祭祀的准备工作。西汉后期王朝财力匮乏,已难以支撑起外出巡游的庞大支出,但当时却需依靠神灵的力量达到政治目的,时人对此议论纷纷,这也可以看作是西汉后期礼制变革的一个缩影。
汉代汾阴后土故事在后世考古中有所发现。从出土文物看,学者在汉武帝祭祀汾阴后土的行宫遗址旁,发现过长乐未央瓦当、回纹铺地方砖、砖瓦等建筑材料[3]88,96。这些信息明显指向汉文化,且“长乐未央”内容的瓦当本就是皇家宫殿所用。在汾阴出现此类遗迹,即可说明原先建筑的等级之高,规模之大,也可想象当时汾阴后土祠的宏伟和祭祀场景的盛大。另外汉代在此出现的宝鼎,在后世仍有出土。结合史料,此地春秋战国时期为魏国汾阴故城,对岸即为芮、梁等诸侯国,说明此地曾存在大规模的诸侯贵族墓葬,梁带村芮国诸侯墓就在汾阴对面。此地又处黄河、汾河交汇处,在河流冲刷下,诸侯陪葬物被冲击在黄河中不断冒出,这种情况实属正常。但因地质变迁,如今尚缺乏强有力的考古资料予以证实,因此只能在借助现有资料予以分析。汾阴后土祭祀虽在汉光武帝之后再无兴起,但后来的前秦苻坚、唐玄宗、宋真宗等都在汉代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了汾阴后土祭祀,而且规模和礼制更加健全。汾阴乃至河东郡因皇帝的到来,焕发出新的生机。
因帝王的重视及自身独特的文化意义,汾阴后土祠成为延续至今、唯一存留的汉代祠庙。从这点来说,皇权对后土祭祀的承认与拔高,才促进了汾阴后土的辉煌发展。后世随着统治理念的成熟,神衹祭祀已被皇权加以利用和改造,逐渐成为皇权的附庸。但后土信仰并未因从属于皇权而失去了它本身意义,因时代及科学认知的局限,统治者在无法解决现实困境的条件下,还是会求助于神灵,这使得后土信仰在民众间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因此,汉唐以降,民间后土祠庙增多,后期更是遍布基层。汾阴后土祭祀真正始于汉武帝时期,并最终成为官方祭地之所。汾阴后土实现了历代帝王的宏愿,而历代帝王的亲祀,也最大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祠庙祭祀和民间信仰的形成。二者相互作用,充实并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