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傅雷的“君子之交”(下)
2020-05-19周立民
周立民
上海巴金故居 辽宁省作家协会
“算是替中国出版界开开风气”
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翻译多了,傅雷想换换口味,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以后想先译两本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换换口味,再回到巴尔扎克。”[1]对他要译的梅里美的这两部小说,傅雷谈过看法,还保留了钱锺书对于别人译本的看法:“梅里美的《高龙巴》,我即认为远不及《嘉尔曼》,太像侦探小说,plot 太巧,穿插的罗曼史也 cheap。不知你读后有无此种感觉?叶君健译《嘉尔曼》,据锺书来信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2]大约正是对于原有译本的不满意,傅雷才再译一个本子。《嘉尔曼附高龙巴》,平明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印数为一万册。傅雷翻译用的底本(或参考本)借自巴金,于是便有了傅雷这封还书帖:
前承
惠假《嘉尔曼》原作二种,谬以为早经奉赵,顷整理书柜,方始发见仍在敝处。未老已昏愦若此,愧甚愧甚。敬乞
巴金先生 见谅为幸
弟怒庵拜启
二月二十七日[3]
梅里美,傅雷译作“梅里曼”。对这个译法,巴金在给妻子的信里表示过不同的看法:“这两天在这里看了好些书,采臣寄来的书大半都看过了。梅里美的东西不错。傅雷译文还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译作梅里曼,我颇不赞成,因为嘉尔‘曼’和梅里‘曼’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拼音。‘育才’照原来的音应该是‘何塞’。”[4]“颇不赞成”,然而印在书上的依旧是“梅里曼”,说明平明社和巴金不以己见为尺度,尊重傅雷。
傅雷与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这基于作为文化人的巴金对文人个性、习惯的尊重,他放手让傅雷按照自己的标准、个性去译书和处理稿件,从排版、校对到装帧设计,作者都享有极大的权力和自由。这一点,傅雷跟朋友们提起甚至不无得意,他说是“为所欲为”:“问题到了我的‘行内’,自不免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好在我老脾气你全知道,决不嗔怪我故意挑眼儿。——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书均由巴金办的‘平明’出版,我可为所欲为。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鞭长莫及,只好对自己的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5]傅雷说,他在装帧、版式乃至书的校对上的讲究,“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此言不虚。他有一封信中谈到工作状况:“这一年来从头至尾只零零星星有点儿休息,工作之忙之紧张,可说平生未有。……除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之极!),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气了。但第三四册的校对工作仍须继续。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6]
平明社,同在一城,相互来往的工作情况,没有留下太多文字材料,等傅雷的书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出时,因处两地,倒是留下不少工作信件。傅雷的“最严格”从这些文字中清晰可见,而且傅雷无形中将人文社与平明社对比起来,以平明社为标准要求人文社。将译本移到人文社出,一是平明社即将面临公私合营,行将不存;二是时任人文社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楼适夷是傅雷的老友,屡屡邀约。“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了,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7]三是傅雷没有直接说,人文社是国营社,平明是私人社,当时的文学出版正逐步纳入整体规划,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中,私营社给国营社让路责无旁贷,巴金和傅雷都不好多说什么。
移到人文社中,傅雷降低要求但是也力争自己的权利,关于校对,他致信出版社强调:
二、校样本人需看初校二校两遍(过去前后四校均由本人亲自,今在北京排,为节省时间起计,减为二遍),但有数点声明:
甲、本人每次校对,文字均有修改,虽然不多,但是一定有。因文章多看一次,必然多少会找出毛病来。
乙、版式的整齐美观,本人十余年来无时不加注意,故初二校样上常有统行情形批出,务请谅解。[8]
在版式美观上,他始终坚持:
兹为服尔德《查第格》及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二稿事奉渎。自胜利以后,所有书稿前后校对,均亲自负责对底,因(一)对于出版格式,可随时批改,力求美观,合理;(二)对内容文字,多看一遍,即可多发现毛病,多修改一次。故一九五三年十月,适夷兄来沪商谈为将由平明转移人文,并约定以后专为人文翻译时,弟即提出均在上海发排,以便亲自照顾,免京沪间寄递校样,耽误时日。
至于弟坚持要各章节另起一面的理由,是因为古典名著不能与通俗文艺同样看待;《查第格》全书不到一八〇面,薄薄的本,很像小册子,不能单从节省纸张着眼。《于絮尔·弥罗埃》也要每章另起一面,是因为巴尔扎克的作品都很复杂,有时还相当沉闷,每章另起一面可使读者精神上松动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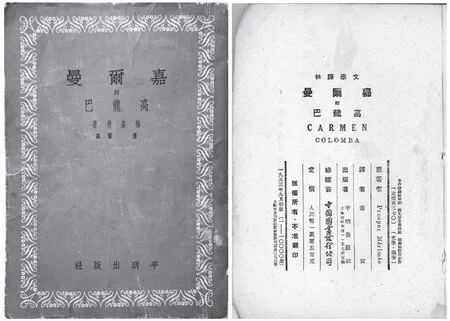
傅译《嘉尔曼附高龙巴》封面及版权页

1954年2月27日傅雷致巴金信
总的来说,我处理任何事情,都顾到各个方面。校样从头至尾要亲自看,为的是求文字更少毛病,也为的是求书版形式更合理美观,要在上海排,为的是求手续简便,节省时间,也免除与排字房的隔膜。[9]
他甚至为书名中的书法题词中,改用繁体字和简化字,而与出版社争辩:“在此全国上下提倡百花齐放之际,不知贵社能否考虑封面手写字体可由书写者自由,一方面为我国留此一朵‘花’,一方面也不必再在此时此刻立下清规戒律。”[10]
傅雷的这种认真、细致,有时候未必得到出版社及时呼应,对此他只有焦急地一遍遍写信强调、呼吁,也有伤心地慨叹。“巴尔扎克各书移转人文后,先出精装本;但北京印刷条件甚差,公家办事亦欠周到,故样本寄到上海,本本皆有污迹,或装订,或印刷上的毛病。”[11]“‘人文’新印的巴尔扎克精装本,已有三部寄来,可怜得很,印刷与装订都糟透,社内办事又外行,寄书只用一张牛皮纸,到上海,没有一本书脊不是上下端碰伤了的。封面格式也乱来,早替他们安排好了,他们都莫名其妙。插图铜板还是我在上海监督,做好了寄去的;否则更不像样了。”[12]
傅雷对于精装本的质量有着自己的要求,“五四年十一月所印前五种巴尔扎克的精装本,成绩反不及平装本。”[13]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毛病,确定标准,等于是手把手在教出版社怎么印书:“精装书外面加的彩色包皮纸,折进书里的一段纸往往太狭,拿在手里容易脱出,不久就破碎。原来是为了节约纸张,但到读者手里用了几天就破碎,岂不因小节约而造成大浪费?这也是我说的‘只打小算盘,忘了大算盘’的一例。光从降低成本着想而不替读者用的时间长短着想,就是我说的‘只顾眼前’的一例,而且是极端片面的。真要节约,就干脆取消那张彩色包皮纸!”[14]从文字中,能够看出他的焦虑乃至恼火:
(二)即使是布面精装,如适夷兄译的《高尔基选集》:甲、封面凹凸不平;乙、胶水污点不少;丙、烫金有缺笔,或一字之内部分笔划发黑;丁、书角也有瘪皱情事。总结起来,仍是浪费。以国内现有技术水平,并非精装本不能做得更好;但在现行制度之下及装订人才极度分散的现状之下,的确是不容易做好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今在大机关里头,像那样细致的工作在短时期内恐怕没有希望办到。——装订也是一门高度的工艺美术,只能由一二人从头至尾抓紧了做才作得好。[15]
显而易见,限于条件,平明社的精装本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平明社的工作作风却给傅雷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对人文社的领导说:“将来倘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印精装本的话,希望注意一点:就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国营的出版社成绩,决不能低于几年以前的私营出版社。这是有关原则性的问题,务盼赐予注意为幸。”[16]他对重印《约翰·克利斯朵夫》直接提出硬性要求,第一条就是要保留平明社印本的“旧样式”:“封面装帧、题字、排印字体、书脊题字式样、各册颜色,希望全部维持原样,只改动出版社名称一项理由:倘没有充分理由肯定旧样式不美观,即无改头换面之必要;同时也可节约人力物力。”[17]他甚至放出狠话,倘若达不到要求,宁可不印精装本,“希望郑重考虑承装工厂的技术水平;希望不要花了钱得不到效果,我们更不能忘了原来是私营出版社做过的工作,国营机构不能做得比他们差。倘无适当技术水平的装订,宁可不印精装本,以求节约。”[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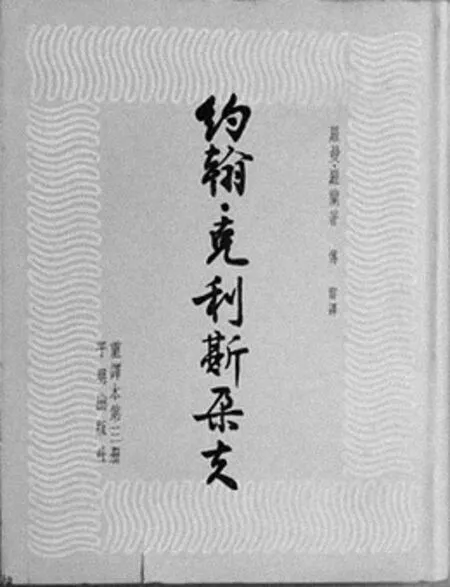
平明版《约翰·克利斯朵夫》1953年9月版书籍纸精装本,该本印2900 部,另有100 部字典纸精装本
傅雷的要求处处以平明社的书和做法为标准,由此返观,可以想象,他和巴金的合作之默契和满意度。至于他一再提到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的确,这套书的印装在今天看来也是难得的精品。四大卷,开本近乎方型,书封有外函套,封面简洁、经典。在普通本之外,平明社还有给作者加印特装本的传统,让作者送人,也体现书的尊贵。黄裳、穆旦、萧珊的书,都见过这种特装本。傅雷在另外的信中称这算是开风气之举:“又《约翰·克利斯朵夫》,北京有指示要上海印精装本二千部,平明自己另外加印了一百本圣经纸本的,算是替中国出版界开开风气。但成绩因条件限制,不能完全合乎理想。”[19]我在1955年12月编印的《平明出版社图书目录》中看到:《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有四卷本的书籍纸精装本,定价是12.50元;另有上下两册的字典纸精装本,定价是16元。这种两卷本的字典纸精装本,我未见过,大概就是傅雷所说的“平明自己另外加印了一百本圣经纸本的”。
文人爱书,傅雷很珍惜这样的印本,在给儿子的信中也曾叮嘱:“新出的巴尔扎克,收到后来信提一笔——这是特印非卖本,勿随便借出去,搞丢了!”[20]“特印非卖本”这并不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在计划经济中,国营大社怎么会有这种例外,反倒是私营出版社有这种灵活性。还有一层不能忽视,巴金本身就是一个文人,他懂文人的情趣和需要。
“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平明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延续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译文丛书”的路子,编辑“文学译林”丛书,意在推出翻译精品,傅雷是第一批受邀加入的作者,他一直关注平明社的这套丛书。“西禾谈及巴金新组一书店(已与文化生活分家),想专出一套最讲究的文艺翻译,由西禾与他二人合编,说是决不马虎,迄今只收了杨绛一本译稿,听说好得很。此外又来问我要稿,也许新译的巴尔扎克会给他们。此外他们还想不出别人。不知悌芬有意半玩儿半工作的试试吗?但书店方面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你不妨与他谈谈,让他想想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有些什么,可以来信商量。巴金的条件,仍是百分之十五的版税,他是反对新办法的。”[21]“《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阻四,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搞不出一些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22]这两封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文学译林,由巴金和陈西禾合编;第一批稿件中只有杨绛译《小癞子》(1951年4月初版,印3000 册)和傅雷译《贝姨》(1951年8月初版,印2500 册),后来陆续增加的是傅译巴尔扎克诸书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傅雷特别强调巴金他们收稿之“严”“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严格、标准、眼光,巴金的出版社的这些品格都是傅雷看重的,这也是傅雷与巴金两个人作为朋友最重要的精神联系点。两个人的性格虽然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认真的人,都是切实做事的人,都是心怀理想的人。
傅雷还是一个热心人,他鼓励人译书,也为平明社这套丛书拉稿。1953年1月给巴金的这封信,就是介绍杨必译稿的:
巴金先生:
兹另邮挂号寄上杨必译《剥削世家》,约共四万余字。除锺书夫妇代为校阅外,弟亦通篇浏览一过,略为改动数字,并已征求译者本人同意。该书内容与杨绛所译《小癞子》异曲同工,鄙见将来不妨将该书重版与本书初版同时发行。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其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好在字数不多,轻而易举,可否请采臣兄一查平明本年春间出版计划是否可能早出。
又倘尊意认为《剥削世家》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则排版格式可与巴尔扎克各书一律。红笔批注均出弟笔,冒昧处乞鉴谅为幸。
正文“小引”请先生细阅一过,若有问题,务请见示,以便修改。勿此祗候
俪绥不一
弟 傅雷拜启
二十一夜[23]
杨必(1922-1968)是杨绛的妹妹,在她们家姐妹中行八,后曾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傅雷曾请她教过傅聪英文,很赏识她的才华,在傅雷和钱锺书夫妇的鼓励下,她开始涉足文学翻译,信中提到的《剥削世家》是一部小书,她后来还译过萨克雷的那部大书《名利场》,很受推重。虽说初涉译坛,杨必的“师傅”却非同一般:姐夫钱锺书、姐姐杨绛“代为校阅”,一代译宗傅雷“通篇浏览一过”,《剥削世家》译文质量大有保证,傅雷给出的判断是“译文标准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他甚至用红笔把排版格式都在原稿上批注出来了,如此推重和为其尽心,令人叹服。傅雷还向巴金提出一个要求:“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其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共和国初立,百废待兴,私营出版社(排字房、印刷所)的排书能力很低。这一点,傅雷在1951年给宋奇的信中谈到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篇幅太大,私人出版社资力和能力都有限,他暂时不转到平明社[24]。我在平明社1952年9月初版、1953年2月再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页还看到一则声明,也谈到工厂繁忙,排印不及:“本书第二册原定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版,因排印工厂工作繁忙,致脱期甚久,劳读者悬望,甚为抱歉。第三第四两册决定于本年六月份同时印出,特此预告。”按照傅雷“一手包办”的说法,我怀疑这则声明出自他之手。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完全按照傅雷的要求以尽快的速度出书。《剥削世家》,平明社1953年5月初版,印5000 册,也就是说在傅雷把稿子寄给巴金之后三个多月就印出了。该书在当年8月再版,增印3500 册;1954年1月第三版,增印4500 册,总印数达13000 册,看来挺受欢迎。

1953年1月21日傅雷致巴金
杨绛在回忆杨必的文章中说:“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25]杨绛补充的信息是,《剥削世家》《名利场》都是钱锺书帮忙选定的书目并且确定了书名。傅雷在给宋奇的信中补充的信息是,这书初译稿,钱锺书不满意,杨必重译了一稿:
信到前一天,阿敏报告,说新华书店还有一本《小癞子》,接信后立刻叫他去买,不料已经卖出了。此书在一九五一年出版后三个月内售罄,迄未再版。最近杨必译的一本Maria Edgeworth;Castle Rackrent(译名《剥削世家》是锺书定的)由我交给平明,性质与《小癞子》相仿,为自叙体小说。分量也只有四万余字。我已和巴金谈妥,此书初版时将《小癞子》重印。届时必当寄奉。平明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扎克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挤进去(他还是平明股东之一),也被婉拒了。前年我鼓励你译书,即为此丛书。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26]
杨绛的《小癞子》初版印3000 册,两年后已经一册难求了。在傅雷的建议下,平明社重新排版重印,于1953年10月出了重排一版,印4000 册;1954年5月又印重排第二版,增印2000 册。傅雷对杨氏姐妹的译笔很是推崇,也曾感叹自己的文字“太死板”,不如杨氏姐妹那么灵活:“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内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27]傅雷曾对杨绛说过“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28]看来他是真心喜欢杨氏姐妹的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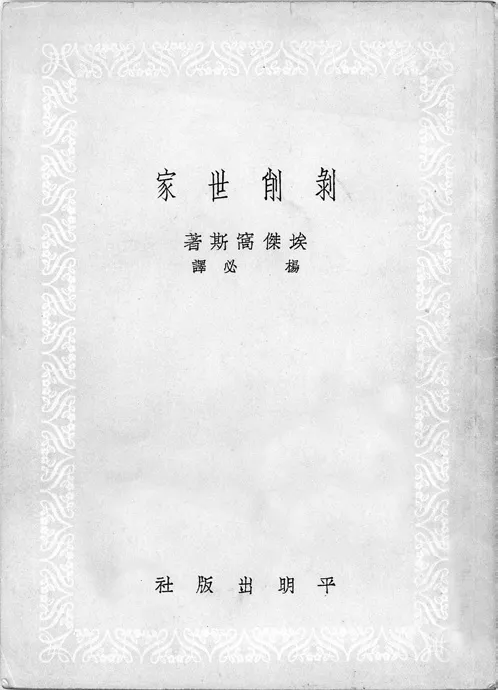
杨必译《剥削世家》
杨必之外,傅雷还动员宋奇(宋琪)译书:
只要你认为好就不必问读者,巴金他们这一个丛书,根本即是以“不问读者”为原则的。要顾到这点,恐怕Jane Austen 的小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我个人是认为 Austen 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 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西禾我这两天约他谈,还想当面与巴金一谈。因西禾此人不能负什么责任。[29]
傅雷屡次提到“文学译林”丛书,乃是他极为欣赏巴金办出版社这种“不问读者”的原则,其实是为了文学、出版、文化的积累不计名利的气魄。朋友有各式各样,有的朋友,可能不在于世俗生活中来往多少,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认为傅雷和巴金的友情就属于这一类。
遗憾的是,平明出版社只在出版史上存留了短短的五六年,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也提到了它的结束,虽未置一词,但我隐约能读出几分惋惜:“平明出版社年底归并公家,与‘新文艺’合。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嘉尔曼》则移交‘人文’,楼伯伯来信,说钱伯母,必姨的两本小书也要向平明讨过去。”[30]
俱往矣,距离此信六十年后的2014年,在傅雷夫妇忌日(9月3日)的前一夜,外面下着大雨,我在武康路巴金故居中整理资料,突然发现一个印着黑字的信封,打开看,里面是“举行傅雷先生骨灰安放仪式通告”,里面,还夹了一张代办花圈的通知。通告的内容简单,又冰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受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逝世。现定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半在漕溪路210 号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傅雷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特此通告。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几十年过去,这张冰冷又沉重的通知在那一刻出现,仿佛是天意?在我的书房中,有一尊青年雕塑家高旷寓送给我的傅雷雕像,傅雷围着围巾,手执一卷书,身材颀长,飘逸,我想到人们对他的评价“孤傲如云间鹤”。我也想起1987年巴金写给苏叔阳的一封信,是回答苏叔阳关于老舍之死提问的,由老舍,巴金谈到傅雷:
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也就是您举出的第三种说法,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傅雷同志也有这样的表现,我佩服他们。

傅雷像(高旷寓塑)
我们常说“炎黄子孙”,我不能不想到老舍、傅雷诸位,我今天还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31]
巴金把他们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钦佩他们“有骨气”,表示他们是不能被遗忘的“炎黄子孙”。是啊,“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毕竟是知识分子,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传统。
注释:
[1][6][26]傅雷1953年2月7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06—208 页。
[2]傅雷1953年11月9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10 页。
[3]傅雷1954年2月27日致巴金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26 页。
[4]巴金1953年11月5日致陈蕴珍信,《巴金全集》第2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49 页。
[5]傅雷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39 页。
[7]傅雷1954年7月8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13 页。
[8]傅雷1956年3月22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51 页。
[9]傅雷1956年6月25日致郑效洵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98-299 页。
[10]傅雷1956年7月10日致王任叔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309 页。
[11]傅雷1955年1月8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18 页。
[12]傅雷1955年1月9日致傅聪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4 卷,第139 页。
[13][14][15][16][17][18]傅雷1956年12月10日致王任叔、楼适夷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318—324 页。
[19]傅雷1953年9月14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23 页。
[20]傅雷1954年4月7日致傅聪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4 卷,第46 页。
[21]傅雷1952年3月20日致宋希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21-222 页。
[22]傅雷1951年9月14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01 页。
[23]傅雷1953年1月21日夜致巴金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225 页。
[24]傅雷1951年6月12日致宋奇信。
[25]杨绛:《记杨必》,《杨绛全集》第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48 页-49 页。
[27]傅雷1954年2月10日致傅聪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4 卷,第29 页。
[28]杨绛:《〈傅译传记五种〉代序》,《杂忆与杂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6月版,第320 页。
[29]傅雷1951年4月15日致宋奇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6 卷,第195 页。
[30]傅雷1954年11月1日致傅聪信,《傅雷著译全书》第24 卷,第104 页。
[31]巴金1987年5月14日致苏叔阳信,《巴金全集》第2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5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