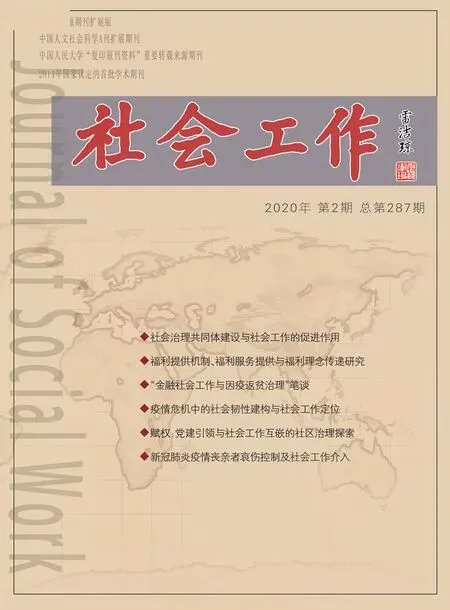集体赋权视角下的情境叙事研究①
——基于D协会服务失独群体的案例分析
2020-05-15程激清程秀敏
程激清 程秀敏
一、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一直被赋予“通过助人以及相应环境的方式来支持人类的成长、健康和社会功能恢复”(Gitterman&Germain,2008:51)的意义。其旨意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应充分考虑“人在情境中”,即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情境和实践者所面临的情境。在这种假设之下,社会工作的实践除了协助个人适应周围生活环境外,还要考虑改造环境使其更适合人们的日常生活(Elizabeth A.Segal,Karen E.Gerdes&Sue Steiner,2008)。由此可见,社会情境是社会工作者改变案主的重要实践场域。当然,社会情境或者说社会结构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形塑个体的“实践意识”,而是呈现二元互构的状态,即,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情境的结构张力,实施专业干预、塑造案主自身对情境的掌控,达成对案主的赋权与增能。在增能与赋权行动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借助西方的运动式争取方式,即注重个体如何发挥实践意识以获得权力,以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然而这种方式忽视了社会工作的实践性,具体来说,在本土进行赋权时需在现有体制中寻找空间,并且充分运用好现有的体制规则和主流话语,去塑造能让服务对象自身权能增加的社会情境。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充分运用情境的力量为案主赋权。并尝试以D协会干预失独问题的“情境转换”实践,分析其外在情境、内在情境如何在案主中产生内在赋权、外在赋权效果,以此解析服务失独者“受助、互助、助人”过程的情境体验,从而为社会个体进行赋权的理论和实践提供镜鉴。
(一)失独群体面临的情境与赋权
社会学基本假设认为“人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戴维·波普诺,2009)。社会工作认为人的情绪、心理、行为受到其社会情境的影响,人所处的情境既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物理环境。社会环境指个人、家庭、社区、阶级和文化;物理环境指气候、地域、住房等。对于案主,这些情境不仅仅是客观的外在的,更是他人和自我叙事建构的(Beulah R.Compton,1999)。失独者子女离世后,其面临的情境对他们自身进行相应的塑造,即,内在情境与外在情境对他们情绪、心理、思维、行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要转变他们这种既有的状态,必须改变情境,从而提升“掌控自身生活”的权能感。
现有研究指出,失独者面临情境主要分为自我叙事情境及外在环境,且两者互为因果。首先面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且将之内化为自身认知。如“因果报应”(陈恩,2016)“传宗接代”等观念的内化,让失独者面临长期的自我边缘化、自我标签化、污名化(安真真、徐晓军,2018),以及对未来生病无人照料、故去无人“送终”等担忧心理等,使其长期沉浸于悲伤。具体来说,失独者经常出现极度相思、抑郁、焦躁等痛苦;产生愤怒、仇恨、绝望、自杀等悲伤(李怡心,2014)。其次是面临相对封闭的社会、物理情境,自身同质化交往增强,从而减少社会化程度(安真真、徐晓军,2018),使得他们长期陷入“心态内卷化”(Yongqiang Zheng,Thomas R.Lawsonl&Barbara Anderson Head,2017)。由于个体与社会相互构建的较强相似性,所以产生了“失独群体文化创伤从个人认知到集体认同、从客观事实到自觉建构、从私人领域到公共话语”的逻辑(徐晓军、彭扬帆,2017)。围绕失独者走出困境,有研究认为必须通过政府及其他第三方进行正确引导(方曙光,2018),特别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救命稻草”式的关怀,引导他们参与、融入社会(方曙光,2013)。
赋权概念自产生起就面临着不断的变化。学术上的赋权被用来描述人们在社会中有权与无权的关系化(Humphries,1996;Rees,1991)。宋丽玉(2006)综合相关研究后认为赋权是“个人对自己的能力抱肯定的态度,自觉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在需要时影响周围的环境。”现有的赋权实践架构包括自我赋权、个体赋权、团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政治赋权等(Robert Adams,2013),常从个人、人际、社会三个维度来讨论,其旨趣是赋予个体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政策改变的能力(何雪松,2007)。而在具体干预实践中,更加强调案主的参与,并强调其过程的社会性建构(Robert Adams,2013)。从这点来看,赋权本身具备个体能力与社会情境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具备社会结构性的“立体维度”。但作为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赋权更有个体如何运用权力、政治等资源的理论偏好(Ress,1991),如,西方民主“自下而上”的实践模式,与我国社会工作的实践环境存在差异(孙奎立,2015)。
具体到失独者干预的研究,结合情境因素的赋权是不断强化的。姚金丹(2012)认为对失独者进行增能赋权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黄耀明(2014)认为从生活重建角度建构社会支持体系;张必春、李亚男(2018)主张从失独者优势资源激发“潜能”;汪鸿波、程激清(2019)分析情境“关系”能量对失独者的干预效果。还有不少学者则从社会赋权的角度展开研究,如,社会救助(王文静、王蕾蕾、闫小红,2014)、社会融入(谭磊,2014)等。
(二)情境赋权的分析方法
在上述研究中,不论是赋权理论还是运用到失独者的赋权研究,都与失独者所处的情境结构——社会支持体系、潜能、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等有关。虽然在情境与赋权的研究中,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即在赋权中提到运用情境,或者从情境的角度探讨过赋权,但二者交叉的服务实践研究都相对较少。
我国社会体制与西方“自下而上”的社会体制不同,倘若纯粹将西方赋权方法移植而来,不考虑情境对案主体验影响,则容易陷入“无法被赋权”困境(郑广怀,2005)和无效的“赋权陷阱”(吴帆、吴佩伦,2018)。从我国社会工作实践层面来看,赋权行动除面临案主自身情境外,还面临社会结构、制度习惯、文化特质等,即现行制度框架的规制。在具体赋权过程中,不得不寻求其他实践策略或“智慧”,绕开问题,或者暂不进行某一维度的赋权,甚至“牺牲专业性”,以达到案主自我权能的某种平衡。
为此,在我国制度文化结构中的赋权行动,不得不考虑被赋权者所面临的内外情境,及其在介入过程的转变。对于失独群体的赋权来说,内在情境主要包含失独者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人格特质及其群体内部关系等;外在情境则是他们所面临的空间结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与政府、社区的关系等。概言之,对失独群体的赋权,需要从外在情境与内在情境的双重渗透,促进其外在权能——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掌控,内在权能——对自身的认知和掌控双提升。
(三)案例选择
一直以来,触及失独群体的服务,相关部门讳莫如深,对失独群体组织及帮扶组织大多采取不支持、不鼓励的态度,导致关注失独群体服务的社会组织不多,且做出成绩的更少。在这一背景之下,笔者选择专门服务失独群体的南昌市D协会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其具有社会自发、服务对象自愿、社会认可,且受到权力和资本干预少等因素。D 协会在专业理念指导下,有意识地促成了失独者受助、互助、助人的变化过程。100余名服务对象中,20多位已经成长为D协会志愿者。2016年以来,笔者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其中,通过非正式观察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试图分析其3年来服务过程动态与效果。同时收集失独者成长及社会组织运行的相关资料,涵盖失独者自我认知转变过程、活动过程评价、活动效果评价等。
二、受助情境:去标签的个体自我赋权
就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组织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而言,社会组织大多以“主动出击”为主,诚如童敏、周燚(2019)所提出的“我找你”服务模式。但失独者与其他群体不同,其主动寻求帮助的意愿并不强烈,甚至拒绝参与和接受服务(方曙光,2017)。在这一情况之下,D协会结合失独群体抱团的特点,尝试采用吸引受助的方法,在失独群体内形成了聚集效应。本文所说的D协会对失独者的介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个案、小组、社区“专业服务”,而是针对失独者的心理结构特点及需求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在这种行动逻辑下,D协会制定自愿参与活动规则,以“非专业化”活动为失独者接受服务提供契机。之所以用淡化专业化名义开展服务,是尝试在与失独者互动氛围中摆脱某种标签,从而帮助其克服赋权的障碍,从而实现个体赋权——形成良好自尊、自我效能及内控等。具体实现的路径如下:
(一)避免过度关怀的去标签情境
D协会为吸引失独者参与活动,主要经过现有微信、QQ群发布活动通告,失独者自愿参与、自愿邀请“同命人”参与活动的形式,获得活动成员。在这一阶段,所设置的情境主要是自由、宽松、愉悦的活动氛围,即采取避免对新来的陌生失独者过度询问的方式获得其继续参与的意愿。因为“过度关怀容易让他们产生警惕,在他们没有主动跟我袒露心声的时候,我们都不会主动去多问什么。”(D协会会长)在长期参加活动之后,在这个过程中,D协会会长及主要志愿者成员暗中观察参与活动的失独者性格、爱好以及心理特征等。除此之外,D协会会长在这过程中的角色扮演是“陪伴者”,即与他们一起同行的角色。如在活动中组织唱歌、组织一些游戏,且在聚餐的过程中直接“袒露心声”:“我就是你们的弟弟,叫大家出来,就是陪伴大家。”因参与活动的都是“同命人”,失独者并不会因为被“异样眼光看待”,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访谈对象CL)。
最开始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基本不会说什么话,来了就是跟自己几个比较熟的人交流,不会主动提及自己的事情。当大家熟悉了之后,也知道会长不是坏人,就开始慢慢袒露心声,也会开始在群内活跃起来。(访谈对象CL)
我们最开始是不愿意走出来的,总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后来参加完活动之后,觉得并没有什么,大家都一样,就不会用孩子什么的刺激到我们。加上会长和志愿者都是长期做这件事情的,心里就不会有什么芥蒂了。(访谈对象WXB)
D协会会长之所以采用非直接服务方式,即并非运用直接谈话或访谈的方式对失独者的状态进行深度了解和调试,而是采用吸引其参与娱乐活动的间接方式开启服务,其原因有二:一是基于失独者长期形成的心理敏感特征做出的选择。由于长期处在封闭物理空间结构、封闭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且内化于心理结构,失独者对走出原有情境恐惧心理,且不愿意接受外人的帮助或者交往,“蜷缩”于这种“安全圈”内。一旦走出,他们可能就认为是一种“不安全”。二是基于失独群体长期将外界“异样眼光”自我标签化的特征。为避免加剧对他们“问题化”和标签化,采取服务过程中,尽量避免将其划入“受助者”或“有问题的人”。
质言之,此阶段的情境要求,重点是尝试营造轻松愉快的活动氛围,绕开“失独”话题,或者“被标签化”的行动。
(二)营造新关系的去标签情境
户外活动直接改变的是失独者所面临的空间情境和社会关系情境。从空间结构上来说,户外活动可以避免失独者在家中陷入“关禁闭”,开阔的户外空间释放失独者的空间压迫感;户外活动的轻松愉快氛围,使失独者在参与活动中逐渐形成新的社会交往。D协会在这一阶段的重点活动则是以户外为主,比如“春天踏青”“冬天采橘子”等活动,并在活动过后聚餐举办“生日会”。在诸如此类活动举行较多之后,群组内互动频率的增加,新参与者、原有参与者和志愿者逐渐增进信任,形成群体内的自我认同和凝聚力,以实现失独者拥有良性体验。
自从孩子走了之后,我们基本上两个人都躲在家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就这样没啥事儿的时候啊,就会想起孩子这么一件事情,越想越聊就会沉浸于悲伤的状态里。走出来,可以和自己一样的人,在外面走走,认识新的人,就不用长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心情也会愉悦很多。(访谈对象LSM)
通过户外交往方式,帮助失独者突破内在“自我情境”,即自我认为的“他们对他人‘异样眼光’”的“自我叙事”式的预设和信念,不仅是转变他们的内在信念,而是创造健康的适应环境。其空间充满轻松的氛围,富有仪式感的活动,以及更为包容、温情的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他们内在认知。在介入的技术层面,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营造户外情境和外展关系,让失独者走原有封闭的空间和社会关系结构,促进他们在同类群体中开展良好的社会交往。
(三)去标签化的情境构建
在情境建构之外,由于失独群体本身的敏感特性,易对外界环境持有一定的不信任,甚至是偏见。如,对社会组织“非此即彼”的评判,即志愿服务不是“有企图的”就是“坏的”的认识建构,使得他们与社会组织的接触更为谨慎。这种认识,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个别社会组织为失独群体服务时,确实存在“谋取政绩”和“谋取私利”等现象。由此加剧了失独者对社会的不信任。
我们不会利用他们做什么,特别是利用他们谋取自己的名声什么的。我自己从来不评什么“中国好人”“优秀志愿者”等称号,新闻报道也不报道我个人的事迹。就是自身要硬,不能出现“谋政绩”“谋私利”,甚至鼓动他们上访,敲诈政府一笔等。(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对社会上的另一种说辞,D协会也是不以为然:
王大哥他听了居委会的“唆使”,想当官,想成为带头人。本来我们在他们居委会,搞搞活动,也算他们的“政绩”。那边居委会主任就“唆使”他来当会长,但他没有这个能力当会长。我带着失独者来了XJT社区之后,就没有人参加他那边的活动了。(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D协会不仅保持了以案主为中心的初心,且保持了长期维护良好声誉的状态。如坚持协会工作者具有高度自律的志愿精神,和持续的服务时间,同时,坚持协会内部治理的公平正义。从而避免失独者在参与活动中产生不信任,离队等现象,也提升了协会的凝聚力。
去标签化的情境设计营造了良好的服务氛围。服务对象被吸引参与,且在一个良性的沟通环境中释放一种自信,即践行了Solomon和Freire所提的培养信心、倡导与自我倡导、协商资源、网络链接等个体赋权实现的可能方法(Robert Adams,2013)。具体来说,一是通过去标签化的活动,使他们消除被“特殊化”“问题化”的疑虑,从而避免其自我问题化,达到增加内在权能的效果;二是营造新的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从而他们实现走出封闭空间、获得消除孤单等外在权能感;三是通过营造纯粹以案主为中心的声誉情境,增加失独群体对他们的信任,消除怀疑等负面情绪等。
三、互助情境:互助获得的群体内赋权
失独者“抱团取暖”是一种自发性疗愈。D协会作为失独群体的服务者,充分开发其可能存在的潜能,并利用这种内在自愈力量。失独者是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并且极易受到群体内的氛围影响,形成一种“劫持”式的力量。即团体内如果形成集体悲愤,则容易感染到其他参与活动的失独者;当产生具有相互支持的氛围时,则能促成他们相互扶持的行动。与团体赋权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团体提供个体支持,能降低孤立的风险,提供一个环境体系,使个人能力得到发展和锻炼(Robert Adams,2013)。这一阶段,D协会不是仅对群体内自我叙事进行设计,而是特别强调通过提升失独者个体沟通技能与自我决定能力、丰富社会资本等改变外在情境的手段,提升权能感。这个过程D协会主要构设了互助实践情境。
(一)互助:发掘失独者群体内在信赖
失独群体长期参加活动之后,逐步建立了信任感,并且形成了群体内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D协会开始在失独群体内征集志愿者来服务其他失独者。即以看望、协助就医等方式服务因生病而无人照料的失独者。在这一阶段,D协会创造了失独群体内的互助氛围,让他们避免生病、特殊日子①特殊日子,是指逝去子女的忌日、生日等。等时候的孤独和悲伤,从而以内部群体的方式给失独者以“力量支持”。“同命人”相互帮助时,首先是消除生病无人照料的疑虑,不用再极度恐惧生病后无人照料;其次是让他们发现自己亦能对他人有意义,能够帮扶到像自己一样的人,从而形成对自己“是具有能力的”认可。
当他们在形成互相扶持的状态,能够让他知道,还有人会愿意来帮助自己,自己也能够为他人帮助。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孤独、无依无靠的,是有人担心,有人愿意陪着一起度过难关的”,同时也让他们相信“我自己走出困境,也能带动别人走出来”。(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在长期互助实践之后,他们形成了较强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基于共同生活实践的认同,而不再是简单的“同病相怜”。归属感作为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情感和经历,是指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群体或环境中并认知到在其中扮演的一种特殊角色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经历(吴龙海,2013)。D协会通过形成营造群体内互助氛围,在失独群体内形成两种心理归属期待:一是不用担忧无人照料的安全感;二是积极投入照顾他人的荣誉感。这二者使得他们焦虑缓解,并且形成了较强的依赖与信任。
事实上,失独者相互照料和慰藉的效果比外人更为明显。失独,具有相对特殊的人生体验,因此没有类似体验的服务者在服务过程中难形成相应的同理心等。D协会充分开发恢复较好的失独者承担心理慰藉服务的角色,进一步帮助其他失独者走出原有的困境。如以自身心路历程分享、表达同理心、分享参与活动后的心理变化等。这类具有亲身体验的心理慰藉相比于无体验的人士,更加具备说服力。在这个过程中,“失独者”帮助“失独者”,且形成团体互助效应。
相比我们去说,他们更加相信失独者自己说,我现在都不怎么去劝他们走出来。遇到的时候,我可能会叫和那个人关系比较好的失独者去劝说,或者带失独者一起到他家里去走访。我说什么没用,没有这样的体验,但失独者说出来的,更加有份量。(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失独者之所以愿意参与,甚至热情承担慰藉他人的角色,一方面是因为自身长期体验了其中的悲伤与痛苦,期待走出困境;二是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在慰藉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价值。
(二)互助:“主人翁地位”的重塑
在这一阶段,除了生病及活动中互助之外,失独者同样充当“志愿者”,策划活动、安排经费用途、监管经费等,承担着群体内“主人翁”角色。D协会为其创造出“自决”的实践情境,让失独者在群内协商、协会志愿者从中协助或引导,从而实现失独者对协会和活动的掌控感,增加其实践的权能。这样的实践方式主要发挥了三种作用,一是传递协会对参与者的信任;二是让失独者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训练自身的能力——如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等;三是通过这样的训练形成相对稳定的群体内结构,开发出一批具有热心、热情的失独者参与到助人活动中。
我们这里都是实现财务随时公开,来参加活动的任何人都可以查账,而且管账也不是我自己直接管,是安排稍微年轻一点,有会计经验的失独者来管。(D协会会长)
当具备热心与热情的团体形成之后,不仅仅在协会内发挥简单助人的作用。并且能形成“示范效应”——以现身说法劝说失独者走出原有的情境,开导未走出心理困境的失独者,并且参与到活动与服务中来。在这种氛围形成之后,逐步传播开来,D协会逐渐成为失独者参与的“家园”,并发挥着“主人翁”角色。之所以需要D协会会长及其他志愿者进行引导,一方面是避免他们集体陷入悲伤之中,二是缓和失独者在活动过程中的冲突。
在这一阶段,不仅仅是通过情境对他们个体进行赋权。而是将对个体的赋权融入到失独群体之中,将其权能在群体中实现。这样一来就践行了在互助中实现集体赋权。在这种赋权中逐渐消除原有的抑郁、焦虑、哀伤等状态,实现了集体的角度对失独者个体进行赋权,同时在凝聚的过程中实现集体权能增加。
D协会注重引导失独者在协会承担互助的角色、协会事务、慰藉服务等,不仅仅是分担协会的服务任务,更多的是尝试通过在互助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已有的效果,在实践情境中不断提升自我能力,获得权能感。
四、助人情境:以助他行为获得社会赋权
如前所述,失独者面临子女失去之后人生意义缺失,加上长期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内,陷入自我否定与环境否定的双重否定状态。由于年老体衰,身体控制感和思维都在退化,加之社会氛围中“老人无用论”的标签化内化等,加剧失独者对自身无用的建构,甚至自我标签化。在受助、自助之后,D协会尝试通过运用助人的情境巩固原有的成果,即构建“助人”情境,使失独者认识到“我还有价值”,褪去某些部门所称的失独者“难缠”的标签。这种行动策略实现的是与“主动争取权力”做法有差异,而是通过助他行动获得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认可和包容,从而实现某种“社会公约”“社会契约”,从而获得社会赋权和政治体系赋权(Askonas&Stewart,2000)。
(一)助人实现社会价值
“助人”实现其自我价值,也实现其社会价值,形成失独者去标签效应。D协会倡导接受服务的失独群体参与助人活动,让他们在助人的过程中,形成“我也可以帮助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价值体验。由此赋予他们自如的实践空间和氛围,减少自我标签化及警惕心理。
从具体的情境构建来说,D协会开展发挥失独者特长和能力的活动小组,如组建学雷锋小组、广场舞表演队、乐器表演队、社区书法课堂等。学雷锋小组则是以志愿形式参与走访和关怀留守儿童、环卫工人等;广场舞表演队、乐器表演队则以队伍的形式参加各类比赛和公益演出等;社区书法课堂则是发挥部分具有书法特长的失独者服务社区内具有书法爱好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服务过程中,不仅增加他们与其他人群的接触,增加社会接触;还在发挥他们的特长,服务社会,且帮助他们建构自我价值。即此类活动的价值部分受到社会认可,亦有部分纯粹是为了让失独者获得对自己价值的认可。也就是说即便他们的活动价值可能不被普通人认可,但在助人的现场情境中,却能够发挥有意义的功效,以实践的方式重构了他们的部分人生意义。
用他们的行动、笑容来引导。以后我就着重让他们参与,体现他们还能帮助别人。就像小时候对学雷锋小组,增加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活着有意思。比如有一位80多岁的失独老先生,他在社区内开设一堂公益书法课堂,让有兴趣的小学生参与书法课堂。在教学的过程中,他特别积极,而且倾心教学。(D协会会长)
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说能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想着告诉社会、政府,我们和正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为别人服务。(访谈对象LSM)
在这个服务情境之中,不仅有被服务者(被失独者服务的人)认可他们的助人活动,而且D协会引入基层政府(街道办)和社区工作人员参与观察,从而为失独者提供被官方认可的机会,扭转他们在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印象。这种印象的转变直接体现为政府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上,如不再将他们作为长期上访的“钉子户”对待,而是作为能够沟通的群众。
这种助人情境与其说是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建构,不如说是失独者根据自身需要建构的过程——失独者根据自身需要建构自身价值。在这种具体的实践和行动中,让参与者感受到切切实实的自我价值,并且在反复实践中得以巩固。服务者仅仅是在满足他们这种需要中进行情境创造,并且引导他们在情境中的实践方向。
(二)获得与政府良性沟通机会
引入政府部门的参与,可实现政府干部、社区干部、社会他人对他们认知的转变。通过助人活动除了在群体内和社会他人中产生“我还有用”的意义建构之外,同样传递出了另外一个信息:即在社区的场地活动,让参与观察的社区干部、街道办官员看到失独者在活动过程中的“正常”状态,化解基层干部对失独者的“维稳重点群体”刻板印象。
我们举办生日会的时候,每年就会叫几次街道办主任过来,看看大家的状态。在看的领导多了之后,他们会把我们当作“宝”,舍不得我们离开。于是我们这里有人有需求,有人生病了,街道社区都会高度重视,要么社区自己去走访,要么会找我们帮忙看望。(访谈对象D协会会长)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政府也不会把我们放在对立面,不会认为我们是上访专业户,不是那种反复缠访的人。他们工作也忙,要推进我们这些工作也是需要时间的,只要他们愿意关注我们,就已经有进步了!(访谈对象HMH)
除了化解这一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获得沟通机会。在活动中加入政府工和社区工作人员之后,失独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困境获得了表达的机会。如针对失独者表达“三节没人看望”“生病没人照料”等,街道和社区则开始转变原有工作方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开展走访,或者委托D协会进行走访。最后达成“和解”,即失独者表示“也能理解街道和社区工作忙”(访谈对象HMH)。
这种邀请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参与的情境设计,对失独者本身是一种“鼓舞”——“我们是受到重视的”;也是为他们提供沟通机会,表达需求的场境;更是让他们在这种情境中获得表达的机会。因此,这种情境的创造,从某种程度上区别于西方鼓励抗争或者运用政治资源的抗争式“赋权”,更多的是采用让基层政府可以接受的方式——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向政府进行求助的过程。
基于互助的情境,加上与群体外的人员正向互动,让失独者在轻松氛围中进行活动,在这种互动中他们的自我认知亦发生变化——能够通过温和的方式改变他人对自己的认知,且具备与他人良性沟通的能力,从而增加他们自身的权能感。D协会在失独群体转变之后,借助街道、社区干部参与活动的形式,并前往与失独群体进行沟通,倾听其需求,从而增强失独者对政府影响的权能感——即诉求可以被听见和看见。政府官员、社区干部等参与,来了解和关注失独者的需求,且具有相对良性的沟通,也增强了与政府部门沟通的信心。这样一个过程,增加了失独者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技巧,最终实现了其在社会层面获得认可,实现政府及社会层面的赋权。
五、结论与讨论
失独者在受助、互助、助人三个情境中部分实现了权能增加。即对内部情境、外部情境的构建,使他们获得部分权能感(如图1所示)。这种赋权过程体现了西蒙赋权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基本框架:“第一,和案主、案主群、社区领导人等建立互相合作的伙伴关系;第二,强调案主和案主群的能力而不是无能力;第三,支持着眼于个人及其社会和物质环境的双重工作焦点;第四,承认案主和案主群是积极的主体,具有相互关联的权利、责任、需求、要求;第五,利用自觉选择的方式,把专业的能量指向在历史上被去权的群体及其成员”(Simon,B.L,1994;转引自陈树强,2003)。而本文重点聚焦情境建构带给失独群体的改变,D协会通过人情关系,在中国本土情理社会中达成了“去标签”“互助”“助人”等专业叙事,与西方直接表达方式不同的是,采用了被“看到”的方式,具有较为强烈的本土化实践色彩。

表1 失独者受助、互助、助人阶段的情境叙事
(一)赋权效果受到案主个性的影响
情境建构能否实现赋权效果,仍受到案主“个别化”影响,即在同一情境之下,不同特质的案主所获得的效果不同。具体来说,在D协会服务过程中,并非所有失独者能够随着服务者的情境建构进入到“助人”层次。这与他们自身的学历、性格特质等因素有关。相对而言,高学历者往往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包容性,且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且对“贡献社会”的价值更为认同,更容易产生助人行为。而学历层次较低者,更多注重参与服务活动能否实现自我利益,如能够在参与活动后聚餐,或者具有部分礼物等。换言之,集体赋权仍受到案主个别化特质的影响。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层次失独者,分层设定目标和方案。即针对案主的不同追求维度,可以尝试针对不同追求的失独者给予引导:如对物质追求者,可采取渐进引导方式,提供部分便利;情感需求者,则可以尝试提供群体活动、互助活动等;对于人生意义追求者,可以采取鼓励他们助人的策略等。
(二)赋权效果受到组织者人格的影响
情境建构达到赋权的方式还受到组织者的人格特质、文化特质和社会能力,以及组织本身能力和品性等影响。D协会会长本人的特质既是赋权成功的关键,也是其受限的关键。首先,长期生活于中国底层社会,有较强的交往能力以及整合政府资源和获得合法性能力;其次,具备长期有志于此的“执念”式坚持;最后,长期从事该领域服务,能运用好具有中国“人情—面子—关系”等交往的手法,获得失独者逐渐认可,并且逐渐塑造成魅力型的领导者。这些特质让他更适应当下中国社会服务的实践情境,即基于日常生活互动模式进行行动,超越传统社会服务“文牍主义”的陷阱。但他文化不高、记录简单,难以描述和解释已有服务效果及发生原理。D协会会长出身草根社会组织,在服务过程中,通过以“亲情打动”工作方式和人情练达的行动选择,往往是其他社会工作专业人士难以拥有的特质。
(三)赋权效果更依赖深层次叙事结构的拓延
将情境建构纳入赋权实践,是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郑广怀、向羽,2016)的有益尝试。然而,从具体过程来看,小范围的外力环境改造实践,未必能够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失独人群面临困境——老无所依、亲情关系断裂及人生最后时刻无人照料等,亦即不能解决影响案主的根本需求或结构性因素,案主仍难在脱离服务后形成独立人格的“自助”状态。从某种意义说,这仅是一种“浅赋权”。因此,进一步化解他们的困境,仍然需要社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需要依靠于失独群体自治式服务,形成完整“主体性”,实现个体在人格上的“自助”,以达到“深赋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