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生成
——以马君武对密尔《论自由》的翻译为个案的讨论
2020-05-12李宏图
李 宏 图
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思想家所写的文本,不同的思想史家对此理解不同。例如在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看来,不能够把思想家在文本中所表达的这些观念都看作是思想家自己的观念,甚至是其思想信仰的表达。由此斯金纳批评将作者与文本所表达的观念之间直接对应等同的实体论观点,他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个案来说明,我们在处理他的这一文本时,并非全然将其作为信念的表述,而是应看作为其对当时的政治辩论一种特定且相当复杂的介入(intervention)。1○
昆廷·斯金纳对此可谓言之有理。不过在我看来,思想家的文本不仅仅是对当时政治论辩的一种介入,而且作者的意图对文本思想内容的形成的确也会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作者在文本中的思想表达实际上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观念以及意图的体现。如果我们把翻译思想家的文本也看成为是翻译者在对文本进行再创作,生成为一个新文本的话,那么翻译者作为文本的再创造者,他的主观意图和文本的翻译之间就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被翻译的译本常常变成翻译者主观意图的产物,由此导致要么误读,要么漏译与添加,从而形成了新的转义。这一情况在20 世纪初中国对西方思想家著作的翻译过程中表现特别明显。本文从全球思想观念流动和迁变的视角,聚焦于作者意图与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对1903 年马君武对约翰·密尔《论自由》的翻译来做一个案分析,也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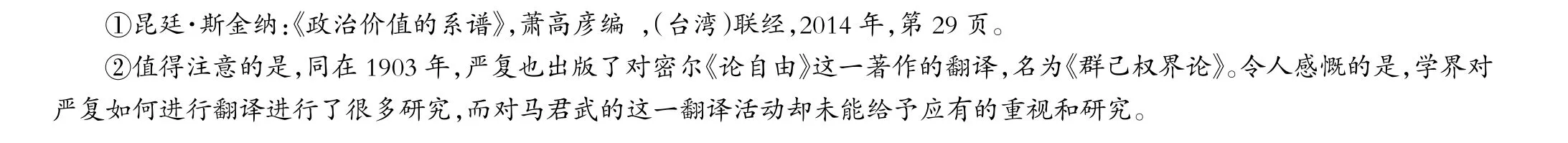
一
马君武(1881—1940)出生在广西一个官僚家庭,是第一个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学位(1915 年)的中国人。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0—1926年为前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成为主张共和的革命派,其中突出的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的政治宣传;后期一直从事教育活动,先后担任过大夏大学校长(1924 年11 月),北京工业大学校长(1925 年4月),广西大学校长等。作为在思想理论上主张自由共和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传播西方思想的翻译家,更是在教育活动中躬身实践这些理念的教育家,马君武获得了当时人们很高的评价。著名学者柳亚子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来赞美马君武:“江南握手笑相逢,识得而今马贵公。海内文章新《雅》《颂》,樽前意气旧英雄。摆伦亡国哀希腊,亭长何年唱《大风》?右手弹丸左《民约》,聆君撞起自由钟。”1○
作为思想家,马君武很早就确立起了自由、共和的思想。1901 年他就获得密尔《论自由》一书,即对此加以研习。1902 年3 月17 日,马君武在“女士张竹君传”一文中就谈到自由问题:“竹君又曰:欧西之论自由者,曰个人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吾谓自由可以行星之运行比之。其运行,自由也。其运行而遵其一定之轨道,此其界也。”2○这些表达和密尔《论自由》的主题非常相近。在1911 年,刚刚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获得工学士回到上海,马君武就为当时的民立报撰写社论和评论,介绍共和主义思想。1911 年11 月9 日,他发表了《共和政体论》,11 月10 日,又发表《论共和国之秩序》。这两篇文章,不仅体现了他的共和主义思想,也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一批共和派的主张。当然他的共和主义思想还散见在他所写作的很多文章中。
在《共和政体论》中,他首先就对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或者政治合法性做出了阐述:“君主政体基于神权,共和政体基于人权。共和政体之国,有真实强固及永久的主权,每一国人皆主权之一分子,而寄此主权于一选举体者也。”3○
其次,他认为现今共和体制是世界潮流。他曾经这样说:“共和政体者,今世界上最合于理论之政体也。”4○的确,从当时的世界历史来看,“新学渐兴,文化日进,全球君主之数每年减少,此世界上不可逃之命数也”。5○这里他用了传统的中国语言“命数”来表达了共和体制是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为什么共和是一种命数,在他看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君主所以不能见容于世界之故,盖基于平权学说之原则,人人公权平等,而不容一部分一阶级之人享有特权。因此,在这里,共和体制和君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特质就被挖掘了出来,两种体制的后面的支撑就是人权或者说公权、平等和特权的不同。因此,随着人权潮流的到来,共和体制的建立也是应有之意,也必将冲垮君主制存在的基础。所以,在马君武看来,现在还有君主体制的存在,其基础也不过就是用武力维护,以最强固之兵力自拥护,如俄是也。另外就是其先人有大武功于国,而国人尚未忘之,如英、德是也。6○

第三,他心目中的共和国的典范为法国、瑞士和美国。提到瑞士的共和体制,这在当时的一批共和派和近代思想家当中是不多见的,这也许是因为他曾经在德国学习过的缘故。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瑞士等共和国的体制作出专门的介绍,只是对其原则作出了概括。例如,他在《论共和国之秩序》中认为,在专制国家,秩序的建立是人为的,而在共和国里则与之相反。马君武先生写道,其在瑞士及合众国反之。国人各有职业,而其职业为选择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平等,有自由,故瑞士及合众国有秩序,而其秩序为自然秩序。另外一个共和国的样板是法国,早在1902 年,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翻译了《法兰西近世史》,想借用法国的经验和样板来为中国找到走向共和的路径。他在本书的译序言中写道:“法兰西,欧洲文明开化最先之域也……共和之政,固立于上,自由平等博爱之风,大昌于下。法兰西当一千七百九十三年路易十六未伏诛以前,其困于暴君之专制,法国人民之困苦,正与吾中国今日地位无异也。”7○在马君武看来,和已经实现共和制的这些国家相比,“故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至于今日”。8○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君武对中国要进行变革是多么的迫切。
第四,为了实现共和政治体制,可以用流血革命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革命是铲除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共和体制,建立共和国的最好方式。他在《共和政体论》一文中写道,中国人信奉两大主义,“曰:光复中华,建立民国……法人革命时,语曰:誓杀尽君主,使流血满地球。盖法人受君主之虐毒至酷,故痛之也深。吾中国之视法国,受尽君主之恶毒有更甚焉。泱泱神州,吾国民今方以血洗净之,岂能复容野蛮时代之遗留物、所谓君主者混迹其间乎?”1○这一主张,一方面体现出对法国革命的简单理解,但更反映了当时马君武作为革命派面对着维护君主体制和改良派双重包围下主张革命、建立共和的决心,与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今天,回顾革命派为什么会使用这一修辞和走上不怕流血的革命道路,和当时能够给予选择的环境和条件密切关联。
第五,共和政治体制自由、平等,公共利益等自然秩序。他写道:“自然秩序,为共和国,取国利以兴公事,开通富源,而为纳税者谋其利益。今为吾中国建立共和之初期,反正诸省汲汲然兴修民政,维持秩序。吾尝思孟德斯鸠之言曰:共和国之精神为道德。卢骚之言曰:共和国之所最忌者为谋取私益而害公事。窃愿职事诸公,三复斯言。而今日之革命,建立共和,排去贵族,乃所以破坏人为秩序而回复天然秩序也。”2○

二
在马君武看来,共和体制最重要的是关乎人民的权利,因此,人民主权,自由、平等,公共精神等内容则是其最为关切的主题,也是他最为希望改造中国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为了让中国成为共和国,实现人民的自由,马君武决定要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一书,借以唤醒国人。他在谈到密尔时说道:“弥勒诚十九世纪之大政论家也。彼所著《自由原理》( )之价值,与卢骚所著之《民约论》等。卢骚谓:国民之学绝对。弥勒谓:个人之独立不可限制。弥勒诚十九世纪之大经济学家也。向之论经济学者,谓人所以为生产。弥勒反之,谓生产所以为人。虽然,弥勒固不仅为大政论家、大经济家而已,彼实十九世纪之一大哲学家也。”3○
自1901 年马君武读到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这本书后,他就立刻着手进行翻译,经过断断续续的工作,终于在1903 年完成出版,名为《自由原理》。对这一翻译过程,他在1903 年1 月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二年前获见弥勒氏之《自由原理》元本,且读且译,成‘总论’一章。闲[间]以他事,遂尔中止。后又得见槐特氏之法文译本,名La liberte,及日人中村氏之日文译本,名《自由之理》。壬寅十一月复渡日本,居东京上野之一小楼。北风已至,林木萧然,独居无事,复取弥勒书续译成之,十五日而毕。总计不过费二十日耳。近日自由之新名词已渡入中国,而其原理未明,遂多有鳃鰓然虑其有流弊者。欧文书善阐自由之原理者,莫如此书,故急译行之。词取达意,不求工丽也。壬寅十二月马君武。”4○
据考证,马君武是在1902年12月完成翻译,其间他参考了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なかむらまさなお)1872年的翻译本《自由之理》。此书出版后立刻在日本引发轰动,鼓舞了热衷于自由民权运动的人们。何野广中(1849—1923)读后感叹到:“向来的忠孝至上思想一朝被颠覆,瞬间化为木叶微尘”,他开始认识“人之自由、人之权利莫此为大。内心深感国家必须施行奠基于广大民意的政治,胸中铭刻自由民权之信条,吾之生涯因此划下至重至大之转机”。5○
正因为日译本在日本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马君武认为翻译这本书也将会击中中国之要害,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十九世纪之有弥勒约翰,其犹希腊之有亚里士多德乎。论古代学术之起源,无论何科,殆皆可谓滥觞于亚里士多德;论今代学术之进步,无论何科,殆皆可谓集成于弥勒约翰。弥勒约翰在数千年学界中之位置,如此其崇伟而庄严也。顾吾国人于其学说之崖略,曾未梦及,乃至其名亦若隐若没,近数年来始有耳而道之。吁!我思想界之程度,可以悼矣。弥氏著作始入中国,实自侯官严氏所译《名学》。虽然,《名学》不过弥氏学之一指趾耳……《自由原理》一书,为弥氏中年之作,专发明政治上、宗教上自由原理。吾涉猎弥氏书十数种,谓其程度之适合于我祖国,可以为我民族药者,此编为最。久欲绍介输入之,而苦无暇也。壬寅腊将尽,马子君武持其所译本见示,则惊喜忭跃。以君之学识,以君之文藻,译此书,吾知弥勒如在,必自贺其学理之得一新殖民地也。”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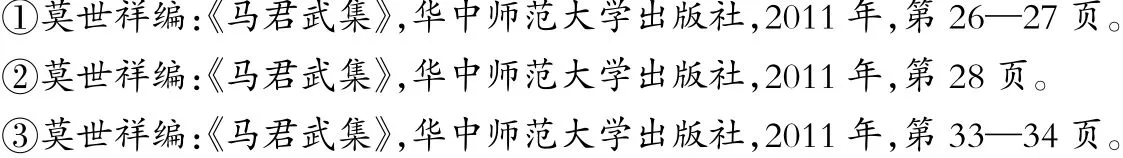
三
就内容而言,马君武选择了书名为《自由原理》,而没有象严复那样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即表明一是受到了日译本的影响,二是通过参考日文和法文译本,故能够准确地翻译为《自由原理》。同样,在马君武翻译本的开头就写道:“此书论自由之大旨,乃解明人民社会之公众自由,而社会加于个人之权,如何依法而行;且讲究其权之本性及界限,非如哲学家言之仅托空想也。”2○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君武将社会与自由都加上了限定词,“人民社会之公众自由”。这样的理解基本符合密尔《论自由》原书的意旨。尽管如此,细读马君武的译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在共和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他对译文进行了的改造,将自己的意图加入到了所翻译的文本中,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新“文本”。例如他对密尔的这段话做了这样的翻译:
The object of this Essay is to assert one very simple principle, as entitled to govern absolutely the dealings of with the individual in the way of compulsion and control,whether the means used be physical force in the form of legal penalties, or the moral coercion of public opinion. That principle is, that the sole end for which mankind are warranted,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in interfering with the liberty of action of any of their number, is self-protection. That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sed community, against his will, 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His own good, either physical or moral, is not a sufficient warrant. He cannot rightfully be compelled to do or forbear because it will be better for him to do so, because it will make him happier, because, in the opinions of others, to do so would be wise, or even right. These are good reasons for remonstrating with him, or reasoning with him, or persuading him, or entreating him, but not for compelling him, or visiting him with any evil in case he do otherwise. To justify that, the conduct from which it is desired to deter him must be calculated to produce evil to some one else. The only part of the conduct of any one, for which he is amenable to , is that which concerns others. In the part which merely concerns himself, his independence is, of right, absolute.Over himself, over his own body and mind,the individual is sovereign.
这种明显的改动表明了马君武的意图,把密尔原文中的“社会”,翻译成为了“政府”,将其理解为政治上的含义。在另外一处的翻译中,马君武又格外强调密尔思想的政治性维度:“诚欲社会之发达,当许各异之人,显其各异之品行,图其各异之生涯。不观历代已往之陈迹乎?专制政体者,乃败坏个人品行性质之一大毒药也。屈万人之心,以从一人之欲,故专制政体下之人民,断无能发达之理。而信教最笃之人民,亦决不能发达。因彼既笃信上帝之教条,其人群之本性,必已失坏,其被祸盖与服从于专制君主之下者同也。”1○
在翻译密尔的第一章中,马君武觉得仅仅讨论密尔的社会性自由还不够,为了获得阅读的效果,增强其说服性力量,他还特地增加了这样的段落:“政府亦然。政府加害于人之大者,即不阻恶事之流行是也。政府者,保护人群团结之力也。一切事之有关于个人者,政府当尽其责任而不可坐视不理。夫不理民事,不图民益,不防民害者,为不尽政府之责任。不尽责任之政府,人民固有权以改易之也。”2○
在第二章讨论思想自由这一部分中,马君武增加的段落比较多,例如:“此章之理,从未发现于中国。周秦诸子之辩论,徒尚意气,而不求合于事理。自汉武帝定孔说为一尊,而中国微矣。”3○
“中国自儒术一统后,国人之思想极不自由,人才日下,凡词章考据等科之杰才,皆因为思想界之所限,遂旁发为此曲艺小技也,可悲矣!夫思想之大家,必出于思想自由之国。思想自由之国,人类各尽其天然固有之心才,而发达之,故国人之智识,遂蒸蒸而日上。思想自由者天职也,发达个人之思想,以献之于普世界,不可避也。自有异端之说兴,而人民之心才,遂为奴隶。思想之境狭,辩论之事息,人类之问题消灭不兴,个人之天才,遂无由以见矣。”4○
“中国战国时代,诸子并兴,孔子集其大成,诚智识进步一大关键。然自是遂戛然而止者,因更无非难孔说者出也。”5○
为什么马君武要增加这些段落?这和他对中国现状的思考密切相关。早在1902 年,他在翻译《俄罗斯大风潮》一书的序中就这样写道:“美哉!言论自由乎!凡非人间最黑暗之地狱,未有不许国人言论自由者也;凡非人间最无耻之卑下奴隶,未有不出死力争言论自由之权者也。”6○他认为俄罗斯无宪法,无议会,而要求自由的革命者又多被处死杀害,因此,“俄罗斯诚人间之最黑暗地狱也”。相比较而言,在欧洲范围内,“法兰西之国民者,世界上思想最高之国民也”。7○因此,在这一序言中,马君武表达了这一观点:为了获得人的自由,首先就要得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并且立志要为此而斗争,要做一个这样的人。他说:“休乎哉,报改造社会思想之子,豪杰乎!其目的或全达,或全达其一小部分,或历数世而达,或历数十世而达。当其生时,世人皆辱之、逐之,以至于戮之,谓其人为诞人,视其说为邪说。然历数世或数十世之后,则莫不敬而崇拜之,至读其书而咏叹曰:吾何不幸,不生与斯人同时也!”8○因此,在马君武看来,言论自由关乎自己的使命,更关乎社会是进入文明还是陷入野蛮,光明还是黑暗。不仅在早年他就确立起这一思想,在随后的1911 年,三次撰写发表了题为“言论自由”的文章。在1903 年所写的《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一文中认为,改变中国道德风尚的路径在于获得自由。他说:“自由独立者,人群进化之真精神也。人类之三大自由,曰思想自由,而议论自由、著书自由附焉;曰结会自由;曰择业自由。是三大自由者,横绝天地,无所限制也。至于行为之自由,则不能无界。然不能执界之一字,遂钳制人群之行为之自由。日耳曼大儒汉保德
W.von Humboldt 曰:‘人当自强不息,各自发达其心才,而不为同类寻常之耳目所欺,是之谓个人之权势,是之谓个人之发达。’近日新党之议论,颇有以少年之误认狂妄为自由,鳃鰓然虑之者。然是乃自由原理未明之故,非自由之不适用于中国也……忧时之士,不务考泰西所谓自由者之原理,执一二细事,遂谓自由之理不可倡,倡则流弊滋多。呜呼!天下岂有无自由之国乎?”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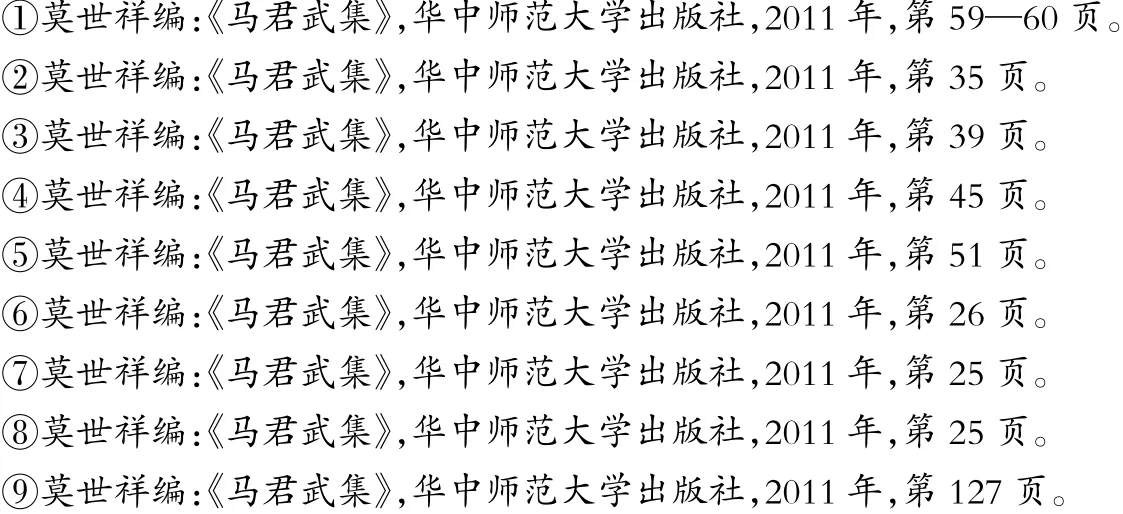
因此,密尔将阻碍人们自由的原因归之为集体性的一致性观念、习俗和趣味等等社会性因素,而在马君武这里,人们没有思想自由,也实在是由于专制政治的统治,一个国家的专制君主拥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致使人们不敢言论,专制君主也成为了社会习俗的根源。
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出发点,马君武在翻译中对密尔《论自由》一书中的这段话做出了这样翻译处理: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world has, properly speaking, no history, because the despotism of Custom is complete. This is the case over the whole East. Custom is there, in all things, the final appeal; justice and right mean conformity to custom; the argument of custom no one, unless tyrant intoxicated with power,thinks of resisting.
东方诸国,每以风俗规矩为最后之断案。其所谓正义、所谓公理者,皆指风俗而言。风俗之势力极大,无一人敢抗之,惟其国中之暴君,有制造风俗之权。1○
在另外一段落中,他写道:“社会固有保护个人之义务,至社会之权,则不可过大。苟社会之权过大,而干涉人民之一切私行,则必至人民之一举一动,皆无势力,其强烈独立之性质必渐失去。盖人民合理之行,已所以为是者,而社会托于免害他人之名以干涉之,是他人未受而我已先受其害矣。是之谓越权行霸,是之谓专制。因是之故,人民因自求免祸也,可以兴革命,以脱其轭而不为背理。”2○
很明显,马君武将密尔的社会控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通过翻译处理,巧妙地改换为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由此他在这里增加了“革命”这样的字眼,实际也是为未来在中国进行革命做出了理论准备,也为通过革命方式改造中国找到了思想上的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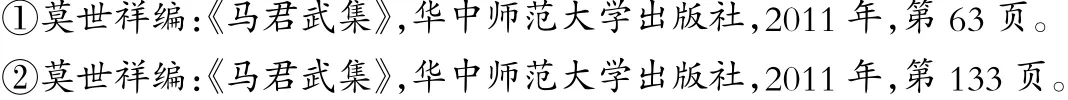
为此,在关于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章中,密尔仅仅只是提到了卢梭的思想,而马君武在这里又将此发挥引申为“革命”。
Thu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en nearly all the instructed, and all those of the uninstructed who were led by them, were lost in admiration of what is called civilisation, and of the marvels of modern science, literature,and philosophy, and while greatly overrating the amount of unlikeness between the men of modern and those of ancient times, indulged the belief that the whole of the difference was in their own favour; with what a salutary shock did the paradoxes of Rousseau explode like bombshells in the midst, dislocating the compact mass of one-sided opinion, and forcing its elements to recombine in a better form and with additional ingredients. Not that the current opinions were on the whole farther from the truth than Rousseau's were; on the contrary, they were nearer to it; they contained more of positive truth, and very much less of error. Nevertheless there lay in Rousseau's doctrine, and has floated down the stream of opinion along with i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exactly those truths which the popular opinion wanted; and these are the deposit which was left behind when the flood subsided. The superior worth of simplicity of life, the enervating and demoralising effect of the trammels and hypocrisies of artificial society, are ideas which have never been entirely absent from cultivated minds since Rousseau wrote; and they will in time produce their due effect, though at present needing to be asserted as much as ever, and to be asserted by deeds, for words, on this subject, have nearly exhausted their power.
十八世纪开化之迹,岂不可惊乎?无论学者、未学者,莫不受其风潮,而遂造成今日文艺、学术、哲理之新世界。以今人与古人较,其不同之度,自是而差异甚大,盖几尽扫古人之说矣。其主动力实惟卢骚。卢骚所倡奇异之学说,如炮弹之爆裂于人世,凡自来流俗一偏之见,皆因此所破散而无余。经此大震动,举世人莫不有健旺之精神焉。夫流行斯世之学说,非无更善于卢骚者,然自其卢骚之新说出,乃如大潮澎拜,小川无声,大唱人权天赋之理,尽扫旧社会之弊俗,而一空无余。盖自其学说出而革命兴,革命兴而新社会出,百世之下,莫不食卢骚之赐。言论者,
事功之母,其效力岂不伟乎!1○
其实,在密尔原文中,其所列举出的卢梭的思想不是指社会契约论和革命的思想,而是与密尔自己心境有关的一些卢梭的思想内容,如生活的简朴有着更高贵的价值,虚伪社会的罗网和伪善导致耗丧精力和败坏风气的恶果。而马君武则借用密尔提到卢梭,趁机将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插进自己翻译的文本之中,让读者以为这是密尔的原意,从而起到宣传自己革命思想的主旨。
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君武在翻译完密尔的《论自由》一书后,深感自己的国家还没有自由,因此,特地在“论自由”的结尾处增加了这段感叹性段落:
呜呼!一国之政,大事也。人民不知自由自治,甘心坐视,为小人之所坏尽,是岂惟彼小人之罪而己乎?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2○
正如梁启超在为马君武的译本所作的序言所说,“《自由原理》一书,为弥氏中年之作,专发明政治上、宗教上自由原理。吾涉猎弥氏书十数种,谓其程度之适合于我祖国,可以为我民族药者,此编为最。”3○这一概括实在是误读了密尔此书的原意,因为密尔这本书并非是着重论述政治和宗教自由,而是社会性自由,即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免受社会对其的干涉。正是马君武在翻译的文本中的一些误译造成梁启超一种误读,或者也可以说,梁启超的这段话只是更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和马君武等这批知识分子在当时所发出的共同心声,他们在内心并非是要在学理上理解密尔的思想,而是借用密尔的思想来传递自己的思想观念。

四
如果仔细阅读马君武撰文介绍密尔思想的其他文章将会进一步发现,马君武的误译和梁启超的误读实在是带有鲜明的主观意图。换句话说,他们在利用翻译创造新文本的机会,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意图加入其中。例如马君武在翻译完密尔的《论自由》后,又在当年的4 月11 日发表了题为“弥勒约翰之学说”一文,详细介绍了密尔《论自由》一书的基本思想。从这篇文章来看,马君武对密尔《论自由》一书的基本主旨总体上说是还把握得当,理解准确的。例如在谈到个人自由的边界时称:“苟人人有完全之自由之完全自由,而无所防制,同群之人亦不立德制及形制以限之,则其为害于此世也必甚。夫行为自由之不能如思想、择业、结会之自由无界限,实天下之公言也。其界限惟何?曰:不犯害他人。”4○这和密尔所说的个人行为的界限为不得伤害他人是一致的,也与翻译的文本中把“社会”理解为“政治”有所不同。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马君武这样介绍密尔的关于人的个体性的思想:“弥勒约翰曰:人之行为自由固须有界,然而不可误会此意,而立一定之规矩以束缚世人之行为,使出于一辙也。一人当有一人之特别品行。人世之大恶,莫甚于不务发达个人特别之思想,以造出个人特别之品行。个人之价值甚高,勿沉滞于今世界之程度,限于习俗,而不思更有所进也。世俗之论,动曰法古。此最不可通之论也。若是,是教世人空无所为,徒抄袭古人之蓝本而已。世俗之论,动曰勿自作聪明,勿轻下论断。此最不可通之论也。若是,是教人失其生活之方法,弃其适宜之行为,废其特别之性质也。人当有特权,依自己之境地及性质,独断独行,不可有一毫依赖古人之心。以古人之遗言遗行为鉴,而不以为法。人不可如机器,而当如树。机器者,死物也,依一成之式而不能自变。人则不然。人也者,断断不可依一成之式,以作一定之工者也。人之精神,当似一树。春日既阳,生长发达,自由无碍,如其内力之所向,其生机活泼而不滞也。”5○
但在马君武所翻译的文本里,他却这样翻译道:“既知汉保德之理,必须思个人价值甚高,勿沉滞于今世界之程度,而不图更有所进也。世俗之论动曰法古。此最不可通之论也。若是,是教世人空无所为,徒抄袭古人之成本而已。世俗之论动曰:勿自作聪明,勿轻下论断。此最不可通之论也。若是,是教人失其生活之方法,弃其适宜之行为,废其个人之性质也。虽然,若谓世人当茫然不知此世界已往之事,则不合理。考世界已往之事方知前人存活之法,行为之序,而后一己有所抉择也。故幼年时代,必须受教育,以知人类所已经历之局焉。至于年岁已长,心才已熟,则当有其特权全依已法行事,依自己之境地及性质,独断专行,不可有一毫依赖古人之心。以古人之遗言、遗俗为鉴,而不以为法。”1○
在这里,尽管马君武对密尔《论自由》中突出个性的思想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他还是改动了密尔在原文中的参照,提出了古今之时间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在密尔那里,他承继着托克维尔的思考,认为在现时代,随着民主的发展,平等的盛行,习俗与行为一致性的形成,整个社会会形成一种整体性的专制力量来压抑每个人的个性。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依然面临如此的问题。因此,在密尔这里,他提出的是今日与未来的时间性概念。但在马君武这里,他转换了密尔所提出的问题视角,重点强调古今之分。认为,世俗之论,动曰法古,徒抄袭古人之蓝本而已,不可有一毫依赖古人之心,以古人之遗言遗行为鉴,而不以为法。等等。这些理解也突显这在那个时代,影响人的个性张扬,阻碍人的特立独行的往往是师古,从古流传下来的风俗传统一直在起着作用。因此,要实现人的个性张扬,就需要打破这些传统,不能生活在这一传统所编织起来的天罗地网之中。
其实,这一改动完全是马君武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他认为,现今的中国,为什么专制体制能够延续,其实是因为中国没有培养起独立自由的持有公共道德的人,而一味地以祖宗之法限制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如他在《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一文中所指出:“中国士大夫有恒言曰:‘遵先法古。’中国乡人有谚语曰:‘不听老人言,灾害在眼前。’此实断送中国生命之绝命词也。古有古之时代,今有今之时代;古人有古人之心才,今人有今人之心才;而何可遵之有?而何可法之有?惟法古也,惟尊先也,士守残缺之义理,农守笨滞之耒,商守狭小之局面,工守粗野之规矩。莽莽乎二十行者之土地,为强邻角逐之场;芸芸乎四万万之人民,为异种籍制之奴,夫复何言!”2○
因此,在这里隐含着密尔作为原作者和马君武作为翻译者俩人在历史观和时间观上的差异。密尔着重的是当下,在19 世纪的当下,社会正在进入到一个齐一化的状态,形成了一种社会性专制的暴政,从而取代了原先的政治上的专制暴政。这是和17 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相吻合。而在马君武这里,则在时间观和历史观上追溯中国古代以来的专制暴政统治,压抑了人的个性,以及思想和言论自由。特别是在汉代以后,思想定于一尊,从此人们失去自由。而选择这一时间性维度则是要表明与更为凸显中国思想言论自由之紧迫与必要,和推翻专制统治实现共和成为时代重任。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专制统治已是积重难返,通过缓慢的渐进性的改革无法实现中国体制性的变化,亟需要通过革命来完成。而密尔与卢梭等思想正符合当下中国的需要。由此,也可以说,密尔思想的时间性基础和马君武思想的时间性基础完全不同,正是对密尔思想基础的时间维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解进行了彻底性的调整,作为翻译者的马君武将密尔的“今”转变成为了“古”,由此也将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成功地移植作为了在中国进行革命、推翻政治上的专制统治以及实现包含思想言论自由等在内的人的自由的重要思想资源。
纵观马君武对密尔《论自由》的翻译以及对其思想的介绍,马君武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密尔文本中的“社会”等概念,实际上他能够理解,在一些段落中,他也都将“Society”翻译成为“社会”。然而在一些关键性段落中,他就将其转换为“政治”。这样,他所进行的这一转换就是一种基于主观认识的意图,从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原作者的新的文本。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不仅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也产生了概念内涵的转义,看起来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内涵和指向却大相径庭。而这样一种文本的创造性转换随后通过阅读而传播,变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理解以及新的社会实践。由此,也可以理解,在20 世纪初年的中国,面对风云际会的时代大转折,各种思想、观念以及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在不同文化空间中流动,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转义,在转义之后又通过阅读与传播等方式,形成了和原先文本有些差异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又在实践中转化为建构实体性社会系统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