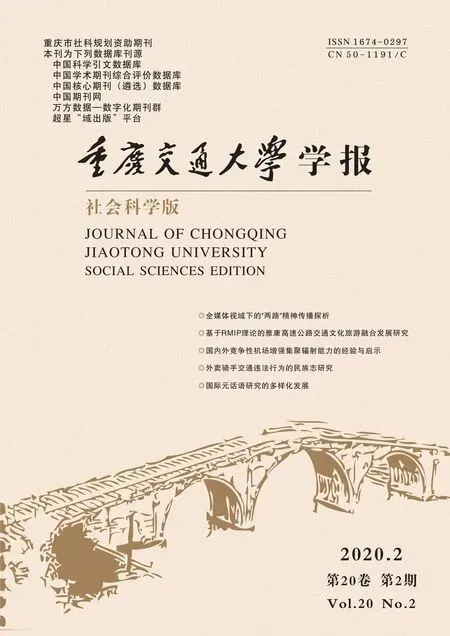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的存在性论证
——基于1010份调查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
2020-04-29朱振亚汪阳春
朱振亚, 汪阳春, 肖 洁
(1.三明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2.井冈山大学,江西 吉安 343009)
一、引言
当前,城乡一体化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如何另辟新途,以更好更快地助推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学界对此做了诸多有益探索,如不少学者对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进行了多维解析[1-5],但未见一种动力机制是指向“新市民”群体的。本文所讲的“新市民”不是学界惯指的进城农民工或进城失地农民,而是特指首代进城落户工作且拥有大中专文凭的农家子弟(县城为最低级别城市,文凭为普通大中专院校颁发的文凭)。农民新市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已有研究表明,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失地农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6-11],称呼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失地农民为新市民还不准确。基于此,笔者另辟蹊径,重新界定“新市民”为首代进城落户工作且拥有大中专文凭的农家子弟。他们已很好地融入了城市,完全或较好实现了市民化必需的身份“变态”和素质“变性”过程,是真正的新市民。
笔者前期从理论上分析了“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作用[12]。新市民的城乡粘合性主要表现为城乡情感粘合、生活粘合与工作粘合,这三大粘性像双面胶(或粘合剂)一样,将城市和乡村粘结在一起。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催化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反哺”和“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是指新市民通过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反哺,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是指新市民通过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作为城乡粘合剂和催化剂的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与催化作用可概括为“两头粘合、三个反哺、四个带动、一体催化”。
以上有关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作用均是理论上的分析推断,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以论证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的现实存在性。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一)数据来源
本问卷调查基本遵循了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原则,样本代表性较好。需要说明的是,问卷调查对象全部是政府公务员、国有企业和全民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如此安排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全民事业单位里新市民比较集中;二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全民事业单位的新市民已经较好地或完全地融入了城市,其身份“变态”和素质“变性”最彻底;三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全民事业单位的新市民所处社会能级较高,控制和支配的社会资源较丰富,他们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作用比较明显。
问卷调查范围涵盖北京市顺义区、海南省海口市、江西省南昌市、安徽省合肥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州省贵阳市、辽宁省大连市、海南省儋州市、安徽省安庆市、江西省吉安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安徽省枞阳县、江西省井冈山市、江西省吉水县、四川省浦江县、四川省茂县共18个县市区。其中东部地区4个,中部地区7个,西部地区7个;省级城市(含直辖市)6个,地级城市(含副省级城市)7个,县城(含县级市)5个。样本区域代表性和城市代表性较好。共收回新市民群体填写问卷1100份,其中无效问卷9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010份,问卷有效率为91.8%。
(二)样本详情
样本详情如下:第一,男多女少。在新市民回答的1010份有效问卷中,男性775人,女性235人,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76.7%和23.3%。第二,以中年人为主。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以30~49周岁的中年新市民为主,占到样本总数的68.6%,新市民样本年龄基本呈帽形的正态分布。第三,已婚者居多。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未婚120人,已婚890人,比例分别为11.9%和88.1%。第四,学历层次较高。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中专学历30人,大专学历112人,本科学历563人,研究生学历305人,分别占总人数的3.0%、11.1%、55.7%和30.2%,本科学历者超过半数,研究生学历者接近1/3。第五,党员比例较高。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群众186人,民主党派79人,中共党员745人,分别占总人数的18.4%、7.8%和73.8%。第六,行政职级分布呈金字塔型。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科员及以下级别409人,科级干部286人,处级干部291人,厅级及以上干部24人,分别占总人数的40.5%、28.3%、28.8%和2.4%。第七,单位行政级别有高有低。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工作单位为科级及以下级别的有285人,工作单位为处级的有455人,工作单位为厅级的有255人,工作单位为厅级以上的有15人,分别占总人数的28.2%、45.0%、25.2%和1.5%。第八,职称分布比较合理。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初级及以下职称(含无职称)的402人,中级职称的377人,高级职称的231人,分别占总人数的39.8%、37.3%和22.9%。第九,大部分人至少有父母双亲中的一位生活在老家农村。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只有父亲健在的有56人,占样本总数的5.5%;只有母亲健在的有181人,占样本总数的17.9%;父母双方均健在的有636人,占样本总数的63.0%。第十,大多数新市民乡下还有亲人。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乡下有亲人的有894人,乡下没有亲人的有116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88.5%和11.5%。第十一,大多数新市民在乡下仍有保持走动的亲戚。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乡下还有保持走动的亲戚的有980人,乡下没有保持走动的亲戚的有30人,分别占到样本总数的97.0%和3.0%。第十二,工作地点分布比较均匀。如果以新市民家乡为参照点,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本县工作的有233人,在本市工作的264人,在本省工作的251人,外省工作的有261人,分别占到了样本总数的23.1%、26.2%、24.9%和25.9%,在本县、本市、本省和外省工作的新市民约各占总数的1/4。第十三,工作地离老家距离有远有近。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工作地距离老家100公里以内的有424人,工作地距离老家101~300公里的有221人,工作地距离老家301~500公里的有96人,工作地距离老家501~1000公里的有134人,工作地距离老家1000公里以上的有135人,分别占到总人数的42.0%、21.9%、9.5%、13.3%和13.4%。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距离老家最近的是1公里(估计老家就在城郊),距离最远的是4200公里,平均距离为522公里。第十四,城市级别分布比较均匀。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有333人在县城或县级市工作,有372人在地级市工作,有305人在省城或直辖市工作,分别占总人数的33.0%、36.8%和30.2%。第十五,家庭经济情况多为一般。在1010个样本新市民中,城市小家庭经济状况非常困难的有46人,比较困难的有59人,一般的有694人,比较宽裕的有211人,非常宽裕的有0人,分别占总人数的4.6%、5.8%、68.7%、20.9%和0.0%。
三、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一)新市民城乡粘合性的存在性
1.新市民情感粘合性的存在性
新市民情感粘性(情感粘合性的简称)是指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市民思想情感上具有的拉近城乡距离的心理倾向和情感特性。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情感粘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大多数新市民梦境中常现农村景象。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您的梦境中常常会出现农村的景象”问题时,有160人认为“非常符合”,294人认为“符合”,还有326人认为“难以确定”。若将“难以确定”人数一分为二,即回答“难以确定”的新市民中有一半倾向于“符合”,另一半倾向于“不符合”(下同)。折算加总,共有61.1%的新市民承认梦境中时常会出现家乡的景象。只有230人回答“不符合”与“非常不符合”,加上一半“难以确定”的新市民,否认梦回故乡的新市民仍是少数,比例只有33.9%(见图1)。可见,大部分新市民进城后,梦境中仍会时常出现农村的景象,乡愁藏在梦中。分性别来看,男性新市民“梦回故乡”的平均比率稍高于女性新市民,男性回答的平均吻合度为61.6%,女性回答的平均吻合度为59.6%。
大多数新市民曾经经常下地干农活。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您曾经经常(下地)干农活”问题时,有350人认为“非常符合”,350人认为“符合”,还有110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起来,共有74.8%的新市民承认曾经经常(下地)干农活,只有不到30.0%的新市民认为“不符合”或“非常不符合”(见图2)。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对“经常干农活”的评价,不排除在不到30.0%的新市民中还有部分人偶尔会参加农业劳动。可见,大多数新市民在进城之前均接受过很好的“农业劳动教育”,这对新市民农村情怀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分性别来看,男性新市民“务农”的平均比率稍高于女性新市民,男性回答的平均吻合度为75.8%,女性回答的平均吻合度为71.3%。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发现新市民的情感粘性还表现在如下方面:大多数新市民在农村有过较长时间的生活经历;大多数新市民在农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大多数新市民在农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大多数新市民认为农村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大多数新市民对农村有种亲切感;大多数新市民对农民怀有好感;大多数新市民都能尊重城市里的农民工;大多数新市民都会同情城市街头的农村乞讨人员;大多数新市民的乡愁记忆在农村;大多数新市民认为自己的“根”在农村;大多数新市民对家乡母校怀有深厚感情;大多数新市民对家乡中小学老师怀有感恩之心;大多数新市民有从农民中走出来的情怀;大多数新市民为农村落后而痛心;大多数新市民欢迎新农村建设;大多数新市民爱家乡农村胜过爱其他地方农村;大多数新市民对家乡的好感程度随着离乡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大多数新市民对家乡的思念随着离乡距离的递增而递增;大多数新市民在他乡听到乡音会倍感亲切;大多数新市民期盼早日消除城乡政策不公;大多数新市民渴望城乡平等;大多数新市民希望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加力;大多数新市民希望农民生活越来越好;大多数新市民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三农”需加速发展;大多数新市民认为对农民好就是对市民好;大多数新市民希望城乡友好交流、互通有无。
2.新市民生活粘合性的存在性
新市民生活粘性(生活粘合性的简称)是指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农村习性(爱好)的延续性,以及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城乡交流互动特性。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活粘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有:
大多数新市民基本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去看看。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您基本每年都要回老家看看”问题时,有679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221人认为“符合”实际,还有66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共有92.4%的新市民坦承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看看,仅有很少比例的新市民对此问题持否定态度(见图3)。可见,大多数新市民基本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看看。分性别来看,男性新市民和女性新市民在上述问题的群体倾向高度一致,男性新市民的平均支持率为92.3%,女性为92.6%。
进一步研究表明,新市民回老家次数与工作距离负相关,即距离老家越近,回老家次数越多;距离老家越远,回老家次数越少。新市民每年回老家次数以4次以下为主。约有四成的新市民每年回老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或有超过半数的新市民每年回老家次数不超过4次,或有接近80.0%的新市民每年回老家次数不超过10次。整体看来,远距离新市民回老家每年以4次及以下为主。新市民每年在老家逗留总天数与回家次数正相关,与工作距离负相关。新市民平均每次在老家逗留时间与工作距离正相关,即离老家越远,每次在老家逗留时间越长。新市民回老家在时机选择上以春节和清明为主,回老家以看望父母、走亲访友和祭祖为主。
大多数新市民在农村有祖坟。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您家还有祖坟在农村”问题时,有743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252人认为“符合”实际,还有0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共有98.5%的新市民承认老家农村仍有祖坟,仅有个别新市民持否定态度(见图4)。可见,大多数新市民在农村仍有祖坟,和前面新市民回家祭祖相互印证,说明新市民“血脉之根”在农村。分性别来看,男性新市民和女性新市民在上述问题上的群体倾向高度一致,男性新市民的平均认可率为99.4%,女性为95.7%。调查结果还表明,84.4%的新市民愿意出钱支持修缮祖坟,80.2%的新市民愿意出钱重修宗祠,有86.4%的新市民愿意出钱支持重修家谱。可见,新市民对维护农村祖坟及宗祠的积极性非常高,对家谱与家族也非常重视和认同。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发现新市民的生活粘性还表现在如下方面:大多数新市民在农村仍有继续来往走动的亲戚和朋友,大多数新市民爱看农村题材的影视剧,大多数新市民爱听乡土音乐,大多数新市民喜欢聆听或哼唱家乡戏曲,大多数新市民仍然保留着某些家乡的饮食习惯,大多数新市民仍然偏爱家乡口味的饭菜,大多数新市民请客吃饭偏好“农家乐”或“土菜馆”,大多数新市民支持农产品价格的适当上涨,大多数新市民每年都是过农历生日,大多数新市民生活中仍然受某些家乡习俗影响,大多数新市民平时比较关注家乡的发展,大多数新市民曾回访过农村母校和老师,大多数新市民择偶倾向于选择农村出身的异性,大多数新市民有在退休后回乡生活的愿望。
3.新市民工作粘合性的存在性
新市民工作粘性(工作粘合性的简称)是指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市民及其所在单位所表现出来的能帮扶“三农”发展、促进城乡友好交流的特征。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工作粘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有:
大多数新市民的工作与“三农”直接或间接相关。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您的工作与‘三农’直接相关”问题时,有94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202人认为“符合”实际,还有259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共有42.1%的新市民认为自己的工作与“三农”直接相关(见图5)。评价“您的工作与‘三农’间接相关”问题时,有85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339人认为“符合”实际,有276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共有55.6%的新市民认为自己的工作与“三农”间接相关(见图6)。可见,约有97.7%的新市民承认自己的工作与“三农”直接或间接相关,这是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工作粘合与催化促进作用的现实基础。分性别来看,就工作与“三农”的直接和间接相关性而言,男性新市民与女性新市民群体认可比率基本相同。
大多数新市民所在单位可直接或间接帮扶“三农”发展。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您的单位可以直接起到帮扶或促进‘三农’发展的作用”问题时,有141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279人认为“符合”实际,有310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共有56.9%的新市民认为自己所在单位可以直接起到帮扶或促进“三农”发展的作用(见图7)。在评价“您的单位可以间接起到帮扶或促进‘三农’发展的作用”问题时,有129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492人认为“符合”实际,还有229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共有72.8%的新市民认为自己所在单位可以间接起到帮扶或促进“三农”发展的作用(见图8)。可见,大多数新市民所在单位可直接或间接帮扶“三农”发展。需要说明的是,单位直接或间接帮扶“三农”,与新市民的工作与“三农”直接或间接相关不是相同的概念。如在银行工作的新市民与“三农”工作是间接相关的,但银行本身可直接帮扶或促进“三农”发展。分性别来看,就直接服务“三农”而言,女性新市民群体认可比率高于男性新市民,女性平均认可率为70.2%,男性为52.9%;就间接服务“三农”而言,女性新市民群体认可比率也高于男性新市民,女性平均认可率为84.0%,男性为69.4%。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发现新市民的工作粘性还表现在如下方面:大多数新市民所在单位已通过“结对子”等形式对农村发展进行帮扶,大多数新市民在涉农工作中带有反哺“三农”的情怀,大多数新市民愿为农民代言,大多数新市民工作上积极支持国家“以城带乡”政策,大多数新市民在工作中会潜意识地关照农村群体,大多数新市民工作中会尽力帮助农村求助之人,大多数新市民工作中曾主动要求下乡,大多数新市民乐意接受下乡挂职委派任务。
(二)新市民城乡催化作用的存在性
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催化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反哺”和“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是指新市民通过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持续反哺,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是指新市民通过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调查研究表明,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的催化促进方面确实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
大多数新市民都会从精神和经济上反哺农村父母。新市民对“三农”的反哺首先表现为对农村父母的反哺。前述分析表明,有92.3%的新市民坦承,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看看,新市民回老家次数与工作距离负相关,每年回老家次数以4次以下为主,回老家的时机选择以春节和清明为主,新市民每次回老家平均逗留时间为3.9天,回老家目的以看望父母、走亲访友和祭祖为主,其中看望父母排在首位。“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新市民回家探亲,是对父母的精神反哺,体现了新市民对农村父母的反哺报恩之心。
新市民对农民父母除了精神反哺,还有经济反哺。据调查,新市民每年孝顺父母的花销平均为6697元(将所有为父母的花销折算成人民币统计),最少的为0元(父母已经过世,无须开支),最高的为70 000元。据统计,1010个新市民中每年为父母花销不超过3000元的占总人数的35.1%,每年为父母花销在3000~6000元的占总人数的28.2%,每年为父母花销在6000~10 000元的占总人数的28.2%,每年为父母花销超过10 000元的占总人数的8.4%(见图9)。分性别来看,女性新市民每年孝顺父母的花销平均为6245元,略低于男性新市民的平均值6834元。
大多数新市民愿意为“三农”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您愿意为‘三农’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问题时,有554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396人认为“符合”实际,还有50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共有96.5%的新市民愿意为“三农”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只有不到4.0%的新市民持反对态度(见图10)。可见,大多数新市民有支持“三农”发展的意愿。分性别来看,就支持“三农”发展的意愿而言,男性新市民和女性新市民的平均支持比率基本相等,男性平均比率为96.5%,女性为96.8%。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发现新市民的“三个反哺”催化促进作用还表现在如下方面:大多数新市民更愿意支持家乡农村发展,大多数新市民曾参加过单位组织的节日“送温暖”下乡活动,不少新市民曾策划或运作过有益于“三农”的项目,大多数新市民认为服务“三农”不丢人,大多数新市民都会尽力做好事关农民的工作。
2.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城乡一体化
大多数新市民每年都有农村亲友来城市做客。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每年都有农村亲友来您城市家中做客”问题时,有304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350人认为“符合”实际,还有182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共有73.8%的新市民承认每年都有农村亲友来城市家中做客,有26.2%的新市民持否认态度(见图11)。可见,大多数新市民每年都有农村亲友来城市家中做客,说明新市民与农村亲友仍然保持着比较亲密的联系。分性别来看,男性新市民和女性新市民在上述问题上的群体倾向基本一致,男性新市民的平均认可率为73.5%,女性为74.5%。
大多数新市民有时间会到农村亲友家做客。问卷调查过程中,在评价“有时间您也会去农村亲友家做客”问题时,有412人认为“非常符合”实际,有476人认为“符合”实际,还有97人认为“难以确定”。折算加总起来,共有92.7%的新市民坦承有时间会去农村亲友家做客,只有很少的新市民持否认态度(见图12)。可见,大多数新市民有时间会到农村亲友家做客,说明新市民与农村亲友间的往来性比较好,新市民没有因为进城而嫌弃乡下亲友。分性别来看,就回乡到农村亲友家做客而言,男性新市民的平均认可率略高于女性新市民,男性平均比率为94.2%,女性为87.2%。
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我们发现新市民的“四个带动”催化促进作用还表现在如下方面:大多数新市民的农村亲友进城做客常常会捎来一些农特产品,大多数新市民经常携带工作地特产回老家,大多数新市民从老家回城要捎带家乡的农特产品,大多数新市民曾在乡下多次购买过农特产品,大多数新市民几乎每年都要带着家人去农村度假、休闲或旅游,大多数新市民曾向外人宣传过自己的家乡,大多数新市民或多或少充当过城乡信息交流的桥梁,大多数新市民在许可的范围内愿意安排涉农资金向农村倾斜,大多数新市民在许可的范围内愿意将涉农项目向农村地区倾斜,不少新市民工作中曾主导并推动过城乡某方面的交流,大多数新市民愿意推动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新市民群体的调查及数据分析发现:第一,新市民的情感粘性主要表现在28个方面,如大多数新市民梦境中时常出现农村景象,大多数新市民曾经经常下地干农活等。第二,新市民的生活粘性主要表现在16个方面,如大多数新市民基本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看看,大多数新市民在农村老家有祖坟等。第三,新市民的工作粘性主要表现在10个方面,如大多数新市民的工作与“三农”直接或间接相关,大多数新市民所在单位可直接或间接帮扶“三农”发展等。第四,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7个方面,如大多数新市民都会从精神和经济上反哺农村父母,大多数新市民愿意为“三农”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等。第五,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13个方面,如大多数新市民每年都有农村亲友来城市做客,大多数新市民有时间会到农村亲友家做客等。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与催化促进作用真实存在。